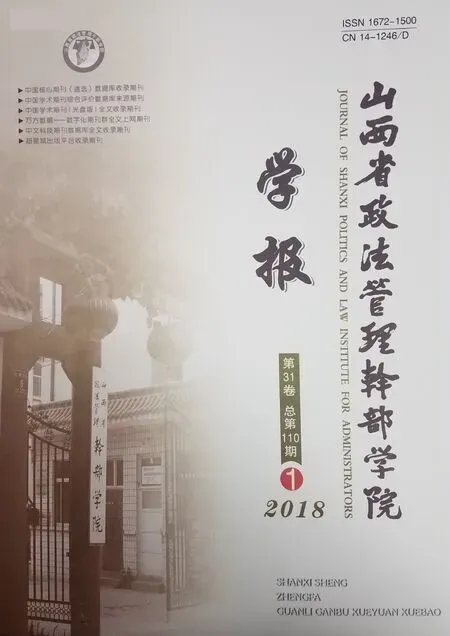买卖合同交付主义风险负担浅析
——以“一房二卖”为切入点
周 琼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买卖合同关乎民生问题,始终是人民大众关注的焦点。买卖中,标的物意外发生毁损、灭失的情形时有发生,尤其是近期屡见不鲜的“一房二卖”中,这种风险由谁承担,如何定分止争,是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有学者指出,从查士丁尼(Justinian)到拉贝尔(Rabel),风险转移一直是买卖合同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关于风险负担的内涵,大多数学者认为仅指价金风险,即买卖的标的物如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买卖价款是否仍需支付,进而相应的不利益由谁承担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交付主义与所有权主义之争
关于风险负担规则,有交付主义与所有权主义两种模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风险负担移转的时间点是标的物的交付,后者是所有权的移转。交付主义与所有权主义在很多场合会有相同的外观,这是因为动产所有权转移的标志是交付。在动产买卖中,交付与所有权转移同时发生,少有争议发生。但在不动产买卖中,由于交付与作为物权公示方法的登记并不一定同时发生,此种情况下交付主义和所有权主义的区别比较明显。《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交付主义的风险负担规则。有学者质疑风险负担规则中的交付主义模式,建议重新复活所有权主义模式,以使风险负担规则能与物权变动规则相衔接。本文以“一房二卖”为例,从《合同法》风险负担制度的规范体系内部,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就交付主义所受的质疑,予以分析,并在现行法框架下提出可行的救济路径。
二、交付主义的现实困境:以“一房二卖”为切入点
案例:房产销售公司甲(出卖人)就其开发的某住宅区的一套别墅与乙(第一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该别墅,乙支付了全部房款,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之后,甲与不知情的丙(第二买受人)就上述同一套别墅签订买卖合同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而后,该别墅被意外焚毁。本案中谁承担别墅意外焚毁的风险?
(一)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之间的风险负担
出卖人甲交付标的物别墅于第一买受人乙,乙实际占有了该别墅且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义务,但由于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故该别墅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甲。标的物别墅在乙实际占有期间意外灭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别墅灭失的价金风险因甲的交付而移转至乙,乙不得请求甲返还已支付的价款。
(二)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风险负担
出卖人甲与第二买受人丙(不知情)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时,甲仍然是所有人,此份不动产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因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标的物别墅的所有权从甲移转至丙。但是由于甲没有交付该别墅于丙,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该别墅灭失的价金风险不发生移转,仍然由甲承担,甲不得要求丙履行对待给付义务即支付价金,丙可以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价金。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一房二卖”中交付主义的困境在于:出卖人甲具有主观恶意进行“一房二卖”,并将别墅过户至第二买受人丙名下,完成所有权转移手续,对于第一买受人乙来说,意味着甲在法律上已履行不能,乙无法取得别墅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别墅意外毁损灭失,对于第一买受人乙来说,意味着甲在事实上亦履行不能,乙无法继续占有该别墅。在法律和事实上履行不能的双重打击下,第一买受人乙基于《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还要承担别墅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即不得请求出卖人甲返还价金,使得非违约方无法在风险下得到救济,也间接助长了出卖方“一房二卖”的势头,不利于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以及交易安全的稳定。
三、交付主义的理论困境:与物权变动模式有关
《合同法》分则“买卖合同”一章并没有区分动产买卖与不动产买卖。在不动产买卖中,交付主义对比所有权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需要结合物权变动模式来理解。
通说认为,《物权法》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此模式下,作为债权合同的不动产买卖合同除了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之外,同时肩负着物权变动的使命。这种模式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还另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是事实行为,不是一种物权合意。没有进行登记并不影响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效力,只是当事人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这种模式下,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是相分离的,债权变动并不引起标的物的所有权的转移,只有债权合同结合登记手续的完成才会引起物权变动。因此,在不动产买卖中,交付与所有权移转的时间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果采纳交付主义,意味着交付之时所有权可能未发生转移,这种风险与所有权的不相关性,正是交付主义存在的前提,但交付主义因此在动产买卖场合与所有权主义的法律构成及实际效果相差无几。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交付主义的理论困境在于:风险真的能随着交付而转移,从而与所有权分离吗?风险及利益本质上均是所有权的法律后果,交付之后,虽然所有人无法再实际利用标的物,但仍然享有所有权,这种享有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而受领交付者并未享受此种利益,进而言之,其在法律上并未取得所有权。交付主义之下的上述风险与所有权分离的合理性,难免面临拷问。
四、寻求困境的救济路径:从体系解释出发
《合同法》中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交付主义规则主要移植自CISG,《物权法》中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深受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的影响。这种广泛参考借鉴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值得肯定的。相同规定的适用效果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及其理论构造中可能是有差异的,在借鉴继受的过程中也会有杂糅综合并给予本土化改造。要准确理解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交付主义规则,需要结合两大法系的理论构造,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理清相关法律条文之间的逻辑结构,寻求困境的救济路径。
(一)针对交付主义的理论困境
“风险利益相一致原则”足以支撑交付主义模式的立法价值判断的合理性:第一,观念上,标的物的实际占有人通常是最易管理风险的人,也最容易控制不利后果和计算损害的大小,这与所有权无关;第二,体系上,《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设置了与交付主义风险负担规则相衔接的利益承受规则,贯彻了“利之所在,损之所归”;第三,比较法上,美国《统一商法典》改变《统一买卖法》的所有人主义而采纳交付主义后,有关风险负担的诉讼锐减,可见交付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实务中的讼争。
(二)针对交付主义的现实困境
《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设置,立法旨意是“救济非违约方”,达到风险回溯的效果即由过错的违约方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可以说是为应对出卖方根本违约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案例量身定做的。有学者指出该条蕴含的立法者价值判断是:“出卖人根本违约场合,为充分保护买受人利益,赋予解约(拒绝)权以优先地位和更高位阶,期使买方救济的最终效果,免受风险移转常态规则的不当减损”。[1]《合同法》制度设计上,如果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是由可归责的事由所引起的,则由违约责任制度来调整。如果是由不可归责的事由所引起的,则由风险负担制度来调整。[2]本文讨论的是在上述两因素并存时,例如“一房二卖”下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如何协调违约责任制度与风险负担制度的关系?《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可以说是为违约行为与风险损失并存场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设的。但是,依文义解释,该条的适用条件仅限于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如果严格限制在质量瑕疵这种情形,“一房二卖”下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非违约方就无法得到此条的救济。这明显与该条设置的救济非违约方的内在价值相违背。补救方法可以将此条的适用条件作扩大解释,以“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核心要点,囊括所有的根本违约情形,只要出卖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根本违约,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均发生回溯,仍由违约方出卖人承担。那么在上述“一房二卖”案例中,出卖人甲将该别墅的所有权移转给第二买受人丙致使第一买受人乙无法取得所有权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第一买受人乙解除合同的,该别墅毁损、灭失的风险仍由出卖人甲承担,第一买受人乙可以要求出卖人甲返还支付的价款,同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这两种救济途径并不冲突,而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第一买受人乙作为非违约方的利益,合理加重违约方的义务,从而对“一房二卖”等根本违约行为进行一定的遏制。
五、结语
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如何规制,调整模式并非唯一,有交付主义和所有权主义之争在所难免。但不论采取哪种路径,孰优孰劣,要从最终法律效果去考察,而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或者接受。在《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借鉴CISG采纳交付主义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结合《物权法》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针对不动产买卖中根本违约与风险负担并发的情形,从对《合同法》一百四十八条进行扩大解释的角度切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刘 洋.根本违约对风险负担的影响[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6).
[2]易 军.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