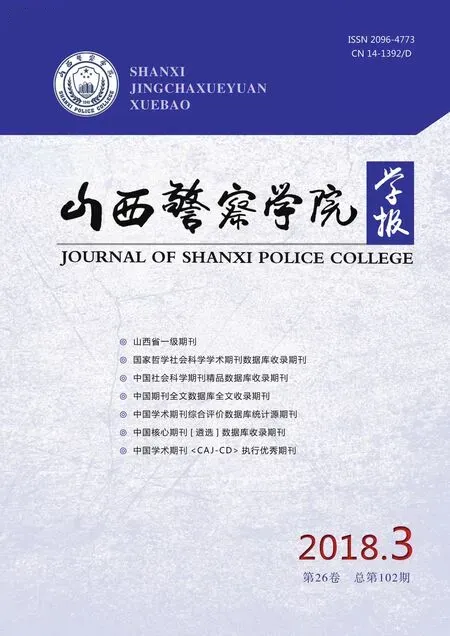重复性供述的排除问题研究
□卫国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一、问题的提出——作为毒数之果的重复性供述
毒树之果,简单说,是指执法人员通过不合法程序取得的材料。毒树之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却并未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施行中必然会受到阻碍或在司法实践中会被架空或规避。在司法实践中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口供为线索获得实物证据的过程中发生规避,也就是说嫌犯所交代的口供是侦查部门借助非法手段得到的,进而以该口供为线索发现与案件相关的实物证据。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对毒树之果并没有相关明确的规定,那么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将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方法获得的有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然而对于以其有罪供述为线索获得的实物证据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作为根据进行排除,因此实物证据仍可能作为有效证据被法庭采纳。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初衷是相违背的。二是由口供到口供的规避。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方法获得犯罪嫌疑人第一份有罪供述,根据第一份有罪供述进行讯问,可能会获得第二份有罪供述。而第二份有罪供述的获得过程并没有相关违法行为,因此不能认定其为非法证据。其中,第二种可能存在的规避情形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重复性供述”。
二、域外重复性供述的证据效力或排除规定
(一)严格的美国本土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毒树之果”理论认为“毒树”产生的果实也一定是有毒的。该规则是美国司法体系所独有的,且在美国证据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毒树之果”理论要求,收集证据的行为如果违反被告人宪法性权利,则该证据在庭审中不被采纳,且以该证据为线索收集到的其他证据也会被认定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毒树之果”的概念第一次完整的出现是在1939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纳多恩诉美国案的裁决意见中。该案中,检控方指控被告人纳多恩有偷税漏税等行为,而证明该指控的主要证据就是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监听所获得的谈话记录。初审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然而该有罪判决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理由是谈话内容是通过非法监听得到的,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检控方更换指控罪名后再次提起诉讼,但其提交的证据仍然是通过非法监听得到的谈话内容,初审法院再次做出有罪判决,但联邦最高法院毫不犹豫再次将有罪判决予以推翻。最高法院在裁决中阐述其理由:一旦执法人员初始行为的违法性被认定为“毒树”,则后续诉讼中检控方对被告人的指控就构成“毒果”,不应作为证据被采纳,其指控不得被支持。也即,如果警方收集证据材料的过程中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则该证据材料在庭审中绝不应作为证据被采纳,即使证据材料有很大的可能性能证明犯罪事实。然而在美国司法体系确立“毒树之果”理论后,很多犯罪嫌疑人运用该项规则规避了有罪判决,从而导致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造成美国社会犯罪率的上升,联邦最高法院迫于社会公众的压力和犯罪率上升对社会带来的危害,通过判例制定了一系列毒树之果的例外来限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过度适用,其例外原则包括:
1.“善意例外”(the good faith exception)。在合众国诉莱昂(United States v. leon 468 U.S.897[1984])*United States v. Leon,468 U.S., 104 S. Ct. 3405案件当中,警方根据线报认为存在合理的依据从而申请并取得了搜查令,以该搜查令为依据警方从犯罪嫌疑人的三个住处均搜查出大量毒品。然而由于警方申请搜查令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按照搜查令所得到的证据一开始就被视作非法证据而不被认可。最终,该证据通过“善意例外原则”使其证据能力得到认定从而在庭审中被采纳。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该案认为,如果警方在采取行动时,有充分且合理的理由相信该行动并没有违背相应法规,则该搜查就是合法的,在此期间所得到的凭证也因作为合法证据在庭审中予以采纳。
2.“公共安全例外”(public security exception)。在纽约州诉夸利斯(NewYork v.Quarles 467 U.S.649[1984])案件当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在危急形势下,警方出于保护公共安全的考虑,既使其并没有履行“米兰达规则”相关规定,但所获得证据依然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在庭审中使用。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陈述,亦可在法庭上使用。*Rolando V. Carme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M], 2001.
3.“必然发现例外” (inevitable discovery exception)。在尼克斯诉威廉斯(Nix v.Williams 467 U.S.431[1984])一案中,警方通过非法讯问获知了犯罪嫌疑人藏匿被害人尸体的位置。与此同时,200人的志愿者团队已经根据警方的推测朝尸体所在方向展开搜索,而尸体被藏匿位置已经被确定在搜索范围。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其裁决中指出,因尸体藏匿位置被包含在搜索范围之内而“必然被发现”,所以尸体藏匿位置可以被检控方作为证据在庭审中使用。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公诉方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既使没有非法搜集的证据,该证据依然可以通过其他合法行为而发现并且获得,那么检控方依然可以在庭审中使用该证据。
4.“独立来源例外” (independence source exception)。1960年在贝纽诉美国案一案中,警方怀疑犯罪嫌疑人参与过一起抢劫案,虽然并没有达到法定的逮捕标准,警方依然对被告实施了逮捕,并采集其指印。当检控方对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指控时,检控方使用的指印是档案中保存有犯罪嫌疑人的旧指印,该指印与案发现场的指印吻合。尽管犯罪嫌疑人认为警方使用的指印是通过非法逮捕行为获得的因此警方提交的证据其证据能力不能被认可,但由于警方对与非法逮捕行为无关的指印有权进行检验,且警方作为证据提交的旧指印并不是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因此巡回法院认为,旧指印“与非法逮捕行为并没有关联”,因此可以作为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而予以采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公诉方能够证明警方发现证据的过程与其在侦查取证过程中采取的非法行为是相互独立的,此类证据可作为“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而予以采纳。
5.“稀释原则” (违法被消除的例外情形)(purged taint exception)。196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王森诉美国案中确立了这一例外规则。该案中,联邦缉毒人员在没有任何合法搜查令的前提下进入托伊的住宅并将其逮捕,托伊立即供述其毒品是从一位名叫“伊”的人处所买。警方根据其供述找到了伊,伊交出其藏有的海洛因并做出供述称这些毒品的来源是托尹贺王森,警方随即对王森进行逮捕,在传讯后允许其保释。几天后,王森到警察局向警方作出有罪供述且保证其供述是出于自愿。联邦最高法院据此认为,警方在没有任何合法搜查令的前提下进入托尹的住宅并对其逮捕,因此从托尹处获得的毒品以及托尹的证言来源均为非法,因此该证言和所得毒品都应作为“毒树之果”予以排除;而王森随后自愿到警察局做出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证据,虽然王森第一次供述是因警方对其非法逮捕,但在其被允许保释且获悉其所享有的权利后,依然自愿做出有罪供述,因此其后来供述行为的自愿性已经起到清洁阀的作用将非法逮捕与有罪供述之间的“污染”进行稀释。联邦最高法院对此作出解释,如果警方最初的非法取证行为与受污染的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被告人后来的自愿性供述的有效介入而被打破,那么该自愿性供述就会对被污染的证据本身起到稀释作用,从而使该证据在庭审中可以被采纳。
以上5条例外原则的意义在于,减弱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框架中的绝对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该规则的适用范畴。它所展现的是立法者在惩处犯罪的客观需要与确保刑事诉讼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宪法性权利需要二者的矛盾中谋求一种价值平衡的取舍。
(二)相对主义的日本
日本刑事司法体系在引用“毒树之果”理论时,不仅仅是考虑该规则在法理层面的积极意义,同时将本国法制和社会实情作为影响因素进行整体考量。因此,日本刑事司法体系在其司法实践中只是部分吸收了美国“毒树之果”理论,并结合其自身特征确立了“反复自白”规则。对“反复自白”作为证据的资格判断需要经过以下过程:首先,如果警方的首次侦查取证行为是违法的,那么法院要对该取证行为的违法程度进行确认,只有该侦查取证行为涉嫌重大违法时才考虑适用“毒树之果”理论;其次,法院需要对第二次讯问获得的“自白”与第一次获得“自白”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审核,若关联性较弱或者不存在关联性,则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第三,衡量第二次所得“自白”的重要性时将社会公共安全作为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如果排除第二次所得“自白”将会造成检控方的指控不成立,使得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时,则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最后,衡量该案对社会的危害性以及对个人宪法性权利的侵害程度,如果该案件对社会有较大影响时,则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从上述四项判断标准中可以看出,日本刑事司法体系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和对“毒树之果”理论的运用远不及美国,甚至不能称之为“体系”,因其在日本法律中并不独立而完整。
(三)宽容的英国
在英国,对待“毒树之果”理论较之美国则比较宽容,表现为无论其普通法还是成文法都可以适用毒树之果。如果根据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发现了能证明案件的重要证据,既使该有罪供述是在不合法的讯问压力下取得的,但该证据仍然可以作为定案证据被法庭采纳。也就是说,警方的非法取证行为并不能导致所得证据作为“毒树之果”被一概排除在外。法官在自主决断是否采纳之时,需同时对两方面的利益加以思量:其一,凭证的证据意义;其二,侦查活动的违法等级及其所导致的消极干扰,特别是对审判的公正性及司法的正义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1]倘若警方在侦查取证过程中违法程度比较轻微,即只是发生了程序性违法(如未告知沉默权、搜查缺乏必要手续等),法官有权对警方所提交的证据进行裁量排除。但是,如果警方的非法取证行为不是轻微的程序性违法,而是重大违法甚至侵害犯罪嫌疑人宪法性基本权利,如在获得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过程中采取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等手段,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证据将被法院视为“毒树之果”坚决予以排除。英国刑事司法体系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是最大限度地采用非法证据。其早期法律仅对非法自白证据予以排除,但依然规定自白证据是否具有实际效用并不受其获取手段的影响,而是取决于其本身的可信赖度。换言之,法官在选择对自白证据的采纳还是排除时关注点在于证据本身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自白证据的来源是否违法。只有在警方取证过程中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性基本权利并且所得自白证据并不是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时,该非法自白证据才会被排除。
(四)明确排除的德国
德国《刑事诉讼法》136a对严禁讯问的方式进行了详尽的罗列,因为此条是《基本法》第1条的实际展现,所以倘若不对其加以严格遵从,“那么所获取到的证据无法被视作有效凭证。即便后来的讯问方法全都合法,但是其陈述依旧会受到过去以非法方式讯问的不良干扰时,那么此时的陈述就算是合法的,也依旧不能被认定为有效。”
卡夫根案是德国的一个与重复供述证据能力有关的现实案例。2002年9月30日,法兰克福警方以涉嫌绑架犯罪对卡夫根进行了逮捕,并且使其知悉了自身应当具有的权利。为了尽快找到受害者,10月1日上午,警察对嫌犯进行了胁迫,告诉他倘若还不将受害者的具体位置说出来,就会对其用刑,使其身心备受摧残而且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因为害怕受到折磨,嫌犯在历经10分钟左右的思想斗争之后选择了如实交代,警察也因此而找到了受害者的尸体。在返回的路上,嫌犯被警察再一次讯问,并且对自己绑架和杀害的行为供认不讳,而后又在庭审之前接受了多方的多次讯问。在诉讼期间,初审法院指出,因为警方所使用的方式涵盖在《刑事诉讼法》136a严禁使用的讯问方法范畴之内,所以嫌犯在受到胁迫之后马上做出的以及在此种违法行为持续影响下随后所给出的所有供述都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向警察和检察官所作的供述都不能被采纳。法院同时指出,在随后的讯问活动当中,倘若每一次开始之前都使嫌犯清晰知晓第一次讯问因为违反了法规而已经被排除在外,那么后期的所有供述就能够被作为证据加以采纳。
三、决定重复供述可采性的因素
在各个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当中,供述所起的效用不可小觑,基本上都是定案中必备的证据形式。但是由于有多个利益间的矛盾隐藏于此类证据当中,所以公众对它的担忧与喜爱程度不相上下。[2]在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形成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思维模式,因此在侦查取证过程中难免以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第一要务,不惜使用刑讯逼供等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往往造成“屈打成招”,出现冤假错案。随着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对供述的获取与应用需要法律进行苛刻地规制,核心内容就是对非法取得供述的排除。新刑诉法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做出了详细规定,包括对讯问主体、讯问地点、讯问时间、讯问手段的限制。然而现行法律,对讯问次数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和要求,因而对于同一个被追诉者,侦查机关通过多次讯问后形成的多次口供,即形成了形式上的重复性供述,其可采性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即成为需要讨论的内容。重复性供述是不是出自于自愿基本上决定了其自身是否能够具有证据效力,尤其要重视先前非法取证手段与后续获得重复性供述之间的关联性,即前者是否持续对后者的自愿性产生影响。而评价重复性供述的自愿性与真实性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种:
(一)先前非法取证行为的严重程度
通过对美国“毒树之果”理论相关“例外规则”的阐述以及对日本、英国对“毒树之果”理论相关引入的简单概括,我们可以看出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与讯问过程违法性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非法讯问行为越严重,对犯罪嫌疑人产生的伤害和心理压力也越大,越难以断开重复性供述与非法讯问行为之间的联系,导致重复性供述越难以被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纳。而非法讯问行为如果只是简单的程序性违法,那么并不会对重复性供述产生排除的波及效应,即可能导致第一次供述被排除,但不会直接影响到后续供述的可采性。因此在判定重复性供述排除与否亦或排除到怎样的程度时应该对违法取供的具体性质及程度加以深度思量。[3]
另一种情况是:侦查机关通过非法讯问手段获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在后续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翻供并且举报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但是遭到了严重的报复,导致其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再翻供,继续做出有罪供述,那么该重复性供述也不会作为有效证据被采纳。此外,非法讯问行为对犯罪嫌疑人的影响越大,之后获得的派生性证据越有可能受到污染。对非法讯问行为严重程度的判断与犯罪嫌疑人本身特点也有关系,如果犯罪嫌疑人本身属于弱势群体,如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则对成年人并不构成影响的非法讯问行为,对未成年人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影响使其产生心理压力,从而导致非法讯问行为与重复性供述之间产生关联。所以,美国在判断重复性供述是否出于自愿作出时,通常要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教育程度、智力状况、生活经验、身体状况等。[4]因此,我国在对重复性供述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时也应当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二)侦查讯问人员的更换
取供不单是此类人员借助口头语言对被追诉者产生影响的整体经过,同时也是前者的自身人格魅力等语言以外的行为对后者产生心理优势的经过。[5]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多次讯问笔录的制作往往并不是由同一讯问人员完成的,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多次讯问也可能由不同的办案人员进行。而不同的办案人员对多次讯问笔录的制作显然影响犯罪嫌疑人多次供述的可采性。犯罪嫌疑人通常将非法讯问行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与该行为实施主体加以关联。倘若未对第一次施行非法讯问行为的人员进行更换,那么在后期的讯问中既使其没有继续实施非法讯问行为,或者只要其出现在讯问地点,犯罪嫌疑人也会出于恐惧心理或者产生压力而违背其意愿继续做出供述。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所作出的供述显然不具有自愿性,因此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而予以采纳。而对讯问人员进行更换却可能减轻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隔断前次非法讯问行为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转变供述的态度。但是在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犯罪嫌疑人在遭受非法讯问行为之后,既使更换本单位其他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依然认为讯问人员都是一伙的,仍然感觉自己处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中,进而不敢改变其供述,那么其后续讯问中获得的重复供述仍然不可采。此种情况下,需要变更的讯问人员就不能是本单位的,可以申请上级办案机关或者检方在审查供述真实性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再次讯问,以达到向其传递新的信息,让犯罪嫌疑人不再感觉自己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中,使其转变供述态度,增加其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三)侦查讯问人员的主观目的
在美国,对于警方因疏忽未给予犯罪嫌疑人米兰达警告而获得首次供述,而后来警方告知犯罪嫌疑人米兰达警告,使其获知所享有的权利。此时,既使再次供述作为第一次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影响再次供述的可采性。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米兰达权利并不是宪法性权利,警方的“疏忽”并不是违宪行为。于是在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美国警察部门在对警察的培训中,教导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可以不进行米兰达告知获得口供,之后再对犯罪嫌疑人宣告米兰达告知,引导犯罪嫌疑人再一次做出有罪供述,显然该有罪供述其实并不具有真实性和自愿性。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塞伯特案中对这种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予以否定。其理由是,供述的可采性取决于警方未告知犯罪嫌疑人米兰达告知是出于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对重复性供述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因此讯问人员极有可能为了得到合法有效的重复性供述,而在自身清楚知晓通过非法讯问而获取的首次供述会被排除掉的情况下依旧选择此行为,但是可以在后续讯问中保证其讯问行为的合法性,以此来保障其获得的重复性供述被法庭采纳。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保证犯罪嫌疑人做出的重复性供述是出于其自愿且真实。借鉴美国对米兰达告知的规定,我国在制定重复性供述可采性的法律法规时,可以考察侦查机关首次讯问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主观目的,如果其目的是故意的,则该重复性供述不予采纳,如果该行为是侦查机关疏忽大意且并不会对犯罪嫌疑人造成影响时,该重复性供述依然可采。
(四)间隔时间的长短
前次非法讯问行为与下次讯问之间的间隔时间长短也对重复性供述有直接影响。两次讯问之间间隔的时间越长,越可能消除前次非法讯问行为对犯罪嫌疑人的影响,增加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反之,如果两次讯问的间隔时间越短,那么第二次讯问越会被犯罪嫌疑人当成是前次非法讯问行为的延续,而前次非法讯问行为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越难以消除,犯罪嫌疑人越不可能依其自由意志做出供述,因此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也越低。事实上,不管前次侦查机关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非法讯问行为,如果进行下次讯问的间隔时间太短,那么讯问本身对犯罪嫌疑人就是一种压力甚至是强迫。因此,两次讯问的间隔时间长短也应该是重复供述可采性的考虑因素。
四、重复性供述的排除模式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做出如下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采取的是刚性(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的是裁量(相对)排除。那么对重复性供述应该怎样排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前述新刑诉法相关规定来研究重复性供述的排除方式。
(一)全部排除还是部分排除
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指出应当部分排除,需要考虑讯问间隔时间长短、讯问人员的变更、讯问场所的更换、非法讯问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后续讯问对前次讯问造成影响的减轻等因素,以此来决定对重复性供述予以采纳还是排除。该观点对重复性供述秉持的态度是需要建立对重复性供述的考量标准,然后利用考量标准来决定采纳还是排除。有学者强调,可将非法行为是不是已经违反排除规则视作一个判定标准,以确定是否对重复性供述加以排除。倘若违反了此规则,那么就本质来说,侦查及控诉部门的后续口供都将会因为波及效应而被排除在外。[6]然而,如果真正适用此方法,则会造成重复性供述排除范围被不当扩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将重复性供述全都排除在外。有学者强调,此类供述不可被视作证据,反之借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对刑讯逼供加以严禁就不再具有任何的价值。[7]由于法律尚无固定的标准去鉴别重复性供述和非法取证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考虑到避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规避或架空,重复性供述一般会在庭审中被全部排除。部分实务部门对重复性供述的态度是如果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被查实,那么后续获得的重复性供述一律予以排除。那么对重复性供述全部予以排除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来说真的是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吗?其实不然,前文提到的王森诉美国案中,王森被允许保释后又到警察局自愿做出有罪供述,如果按照全部排除的观点,那么其具有自愿性的有罪供述也会被排除,侦查机关需要重新进行侦查取证或者被追诉人会因指控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侦查机关重新侦查取证则无疑是对侦查资源的浪费,增加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而被追诉人的无罪判决则会违背法律打击犯罪的目的,对我国司法体系的公信力造成冲击。因此,两相比较,部分排除显然更为可取,但需要制定明确的标准来判断如何实施重复性供述的部分排除。
(二)绝对排除还是相对排除
在全部排除与部分排除已做出选择的情况下,接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排除方式选择:绝对排除还是相对排除。持绝对排除态度的学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较为严格的刚性标准。该种观点认为应该以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为基础来实施对重复性供述的排除,如在侦查取证阶段,发现取证过程中出现了法律规定予以排除的情况,则应将确认非法取证行为之前获得的重复性供述全部排除。如果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出现适用排除规则的情形,则在其被认定发生之后,侦查取证使其得到了此类供述应该全部都被排除在外,“可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过程中提审嫌犯而得到的认罪笔录涵盖在内”。[8]而在审判时期出现适用排除规则情形的,应当将确认该情形产生阶段的所有重复性供述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则认为,如果在审前取得的被告人的重复性供述内容与已经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不能用于定案证据的原供述相一致,则审前取得的重复性供述亦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9]
与之相对应,持相对排除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应该确立的是一个相对性的排除标准。此种观点认为,决定重复性供述是否被排除的关键是侦查部门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此类供述的干扰状况,即相应供述受到非法取证行为的影响越小,其被采纳的可能性越高;反之,重复性供述受到非法取证行为的影响越大,则重复性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越容易受到怀疑,其被采纳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因此,该观点认为重复性供述是否被排除,应考虑非法取证行为的后续影响,如前述非法取证行为的违法程度较高,那么对犯罪嫌疑人产生的伤害和心理压力也越大,消除压力所需要的时间也越长,则不能认定其后续重复性供述的效力。
其实,所谓的绝对排除规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重复性供述是否应当被排除,重要的一点是认定犯罪嫌疑人在做出重复性供述时是否出于其自愿且真实,而在认定其自愿性和真实性的过程中法官不可避免地会进行自由裁量,因此适合决定重复性供述是否应该被排除的标准应为相对性标准。
(三)主动排除还是被动排除
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中立地位,因此其司法裁判活动应保持被动性,表现为:第一,“不告不理”,也就是说仅在有人提起申请之后,法院才会开展相应的司法活动,反之,则不会开展。换言之,即法院不会自主介入社会,也不会自发地对某项社会冲突展开裁决判定。第二,即使因当事人的控告起诉而受理案件,法庭裁判范围也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当事人和特定的事实,而不能超出该范围去审理未经指控的当事人或案件事实。那么涉及到重复性供述的排除问题,法院应实行主动排除,即主动审查重复性供述的有效性如有排除事由则予以排除,还是实行被动排除,即只有在诉讼当事人提出重复性供述的排除问题时才去审查其有效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实行被动排除原则,因为如果实行主动排除原则,那么是否会影响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保持的中立地位进而影响判决公信力?而且实行主动排除原则可能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可能会导致法官在形成内心确信,倾向于相信被告人有罪,甚至可能做出向公诉方倾斜的判决,从而导致冤假错案。因此在进行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过程中,应实行被动排除原则保证法官在庭审中的中立地位,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五、结论
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应当涵盖基本框架、具体的范围、裁判机制、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司法救济机制的建立。新刑诉法已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如果在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基础上再将重复性供述予以排除,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比较尴尬的状况,即案件中没有可供利用的有效供述。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又过度依赖,没有口供导致破案效率下降进而犯罪案件的数量上升,威胁社会安全与稳定。鉴于此,对重复性供述的排除问题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障碍。因此,如果可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进行完善,法律应当对重复性供述的排除标准及实施做出明确规定来指导司法实践。然而我国法律法规的一个特点就是滞后性,决定了在法律颁布之时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的现状,因此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之前,最高法院可以利用其优势,借鉴美国判例法的优点,对典型性案件做出相关案件裁决,下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其判例做出判决,以此对重复性供述排除达到初步实现,为制定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进而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可行性提供有效参考。
——以被告人翻供为主要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