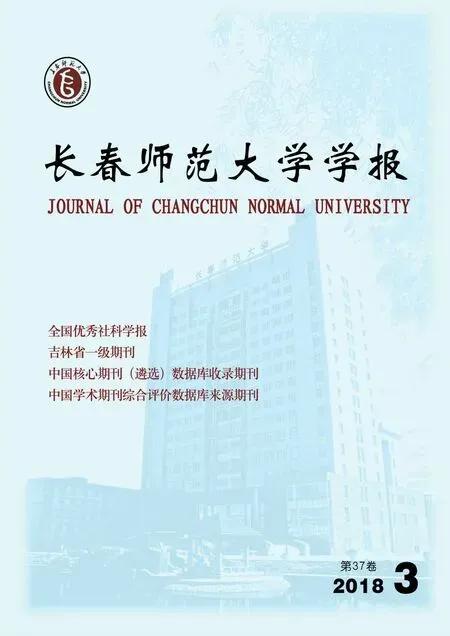论卞之琳的莎士比亚研究
肖曼琼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剧作家,也是人们研究、评论最多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同时代诗人、剧作家琼生曾赋诗对他进行评价,称其为“时代的灵魂”、“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1]45,47。400多年来,世界上众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进行过评论。20世纪20年代,莎士比亚剧作传入中国,受到诸多文学爱好者的追捧;50年代,中国掀起莎学研究高潮。在众多莎学研究者中,卞之琳自成一家,发表了20多万字很有见地的评论文章,为世人留下了颇具价值的莎剧“论痕”。
一、卞之琳莎学研究的缘起
卞之琳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莎学家,其莎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此时他已年届不惑。但是,他与莎士比亚的缘分早在孩提时代就已开始。卞之琳念初中时,其英文课本选有兰姆姐弟合编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这是他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最初接触,也是他日后热爱莎剧、译介莎剧的“触发剂”。从此,他与莎士比亚结下不解之缘,莎士比亚的著作伴随他度过了读书、翻译和研究生涯。
1927年,卞之琳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念高中。该校实行学分制,设有选修课。卞之琳选修莎士比亚戏剧,并阅读了原著《威尼斯商人》。1929年,他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该系一年级就开设莎士比亚戏剧课,这门课程的学习为他日后从事莎剧翻译与研究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实际上,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初试牛刀,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大学毕业后,虽然卞之琳的工作较少涉及莎士比亚,业余时间又忙于创作与翻译,但其意识深处始终晃动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始终怀着一种解不开的莎翁情结。
促成卞之琳最终研究莎士比亚的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一年,他调到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而能集中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他申请了“莎士比亚研究”这一课题,期望在他情之所钟的莎剧翻译与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卞之琳以“四大悲剧”作为其莎学研究之发轫,陆续发表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1956)、《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1956)、《<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1964)、《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1964)等一系列被视为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颇有分量的莎评文章。同时,他将研究与翻译结合起来,翻译出版了《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的七首十四行诗,并计划在50年代末完成“四大悲剧”的翻译。然而,由于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他未能如愿以偿。
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卞之琳作为“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批斗,其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煽动“大、洋、古”的“孽绩”。他一度想放弃外国文学翻译与学术研究,但莎士比亚在其脑海中挥之不去,译介莎士比亚、传播外国文化始终是他难以释怀的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莎剧翻译与研究。1985年,卞之琳终于完成“四大悲剧”的翻译和系列莎剧评论文章,并将这些翻译与研究成果分别收入《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和《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这两部著作是卞之琳建国后最重要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也是他一生译介莎剧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二、卞之琳莎学研究的结晶
在《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中,卞之琳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他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莎剧作品置于社会生活中进行考察,置于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分析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特征,分析莎剧作品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对剧中人物命运的影响,分析剧中正面人物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与阶级局限性,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这一时代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
卞之琳指出,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辉煌而又残酷的时代:一方面是工商业的发达兴盛及资产阶级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是社会各阶级间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以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这个时代孕育了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既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又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愿望与理想。而始终贯串莎士比亚作品的思想,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进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莎翁作品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表现出深广的人民性。莎士比亚是爱人民、反映人民的愿望和理想的人文主义作家,但他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人民群众的集体行动是盲目的,这显示了他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2]2-11卞之琳的辩证分析方法,避免了简单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562的观点。这一观点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物,在思想认识上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制约与影响。认识到这点,我们才能对评论对象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莎剧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是卞之琳莎学研究最显著的特征。在其所写第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莎学论文《论<哈姆雷特>》中,他开篇即表明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他站在历史与时代高度探讨哈姆雷特这个典型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该典型形象表现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艺术。他指出,莎士比亚在该剧本中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深刻的矛盾,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和它烛照下的社会现实矛盾,歌颂了人类为理想而进行的不屈斗争。他还指出,哈姆雷特虽然有理想、爱人民,也深受人民爱戴,从体味人民的苦难里感受到超乎个人的斗争力量,但是他孤军奋战。时代的局限使他未曾意识到应该将先进思想与广大人民结合起来,以形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他的代表人民的先进思想和脱离人民的斗争行动产生了悲剧——时代的悲剧。[2]1,36-37,48
人们进行文学批评需要把握两个标准:一个是思想标准或意识形态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建国初期,中国学术界强调意识形态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时甚至只强调意识形态标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时的莎学研究偏重思想内容分析,极力发掘作品中的教育意义,无视莎剧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这方面,卞之琳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观点,不仅详细探讨了莎剧进步、深广的思想内容,而且从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体特征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剧本生动优美的艺术形式,把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辩证有机地统一起来,融进自己的莎学批评之中。在评论《哈姆雷特》时,他不同意艾略特所说的《哈姆雷特》是一个“艺术性的失败”[2]22-23,而认为“这个剧本所以是世界名著、所以有极高的价值、所以能教育人民,最后还是靠它直接诉诸读众或者听众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吸引力、艺术感动力、甚至不妨说艺术震动力。帮助达到这种艺术效果的艺术手法,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莎土比亚化’的具体手法”[2]106-107。显然,好的思想内容和好的艺术形式是《哈姆雷特》具有巨大感染力、成为经典作品的根源,“艺术性的失败”之作是不会历久弥新、魅力长存的。
在其他莎学评论文章中,卞之琳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作品放在历史时代背景中进行辩证分析。他分析作品中所包含的广泛社会内容,所表现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反映的深刻社会矛盾和思想危机,以及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精神。他指出,莎士比亚最基本的创作倾向实质是“当时在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交叉发展面前的最开明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两面性”,其表现“是以符合当时人民大众的愿望这一面为主的”。因此,他的剧本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2]265-270
总之,卞之琳的莎学论集《莎士比亚悲剧论痕》是我国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三、卞之琳莎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必然受特定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他们在理解、阐释文本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其所处时代的精神与思想潮流的影响,对文本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评析。
卞之琳的莎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刚刚从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年轻共和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国际援助来帮助自身恢复经济、巩固政权、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不但政治上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而且经济上给予大力援助,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与封锁。这决定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基本依照苏联模式。当时,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写过一篇题为“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文章,指出:“苏联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老师,而首先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老师。”“苏联人给中国介绍马列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一种重大无比的帮助,其意义‘胜过百万雄兵。’”[4]46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中国莎学研究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基本采取了全盘接受态度。他们大量译介俄苏莎学文章及论著,翻译或重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俄国文学巨匠的莎评文章,以及苏联莎学家莫洛佐夫、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莎学论著,将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视为中国莎学发展的指南。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卞之琳认真学习和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莎学研究。1963年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语言文学教研室编辑出版的《文艺理论专业外国文学学习参考材料(一)》收录了四篇篇幅较长的莎学论文,分别是莫罗佐夫的《莎士比亚论》、阿尼克斯特的《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以及卞之琳在1956年发表的两篇莎评文章——《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阅读它们,读者可以发现两位苏联莎评家对卞之琳莎学研究的影响,也可以从论文集的选择与编排中看出卞之琳的莎学观点与这两位苏联莎评家的莎学观点之间的联系。
卞之琳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莎学研究。同时,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他的莎学研究还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新中国成立之初,阶级矛盾依旧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敌对势力不甘失败,千方百计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颠覆新中国的政权。长期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使得我们党及其领导人形成了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的政治经验和思维模式。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党仍然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将阶级矛盾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建国伊始,我们党就紧锣密鼓地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1951年秋,北京、天津等地的高等院校开始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要求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牢固的阶级斗争观念,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争。
卞之琳与我国其他莎学家一样,不可能不受这种四处弥漫、深入人心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不可能不将阶级斗争理论应用于自己的莎学研究之中。他努力发掘莎剧中蕴涵的阶级矛盾,认为应该把实际社会的阶级关系分析主要放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并以此看待莎剧作品里的世界。他肯定莎士比亚的反资产阶级倾向,指出莎士比亚在戏剧里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封建罪恶,反对资本主义罪恶[2]65,16。他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详细论述莎士比亚的时代、社会以及各种阶级关系,透彻分析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譬如,在对《里亚王》①中的人物考黛丽亚和里亚王进行分析时,他说考黛丽亚最初表现出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倾向,但最后变得目光短浅,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一副圣母形象。卞之琳认为这一形象的矛盾主要在于“不受资产阶级狭隘性局限的创作倾向,在贵族和平民相结合的幻想中,在从贵族人物找表达理想的形象中,还是受了不自觉的实际是最基本的当时资产阶级倾向的两面性局限,还是沾染了封建思想的残余。”[2]221至于里亚王,卞之琳则认为他起初代表腐朽反动的社会阶级力量,是一个倒行逆施、昏庸老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统治者;后来,里亚王变得一无所有,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仿佛代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代表正面的广大社会力量。[2]222-228类似阶级分析的例子在《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中所在多有,阶级分析方法使卞之琳的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卞之琳的莎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性质不同的社会大变动当中,前后断续摆了30多年”[2]4。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在他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中留下了印记,这从其莎学研究中几个概念的变化可见一斑。他在这部专著的《前言》中对此作了说明:从最初照搬苏联莎学家的“人民性”概念到后来为避免“徒然给当时日益升级的一种极端倾向提供靶子”而不再搬用,从搬用苏联术语“人道主义”到恢复与人的觉醒、人的解放、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有关的本来译名“人文主义”,从对莎士比亚作品现实主义的评价到浪漫主义的认同,其探索过程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轨迹。[2]4-8因此,他将自己30年来历经坎坷却从未放弃的莎学研究“用时代这条线……贯穿成集”[2]7,取名“莎士比亚悲剧论痕”。
四、结语
陈丙莹在《卞之琳评传》中说:“严肃的学者严肃地看待别人的学理,也严肃地检验自己的研究。”[5]292卞之琳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他学习、批评别人的学理是认真思考,而非人云亦云;审视、检验自己的研究也是客观对待,“不因‘时髦西风的冲击’而‘随声附和’,不因‘老一套’而‘金蝉脱壳’”[6]185。他指出,自己的莎学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莎学研究曾出现过繁琐、偏激的倾向,对莎剧所作的阶级分析有点简单庸俗、机械生硬[2]5-6,在分析《哈姆雷特》之类悲剧的社会反映和社会意义方面也趋简单、机械,探讨其艺术特征则过于繁琐[7]40。他在将自己30年的莎学研究收编成集时,删去一些特定时代和特定政治环境带来的废话、套话、浮夸语和过头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自己莎学研究中的主要论点。尽管卞之琳的莎学研究受到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但其中蕴涵着许多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今天,我们阅读他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仍然感到深刻透辟,不禁为他深厚的莎学学养所折服。
[注释]
①即《李尔王》(King Lear),卞之琳译为《里亚王》,本文采用其译名。
[1]卞之琳,编译.英国诗选(英汉对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艾思奇.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A].钟离蒙,杨凤麟.解放战争时期哲学思想战线上的斗争[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
[5]陈丙莹.卞之琳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6]王佐良.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7]卞之琳.关于我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无书有序[J].外国文学研究,1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