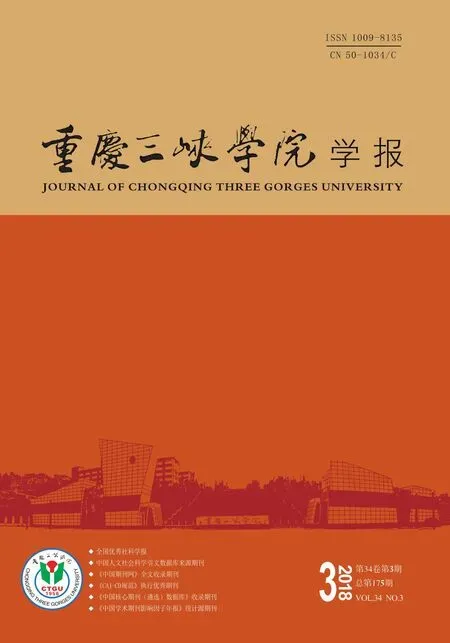《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新探
(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国学研究所,山东济南 250031)
刘勰(约 466—532)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很明显,他是把《文心雕龙》前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作为“文之枢纽”来设置的。而所谓“亦云极矣”,是说达到了极致,至尊、至重、至高、至大,无以复加,更不可移易。由此不难看出他对这部分内容的高度重视,以及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何谓“枢纽”?“枢”,《说文》:“枢,户枢也。”户枢即门轴,没有门轴,门户就无法开合;用来比喻事物重要的、中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纽”,《说文》:“系也。一曰结而可解。”本义为绑束,后称提系器物的带子为纽带,用来比喻控制事物的机键、系结事物的中心部分。在比喻义上,二者是相同的。两者组成一个合成词,通常用以喻指事物的关键部位或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但用于指称一部学术著作的关键部分,大概是刘勰的独创。现代汉语中“枢纽”一词除了广泛应用于交通或水利工程之外,鲜有用于指称学术著作结构者。今人按照当代学术著作的构成惯例,一般将刘勰所谓“文之枢纽”称作《文心雕龙》全书的“总论”[1]164“总纲”[2],也有称之为全书“导言”[3]的。就是说,研究者大都认识到了前五篇在全书中居于纲领地位并且是一个整体;与此有关的论著不胜枚举,除了范文澜(1893—1969)《文心雕龙注》把《诸子》篇拉入总论而把《辨骚》篇割裂出来作为文类之首划入文体论[4]、牟世金(1928—1989)以为《辨骚》篇虽属“枢纽”但不属总论而属文体论[1]168之外,学界对此大多不存异议。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共同认识还只是初步的、粗浅的。因为“枢纽”与“总论”“总纲”或“导言”相较,不仅是古今用语的不同,在含义上也存在某种差别。对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如果缺乏精确的认识,就可能导致对全书理论体系的把握和对刘勰文学观的认识上出现很大的问题。而事实上,这样的问题早已出现,并且众说纷纭,愈演愈烈,由最初的“失之毫厘”,已经达到“谬以千里”的程度,乃至形成了若干学术公案。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辨析和进一步阐说。
一、一个还是多个:对“枢纽”的总体把握
在笔者看来,刘勰之所谓“枢纽”与现代学术著作之“总论”“总纲”或“导言”的差别在于:“总论”“总纲”或“导言”是全书的概要,可以包括若干并列的、有某种逻辑关系的条目,分别用来统领全书的不同部分;而“枢纽”,则无论包括了几篇文字,却只能是一个结构紧密的整体。我们知道,多中心即无中心,同理,多枢纽即无所谓枢纽矣。
探讨《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它的前五篇是五个“枢纽”,还是一个“枢纽”?在同一特定语境中,作为“枢纽”,能多个并存吗?
据笔者理解,在刘勰的设置中,它们只是、也只能是一个“枢纽”。看似并列的五篇文字,其实只是构成这一枢纽的不同构件。而在这些构件中,必定有其核心或主轴。这一核心或主轴,不仅统领其余四篇,而且也对全书起到统领作用。其余四篇,只不过是核心或主轴的附属物,是围绕核心或主轴来设置并为其服务的,并不要求每一篇都对全书起统领作用。如果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认为“文之枢纽”部分的五篇文章是并列关系,且为由主到次的线性排列,即彼此分别是不同的“枢纽”,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偏离刘勰的本意。许多年来,不少研究者对此书的误读,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争论,往往是由于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偏差。
“文之枢纽”的核心或主轴是什么?揆诸刘勰的写作意图,显然应为在五篇里处于中间位置的《宗经》篇。因为“宗经”是他主要的文学思想,并且贯穿《文心雕龙》全书。《通变》篇中“矫讹范浅,还宗经诰”八个字,可以视为他对全书作意最简洁有力的表达。而核心或主轴既经认定,其余四篇的附属地位也就可以确定了。当然,这些附属的篇章,刘勰也无一不是精心结撰的,里面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读者不可因其“附属”地位而予以轻视。作为单篇文章,它们也各有其表达的中心,不过相对于《宗经》,却只能是“次中心”;它们主要是分别从不同侧面为突出《宗经》的核心或主轴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
这一点,其实并非笔者的新见。近人叶长青(1902—1948)在其 1933年印行的《文心雕龙杂记》中就曾经指出:“原道之要,在于征圣,征圣之要,在于宗经。不宗经,何由征圣?不征圣,何由原道?纬既应正,骚亦宜辨,正纬辨骚,宗经事也。舍经而言道、言圣、言纬、言骚,皆为无庸。然则《宗经》,其枢纽之枢纽欤!”①叶氏原书为其授课讲义,由福州职业中学印刷厂印行,引文转见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在认定《宗经》为“文之枢纽”之核心或主轴的地位上,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最为明确的论述。刘永济先生(1887—1966)也有类似见解,他在解释《宗经》时说:“舍人‘三准’之论,固已默契圣心;而此篇‘六义’之说,实乃通夫众体。文之枢纽,信在斯矣。”[5]5尽管他的论述只是着眼于“三准”和“六义”,没有顾及到全书,但他指出《宗经》篇才是真正的“文之枢纽”,则是很有见地的。如果不是对全书的理论体系和刘勰的思维脉络有精准之把握,就不可能做出此种论断。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以经典为“枢纽”的观念,还表现于《议对》篇。他说:“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尽管这里的“枢纽”已经活用为动词,为紧密联系、不得脱离(经典)之意,与《序志》篇作名词用有所不同,但名词活用为动词之后,其本义仍然保留,在本句中,以经典为“枢纽”的涵义显然还是包括在其中的。
当然,由于刘勰把前五篇总称之为“文之枢纽”,我们不妨在当下的讨论中将《宗经》篇看作其核心或主轴,以避免在用语上与原文抵牾。
二、“宗经”何以会成为刘勰主要的论文主张
刘勰之所以会把“宗经”作为其主要的文学主张,就其自身说,实际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出于他对儒家经典发自内心的崇拜,其二则是出自他对当时文坛弊端的不满。这可通过《宗经》《序志》等篇中刘勰的一再表白而清楚了解到。
For the sake of clarity,taking the 7-DOF manipulator shown in Fig.1 as an example,the optimal locked angle of the fault joint is solved as follows.
在《宗经》篇里,刘勰写道: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者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不难发现,在刘勰心目中,五经是那样的尽善尽美,实在是作文的最高典范。他认为,依托五经来进行创作,就如同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所以,为文必须“宗经”。
不仅如此,刘勰还认为,自五经以后文学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流弊,即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到了近代,则愈演愈烈,达到了“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的程度。而要“正末归本”,使文学发展回到健康的大路上来,必须“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通变》)。他的认识是否完全正确,宗经主张在当时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可以另作别论,但他之宗经确系出于至诚,则不庸置疑。
除此之外,刘勰选择“宗经”作为矫正文坛弊端的利器,也和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或内在规律直接相关。那么,这种基本性格或内在规律是什么呢?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先生(1904—1982)对此有过很精辟的论述:
五经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正如一个大蓄水库,既为众流所归,亦为众流所出。中国文化的“基型”“基线”,是由五经所奠定的。……中国文学,是以这种文化的基型、基线为背景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文学,弥纶于人伦日用的各个方面,以平正质实为其本色。用彦和的词汇,即是以“典雅”为其本色。我们应从此一角度,去看源远流长的“古文运动”。但文学本身是含有艺术性的,在某些因素之下,文学发展到以其艺术性为主时,便会脱离文化的基型基线而另辟疆域。楚辞汉赋的系统,便是这种情形。其流弊,则文字远离健康的人生,远离现实的社会。在这种情形之下,便常会由文化的基型基线,在某种形式之下,发出反省规整的作用。《宗经》篇的收尾是“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正说明《宗经》篇之所以作,也说明了文化基型基线此时所发生的规整作用。[6]387-388
徐先生站在思想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对五经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予以精到的揭示,可谓独具慧眼。由此我们也可以豁然开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之所以会一再出现形形色色的所谓“复古”运动(或称“古文运动”),个中缘由,原来在此。而齐梁之际,如刘勰所说,已经“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正是到了文化的基型、基线该出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当然,此种基型、基线要发挥作用,必须借助于作家作品,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于是自觉地、也是历史性地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三、“文之枢纽”何以用了五篇文章来完成
既然“宗经”可以确定为《文心雕龙》统帅全书的主导思想,那么,按说有了《宗经》一篇列于卷首就可以了,刘勰为什么要用多达五篇的文字来加以论述呢?
细加推究,可以发现,这是由于在刘勰的意识中,觉得仅用《宗经》一篇尚不能充分、完整地表述他的宗经思想。诸如为什么“文必宗经”,经书的伟大究竟有什么根本依据,与经书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前代著作是否也在应“宗”之列,等等,这些都还需要作充分的阐发和必要的辨正。因而他在《宗经》前后又分别写了两篇文章来作为铺垫或附论。这样的内在理路,可以通过前后各篇与《宗经》的关系来加以揭示。
先来看《原道》《征圣》与《宗经》之间的关系。
在刘勰看来,之所以“文必宗经”,因为五经是由圣人制作的;而圣人之所以要制作五经,是用来昭示“天道”的。只有把这种道—圣—文三位一体的关系彻底地揭示出来,才能使读者充分认识经书的伟大,进而更好地认同他的宗经主张。《原道》《征圣》篇的写作因此便有了必要性,他的这一思维路径应该是不难体察的。尽管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由《原道》到《征圣》再到《宗经》,是循着“道沿圣以垂文”的关系,呈顺流而下之势,而在刘勰的构思和写作中,其实是由《宗经》到《征圣》再到《原道》的,是循着“圣因文而明道”的方向,呈逆流而上之势。他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让人们认识到五经是天道通过圣人在人间的具现,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因之其宗经的主张便具有了“天经地义”的稳固地位。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原道》篇尽管居于全书卷首,但并非“开宗明义”,也不是用来统领全书,而主要是用来为《宗经》张目的。至于《征圣》,则是《原道》和《宗经》之间的必要过渡。究其实,《原道》和《征圣》,都只不过是《宗经》的铺垫而已。其在“文之枢纽”中的地位,只能是附属的构件。如果离开了《宗经》,而在前两篇中抓住某一个或几个片言只语索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走向歧途。例如,把本来只是一般叙述语言的“自然之道也”视为刘勰所本之道、把本来只是一个比喻句的“衔华而佩实”当作刘勰论文的最高标准,就是典型的个案。
刘勰的这一思路和前三篇事实上不同的地位,前贤已有揭示。1970年代,徐复观先生曾撰文指出:“《原道》、《征圣》,实皆归结于《宗经》,所以这三篇实际应当作一篇来看。”[6]385祖保泉先生(1921—2013)也曾正确地指出:“‘体乎经’才是‘文之枢纽’的核心,‘宗经’思想乃是《文心》全书的指导思想。”他还指出:“‘道’是靠圣人的文章来体现的,圣人也只有靠文章来阐明‘道’。……一句话,‘道’和‘圣’离开了‘经’,那便成了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话。”“从‘言为文之用心’角度看,刘勰抓住了历来为人们所崇敬的‘文’(六经),把它说成是创作的范本和评论的最高标准,于是撰《宗经》篇。‘经’是‘圣人’撰述的,于是在《宗经》之前,加上《征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因为他能‘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于是在《征圣》之前,又冠以《原道》。其实,论‘文’而要‘原道’、‘征圣’,都不过是为‘宗经’思想套上神圣的光圈而已。”[7]这是很有见地的。其他学者的类似见解还有一些,兹不具引。所可惜者,几十年来,他们的见解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人们更多的还是孤立地去看待“枢纽”中的各篇文章,而极少有能以《宗经》为制高点俯瞰整个“枢纽”和《文心雕龙》全书者。
再来看《正纬》《辨骚》与《宗经》之间的关系。
通过《原道》《征圣》的铺垫,《宗经》的主张已经成功地凸显出来了,按理说刘勰应该自信不会再有人怀疑其“文必宗经”的正当性了。但是,回顾楚汉以来文学发展的实际,他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厘清,否则人们在践行“宗经”主张时仍然会遇到问题。
首先是曾“前代配经”的纬书。自西汉后期产生的纬书,至东汉乃大行其道,与经书并行。用刘勰的话说,就是“至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那么,“宗经”的同时,是否也要“宗纬”呢?对此,刘勰的态度十分明确,答案是否定的:“经足训矣,纬何预焉!”为了申明这一立场,他专门写了《正纬》篇,用主要篇幅指出纬书的“四伪”,并援引了前贤桓谭(约前23—56)、尹敏(东汉初期人,生卒不详)、张衡(78—139)、荀悦(148—209)等人对纬书的否定性意见作为论据支撑。当然,由于刘勰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的,他对纬书的价值并未完全否定,而是指出其“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可以“酌”取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的成分用于写作实践。但这只不过是附带论及,《正纬》篇的主旨,则是告诉读者:纬书不是其所“宗”之“经”,“宗经”时是不能将纬书混同其间的。
然后是历来“诗骚并称”的《楚辞》。《楚辞》与五经的关系不像纬书那样密切,但它作为纯文学作品却有很高的成就,曾受到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及扬雄(前53—18)、王逸(东汉中期人,生卒不详)等人的高度评价,认为其“依经立义”“体同诗雅”,“与日月争光可也”。其中的《离骚》又曾被称为《离骚经》,刘安还曾为其作《传》。那么,《楚辞》,特别是其中的《离骚》,是否应该属于所“宗”之“经”呢?刘勰认为亟有加以辨析的必要,为此而又作《辨骚》篇。他认为“(刘安等)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属于“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就是说,把《离骚》比拟为经书是褒、扬过分;而说《离骚》全不合经传,则是贬、抑过当。通过对《楚辞》主要篇章和内容的辨析,他指出楚辞作品与经书有“四同”“四异”,换言之,与经书相比,还是存在差距的,此即所谓“雅颂之博徒,辞赋之英杰”;其作者当然也并非圣人。这样辨析之后,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辞作品,能否作为其所“宗”之“经”,答案就在不言之中了。清人纪昀(1723—1805)批语谓“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8],正是有见于此。当然,《楚辞》作为《诗经》变异、发展的产物,刘勰对其成就是有足够评价的,但对其流弊也有充分的认识,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就是他最基本的评断。与此同时,刘勰深知后世的文学创作已经不可能无视《楚辞》的存在,作者们也不可能不在某一方面受其影响;为了避免其“流弊”,尤其是担心后来作者因羡慕楚辞的“惊采绝艳”而忘记了宗经,他谆谆告诫作者们在写作时务必要“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①“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二句乃分承上二句“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而来,“奇”“华”指的是“楚篇”,“贞”“实”指的是雅颂。。研究者如果明确了《辨骚》与《宗经》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致误认为刘勰对楚辞的总体评价高于五经,也不会误以为“《辨骚》是以二十一篇文体论的代表者的身份列入‘文之枢纽’的”[1]168了。至于刘勰对《离骚》及其他楚辞作品的评价与现代通行认识是否一致,则是另一回事,今人正不可因对楚辞的喜爱而去曲解刘勰的本意。
进行了这样一番“辨”“正”、明确了纬书和楚辞非其所“宗”之“经”之后,刘勰觉得“宗经”的大旗才算真正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所谓“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正反映出了他此时的喜悦和自信。
而这,就是刘勰要把“文之枢纽”写成五篇的内在缘由。其中不仅道、圣、经是三位一体的,道、圣、经、纬、骚也是五位相关的,缺其一则意义失于完备。其用心之良苦、立论之坚实,在古代文论中罕有其匹。
四、《序志》所述与篇名用字之比较
为正确把握“文之枢纽”的准确内涵,有必要对《序志》篇“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与各篇标题中的用字——即“原”“征”“宗”“正”“辨”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笔者认为,彼此两者尽管指涉篇章相同,但并非简单的变文避复,而是在不同语境中,由于立足点不同而进行的精心措置,因此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
《原道》之“原”,是推原,即把以五经为典范的文的根源推原到神秘的天道;“本乎道”之“本”,是说他的论文是以天道为本原的。
《征圣》之“征”,是征验,即揭示作为文章典范的五经都是出于圣人之手;“师乎圣”之“师”,是说他的论文是以圣人为师法的。
《宗经》之“宗”,是宗法,即倡言以圣人传道的五经作为为文的最高标准;“体乎经”之“体”,是说他的论文是以五经为体式的。
《正纬》之“正”,是辨正,即辨正纬书中存在“四伪”,虽曾“前代配经”,但并非其所“宗”;“酌乎纬”之“酌”,是酌取,即可以吸取纬书中有益于文章的成分。
《辨骚》之“辨”,是辨别,即辨析楚辞与五经的异同,指出其地位次于五经,也并非其所“宗”。“变乎骚”之“变”,是变通,即可以借鉴楚辞中文学发展的经验。
综合以观,《序志》中的用词,完全是从《文心雕龙》全书写作的需要或所把握的基本原则来措置的;而各篇的标题,则是暂时脱离了全书写作的需要,紧扣该篇的主要内容和五篇间的内在联系另行命名的。作者的立足点和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存在微妙的变化。相比之下,可以发现,前三篇对应的字眼,即“本”与“原”、“师”与“征”、“体”与“宗”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后两篇对应的字眼,即“酌”与“正”、“变”与“辨”之间,则因所持的角度不同,存在着弃与取的差别,并非正相关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刘永济先生所说“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贬时俗,是曰破他”[5]10,尽管不无偏颇,但并非全无道理。尽管在我们看来,后二篇是正负兼具、有弃有取的,但与前两篇相比,角度及立意均有差别,则无疑义。因此,在阅读理解中,应当兼顾这两处表述的细微差别,以期全面把握刘勰的用意,而不宜把它们简单地等同起来。否则,就容易在理解刘勰的思想观点时出现偏差。例如,有人把《原道》之“原”与“本乎道”之“本”完全等同起来,而忽略了它与《宗经》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看出其事实上作为《宗经》铺垫的作用,以致过分高抬了《原道》的地位,进而对所“原”究竟为何家之“道”产生种种疑窦,做出种种曲解,引发出种种论争;又如,有人对《辨骚》之“辨”的作用忽略不计,只注意了“变乎骚”的“变”字,认为刘勰此篇只是为了研究文学的发展或新变而作,而完全无视文中大段辨析文字的存在,进而忽略了刘勰对《离骚》评价的分寸感,甚至把“博徒”与“四异”之类贬词也强解作褒义,等等,都是由此引起的公案。对此笔者已有专文分别加以考辨[9-10],感兴趣者可以参看。
五、余 论
四十多年前,徐复观先生曾感叹:“今日肯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对一部书作深思熟玩,分析综合的人太少了。大家只随着风气转来转去。百年来的风气,封闭了理解《文心雕龙》之路。”[11]364至于多年来大陆学界的《文心雕龙》研究,则不仅仅是学术跟风问题,而是所受到的学术之外的干扰因素更多,导致了许多简单问题的复杂化和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对“文之枢纽”的把握尤其如此。笔者以为,摒除各种干扰和先入之见,对《文心雕龙》原著“深思熟玩”,根据“实事”来“求是”,切实进入原书的语境,并尽可能抵达作者的心境,弄清其构思、写作的思维脉络,从而在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正确揭示其本来意义,发现其当代价值,服务于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才是龙学研究的正途。这样做,实在要比在原来习熟的道路上进行大量的重复劳动更有必要。
参考文献:
[1] 牟世金.《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初探[G]//雕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305.
[3] 珊德拉.刘勰的“文之枢纽”[G]//户田浩晓,著;曹顺庆,主编.文心同雕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47.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
[5]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徐复观.文之枢纽——《文心雕龙》浅论之六[G]//中国文学论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7] 祖保泉.文之枢纽臆说[G]//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175.
[8] 刘勰.文心雕龙[M].戚良德,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9.
[9] 魏伯河.走出“自然之道”的误区——《文心雕龙·原道》读札[G]//中国文论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10] 魏然.读《文心雕龙·辨骚》[J].枣庄师专学报,1984(1):72-79.
[11] 徐复观.能否解开《文心雕龙》的死结?[G]//中国文学论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64.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