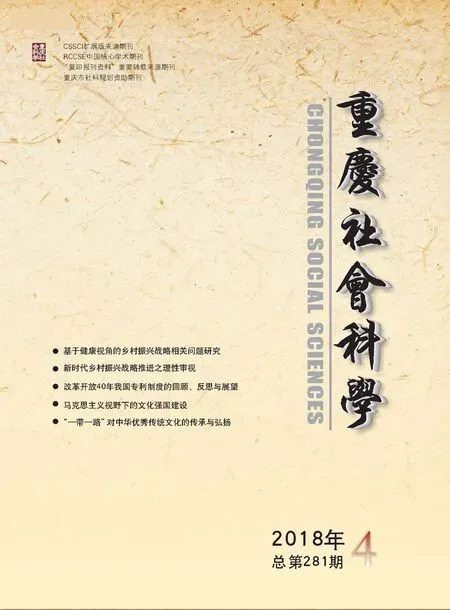司法策略的合法性建构:以乡村司法为背景
王籍慧
(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有两个方面: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化社会转型。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1]。转型期中的“乡村司法”因高度契合于这两个特征描述而备受学界关注。尽管各学者对“乡村司法”概念本身存在争议,但基本上表现为两种理论倾向,即“法治论”和“治理论”[2]。但是,“法治论”和“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忽略了乡村司法的特殊语境:“法治论”忽略了乡村司法事实上承担的政治功能,以及现代司法运行逻辑与转型期乡村背景的不适应性;“治理论”则过于关注基层司法与国家治理目的之间的效果衔接,而对基层司法运作报以过多同情式的理解。因此,在乡村司法中,司法策略通常被视为调和“法治论”与“治理论”冲突以及弥补两者缺陷的重要中介。但是,司法策略本身的合法性建构问题被忽略了。“法治论”不关心(甚至排斥)这一问题,而“治理论”将其理解为一种“实践智慧”而过于推崇。我们过于狭窄地将司法策略的合法性建构问题与它对国家治理目的的助益性问题画上等号,倾向于以司法策略的政治治理功效为标准,从根本上淡化、甚至掩盖司法策略的合法性建构问题。在此,以转型期中的乡村社会为背景,致力于为司法策略的合法性建构提供一种可行方案。
一、司法策略产生的契机
司法策略的产生依托于转型乡村社会中“青黄不接”的局面,即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呈现出衰退趋势,而现代司法在转型乡村社会中却运行受阻,并未真正得以建立。两者都难以为乡村司法提供绝对的权威标准,这一大背景为司法策略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日本一位学者两本著作的中译本,近日在图书市场竟然以同一个书名出现,都叫《低欲望社会》。这样的“撞脸”,让图书市场跟风蹭热点的风气又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
(一)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
乡村社会有其自身的纠纷化解方式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机制。随着现代化转型,包括宗族力量、礼治秩序、道德伦常、风俗习惯等在内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呈现出衰退的趋势。
第一,乡村社会中流动人口的增加冲击着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根基。稳定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了解”。“了解”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其二,关涉了解的要素和程度[3]。乡村流动人口的增加是村民间同一意义体系出现漏洞的重要因素,也会增加人们相互理解的要素和难度,从根本上冲击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社会关系,不断瓦解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根基。
教师应该在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锻炼他们识字的能力,也就是说要对特定环境中的生字有一定的感知力,达到最终掌握的目的。课文里面出现的汉字,会因为语文环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涵义,所以需要与文章的语境进行充分的结合,学生在语境的结合下,就能够加强掌握能力。开展识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的阅读能力得以提升,达到良好的识字效果。基于此,将识字与语言环境相结合,更加有利于学生掌握。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对于身边的发生的事情与相关事物留心观察,养成好的习惯。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发现只要对周遭事物多加留心,就会学习到很多课本之外的生字,有效扩充自己的语文知识。
第三,乡村社会中“关系资本”的减少逐渐瓦解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根基和效果。美国杜克大学的安妮鲁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认为,“关系资本涉及在与他人合作中影响个人行动的价值观、态度、准则和信念”[6]。转型乡村社会关系资本减少的典型特征是村民日益独立、村民之间关系的弱化以及交往的理性化。“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7]。关系资本的减少意味着村民们在集体行动时价值观、态度、准则、信念的变化,以及对集体互利行为的必然削弱,这必然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宗族、道德、风俗等传统因素对人们行为“决定性”影响的逐步弱化,人们对“失礼”“失德”的恐惧大大减少,这些都共同瓦解着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根基和效果。
(二)现代司法在乡村社会中运行受阻
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并不意味着现代司法在转型乡村社会中的必然建立,反而由于现代司法运行逻辑与乡村社会日常逻辑的不契合,现代司法在转型乡村社会中反而遭遇重重阻碍,难以得到真正的建立和运行。
第一,在乡村社会中,现代司法运行逻辑往往将司法权视为国家权力自上向下渗透和扩展的重要方式,司法是实现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但是,司法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司法的自主性要求与司法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方式的工具性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匹配、不契合,这是乡村司法运行的最根本困难。
第二,司法的内在运行逻辑与村民的日常思维模式存在“司法思维”与“大众思维”、“司法逻辑”与“大众逻辑”式对立和差异。转型期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思维和逻辑必然能够接受现代司法的运行逻辑。反而,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可能成为乡村司法运行的内在障碍。
第三,就外在面向而言,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并不意味乡村微观权力的消失。例如,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家庭、宗族因素的减弱意味着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纠纷解决组织——“家族”面临半瓦解的风险,家族已经不足以承担其在传统社会中所承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功能,但这这些因素并未完全消失。并且,随着现代化转型,乡村社会中也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微观权力”,由乡村富民、“乡村混混”等“非国家治理者”构成的乡村微观权力也会为乡村司法运行制造障碍和困难[8]。
2.描述芽的发育和根的生长过程(了解)。2013、2014年没有考查,从2015年开始到2018年,每年均有一个选择题,分值为1.5分,但考点都在考查“根”的内容,“芽的发育”近几年都没有考过。这一考点主要考查根尖,即根冠、分生区、伸长区、成熟区的功能。
(三)转型期乡村社会中“青黄不接”的尴尬现状
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原则上应为司法在乡村社会中的建立提供契机。因为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是全面的,如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管辖范围”的模糊化和缩小化等。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半瓦解”与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转化为一种带有“非人格化”的关系。这有利于强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它所蕴含的主要意味之一,便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日益明显的“制度依赖”或“公共化路径依赖”[9]。这应该会促进作为一种具有制度理性的司法在乡村社会的挺进。司法在转型乡村社会中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仅是“送法下乡”政策的结果,更是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瓦解后,村民们“迎法下乡”需求和态度的体现。乡村司法应该是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衰退后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必然需求和可欲选择。
但是,司法本身内在运行机制的缺陷以及司法与转型乡村社会背景的不契合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在乡村社会的良好运行。这些要素共同造成了乡村社会中“青黄不接”的局面:旧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不断衰退,而新的现代司法却因各项阻碍因素没能真正在乡村社会中得以建立,作为国家权力表现的司法阻却因素未真正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完全掌控。因而,正是这一尴尬的乡村司法现状(不仅仅是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衰退本身)为司法策略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也构成了司法策略运行的大背景。
二、司法策略合法性建构的前提:逻辑转换
司法策略的天然使命必然与法治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治理这一双重目的紧密相关,我们也必须基于这一双重需求来审视司法策略的合法性建构问题。其关键在于探寻司法策略合法性建构的前提,即逻辑转换。
第二,传统纠纷解决方式难以迎合村民利益结构的多元化需求。例如,“新农民阶层是通过职业身份来划分的,它解构了原有差序格局中复杂而稠密的社会关系”[4]。传统纠纷解决方式难以用自身的逻辑来满足新利益结构的需求,或解决多元利益之间和冲突。“历史上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礼治在今天越来越不足以充分料理愈加复杂的乡村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这一论断在当今转型乡村社会中仍然适用[5]。
(一)当前司法策略的建构逻辑
在河道疏浚整治中,苏州市始终按照“两清一建”的标准,把农村河道疏浚与土地复垦、道路建设、环境整治和植树造林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疏一条河道,复垦一块土地,增加一片林地。为确保整治质量和进度,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整体推进”的方针,采取行政手段、经济制约、技术措施,通过召开现场会的形式,把村庄河道疏浚整治搞成典型工程,推动疏浚整治工作顺利实施。同时,把河道疏浚整治工作作为考核基层干部工作目标任务的主要内容之一,把河道疏浚工作作为全市水利土方任务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强检查考核。
本质上,“问题—策略”逻辑是一种政治治理逻辑。这一逻辑预设了国家的积极能动性,“国家成为政治活动的唯一舞台和政治效忠的唯一对象:社会被‘国家化’了,或者说是被国家吞并了。社会问题和政治策略消解为国家问题和国家策略[10]。”在这一逻辑下,政府是社会的总管,贯彻和执行国家的政策是司法的重要任务。国家的治理目的最终将体现在司法活动的内容以及运行方式之中,国家的问题和策略也将转变为司法性问题和司法性策略。在这一逻辑下,司法被过多地赋予了国家治理功能,司法的终极目的也变成了服务于国家的治理目的。“党和国家政法工作的政策导向趋向于司法承担起改造社会、缓和当前社会矛盾、避免人民内部冲突升级、保护弱势群体的政治功能”[11]。
然而,由于国家治理功能具有多面性,严格适用司法的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目的的实现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因此,被赋予了过多国家治理功能的司法为了满足、实现这些功能,为了能够解决这些被提出来的问题,必然会对自身进行相关的改造,或在具体过程中运用能够使司法契合于国家治理功能的制度安排、操作技巧等。司法策略仅仅是这些改造的一个面向,但这并不妨碍司法策略是“问题—策略”逻辑的产物。
(二)“问题—策略”逻辑的弊端
当前司法策略作为“问题—策略”逻辑,存在一系列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司法策略建构容易迷失在诸多“问题”中。“问题—策略”逻辑的前提预设是:司法个案中的纠纷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纠纷,还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回答哪些问题是司法策略建构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司法策略很容易迷失在诸多问题假象之中。并且,司法回应社会问题的方式和程度是很难把握的问题,司法策略有可能因回应过多或过少而陷入困境。并且,司法策略对问题的回应必须依赖社会语境。“如果交往行动不根植于提供大规模共识之支持的生活世界的语境之中,这样的风险就会使基于交往行动之社会整合变得完全没有可能”[12]。在转型期乡村社会中,人们很难在这种具有“大规模共识支撑的生活世界”观念下达成共识。因此,司法策略在转型期乡村社会场域中,在多元主体、理念、话语与知识的共存与博弈中自我准确定位是一个难题。
第二,这一逻辑形成的司法策略本身具有局限性。基于这一逻辑,司法策略的内容、目的与国家治理的目的直接挂钩,它会根据国家治理政策、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将导致司法策略具有“不稳定性”“应急性”和“妥协性”等缺陷。这些缺陷将强化司法过程的武断性,直接影响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并且,这些缺陷也会给其他社会因素诱控司法策略留下缺口和漏洞,导致更多的信息和变量渗入司法策略的形成过程,使司法策略更容易“陷入到一个顾此失彼、循环往复的漩涡之中,易于失却应有的冷静、客观、慎重与全面,表现出背离合理性与统一性的局限”[12]。
第三,“问题—策略”逻辑的最大弊端在于,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对司法策略本身的合法建构。它以“问题解决”为定向来建构司法策略,这意味着它过于强调司法策略解决问题的功能和效果之上,而忽略了司法策略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逻辑很难认真对待司法策略的“司法”合法性,即司法策略与司法的本质、目的、功能、规律之间应有的关联,也无法准确界定司法策略应有的内涵、实施主体、运行方式、实施的限度等问题。
(三)逻辑转换:从“问题—策略”逻辑到“目的—手段”逻辑
司法策略合法性构建的前提在于对司法策略的运行逻辑进行改造。“问题—策略”逻辑对司法策略的合法性建构的忽略并非偶然,因为这一逻辑采取的是一种外在视角,即从司法策略本身之外的问题和任务来建构司法策略,这必然会忽略司法策略本身的内在建构。由此,对司法策略逻辑上的转换必须先从这一外在视角向内在视角转换。笔者认为,用“目的—手段”逻辑来替换“问题—策略”逻辑将是一种可欲的方案。
第三,逻辑转换实际上是将外在的“问题”转换为内在的“目的”,将外在的“解决策略”转换为内在的“手段安排”,这一转换能够增强司法策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逻辑转换后的司法策略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其本身具有主体性和自治性,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内在于主体性之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并行的线性关系,而可以呈现为复杂的网状。在这个关系网中,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应性是多元的,正是这一多元性赋予了策略更多的能动性和自治性。
技术型司法运行模式不足以满足国家治理的政治目的,需要具有更多能动性的司法策略来辅助治理目的的实现。然而,“我国现代社会的治理正从以‘权威—依附—服从’为导向的权力机制,到以‘商谈—合作—服务’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并向以‘理念—规则—程序’为导向的法律机制转变”。[20]单从这三种治理类型来说,在以权力为导向的传统治理机制中,司法策略应被赋予最多的国家治理功能;在以服务为导向的治理机制中,司法策略只应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治理目的期待;而在以法律为导向的法治国类型中,司法策略被赋予的政治治理功能应该是最少的。司法策略在这三种国家治理类型中所承担的政治治理功能应该是一个逐渐减少的趋势。因此,在寻求向法律治理机制转变的当前中国而言,司法策略不应该是国家治理策略赤裸裸的转化,而是应该呈现出一个自我限制的状态,即司法策略仅仅作为司法职业化运作的一个辅助措施,有限承担国家的政治治理目的和功能。
第一,“目的—手段”逻辑采取内在视角来建构司法策略,有助于回归到司法策略本身。“策略”往往出现于存在实际或潜在的冲突的地方,这也是“问题—策略”逻辑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本质上,“策略”是指为了实现特定可欲的目的,根据特定条件、资源、能力而制定的手段安排,并“保持目的与手段、方法的平衡”[13]。因而,“目的—手段”逻辑立基于策略概念本身,有助于内在地构建司法策略。
三、司法策略目的的合法性建构:政治治理目的与法治目的的平衡
第三,司法策略必须为司法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张力提供一种缓和方式。“国家法律与乡村社会的遭遇,更多地体现为知识上的遭遇及其冲突……国家法律在乡村的深入从本质上就存在一种对司法知识垄断的预设”[19]。司法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确具有一定亲缘性。但面临“外来性”的司法知识,地方性知识可能与司法知识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紧张关系或多或少会造成乡村社会中多元知识的混沌现象。中国乡土社会的确具有吉尔兹意义上的“借来的现代化残片和枯竭的传统遗骸奇妙的混合物”特征:作为现代化标志的司法知识在乡村社会中作用有限,而作为传统纠纷解决的地方性知识的遗骸还依然存在。司法策略目的的合法性建构必须为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提供某种方案。
实习单位和岗位的单一化。由于跟岗实习时间较短,很多餐饮企业不愿意接纳学生,所以可以选择的实习单位较少。此外,学生具有个体差异,岗位的单一化,不能提高学生的适岗能力,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因为被安排在了不合适的厨房岗位,对烹饪行业产生了不适应感。
(一)强化司法策略的法治目的
转型期乡村司法存在一种吉尔兹式的“内卷化”困境:“一方面,乡村人民法庭经过多年发展渐趋现代化、正规化,其运作方式亦趋于形式化;另一方面,乡村司法的结果却近乎一种两不是的草率判决,乡村人民法庭本身亦发展成为一种机会主义的运作单位[15]”。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司法策略的建构应首先强调司法的法治目的与功能,致力于实现司法在乡村社会中的良好运行。
当前司法策略的建构逻辑是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为导向、具有工具性质的“问题—策略”逻辑。在这一逻辑下,司法策略通常被理解为解决司法运行过程、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任务和难题的工具。司法策略的任务通常是满足村民对实质正义的需求、弥合司法运行逻辑与村民行事逻辑的差异、缓和司法知识与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张力等。
第一,司法策略应为清除技术型司法运行障碍提供解决方案。司法在转型乡村的运作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可能发生冲突,并在事实上不完全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司法运行逻辑。首先,司法逻辑过分追求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倾向于机械化。它容易忽略或简化个案特征,难以将与案件相关的所有情形进行重新界定。其次,通过法律话语,社会事件向法律事件的转换过程可能遭受误解,“普通的门外汉由于不理解其学术用法而按照通常用法‘牵强附会’地理解这个词语”[16]。最后,严格的司法逻辑无法完全契合村民的利益需求并应对利益结构的变动。因此,司法策略应先关注这些问题,清除或缓解阻碍司法运行的因素,为司法裁判活动保驾护航,以确保司法效果的实现。
第二,司法策略必须致力于实现司法逻辑的自我防御、自我适应,以促进司法的自主性权威。司法运行逻辑主要表现为“事件—文本”的法条关系建构,即将事件纳入法律话语,利用法律的理性修辞技术来表达自身的自主性,具有“给了我事实,我就可以给你法律”的特性,而“法律就是在案卷制作、整理、装订等这样的琐事中完成了它的想象的统一性”[17]。但是,乡村司法“无法对新农民阶层不同群体的选择给出合理解释,反而会衍生一种‘控制的偏见’,即允许乡村司法随时放弃法治精神,迎合民众口味做出所谓‘合乎情理’的裁判”[18]。这是司法策略建构过程中必须预防的另一种极端,因为司法裁判的过程对冲突利益的妥协必须建立在司法自主性权威基础上。
逻辑转换是司法策略合法性建构的前提。基于可欲的“目的—手段”逻辑,本文接下来将主要从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司法策略的合法性建构。司法策略的目的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促进司法的良好运作以及满足转型期国家治理的政治需求。司法策略目的的合法性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两个目的关系的理解。司法策略目的的合法性建构应对二者进行权衡,并应更倾向于司法运行这一法治目的,在此基础上兼顾政治治理目的。
(二)有限强调司法策略的政治治理功能
第二,“目的—手段”逻辑更能够契合逻辑行动结构体系的要求。目的、手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理性逻辑行动的关键问题,“逻辑行动必须包括这种手段与单一目的之间的简单关系,因为这是整个行动体系结构所由以建立的基本‘原子’[14]。”基于行动的视角,司法决策是一个决策性行为,目的—手段的分析范式能够更好地解读司法策略,即司法策略不仅仅关涉一个计划,更是涉及对目的—手段控制、分配、目的与手段关系链条的平衡问题。
有人会有疑问,根据这一类型划分,法治国最终是依靠法律来实现社会、国家治理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法律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应该是逐渐增加的,司法策略在法治国类型中应该承担更多的国家治理功能。但是,法治国治理的核心在于政治治理等方式必须经过法律形式得以表现出来,政治治理的运行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因而,不管法律、司法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如何,司法策略最终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得以建构。因此,司法策略的政治治理目的必须要受到限制,这是司法策略法治目的建构与实现的前提与基础。
(三)对“非法性”司法策略的目的进行排除
在司法策略对政治治理目的与法治治理目的的权衡下,“中国的司法策略主要谋求的是在现有条件与制度环境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统一”,为情、理、法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留下一个开放性的流动空间、渠道[21]。但是,对情理的考量必须建立在司法的合法性运作基础之上。在乡土社会中,影响司法策略选择的因素是多样的,具体包括乡土情理正义观、乡村独特的生存结构等。但对这些情况、因素的同情性理解和考量与司法策略的合法性目的本身是相互冲突的。在现实中,法官的司法策略性行为也有可能偏离司法策略合法性目的本身。在我国司法的结构性背景中,具体法院内部的考核方式、管理方式等因素都会对法官对案件的处理、对司法策略的运用造成一种利益纽带上的影响。因此,当法官对情理等因素的考量超出了司法的合理性范围,或者掺杂了其自身“非法性”利益的考量时,必须排除这些“非法的”司法策略目的。
2.家庭环境方面。学生的课余时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家庭环境对学生诵读习惯的养成有着重要作用。经调查发现,家长陪同下的学生,其诵读能力更强。因而,教师可定期推荐一些诵读的古诗文,要求家长陪同学生一起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也便于家长为学生做一些讲解。《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些篇章侧重于家庭与教师,值得广大家长进行深入学习,与学生共同成长。另外,教师可为家长推荐一些专题网站,引导家长运用这些学习资源,增加学生的学习乐趣,增强家庭的凝聚力。
四、司法策略手段的合法性建构:作为一种程序性互动方式
司法策略的手段是指为了实现司法策略的目的而做出的一系列安排。在笔者看来,司法策略手段的合法性体现在它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方式。当下中国国家治理形态、司法制度本身缺陷以及整个转型期社会背景共同决定了这一互动方式的必要性。我国纠问式的审判方式强调法官对案件的绝对把控,整个庭审以法官为中心,而司法运行的“问题—策略”逻辑要求司法注重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都会导致法律和司法过程对公民个人诉求的某种忽略。在转型期乡村司法中,这些因素可能使司法逻辑难以契合村民的行动逻辑,法官对案件的把握往往也容易被多方面因素牵制。因此,司法策略作为弥补司法缺陷的“衍生品”,是一种为“个人诉求”与“法官控制”、当事人与法官之间通过司法程序得以良好互动的重要方式。司法策略手段的合法性建构也可以转化为这一互动方式本身的规范性建构问题。
(一)互动的前提条件:以价值共识为导向的司法知识的整合
司法与社会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是研究司法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司法策略能够作为法官与当事人互动方式的大前提。笔者认为,以价值共识为取向的司法知识的整合是司法与社会事实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也构成司法策略为法官与当事人提供互动方式的前提条件。
[5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Limits in the Seas, No. 143,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34936.pdf.
司法与社会事实的互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价值共识,那种曾被帕累托、涂尔干从不同的方法、过程得到的同一结论的价值共识。哈贝马斯也以帕森斯的时空双重条件下的社会互动为出发点,认为简单的互动行为是一种以价值取向与利益导向为两个端点的连续系统。一方是纯粹的价值共识,一方是利益的平衡,大部分的互动行为动机取向处于两者之间[22]。价值共识是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主观动机因素,这种价值必须被广大参与者所承认。如果在价值共识上存在障碍,那么,社会事实与司法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价值共识的达成需要一定的促成条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理解的达成或价值共识的形成部分取决于法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司法知识与其他不同性质的知识进行整合。知识上的整合对于理解的达成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司法知识的运用依赖于对其他知识的把握,法官在具体运用专业的、技术性的司法知识时,也会期待其他有关“情”“理”方面的非专业性知识来为案件的良好解决增加灵活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其他方面的知识通过这一过程参与到司法中,因司法知识的积极性实践而使其自身更能够契合司法知识的运行。司法知识与其他知识能够通过司法知识的公共化实践而实现两者之间的良好沟通,达成相互理解的状态及价值共识。
(二)程序性互动的外在建构
从外在视角来看,司法策略作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程序性互动方式主要表现为法官的司法知识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知识的互动。这一程序性互动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教学评价是指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测量、分析和评定的过程。教学评价的功能主要表现在:诊断教学问题、提供反馈信息、调控教学方向、检验教学效果。广义的教学评价包括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和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本文中笔者讨论的教学评价,是指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
第一,获得理解。司法策略作为一种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互动的方式,在整个互动的阶段,司法知识应该对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知识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双向理解是建立在这一开放性态度之上的。理解的双向性表现为:一方面,表现为法官对当事人日常生活知识抱同情式理解,即通过“身体在场”等方式对当事人的“诉求”予以倾听和理解(司法策略往往要求法官理解村民的行事逻辑,甚至对村民的生活知识予以“吸收”)。另一方面,表现为当事人在互动中也通过程序性参与、互动获取了更多的司法专业知识,更理解法官的专业行为。
常见的速度控制算法主要有直线型加减速控制和S型加减速控制等,直线型加减速控制如图7所示,电动机启动时候,其速度沿一定的斜率直线上升,停止时,速度沿一定的斜率直线下降。S型加减速控制算法如图8所示,一般主要采用的是七段式控制方法[3] 。整个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加速阶段、匀速阶段、减速阶段。相比之下,S型加减速曲线在进入低速以及进入最大速度的两个过渡阶段速度曲线都比较平滑,有效地降低了电动机噪声,减少电动机抖动,提高了运动控制的精度[4-5]。
第二,获取博弈中的优势地位。法官的司法知识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知识也是一种博弈的状态。法官通过司法策略与当事人互动的过程也是司法知识在互动过程中获取博弈上的优势地位的过程。
“十二五”期间,辽宁省将以大江大河及其重要支流治理、城市防洪建设及中小河流治理、抗旱备用水源建设为重点,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重点流域和重点地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着重提高水旱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完成辽河、鸭绿江干流及15条主要江河支流、143条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完成116座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总投资191亿元。
第三,通过策略性互动,司法策略的实质内容得以丰富。在策略性互动中,司法策略能够很好地展示其自身的优势,“它将传统治理术‘打包’整合,植入到司法秩序的框架内部或边缘处,重新吸收了传统治理方式的养分,以延续或重构社会治理秩序”[23]。策略性互动要求法官关注纠纷中当事人的心理是否得到了抚平、纠纷解决的多元效果是否得以实现、具体案件的操作是否得到了统一。因此,司法策略的实质内容通过策略性互动也进一步得到了充实。
Brown&Levinson(1987)的礼貌与面子观认为,礼貌的基础是“面子”,面子是个体的自我体现。交际中,为了礼貌起见,人们会尽量避免或减少伤害面子行为的数量和程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礼貌策略:“直接性策略、积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间接性策略和放弃实施威胁面子行为。”[5]与Brown&Levinson的礼貌框架相对应,Culpeper(2005)的不礼貌框架也包括五大类策略[6]:
(三)程序性互动的内在建构
从内在视角来看,仅仅实现司法知识与当事人日常生活知识之间的开放性互动是不够的。如何将通过策略性互动所获得的司法策略的实质内容本身进行合法性建构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司法策略作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互动方式,其本身实质内容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其形成过程的规范性。因此,除了关注外在视角上的通过互动司法策略实质内容的获得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从司法策略本身内在地思考作为互动结果的司法策略实质性内容的建构问题,也即司法策略形成过程的规范性问题。
由于自然资源贫乏,90%的能源需进口,发展核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日本能源政策的基石。福岛事故前,日本共有54台在运核电机组,满足全国约30%的电力需求,并计划将核电份额进一步提升至50%以上。
司法策略形成过程的规范性主要表现为对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做限制性规定。司法策略作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程序性互动方式,这种互动必须符合规则性、程序性要求。在政治治理逻辑下的司法策略中,法官的策略性行为往往会规避规则性和程序性问题,“而把当事人关于规则的争议转化为事实的争议,在事实层面而不是在规则层面解决问题,是结果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和程序导向”[24]。然而,“目的—手段”逻辑下的司法策略要求本身的合法性建构,作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程序性互动的一种方式,必然要求从“结果导向”向“规则导向”,从“实体导向”向“程序导向”的转变。这要求司法策略的具体运行机制、实施过程都必须在法律规范、司法程序规制内,不能超越于司法本身的规范性和程序性要求。并且,这一互动最终必须以规则性、程序性的方式体现出来。
五、结语
从整体现代化社会转型来看,司法策略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价值。然而,在吉登斯意义上,“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已带有实验性质”。现代性范式也正经历着一系列的怀疑和指责。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对现代范式下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批判来反思中国自己的法治发展方向。因此,在思考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司法的具体运作、司法策略问题时,必须从本质上追问以及解答这样的根本问题:即乡村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乡村社会里的人应当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秩序之中,生活在怎样的司法文明之中?
有学者认为,“在处理国民性、国情或国家人情或民情、风俗习惯、传统与法律建设之间的关系时,有两种理解路径:移风易俗并改造国民性以适应和追求现代法治社会;顺应并适合国情民情以调整和建立相应体系与特色的法律制度”[25]。乡村社会在面临现代性的法律面前,理论上来说至少也有两种选择:一是追随现代化的脚步,努力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契合现代性法律的实施条件,构造出一张现代性法律得以实施的社会之网。这涉及如何正当地、合法地将乡村社会、乡村村民的日常生活纳入现代法治进程的问题[26]。二是基于文明缺失状态下重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与自我定位。这意味着对现代性法律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国家法律制度与司法体系必须基于乡村社会自我文化认同与重新定位而做相应的调整。乡村社会中司法的策略化现象正是介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的表现,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是介于这两种进程之间不断交叉式的螺旋状发展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4.
[2][8]郑智航.乡村司法与国家治理——以乡村微观权力的整合为线索[J].法学研究,2016(1):73-74.
[3][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2,42.
[4][18]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J].中国法学,2007(6):157-165.
[5]王露璐.伦理视角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礼”与“法”[J].中国社会科学,2015(7):94-107.
[6]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M].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1-121.
[9]迈克尔·桑德尔.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M].朱东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
[10]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105.
[11][12][20][23]栗峥.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J].中国法学,2012(1):77-88.
[12][22]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6,172.
[13]Lawrence Freedman.Strategy:A History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xi.
[14]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260.
[15]张青.乡村司法的理论困境与法治化治理之提出[J].人大法律评论,2015(1):64-89.
[16]布迪厄,强世功.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C].北大法律评论,1999(2):516-517.[17]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38.
[19]张剑源.管辖权竞争与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J].当代法学,2014(4):120-130.
[21]方乐.转型中国的司法策略[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2):62-71.
[24]陈柏峰.乡村司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11.
[25]罗云峰.礼治与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7.
[26]文丰安.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摇[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6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