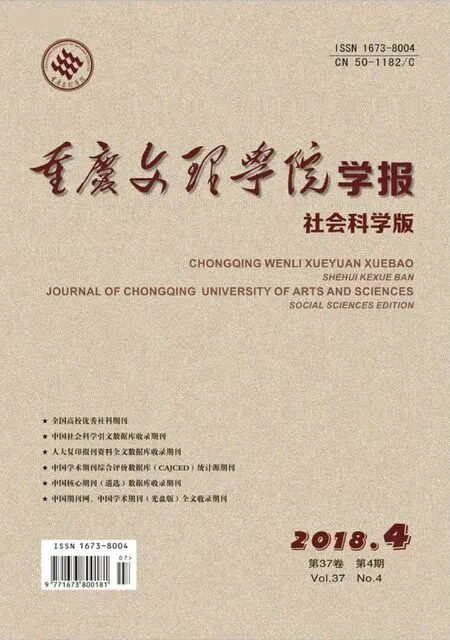清末民初女性留学及其文化冲突境遇探究(1869—1925)
李建
从1869年出现第一个女性留学生开始,到1914年正式全国性选派第一批官费女留学生,再到1925年第五批结束,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中国女性留学由个例到区域性文化交往,而到了官方正式认可的最初发展阶段,实现了中国女性留学活动从萎靡不振到普遍开展的过渡。这时期的女性留学生,是最先受到东西文化冲击的女性群体,其留学行为,是后来留学活动普遍打破男女界限的前奏,具有代表性。选择这一时期探索女性留学问题,或可带来更多关于中国女性、关于教育史与社会文化史的省思。
我国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晚,留学女性的历史更是一个新兴领域。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留学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方面,也有部分民国中后期归国女性在政治运动、妇女救济等方面的个案探究。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停留在20世纪末,其中教育家舒新成,就是较早对整个近代留学生情况做出详细论述的代表,其核心是近代留学教育制度问题[1]。文化方面,李喜所将整个近代留学诸国的学生与中西文化互动、科技发展、思想勃兴等紧密联系起来,并对许多个体人物有较详介绍[2]。他还以“最早沟通中外文化的女留学生”为主题讲述了四位最早在传教士推动下留学欧美的女性,指出早期女留学生出国一直是一种“民间文化”的交往,这种观点未免有些局限。孙石月早在1995年著有《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3],系统整理和论述了近代中国女性留学的渊源、演变、成就、经验教训等,是一部讲述整个近代史上女性留学状况较为全面的专著,为此类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另外,黄福庆对留日活动的发轫做了深入探究,阐述了留日群体办报、结社、翻译等活动[4]。其中对中国女性在留日过程中的表现也有一二概述,指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制度对留学女性存在较大限制,女性潜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留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却停留在20世纪研究范式和基础上,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大多是对留学活动的整体性分析,女性留学问题只是顺带提及,专门性研究成果稀少。二是以整个“近代”为研究对象,着重讨论其一般“共性”,容易浅化各阶段、各方面情况的差异性。并且,更关注后期的蓬勃发展而对开蒙期留学女性只是略有阐述。三是教育、政治层面的研究仍占据主体,对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尚待深入。
因此,以1869—1925年为代表的早期留学女性为观照对象,爬梳其具体历程,进而从社会、文化层面加以考察,拓展既有认识并多层次地探索,可对该领域研究有所补益。最早的中国女性留学是如何展开的,又经历了怎样的阶段?作为第一批走出传统桎梏的女性,她们面临了怎样的困顿局面,是否走出国门便成为世人眼中彻底西化的“新女性”?换个角度看问题,对此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进行信息整理,再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和国人的思想风潮,使用比较、具体个案与一般现象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留学原因及其阶段性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思维范式对女子束缚很深,在时代鼎革的复杂形势下,社会大众及女性自身或主动或被动地在思想和文化上“松绑”,驱使其在行动上有所转变。探究当时女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走出这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一步,从而了解其遭遇中西文化冲突的“前因”,以便考察其“后果”。随着时代的演进,其留学活动由点到面,循序渐进且各具特征。
(一)最早产生:随传教士出国
19世纪中后期,中国出现部分随传教士出国的留学女性,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女子获得西式教育的最早的方式。明朝初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到清末时他们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并直接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他们建立女子寄宿学校,创办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技术的《万国公报》等报纸杂志,大篇幅对妇女解放问题做出探讨、宣传,触碰了女性的自立与自由的神经,还收容一些孤女贫女进行西式教养,甚至带出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第一批女性留学生。
中国第一位留学生金雅妹,是浙江宁波一位牧师的女儿,她两岁半时父母双亡,被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麦加缔收养。5岁时(1869年)被带往美国接受幼儿启蒙教育,随后被带到日本接受了初等及高等教育,1881年考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学医[5]。继之,生于福州一个开明基督教会家庭的柯金英,天资聪颖,未缠足,从小进入教会女校读书,长成后就职于福州妇女医院,受美国的妇女外国传道会资助,于1884年往美国学医。江西九江人康爱德是一个封建的家庭的第六女,其父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算命先生指其命犯天狗,有碍男丁,所以仅出生两个月就被两度抛弃,后被美国传教士侯恪收为养女,1880年,9岁的她被带往旧金山学习英语,不久后回国。1892年又和同乡石美玉及三位男子一同随其另一养护人候威赴美,考入密西根大学学医。石美玉亦生于教士家庭,因从小未缠足而被周遭视为“怪物”。此四人是清末最早出国留学的女性,她们留学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生活的无奈,并非个人追求。1904年,牧师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也由牧师带到美国留学,三年后她的两个妹妹宋庆龄和宋美龄也随其姨父温秉忠(牧师)赴美,成就了至今为人称道的“宋氏三姐妹”。
此类留学女性的主要特点有两点:一是大都出自中国早期牧师家庭,从小跟随传教士,受西方知识、文化的强烈熏陶;二是留学之地首选美国,并且大都先进入教会学校再考入其他大学。这批人后来几乎都发展成了基督徒,是当时传教士实行“文化传教”、思想渗透的结果。也可看出,她们大都是因不良的生存环境、动荡的时局或一些意外的因素,依赖于传教士的“养”和“教”而走上留学之路,并不具思想上的主动性。留学行为和生活的迁徙流转联系在一起,有一些机缘巧合,又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给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以及女性带来的无奈。许多人走上留学这条路往往是由于没有选择,这个情况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有所转变。
(二)逐步发展:随家人出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鼓励官吏出国游历,提倡贵胄子弟出国游学[6],加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等传入国内并产生影响,使得男性出国已不在少数。他们或需女眷的陪伴,或有了自由开明的意识,有意无意地带动了女子留洋。伴夫、父或兄出国而走上留学之路,成为此时期女子留学的主要形式。
裕德龄与裕容龄姐妹二人在1895年和1898年先后随父出游日本和法国[7]。其父裕庚,满洲正白旗人,先后出任日本特命全权大臣3年,驻法公使6年。姐妹二人都曾在日、法读书,裕容龄还进入巴黎音乐舞蹈学院学习芭蕾舞。《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她们被归为和单士厘、赵彩云等一类的出洋钦差眷属,而不属于留学生。但她们进入外国学校学习西方文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和其他“留”而不“学”钦差眷属有本质的区别。有限资料可考的最早的伴读女子应该是浙江的夏循兰,1899年,9岁的她进入日本的华族学校[8]。同年,清廷外交官钱询的儿媳包丰保随丈夫、兄长在其婆婆善士厘的带领下赴日,就读于实践女校。1902年,何香凝随丈夫廖仲恺东渡日本,1903年入读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同年,清末报业女主陈撷芬随父亲陈范赴日躲“苏报案”之祸,就读于横滨基督教共力女校。此外,还有曹汝锦(曹汝霖之妹)、陈彦安、钱丰保、钱媚子等近20名女子在此期间随家人到日本留学。
这类女子大都出自名门望族,在国内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因为时局、地理条件、经费、文化联系密切性等原因,他们所去之国主要是日本。此类女性群体的出现和逐渐增多,表明部分人发生较大转变:一个是对西洋的看法,开始慢慢脱离最初将出洋视同“放逐”,只有社会最底层的人才会为生活所迫前去的阶段;一个是时人对女性“抛头露面”已不那么讳莫如深,逐渐开始“开眼看世界”。但是,陪同家族男子留洋,是当时保守封建的文化风气和伦理体制之下,女子可触及的较为“体面”的方式,依然具有强烈的“从夫从父”的色彩,独立、主动等意识尚浅。
(三)趋于独立:自主留学
20世纪伊始,自中国正式有男子留学已有30余年的历史,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越来越多。随着男性留洋群体的增加,伴读女子也越来越多,甚至许多新兴商人、买办等都积极送子女出国留学。在新风气的感染下,部分女性开始觉醒,甚至对过去因循守旧的状况不满,表现出对新事物的向往。于是,不再依附于男子,自行出洋求学的女性应运而生。
其中,革命英烈秋瑾当属典型代表。生于官宦之家的秋瑾,早年亦禁锢于传统的家庭观念,但她饱读诗书,文采斐然,立志成为花木兰之类的豪杰,更是与思想顽固迂腐的封建官僚丈夫不甚和谐,有“可怜谢道韫,不与鲍参军”之叹。加之救国思想的驱使,她卖掉自己的妆奁首饰,冲破家庭束缚,于1904年独自负笈东渡,于是年八月入读日本帝国妇人协会创办的东京实践女校。随后,其好友兼亲戚的唐群英亦受感染,自费东渡日本,与秋瑾成为同窗,两年后又考入了日本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1905年,更多的女性结伴赴日留学:有自费率女伴7人赴日留学的奉天省旗女静婉;有安徽庐山的吴弱男、吴亚男姐妹;有“湖南王君任秋之子名桓之者,近偕其女弟赴日游学,同行者上有女学生20余人”;还有“广西容县龙胆女学堂学生陆书蕉,年18岁,陆菱绢,年17岁;均于普通学略有低根,且著尚武精神,驯马放枪,并能娴习,近结伴同行赴东游学”等。
这类留学女性也大都出自家底雄厚之家,表明此时的能主动进行留洋的活动的女性,还仅限于少数中上层家庭,而越是底层的女性,越不容易接触到新思想,造成女性思想解放面积小,力量薄弱。但还应看到,这个阶段女性冲破家庭束缚,独立出国留学,较之上一种“伴随”性的方式,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说明社会的开放程度在增高,部分女性潜在的独立自主的愿望和能力也被逐步激发。留学女性的思想日趋从以男性、家庭等为主向看重自身发展转变,其留学行为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追寻。
(四)普遍展开:官费留学
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了持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同时加大奖励游学的力度,江浙、山东等沿海地区派遣官员出国考察政治、教育制度等活动增多,直接推动了与美、日等国在教育上的联系与合作。是年7月,日本实践女校中国留学生分校成立,设立二年制本科、一年制速成师范科以及速成工艺科。湖南省选派20名女子到该校学习,其中“年最长者48岁,年最幼者14岁,从姊妹来者有九人……有统御教育”[9]。此举开中国女性官费留学之先河,推动了地方政府积极输送女性出国留学。紧接着,辽宁、江西等省都官派女子东渡留学;奉天省特派熊希龄考察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和实践女校的校长长田歌子约定,每年选派15位女性前往该校学习师范,共同推动了清末留日小高潮的形成。1907—1908年,江苏省、浙江省前后通过考试选取了10名男子、3名女子赴美留学,其中女性进入威尔仕利女子学院。这一系列活动成为官费派遣女留学生的滥觞。1909年,欧美各国陆续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以资助中国教育事业,其中有一部分用于每年选送学生留美,但没有女性名额。直到1914年,根据教育部女子可以同男子一起竞争官费留学的规程,清华学堂在全国范围内经考试选取10名女子纳入庚款留美,此后每隔一年选一次,每次名额为10人,直到1925年,共5期。据统计,截至1924年,庚款留美共派送留美男子689人,女子43人[10]。此举引发了民国女子留学(尤其是留美)小高潮。
以上四种原因类型的女性留学,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从女性留学生的出现,到被纳入官费留学体系,其留学行为由消极被动演变为积极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是一发展性过程。再者,女性受官费资助留学,从清末的省费发展到民国初期中央正式将全国女性纳入官费留学体系,日趋平民化、普遍化。至此,“女子留学从个案发展为被政府认可的社会现象”[11]。这表现出当时中国政府对女性教育愈加重视,可以说是文化冲击、“新国民”的努力以及民族危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是男女平等、社会公平及其实践的重要体现。
二、文化冲突下的困境与新生
严复先生曾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12],这时候的女性留学生可以说是“半自由人”。她们既受中国浓烈的传统文化氛围、父母的言传身教、周遭人的行为模式、国内中体西用风潮、官方态度等影响,又吸取西方文化的内容及方法,多方矛盾,多重困境。其中,学业、社会性别、生活共同构成了此时期女性留学的面貌主体,也是最能反映当时文化影响的三个层面。故以此三者进行案例举隅和典型探析,以管窥清末民初留学女性所遭遇文化困境的程度和状况。
(一)专业选择:贤妻良母与个人主义之挣扎
所谓“贤妻良母主义”,是指在近代早期,时人倡导女学,高呼女性解放,而其动机、目标、内容和思想都还停留在女子学习知识文化主要是为家、为国服务,培养新式女性以教育后代,和谐家庭,“保种立国”阶段的观念理论。以梁启超为代表,当时提倡女学的主要人士大都持此观点。1988年,梁启超高呼女子求学“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家良善,岂不然哉”[13],又在《论女学》中提出女子善教儿童,可“因势而导之”,强子孙以防弊。此外,女子学习知识以自养,可“生利”而不是与男子“分利”,这样可以减轻家庭负担,避免“极苦”[14]38-40,于是“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15]。此论断在当时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积极响应,严复亦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母健而后儿肥”。“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清末乃至民国初期和中期都在女子教育中占据主要地位,杜元学曾说“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维新运动,就是民国的女子教育中仍强调培养女子的母性,可见其影响力之大”[16]。甚至官方也将其纳入女性留学教育宗旨,做出“所需学术,应以师范,医学,美术、音乐为要”[7]的相关规程。
基于培养贤妻良母的目标,梁启超对女子专业有具体论述:
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受以及蒙养之法),三国语(谓日本文),四汉文,五历史(肇外国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谓格致),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10]40
梁启超的这些观点被普遍接受,引起共鸣,甚至到了1915年,退赔庚款做出修正,正式选派女子留学生之后,对女子留学依旧有如此规程:
留学须知:录取各生须以下列各科中任选择一科为进美校研究之专科。择定后不得擅改。(应选科目为:一、教育,二、稚园专科,三、体育,四、家政,五、医学,六、博物,七、物理,八、化学。 )[1]83
政府补助自费女留学生亦将范围限制在“母教”的研读:
女生游学为养成母教之基……亟补给官费,应以考入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蚕业讲习所女子部三校为限。[17]
由上可知,中国近代早期,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思想风气上,女留学生的学习内容,首推教育、家政以及自身修养,其次为强健体魄,格物致知,治病救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家国观念的驱使下,女子留学生的思想仍然带有很大“服务”“奉献”的色彩。在日本及美国留学的大多数女学生,还要辅修编务、造花、刺绣等。他们还是没有完全跳脱中国传统赋予女性的“天职”,与独立、自由,人格健全的“女国民”[18]相去甚远。
在近代西方,女性的专业选择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或规定,法律、政治、经济、管理、甚至技术种类的不在少数,中国女学生到了国外,当受同等教育模式。而当时中国女性一般以家庭或国家需要为出发点,中国留学女性之中,考取官费的受制度制约自不用说,另投他业是不被允许的。自费留学的女性如林宗素、周淑安、顾淑型等,她们在不受强制规定的情况下,或确是志趣所在,或是出于对自身特长和能力的判断,又或跟随当时主流观念……总之,均未突破当时的专业选择局限。整个近代早期,我国的留学女性在普遍专业攻读上一直处于这种比较困顿、尴尬的局面。直到1930年,留学德国8年的谢志媛女士毕业,才产生“中国女子留德专习理化工程考得博士之第一人”[19],震惊国人。而在她们之后,则出现了银行家张幼仪,建筑学家、文学家林徽因等大胆尝试的新女性。
如此,清末民初的女留学生形成在西方文化环境和教育方法之下,培养东方“贤妻良母”式人才的模式。此种“混搭”形式下异文化间的碰撞,有些怪异,又无意中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礼教大防与男女同校
传统的中国女性,秉承“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严守儒家之“防礼”,“足不出户,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10]41。女性留学生虽然走出国门,打破了这种封闭顺从的状态,但即使是在欧美等较为开放的氛围中,她们依然“自持”,与此时国内的女学生们一样,不与男子同校。这反映出他们思想上保留传统的一面,在跟随国内的主流风气与彻底追随西式习业方式之间无法取得平衡。
美、日等国男女同校的历史均早于中国很多,其风气和认识相较当时的激荡的国内情况更为理性和开放[20]。然而此时期女性留学生中,官费留学者,无论是清末湖南、辽宁、奉天、江西等各省选派,还是民国时期庚款留美的女子,都悉数送往各国设立的女子大学,男子则被送往早稻田大学、耶鲁大学等男女同校的公立大学。自费留学者,并无明文规定他们选择何种类型的学校,但据已知情况,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进入教会女子学校或女子大学。相对来说,女性留学生在国内就拥有比一般女子更优越的教育背景,出国一定程度上是更为自由自主的表现,但他们依然和国内女性一样同男子分而学之,大抵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随主体意志的大流;二是自身还具有潜在的男女接触上自我严格约束的意识;三是仍持男女素质异同的思想,认为进入单性学校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这三者,究其根源,是时人对性别认识不足,分析不客观,是对约定俗成的传统文化认同的表现。
中国的女子教育于1907年才被正式纳入教育系统,并且有“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21]的规定,男女同校求学在当时看来更是荒谬至极的做法。封建保守的顽固派自不必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亦对男女同校持保守态度:男女有别,共处一室不可行;男女在知识等方面所擅长的领域不应相提并论;男女应负的社会职责完全不同,等等。甚至是辛亥革命的先驱章太炎先生也说时人“唯知自守礼教”[22],驳斥男女同校。留学女子在国内就深受这些传统声音的影响,男女大妨的思想在他们身上是顺理成章的,如同日常饮食起居一样成为生活规律,固不可破。因此,留洋初期的女性在男女共同交流学习上势必与西方学生们有一定差异,这也成为男女平等共处的契机之一。
(三)“养”与“立”:旧生活与新环境的摩擦和适应
早期的留洋女性,除金雅妹之类的因生活变故而由传教士带出国的,大都出自富庶家庭,生活优沃,甚至有奴仆服侍,三寸金莲,四体不勤。而出国之后,西式教育主张独立自主,且吃穿用度、生活方式都跟国内大不相同,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中国数千年来以被男性“养”为主的女性,一到国外就被要求独立做事,并且由于刚开始语言不通、饮食习惯差异等,生活上产生较大困扰。
例如,早期中国留学女性多在日本实践女校学习,该校校长下田歌子“针对中国女子终日坐食于家,无所事事的特征,要求在其学校学习的中国女学生,每天早晨五点起床,自己动手打扫房间、厨房、厕所”[3]71。就连以“鉴湖女侠”[23]自称的秋瑾,1904年第一次赴日留学时都深感与国外生活格格不入。她在家书中抱怨出国留学生活艰辛,小脚蹒跚的她怨叹“出门行路,并未坐过人力车也”[24]。秋瑾本身也不喜操劳琐事,如将她引入东京留学的服部繁子回忆她在浙江时到秋瑾房间所见,“书架上胡乱放着书籍和衣服。瓜子皮,果皮撒在屋角里,发出一股恶臭,并不是很清洁”[25]。留日后的生活可想而知。
但是,中国传统的德行、礼数、规矩、仪表等教化,也使得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女性庄重自持,聪颖贤惠。并且礼教重压之下的她们,一旦触及且适应了新事物,很快就能既发挥其聪明才智,又表露出其举止娴雅、知书达理的一面。下田歌子对她们有如此评价:
今之来者于学程皆能自奋,无假督率,已为可喜,且贵国风俗以女子之畏见男子者为守礼节,而来此游学者,初犹畏怯,渐亦更改,竟能倜傥大方,行止自由,论学讲学,一如男子,此尤可敬者。可见贵国女子性格高尚,本非逊于男人,而特无教育以养成之,遂至与国家毫无关系,实为可惜也。[26]
可见,传统文化体制下培养起来的留洋女性,在遭遇外来文化冲击,寻求新知的过程中,既有因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与困顿,又有不亚于他国妇女的良好表现,在文化环境的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前进。
三、结 语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女性的产生和发展,从无到有,自少而多,可以说是教育上、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拓荒,这便是其最大贡献所在。近代留学女性共万余人,其中,早期(清末民初)的数量虽少,但十分具有代表性。这时期女性留学生群体,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四五十岁的妇人都有,“小脚蹒跚闯世界”是其真实写照。其出现并非源于知识和自由的驱动,而是中西文明交往碰撞、男性留洋的“伴生物”,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才逐渐有了主动性。她们开始质疑中国传统伦理思维模式却又始终不能与之脱离,许多人试图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回到国内却还是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于是,在东西文化的冲突下,清末民初的留学女性往往如“两头蛇”般陷入“屈伸非自甘,左右何能以”的矛盾挣扎。
如此的境遇对早期留学女性人生的影响,无论是其学业培养结果、留学后的行为模式还是最后“归宿”等方面,都具有两面性,并不是绝对的。后来人由于种种原因,更为关注甚至容易夸大她们“西化”“先进”的一面,而事实是,由于早期的留学活动存在种种问题和限制,知识体系上也不够完善,她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成绩,甚至处境尴尬。在完成学业后,许多人很快又重新适应中式女性生存法则,做出了妥协。但其行为依然对中国近代女性乃至社会进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女性留学活动的肇兴,以及这些女性的努力,带动了中国女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教育事业和现代文学艺术等注入新鲜血液,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国人观念的转变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其对东西文化的吸收和保留,对于女性来说是突破性的,个性鲜明地对传统既继承又挑战,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她们在东西文化的对立统一影响下的各种言论和活动,引发了更大文化交流及其实践:在这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男女同校问题逐步展开讨论和实践;女性教育开始围绕女子独立性和健全的人格展开;五四以后女子留学拓宽了地域和阶层的范围,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世纪20年代,又兴起女子留苏的热潮,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中国女性留学生也逐渐增多。总而言之,文化的冲突与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清末民初留学女性遭遇东西文化冲突,并积极应对、调整,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新一轮的社会文化变革将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