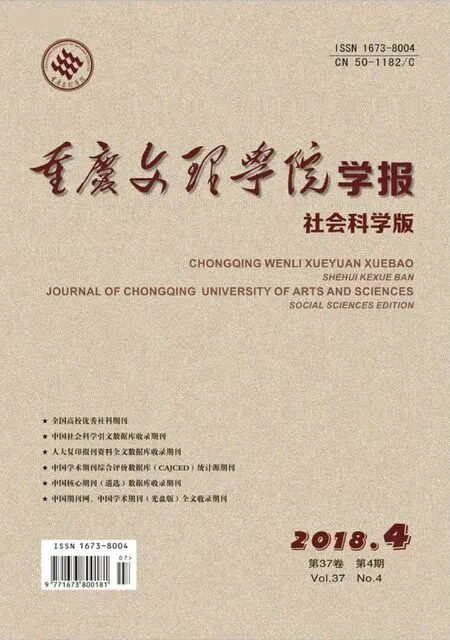域外深耕抉新景
——读《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王园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新世纪以来,域外汉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域外汉籍这扇门渐渐打开,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展开了一片新天地。南京大学卞东波先生的新著《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便是将域外汉籍研究视域与宋代文学研究融合的新成果。此书以域外汉籍为切入点,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结合中国宋代文学的专题进行相关论述,不仅从文献学的角度展现域外汉籍的校勘、辑佚价值,补充和更正中国现有古典文献的不足和错讹,而且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为宋代文学研究增添了很多新材料,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观点,使得域外汉籍的研究走出单纯的“文献学研究”和“实证主义”的误区,回到以域外汉籍的文献考证为基础,以真正的文学研究为旨归,以掘发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为学术境界的研究路径上来,为我们展现了“异域之眼”所看到的文化新景。卞先生在域外汉籍中有关宋代文学的领域钩深抉微,慧眼独具,对开阔学术视野,掌握研究方法,学以致用等方面大有裨益。感于此著视角宏大,选材新颖,兹举以下三例,略述其旨。
一、基于文献,涵盖全面
域外汉籍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献存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宗旨就特别要求“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1]。卞先生在导论中梳理了域外汉籍所囊括的内容,并且在书中将这些传世文献分三辑逐一诠释。从横向阐释来看,第一辑《域外遗珍》,卞先生重点介绍了域外所保存的许多稀见的、珍贵的中国古典文学文献,而这些汉籍大多都是中国本土已经失传或者资料不完整的文献,卞先生用“遗珍”一词,足以看出一个域外汉籍研究者对“吾国之旧籍”的亲切与爱护。第二辑《域外受容》,有代表性地选取了宋代一些经典文献在日本、朝鲜等东亚汉文化圈国家的接受与变容,这些国家积累了一大批注释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同时一些域外文人也用汉语进行一些文学创作,而这些域外汉籍正是国内学人注意较少而值得花时间深挖的宝藏。第三辑《域外版本》,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历来都有学习汉文化的习惯,尤其注重从中国输入文学典籍。为了更好地推广和学习,这些典籍也被不断地加以刊刻和整理,从而形成了诸如“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这类在存真度、完整度上都有较高价值的版本。这三个方面基本囊括了域外汉籍所包含的内容,结构清晰,涵盖全面,一目了然。也是卞先生站在“东亚汉文化圈”的高度,对以往论著的整理总结和升华,力图在求新中求真,发现中发明。
从纵向上,新材料的挖掘、新问题的发现都基于对文献的收集和考辨。张伯伟先生在《域外汉诗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提到:“(域外汉诗学研究)当务之急是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学者应该积极地投入到对基本文献的收集、考辨工作中去。”[2]4身为张先生得意门生的卞东波自然是忠实的践行者,此书中涉及的域外汉籍和版本都从其文献价值出发,最具代表性的是第六章对宋元之际古逸书《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考证,宋元之际于济、蔡正孙所编的诗歌总集《唐宋千家连珠诗格》元代以后在中国本土就已失传,但在日本、韩国流传不替,被翻刻成多种版本,众多版本中以保留元版原貌的五山版为佳。卞先生发现《唐宋千家连珠诗格》对于现在《全唐诗》《全宋诗》及其他唐宋诗歌选本的校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卞先生又从《唐宋千家连珠诗格》考证筛选出约四百首《全宋诗》未收的宋人佚诗,洵为宋诗辑佚之渊薮,卞先生在此章中皆列目辑出。其中既有《全宋诗》已收诗人佚诗,包括宋代著名诗人如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姜夔、赵师秀、谢枋得等一定数量的佚诗和南宋一些小家诗人的佚诗,也载录了大量《全宋诗》未收诗人及其佚作,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的生平资料及其诗歌作品都依赖此书得以流传,于斯即可见《唐宋千家连珠诗格》拥有巨大的辑佚价值。但这部成书七百年前的宋元佚籍,其文本是否完全可信呢?卞先生在细读文献后,又仔细考证了《唐宋千家连珠诗格》中的讹误及其分类,不但有张冠李戴之误,还有割裂原作之讹。鉴于此书巨大的文献价值,卞东波研阅以穷照,结合朝鲜文人徐居正的《唐宋千家连珠诗格增注》,参考各种总集、别集、诗话、笔记对此书的正文及注释加以校勘整理,勒成 《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此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这也契合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3]219的学术典范。
同样展现卞先生深厚文献功底的还有第十章《朝鲜活字本李壁〈王荆文公诗注〉之文献研究》,卞先生不避已有学者对朝鲜本《王荆文公诗注》性质、特点的研究,而是慧眼独具地将在日本蓬左文库发现的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注》与目前的通行本——元王常刊本、《永乐大典》所收本分别进行比较研究,卞先生通过考证认为,朝鲜本和《永乐大典》本皆承袭宋本的版本形态,而且元本形态也很复杂,并非如从前认为的完全没有被刘辰翁删削的“补注”。在此基础上,该文又深掘了朝鲜本《王荆文公诗注》的文献价值和讹误,实乃另辟蹊径,新人耳目。
二、立于文学,新见迭出
整体而言,卞先生在处理这些域外汉籍时涉及传统集部的各个部类,如关于总集的研究,有《选诗演义》《唐宋千家连珠诗格》《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的考证;关于诗文评类的研究,有对《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正中本《诗人玉屑》的研究。同时,其研究的触角还关注到史部文献《宋史筌》中的文学资料,以及子部中和刻本宋代笔记的研究。在探讨《诗人玉屑》在日本的流传的章节中则从书目、史书、日记、诗话中加以考索。卞先生此类处理汉籍的方法深受其师张伯伟先生的影响,张伯伟先生在如何处理书籍的传播和影响上有以下十个分类:(1)据书目以考;(2)据史书以考;(3)据日记以考;(4)据文集以考;(5)据诗话以考;(6)据笔记以考;(7)据序跋以考;(8)据书信以考;(9)据丛书以考;(10)据印章以考[4]385-388。这种研究方法在卞先生近几年的专著《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中都有体现,卞先生在后记中也提到如若不是跟从其师张伯伟先生走上了域外汉籍研究的道路,他自身的学术规划也是接着上面的分类继续诗注、诗评、集序的研究,可见张伯伟先生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但在域外汉籍研究中颇有成效,也同样适用于整个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
此外域外汉籍新资料的发现,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只是文献学上的校勘和记录,这样的话就不是文学研究了,我们势必要从中发掘文献新资料的文学价值。这首先就向我们提出了对于新发现的域外汉籍该如何阐释其文学价值的问题,卞先生在著作中为我们研究域外汉籍的文学价值提供了一个思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第一辑第三章《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文选学”》为例,成书于晚宋的《选诗演义》,中国本土已经亡佚,仅有一部藏于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作为现存唯一一部宋代的《文选》注释书,其巨大的文献价值毋庸置疑。但卞先生有意侧重于其阐释学方面的价值,先分析整个宋代文选学的学术氛围,借以窥视《选诗演义》的成书背景,发现文选学在宋代并没有完全衰落;继而转向曾原一个人文学思想研究,通过对文献的爬梳,卞先生认为曾原一的《选诗演义》多选汉魏之诗而轻齐梁之诗,更是将《诗经》作为最高的文学标准,显示出一种“退化”的文学史观;最后再具体到曾原一对所选诗歌具体解诗方式的阐释,卞先生将其提炼概括为“讽寓阐释”的解诗特征,分析这是受到诗骚阐释传统、晚宋诗学阐释和真德秀经义阐释的影响,并且认为这是宋代“文选学”的新特点。卞先生分别从“论世”“知人”“解诗”三个层面对曾原一及其《选诗演义》的文学内涵加以论述,使我们对宋代文选学的发展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弥补了国内宋代文选学研究的资料短板。卞东波最后也比较公正地指出该论著的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整体上的学术价值不容否认。
除此以外,卞先生对新文献的发现,在考辨其文献价值的基础上,最后都落脚于对其文学价值的阐述,如上文所引的《唐宋千家连珠诗格》的诗学价值,卞先生已在其专著《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第八章《〈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与宋代诗学》中有详细论述;另一部《王荆文公诗注》的文学批评意义,卞先生也在书中提及自己将另文探讨。卞先生关于宋代文学的新见还体现在第一章《宋代的东坡热:福建仙溪傅氏家族与宋代苏轼的研究》,为宋代家族文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第二章《〈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卞先生发现这四种宋人和陶诗注本的注者皆为闽浙之人,这也为宋代地域文学中的“闽学”增添了新的风景。
三、兴于文化,求同存异
东亚汉文化圈是个特殊的群体,虽然有着人种、语言、民族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地区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些相通之处,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5]3人们的文化感知方式、宗教道德理念、心理审美与认同等,貌似都是依据着某种基本原则(如儒家伦理思想)展开,但是因为某一文化区域的独特性和该区域人们心灵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所以东亚文明又因为“存异”而显得多样有趣。
以第八章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在中国、日本、朝鲜的文化接受为例:卞先生仔细考订了中国宋元明清时代多部《感兴诗》注本,兼及《感兴诗》的唱和与评论,昭示了《感兴诗》独特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在整个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了朱子学源远流长的“感兴诗谱系”;《感兴诗》流传至日本,出现了多部《感兴诗》注本,其中以山崎闇斋的《感兴诗考注》影响最大,闇斋引用的“诸家之注”全都是中国的注家,闇斋对禅学、陆学的排斥与朱子排斥“异端”之学思想相通。如果说《感兴诗》在日本只是以山崎闇斋为代表的闇斋学派朱子学的观点的话,那么《感兴诗》在朝鲜的流传,则是渗透到朝鲜士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朝鲜的接受中更侧重于朱子“以理为诗”的哲学意味,甚至产生出一种感发人心的道德力量,“每风清月夜,朗吟朱子《感兴诗》《武夷九曲》《招隐操》,声甚悲壮,若千载感遇焉”[6]115,朝鲜文人已经与此诗产生了一种心灵共鸣。不知不觉中,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注者在朱子的带领下越走越近,心理趋同。
三国注者在理解诗意上有相同的层面,都认为这组《感兴诗》在第一首和第二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但在具体诗意的阐释上各国又有不同的观点。中国注家有两派观点:一派是以蔡模为代表的福建建安学派,认为是“无极而太极”的观念;另一派是以何基为代表的北山学派,认为反映的是阴阳变化的观念。但日本的山崎闇斋在《感兴诗考注》中倾向于蔡模的观点,久米顺利在《感兴诗笔记》中则表明了自己与两派皆不认同的见解;朝鲜的两部集注本 《朱文公先生斋居感兴诗诸家注解集览》和《朱子感兴诗诸家集解》则更认同何基的观点。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也始终有接纳与排斥相伴随,求同中存异。更为可喜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域外的受容已经达到了“互通中创新”的文化高度,如第七章论述欧阳修《庐山高》《醉翁亭记》在朝鲜汉文学中的追慕与变形中提到:朝鲜文人已经突破原作,在文体和艺术上创新变形,或“以文为诗”,借用《庐山高》的特殊含义写作寿诗;或“变记为赋”,将《醉翁亭记》写成《醉翁赋》,无疑显示出本国独特的文学特性。
汉籍在东亚的流传也极具文化史意义,其中“书籍环流”现象让人耳目一新,卞先生以《诗人玉屑》在东亚流传的版本分析得知:《诗人玉屑》在晚宋刊刻后不久,传至日本,就有了正中本,后流传至朝鲜,又以正中本为底本刊刻为朝鲜本,朝鲜本又传至日本,被翻刻成宽永本。直到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日本看到宽永本,参校此本,才形成现在的通行本。上文所引的朱子的《感兴诗》和蔡正孙的《唐宋千家连珠诗格》同样也经历了“书籍环流”的过程。有趣的是,《唐宋千家连珠诗格》的编者是中国人,由朝鲜人做的注释,最后又由日本人校勘和翻刻,这部汉籍融入了中日韩三国的元素,构成了东亚汉籍史上独特的文化景观。不管是文化的转移还是观念的旅行,通过“书籍环流”漂洋过海而去,中国文化在异域掷地金声,大放异彩;又漂洋过海而来,异域文化使中国典籍鲜活如初,又添新意。“书籍环流”背后所承载的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融共同谱奏了“文艺共和国”“众声喧哗”的华美乐章[7]13。
四、结语
陈寅恪先生提出“预流”之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3]266学术研究境界之高低,就在于对新、旧材料与观念的理解与处理是因循守旧,还是点铁成金,而陈寅恪先生本人所提出的“预流”成败之关键,亦在于此。卞先生对域外宋代新材料的审视,发前人未发之覆,使得每一个新材料的发现都能在整个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一席之地,发扬最有意义的价值。张伯伟先生曾对域外汉籍研究的期望作过这样的比喻:“一旦域外汉籍研究‘出其东门’,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只是‘有美一人’,而是‘有女如云’了。”[8]27笔者借此也期待卞先生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展示更多的“域外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