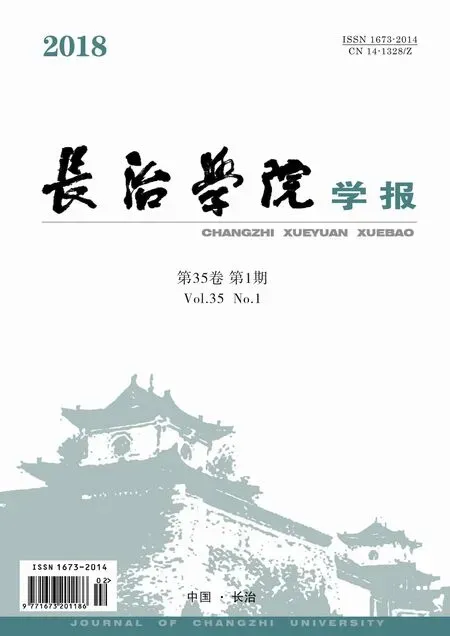民间立场与民俗事项
——对赵树理文本创作的一种文化阐释
杨根红
(长治学院 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11)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开创了“山药蛋派”这一乡土文学范式,其文本创作散发着清新、自然、质朴、淳厚的乡土气息。赵树理热爱农民谙熟农民,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说话,一心为广大民众写作,立志做一名“文摊”文学家。他所独创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填充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难以逾越的沟壑,既开创了新文学的新局面,也昭示了农民本真的欲望与诉求。赵树理将其写作之根深深地根植于广大农民这一肥沃的土壤,展现的是农民的世界、农村的面貌,因此,其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民俗学价值。
一、独特的地域环境与民间化叙事立场
地域性是文学作品的重要魅力之一,同时也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作家的创作思维、创作形式、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与其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这一点在赵树理的文本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晋东南地区相较其它地区而言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属高原山区,周围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交通也极不便利,再加其迈入农耕文明较为久远,由此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然而,在政治方面,晋东南地区却处于封建宗法制统治的中心。这既导致了该地区人民对封建正统文化的潜意识强烈依附,也夯固了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同时更嵌入了浓厚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保守的甚或落后的封建宗法制观念。赵树理的出生地晋东南沁水县尉迟村则更为封闭,更能彰显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环境。封闭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风民俗、封建保守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彼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赵树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晋东南地区的农村度过的,不仅精通农耕劳作各项技艺,而且对当地的戏剧、曲艺、说书、快板等民俗文化相当熟稔。由此,相对保守的文化生态、根深蒂固的家国意识及其成长的宗教家庭背景共同推进了其对晋东南地区民间文化生态、农民生存样态及农村现代性转换的执着探寻与书写。
如果说晋东南独特的地域特征及赵树理所处的外部文化环境(包括政治环境)为其民族化、大众化、群众化艺术风格的形成及作品中彰显的浓郁的地域特征提供了外因的诱发作用,那么,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民间立场则使其文本对民俗事项及文化意蕴的发掘成为了必然。
赵树理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农民的生活、习俗、思想、心理、情感有着透彻的了解。与生俱来的农民性与作家修养相结合,使其高举民众文学、大众文学的旗帜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从农民的视角进行文学创作。赵树理兼具“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是一位农民知识分子,他是一位真正为大众设想的农民作家,他始终将农民的需要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洞悉农村的方方面面,深谙农民的审美习惯,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民俗事项真实、自然、丰富。因此,赵树理作品中展现的是与农民口味相契合的富有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样态。
二、文本中的民俗事项与文化批判
钟敬文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民俗大略可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四个部分。赵树理文本中有大量有关晋东南地区地域景物、民居、婚俗等民俗事项的描画,其中既寄寓着其对山地生态文化的浪漫化想象,也蕴含着其对封建保守落后文化及民族痼疾的批判。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大致可分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三种,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2]晋东南地区身处高地,具有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既不会遇到特大旱灾,也不会遭遇水涝灾害,一年四季气候偏寒,土地大部分为山坡梯田,土质相对贫瘠,农作物主要以玉米、谷物及土豆为主。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世代生活比较贫寒,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养成他们乐天知命、幽默旷达的性格特征。
赵树理文本中很少有静止的地理及社会环境描绘,但在其大部分文本中一开头就会以简笔勾勒的方法描画出故事发生地的沟沟坎坎、方位朝向及自然景观。试以其笔下的自然景物描写为例,其笔下的自然景观没有充满诗情画意的石、竹、菊、梅,也没有令人惆怅的渔船、夕阳、亭台、驿站等传统文人意象,夺人眼目的是遍地的丝瓜、茄子、辣椒、瓠子、玉米等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的农事物象。因此,其笔下的自然景观是晋东南地区特有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在其秧歌剧《开渠》中有一段对山地景观的独特描绘,他没有描写山上的青松绿柏、凉亭小榭,而是描写了棘针、荆条、烂草、干蓬蒿和老雕。有棘针能吃酸枣,有荆条能拢荆蓬,有烂草能沤肥料,有干蓬蒿能当柴烧,有老雕能吓麻雀灭野兔唬野狼。这些农事物象的抒写无疑彰显了赵树理本真的民间写作立场,其在文本创作中以对彼时彼地富有晋东南地域特色的景物刻画实现着与农民的对话与交流,这也是其功利主义文本创作观念的外射与延异,他始终站在对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效用的角度来处理其笔下的人、事、物。不言自明,其笔下的景物描写隐含着农民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主动性。正如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对美感实质所作的阐述,任何事物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喜悦,能使人产生美感,就是由于里面包含了人类的一种最珍贵的特征——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即按照人类认识到的客观必然性,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以达到人类的目的和要求的物质活动。
尽管学界始终将赵树理的文本创作框范在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其文本创作动机、观念、样式所体现出来的浪漫主义因素。黑格尔曾将艺术区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三种,认为:“在浪漫型艺术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本身完满的精神世界,即自己与自己和解的心灵,这种心灵使生、死和复活的直线式的复演变成真正的不断的回原到自己的循环的复演,变成精神的不死鸟式的生活。另一个是单纯的外在世界,它由于脱离了和精神的紧密结合,就变成一种完全经验性的现实,对它的形象,灵魂是漠不关心的。”[3]赵树理始终以农民的立场、态度与情感,以农村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进行创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思维模式、价值判断与农民的一致性,事实上,其本真的农民情怀恰恰是以其浪漫主义情怀为根基的,在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激进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中,其文本创作甚至疏离外在现实而在纯粹艺术空间内询唤着浪漫主义理想。譬如其在文本中对上世纪50年代经过农民改造后的山村宏图的描述:坡上修边堰凹里修梯田,岭头栽大松高柏沟岸栽桑树柳条,再栽些柿子梨枣苹果核桃。这些改造既与晋东南的气候条件和地势特征相自洽,同样也寄寓了作家对实干精神的召唤,对农民发家致富的浪漫主义理想诉求。
(二)民居
民居是体现地域民俗特征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晋东南地区的农民大部分傍山而居,窑洞便成为这里的人们居住的主要形式。赵树理在其文本中多处描写了窑洞的样式、方位、格局及内部摆设。如《李有才板话》中对李有才的“三变土窑”是这样描述:“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像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象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这孔土窑是李有才的唯一财产。此处赵树理不仅从整体上多侧面描写了土窑的“三变”,有农民式的乐天知命的幽默;而且对窑洞的内部摆设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的描述,揭示了李有才贫苦的处境和农民的身份。此外,炕的设置“好像石菩萨的神龛”,有民间敬神信巫的民俗意味。再比如《三里湾》中对王宝全的“四孔窑洞”的描述:“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此处将“四孔窑洞”的使用情况作了一个说明。需要注意的是,女儿玉梅住的那孔土窑却是“有窗无门”的“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这种细节描述所要说明的显然是,一方面女儿已长大成人,需要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王宝全夫妇通过此种方式也实现着对女儿人身自由的监管。这与晋东南地区长期以来占据封建正统文化的中心而受到的儒家伦理教化的影响是脱不了干系的。凡此种种,赵树理笔下的窑洞不仅是是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居住场所,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寄寓了传统的民俗民风及晋东南地区彼时农民特有的文化传统及情感心理,也昭示了赵树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时所产生的认同与排拒相互纠葛的复杂矛盾心理。
(三)婚俗
婚姻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的制度和活动,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婚姻形态与婚姻礼仪两个方面,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人们都非常重视婚礼程序的完整进行,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男婚女嫁”、婚后从夫居而建立新家庭的一整套社会文化规范。男女婚姻的自由度既牵涉到人类文明与禁忌的复杂话题,也关联着伦理、秩序、等级、女性诸多文化因子,这一点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赵树理在其几篇文本中详细地描述过彼时晋东南地区盛行的婚姻礼俗,并暗合主流意识形态对婚俗文化中隐含的封建迷信思想、落后守旧观念进行了略带悲悯的批判。
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旧式农民形象。一个是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二诸葛迷信鬼神,“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其以命相不合竭力阻挠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从“不宜栽种”到小二黑被绑架“制钱占卦”再到“恩典恩典”,这一连串的故事情节一方面表明封建迷信思想对其毒害很深,另一方面也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二诸葛的迂腐、懦弱和胆小怕事;另一个是小芹的母亲三仙姑,三仙姑每逢初一、十五都要设香案头顶红布装扮天神,用装神弄鬼掩护轻浮放浪的行为,“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装扮一番。对于小芹和小二黑的婚事,其不仅反对而且嫉妒女儿的幸福,甚至为贪财不惜出卖女儿。从这一系列的行为举止中,赵树理刻画了一个沾染了好逸恶劳风习,心理扭曲的农村妇女形象。二诸葛和三仙姑的性格缺陷充分反映了晋东南地区农村延续已久亟待变革的陋风陋俗。文本以大团圆结局收尾,两个落后人物因为在区上受到了教育都有了变化:“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三仙姑“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小二黑与村姑小芹也获得了婚姻自由。赵树理通过对两个年轻人大胆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旧俗的描述,一方面表达了其对农村现代化变革中移风易俗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其对农村政权民主化的期待。同时,赵树理对三仙姑不无同情的讽刺也闪现着其思想中潜隐的男女平权意识,三仙姑装神弄鬼、刻意装扮吸引异性的变态行为也是出于被动婚姻的恶果。
在《登记》中赵树理不仅通过对小飞娥婚姻悲剧的描述表达了对不合理的封建礼教的批判,更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画了两对青年男女如何争取爱情自由的故事,展示了新旧两个不同的时代婚姻习俗的变迁及农村新一代农民崇尚民主与自由的全新精神风貌。同时,在这部作品及《邪不压正》中还详细叙述了晋东南地区独特的婚姻仪式,如《登记》中作为爱情信物的“罗汉钱”、《邪不压正》中的订婚聘礼仪式。在《邪不压正》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婚俗场面:媒人队伍带着礼物盒子、食物盒子来到女方家,“到门口先站齐,戴着礼帽作揖”,等女方家接过彩礼后,“排成一长串子走进去”。“这地方的风俗,遇了红白大事,客人都吃两顿饭——第一顿饭是汤饭,第二顿饭是酒席。”“这地方的风俗,送礼的食盒,不只光装能吃的东西,什么礼物都可以装——按习惯:第一层是首饰冠戴,第二层是粗细衣服,第三层是龙凤喜饼,第四层是酒、肉、大米。”“按习惯,开食盒得先烧香。”无论是“罗汉钱”还是“彩礼”,都充分说明了在彼时晋东南地区农村生活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农民对物质财富在婚姻中所占比重的重视,同时也具有鲜活的地域特征及民俗文化色彩。
综上所述,有着浓郁乡土情结的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置身于乡村的民间世界,以其浪漫的民间情怀构筑并发掘着晋东南地区特有的民俗场,扎根于民间原生态的文化空间,坚持民间创作立场,以具象民俗场景的描述表达农民的思想、情感、心理与审美诉求,并将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揉入其中,对彼时农民复杂的文化景观作出其独到的观照。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5.
[3][德]黑格尔.美学;第 2 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