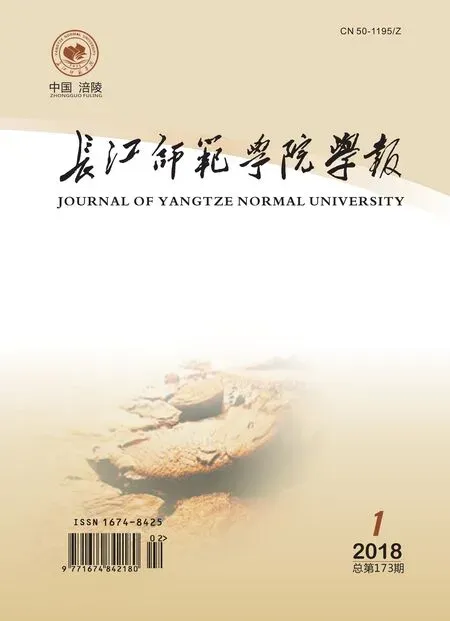从正统到邪说
——浅析神魔志怪小说
张诗瑞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一、序言
对于鬼怪的驳斥大抵始于《论语》中孔子云“子不语怪力乱神”,历来都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译为“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即普遍认为的否定鬼神之说的传统观点是出自孔子,但这并不是《论语》本义。《述而》一章,重在记述孔子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篇中: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
根据原文来看,“子不语怪力乱神”应该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孔子不再言语,惟恐分散了精神”,故不能作为以孔子为首的传统儒家思想反对神异鬼怪的例证,恰恰相反,作为文化起源的诸子百家是相信鬼神之说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鬼故事的正统性也由是得来。
二、鬼故事的正统性
鬼故事的正统性最先源自诸子学说的肯定,再次是因为作为官学的谶纬巫祝学说的功用,以及作为正统文学大家的鬼故事作者群体,皆可证明鬼故事并非游离于正统之外。
对传统文学代表,百家之首的儒家来说,其理论中天然包含了“事鬼神、敬鬼神、顺鬼神、致鬼神、畏鬼神”的因素。《周易》《尚书》《春秋谷梁传》《周礼》《礼记》《孝经》《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都对鬼神之说有所涉及,态度也都是既敬且畏的。《周易上经》说“与鬼神合其吉凶”;《周礼·天官·冢宰》说“三曰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孝经·感应章》说“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可见儒家并不驳斥鬼神,且把鬼神抬到与宗庙祭祀相同的高度上。
墨家则提倡“明鬼神、事鬼神”,《明鬼》篇直言:“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2]墨家是把鬼神作为圣人智者的化身,“鬼神之明智于圣人”,要“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方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阴阳家“任鬼神”,史家“信鬼神”,道家“制鬼神、役使鬼神、鬼神辅之”,哪怕是“反鬼神”的法家、兵家,对此的态度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鬼故事的前身应是谶纬巫祝神学。“谶纬”是古代汉族官方的儒家神学,用以神学迷信附会并阐释儒家经典。至汉光武帝刘秀之后,“谶纬”甚至被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可见古人对神异之说的态度。及至南朝,《文心雕龙》的《正纬》篇对谶纬的形容是∶“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世历两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采其雕蔚。”[3]解释了谶纬向文学性的演化,为鬼故事打下文学基础。巫祝仪式是神鬼之说的另一发端,巫祝重视的是人与灵。狭义的“巫祝”指“事鬼神者”,而广义的“巫祝”则包括所有与神、鬼、人沟通的方法和手段。宗教上反映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氏族上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死亡上的鬼灵崇拜、灵魂崇拜等[4]。这些信仰和崇拜观念诞生了原始巫祝,也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观念。而巫本身就有神秘色彩,人将自己不了解的神异之说编成故事来告诫他人,显示人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使鬼故事有足够的吸引力并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
神鬼之说从官学过渡到文学,载体最初是由史书实现的。中国古代部分史书不鲜见记录异闻怪事的习惯。春秋时期人们重视祭祀鬼神,希望得到神鬼的赐福,“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这种祭祀活动作为一种政治方向被史官们记入史书,神鬼故事也由此纳入正统文学体裁。儒家经典《春秋左传》中鬼神之事就是被正经记录下来的,晋代经学家范宁曾评价其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杨士勋注疏道:“‘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申生之托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是也。”[5]可见至少在晋代前,正统文学领域对鬼神故事的宽容性还是比较高的。而晋代后,南北朝时期,鬼神故事创作达到一个高峰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统计,《新唐书·艺文志》在魏晋时期所收的志神怪小说达15家150卷,后晋时期《旧唐书·经籍志第二十六》还著录鬼神26家。大量的创作使鬼故事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题材,但也导致其良莠不齐,自然显露出鬼故事偏离正统的迹象。又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史书由《新唐书·艺文志》“始退鬼神传入小说”,及至宋代才正式把鬼神故事内容归入小说部而不是放史部,从正统文学转向非主流文学。
三、神魔志怪小说溯源
今可见的传统鬼故事细分题材后大体为“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魏晋以前,神鬼故事尚未独立,附庸在其他文体中难以归类。魏晋时期,“志怪小说”正式成名,现代对“志怪小说”的释义是:“汉魏六朝时期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师和方士的奇谈怪论。”明确提出“志怪”一称,特指汉魏六朝时诞生的有巫鬼色彩的小说作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道: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6]
巫鬼一道,从中华传统文化诞生之初就一并产生。秦汉盛行的是神仙说法,汉代走的是巫术流,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鬼道就偏向了宗教,作为宗教反面的例证而存在。从魏晋到隋唐,文人大量创作鬼神志怪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宣扬其背后的宗教。鲁迅还特别指出,在当时人看来,鬼神是真实存在的,记录鬼故事与记录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鬼故事在脱离历史体裁后,走向了杂记的文体,更加平民化、生活化,读者接触面也愈广。
从内容上看,志怪小说基本可以概括为3种类型:其一,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具体作者尚待考,先托名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等;其二,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其三,演绎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等。以上3种类型依次过渡,恰恰符合了鬼神之说发展至志怪小说的过程:科普著作——野史传记——鬼怪故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志怪小说在魏晋之前的发展脉络和之后越来越向鬼神奇谈靠拢的发展趋势。
与单纯的鬼故事比起来,志怪小说之所以能归入“小说”部,而不是其他文体上附会鬼神之说的只言片语。还在于魏晋时期的鬼怪故事进化出了“小说”的特质。《搜神记》就是魏晋志怪小说中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作者干宝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史官写鬼神已不鲜见,但干宝本人却通晓阴阳术数、神仙鬼怪之事。他在《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7],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的目的。《搜神记》内容一是“承于前载”,在前人笔记野史中进行文学化的再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录入当代奇说怪谈,将作者所知的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化为故事记叙下来。现在对《搜神记》的评价是说它改变了之前志怪小说“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娱乐性和文学性有了长足进步,虽然文字仍保留着史家之文简洁质朴的特点,但已经有了独立成文的意识,开创了志怪小说走向大众的先河。同一时期的《幽明录》相较《搜神记》则在文学上走得更远。《幽明录》采录的多是晋宋当代新出的故事,叙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摆脱了世人对于老旧鬼神之说的固定思维。虽为志怪,《幽明录》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文字比《搜神记》来得舒展鲜活,也更富于辞采之美。这两部作品作者皆为当世正统文坛里的领军人物,又有着官学的背景,兼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这些直接奠定了志怪小说的发展基调,让鬼神故事由小众文学走向大众文学。
在“志怪小说”后兴起的“神魔小说”无疑将鬼故事推向了另一个高潮。虽说这二者体例上略有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属于描述鬼神灵异一类的小说作品。“神魔小说”的概念也是由鲁迅首次提出:“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释道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糊的彼此之争,我就总结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神魔小说。”鲁迅提出“神魔小说”是在儒释道3家教派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然而他并未注明其产生的具体时间。从内容上看,固然神魔小说中多有涉及儒释道宗教特质的素材,但从兴起时间上看,神魔小说风行于明清时期,如此长时间的时间跨度已经足够让其整合完善,不能单纯说它是宗教斗争的产物。小说是明清时期新并入的主流文体之一。鬼怪故事从短篇小说进一步深化,架空历史,系统有条理地叙事,可以将神魔小说视为长篇化、世俗化、文学化的志怪小说。
提到神魔小说,最经典的无疑是《西游记》。吴承恩给我们刻画了一个唐僧师徒4人上西天取经的故事,作者加入了诸天神佛、妖魔鬼怪,唐僧师徒一路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唐僧是凡俗的“人”,而大弟子孙悟空是猴精,二弟子猪悟能是猪妖,三弟子沙悟净是河童。人与非人类,西天与天庭,佛教与道教,种种矛盾冲突构成了《西游记》的背景。《西游记》虽记录的是唐代之事,反射的却是明代后期的宗教纷争。此时神魔小说以其荒诞离奇的内容、混杂的思想、不臧不否的态度,吸引到一大批受众。
有趣的是,不仅仅是《西游记》,中国传统四大名著或多或少都有描写神魔鬼怪的习惯。我们甚至可以将另外三大名著视作半神魔小说。《水浒传》楔子即为“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描写的是洪太尉在龙虎山上误揭了魔君的封印,由此引出了梁山108位好汉出山的缘由。以及戴宗的神行甲马,公孙胜与乔道清的斗法,还有宋徽宗梦游梁山,醒后敕封宋江,盖庙宇建祠堂,妆塑宋江等诸多将士佐以神像为结局,都具有神仙道派的特色。《三国演义》也有不第秀才张角入山采药,遇老人授天书3卷《太平要术》,习得能呼风唤雨的神仙术法。《红楼梦》全篇故事背景就是基于神话传说,以女娲补天后弃在青埂峰下一块有灵性的石头为由头,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手,引出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下凡游历人间以报浇灌之恩、圆木石前盟之梦,演义出宝黛之恋的悲剧故事。男女主角皆是神仙转世,金陵十二钗的命运早已记载在太虚幻境薄命司册子上,还有贯穿全文的一僧一道,《红楼梦》中,儒释道三教思想早已渗入其间。神魔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它不仅写神写魔,还构筑了一个贴近真实、贴近民俗的社会,文中既有世俗欲念乃至某种反传统精神在幻想形态中的表现,也包含着许多宗教因子,如宣扬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满足了底层百姓和广大文人群体对现实种种的倾诉欲望和自我安慰。神魔小说的社会性让读者有代入感,它们不仅仅是文笔优秀的小说作品,还是记录世间百态的历史杂志。
及至清代,神魔志怪小说就不得不提《聊斋志异》,这部被郭若沫评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集大成作无疑是神魔志怪小说的巅峰。蒲松龄明写鬼怪故事,实际却暗讽了社会上种种不公现象。作品中有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罪行的《促织》《红玉》等;有反对封建婚姻,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的《婴宁》《青凤》等;有揭露并批判吏治腐败的《叶生》《考弊司》等;有歌颂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商三官》《席方平》等;还有富于道德训诫意义的作品,如《种梨》《瞳人语》等。这些作品不能直言,只能假借“莫须有”的鬼神来告诫世人。清代或有人还赞同鬼神之说,鬼神之事不再高置于神坛难以捉摸,而是能被人利用驱策,供笑语耳。神魔小说的应用面积增加,发展道路也增多了,所以说神魔小说在明清是继魏晋后第二次爆发期。
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合称为神魔志怪小说,它基本上可以概括所有的中国传统鬼故事。从整体上看,神魔小说是志怪小说发展到后期的必然产物,它经历了一个由“神”到“鬼”的信仰弱化过程。人类开始时畏惧鬼神,到后来习惯并相信鬼神,最后将神鬼故事别置一旁,抱着娱乐、戏谑、嘲讽的态度来看待鬼故事。人类对鬼神的敬畏的心理降低,反而使鬼故事有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虽说偏离了严肃正统的主流文学,但百花齐放的野史杂记为其注入了后续发展的无限生机,神鬼传说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四、神魔志怪小说走向邪说
神鬼故事与传统文学在封建帝制时期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是一个源自正统—独立出去—再次回归正统的过程,鬼故事的正统性毋庸置疑。但封建社会结束后,神魔志怪作品在主流文学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现代时期的几次文学革命先将所有传统文学视为糟粕,起复后独独将神鬼之说视为封建迷信大力批判,到了当代,已没有人会认为鬼神之说是正统文学。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鬼怪故事,甚至越来越走向猎奇和异端,流行的鬼故事无不是为了满足读者寻求刺激的口味。鬼故事不再具有最初的科普性和常识性,也缺少了教育意义和讽喻特色,归根到底,人们不再相信“鬼”,也不需要“鬼”来警惕自身,那么只剩下娱乐特质的神魔志怪作品,必然走向歧路。
神魔志怪小说的非主流还因为“志神”“志怪”与“志人”的差别。志怪小说是小说演变发展中的一种产物,由于魏晋时受佛道及玄言清谈的影响而产生,它承接了记录神话故事的传统。但不管是“神”还是“怪”都是非人的,人类天然的排他性就对神怪有了不信任。如果鬼神不能有利于人类生活,不敬鬼神也不会受到责罚,那么鬼神对人类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没有了敬畏之心,鬼神自然也无可无不可了。
神魔志怪故事自从魏晋时期从主流文学中分裂出去后就已经埋下了再次分裂的因素。“遗事(野史)”相较“正史”总是少了那么一分理直气壮,神魔志怪小说必然走向社会化、文学化,而经过文人二次加工的作品与真实已有不同,虽然内容丰富了,支撑鬼神存在的底蕴却被削弱了。
五、结语
“中古之人咸重灵界而轻物界。凡我们现在视为虚灵玄秘之事在中古皆是‘真实’。”[8]古人视鬼神为理所当然,至高有宗庙祭祀之事,至下有鬼怪神话传说。既然古人已将鬼神融入日常生活中去,就不可能排斥否定它存在的意义或价值。不论是诸子百家、史书传记,这些主流,甚至是核心文学典籍中都可以找到关于巫鬼的记录,四大名著从某一层面上来说也可以被称为明清四大神魔志怪小说。神魔志怪故事的内容被古人视作“真实”,作者多有当世大儒出现,作品载体属于主流文学,影响深远,皆说明了鬼故事的正统性。现当代鬼故事之所以走上歧路是古今世界观、价值观冲突的必然结果,但这不应该成为中国神鬼传统的反例,传统神魔志怪小说中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值得肯定。
[1]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0:63.
[2]吴毓江,孙启治.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336.
[3]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16.
[4]柳岳梅.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古代鬼神崇拜[J].北方论丛,1998(4):75-80.
[5]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58.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7-39.
[7]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2.
[8]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