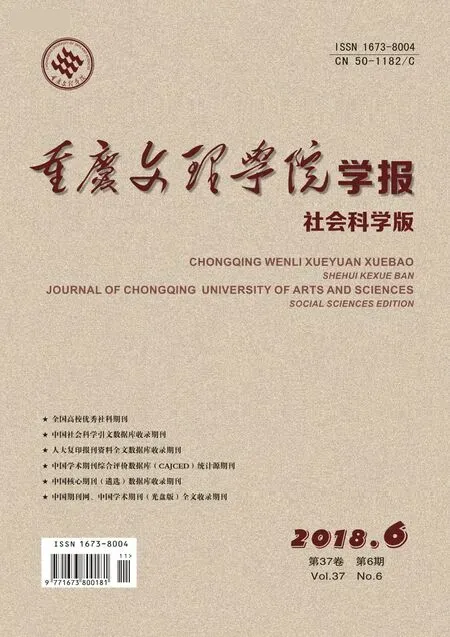蒙白跳园的“申遗”实践与多元“表征空间”
郎丽娜,谭斯颖
(1.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2.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遗产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人类学对于“空间”的研究,体现了从物理性到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发展。最初只注重其物理性的研究,如埃米尔·涂尔干在谈到“分类与社会”[1]时,将空间看作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作为社会中进行分类的工具和各个事物的一个容器。米尔恰·伊利亚德受涂尔干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分类观点的影响,将神圣与世俗视为世界存在的两种样式,把空间分为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2]。维克多·特纳又在伊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这一空间划分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仪式空间。仪式空间的研究不仅体现了空间的文化意义,表征了空间的文化性,而且仪式空间功能的研究也正表征了空间的社会性[3]。对空间的社会性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法的是亨利·列菲伏尔,他明确提出了“空间生产”的“三位一体”概念:“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4]。“空间实践”是指空间的物理性,“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指的是观念意识形态的空间,表达的是空间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其中,“空间表征”指构想性的空间生产,“表征空间”指的是生活、感知以及象征性和体验式空间的生产,生产的都是社会关系。本文研究的蒙白跳园就属于这样的象征性、体验式空间的生产,是通过观念意象以及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象征符号体系直接生产出来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既不同于“空间实践”的物理空间,也不同于构想空间的“空间表征”。它是通过一定的符号与象征,在能感知到的物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行动者进行的象征性实践建构出的新的空间,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在本文中,“表征空间”的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是跳园空间生产的蒙白的区域社会关系网。因此可以说,“表征空间”是从实际生活的空间出发的、可以同时涵盖“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这二者的一个开放性和动态的空间。在现代社会,人群流动性不断增加,尤其是非遗概念的引入使参加跳园的不再只是蒙白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人。人们在跳园这一仪式空间中的各种活动建构出新的空间,进行了新的空间生产,它所表征的范围变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一、蒙白与跳园
本文中的蒙白指的是现居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龙山镇境内的苗族。蒙白在文献中的记载开始于元代,是以“统称”的形式出现的。在元代被称为“猫蛮”,明代称“贵州苗”或“东苗”,清之后称为“白苗”。在清代《黔书》中有“白苗在龙里县,亦名东苗、西苗……”[5]的记载。关于白苗居住于龙里县,在《永绥厅志》所载的二十二种苗的白苗一条里,介绍了白苗的来历:“原出贵州贵定龙里,衣尚白,裸头跣足,盘髻粗簪……”[6]关于白苗在龙里县的主要分布,《贵阳府志》记载:“白苗在府属者(指贵阳府)居中曹司高坡、石板诸寨,在龙里者居东苗坡上中下三牌、大小谷朗诸寨,在贵定者居摆成、摆布、甲佑诸寨,衣尚白,短仅及膝。”杨昌文在《龙里县中排乡和民主乡苗族考察记略》[7]中对其中地名进行了考证,认为文中的龙里东苗坡上中下三牌、大小谷朗,今皆为龙里县草原社区内蒙白苗人聚居地,而中曹司高坡、石板诸寨,和摆成、摆布、甲佑诸寨是被同称为“白苗”的“红毡苗”和“海葩苗”的居住地。
现在的蒙白主要聚居在上排、中排、下排,基本上对应于现在龙里县的行政村——水苔村、中排村、团结村。此外,蒙白在一些与汉族共居的寨子也有分布,如黔南州贵定县沿山镇和平村以及贵阳市花溪区小碧布依族苗族乡的一些自然村寨。据当地人讲,“蒙白”人口总数大约10 000人,主要姓氏有王、李、唐、冯、陈、杨、胥等。
跳园作为蒙白一年一度举行的节日仪式,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于每年正月初五到十二分别在三个地方依先后次序举行。到了这个时节,蒙白的青年男女就聚集到跳园场上。这时的跳园场如同施坚雅笔下的基层市场[8]。在跳园时,人们在跳园场地交流,了解各家的事,建立了一个熟人圈子。跳园仪式展演表征着这一群体的社会区域,表征着这一群体的文化认同和边界。蒙白跳园有青年男女谈恋爱和择偶的功能,他们以跳园为纽带形成了通婚圈。这一通婚圈对于族群文化认同起到的作用是地域上的限制,而在跳园时人群聚集在一起参加本族群共同的节日则是对族群文化认同起到精神上的加固作用,也可以说形成了他们生产、生活的区域和空间,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蒙白跳园的“申遗”实践
笔者于2014年进入蒙白居住区,对蒙白跳园在“申遗”前所做的准备、“申遗”成功后不同群体的表现有全面的参与式观察。
(一)为“申遗”作准备的跳园
在蒙白居住区,笔者目睹了“申遗”前跳园的全过程。2014年正月初十下午1点左右,下排(“排”为“蒙白”苗人对其居住区域的称呼)的跳园开始了。当时从山顶走下来一群人(山顶上有一个寨子叫等鲊,是这个跳园场的场主),走在前面的是几个身穿红袍和黄袍的男人(场主寨上的王、李、陈三姓男人代表)。最前面的一人敲锣,后面两人吹唢呐,再后面的四人抬着两个直径0.3米多、高1米多的大木鼓,接着是5个手里端着牛角的人。在他们之后还有一群盛装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他们都从高山上沿着“之”字形路走下来。
跳园场在群山环抱之中,周围是层层梯田,相当于在一个盆地中央。原先的跳园场就是一块田,与周围田的区别是不种庄稼。2013年下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跳园场周围的一圈用水泥砌成了一级级的看台,中间也用水泥砌起了一个直径约2米、高约0.5米的圆形墩子。据当地人讲,这个墩子是为了方便领导讲话。跳园场场主等鲊寨到跳园场的石阶路也是那时修好的。
从等鲊寨下来的人们进入跳园场后,先是放了五六箱烟花。放烟花时,这些穿红袍和黄袍的人敲着锣、吹着唢呐、抬着鼓,端着牛角围场地转了三圈,进行祭祖和祭场仪式。接着,场主代表人开始宣告跳园场上的规矩,大概就是参与者相互间要友好相处等。接着由本寨子的小伙子吹起芦笙,先跳三圈后,别的寨子的小伙子才吹起芦笙,按照一个寨子站一排的样子陆续加入。各排姑娘们先是站在圈外看,等相中了哪个寨子的男子后才会陆续进场,一排排跟在相中的那排男生后面跳。先由本寨的人来跳,这体现的应该是“场主”的权力。在跳园结束后,参与跳园的姑娘和小伙们都拿到“场主”寨子准备的礼品——一张帕子和一个口杯。
2014年的跳园是由龙里县文化局组织的,因此在姑娘和小伙子进场跳之前的祭祀环节里增加了许多内容。在以上祭祀环节中,许多原本不属于跳园的东西被加了进来。
“披袍”红白或黄白搭配,是蒙白男人在年轻时参加跳园,和去世后入棺时要穿的衣服,也多为下午跳园快结束时外寨子的小伙子在场内跳时要穿的衣服。这时本场主寨上的姨妈、姑妈等亲戚会来抢他们身上的衣服,俗称“抢黄袍”,也即请他们去吃饭、歇息之意。现在的跳园由家族里的鬼师、鼓师、芦笙匠以及中老年男性进行开场仪式。由于现在的交通比以前更快捷,跳园结束时远处的人当天就可以回家,不用在亲戚家歇息和吃饭。因此,“抢黄袍”的环节自然没有了。
木鼓是用来给亡人“开路”(葬礼上的仪式)时敲的,一般一个家族有一对。在等鲊寨,王、李、陈三家各有一对。木鼓平常都挂在小孩子碰不到的地方。鼓不能随意敲,因为给亡人“做鬼”时,鬼师念鬼,鼓师敲鼓,芦笙匠吹芦笙,这样就把祖先的魂魄请来了,请来后要用酒和肉招待,所以鼓平时一般不能敲。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地流传的关于“伏羲姊妹制人烟”的故事:鼓是用来关雷公的。雷公因与伏羲打架被伏羲关在鼓里,后来因小娃娃不懂事将雷公放出,导致了洪水滔天。所以,敲鼓是告诉年轻人不能与老人抵斗(吵架),否则天理不容。对于现在把木鼓抬到跳园场上来敲,下排等鲊寨的王光兴老人(鬼师)是这样讲的:“将鼓搬到跳园场来敲,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过的事情。但这次我们听从龙里县文化局的意见,将鼓搬来跳园场敲是能说得过去的。因为即使把祖先的魂魄请来了,正月间也是有酒有肉的,是可以招待好老祖先们的。”
牛角是“敲巴朗”祭祖和给亡人敲牛后的牛角,平时摆在“神道”(神龛)那里。每一个家族里的鬼师、鼓师、芦笙匠去世时,要将一个牛角摆在头边,一个摆在脚边,这是一种象征身份和财富的物件。将牛角端到跳园场上来,是想增加跳园的神秘与古朴。这是龙里县文化局的意思,亦被等鲊的“三班人”(鬼师、鼓师、芦笙匠)所认可。这些新加入的内容,使跳园的观赏性增加,显得神秘而古朴。
(二)“申遗”成功后的跳园
2015年,跳园成功被列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龙里县文化局和蒙白来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当时,龙里县政府给予4万元作为鼓励和支持的经费,希望将跳园这项民族文化活动很好地传承下去。下排的团结村村干部决定利用这4万元经费将2015年的跳园搞得热闹一点,于是他们到周边请来了一些“助阵”队伍:有红毡苗的“广场舞”,有海葩苗编排的舞蹈,有县文工团退休人员表演的彝族舞蹈“阿西里西”,以及“场主”等鲊寨的年轻姑娘、小伙子们编排的舞蹈等。2015年的跳园如同2014年一样,先是由场主寨上的人敲锣打鼓、手端牛角进行开场仪式。因为那一次跳园有龙里县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领导在场,所以在开场仪式结束后有“助阵”队伍按先后顺序进行的文艺表演。待有关领导离开后,大家先是在跳园场里找一块空地,然后将自己所带的大音箱摆好,将音量调到最大,在音乐的伴奏下,大家都穿着自己民族的盛装尽情地跳舞。传统的跳园方式也在进行,大家各跳各的,互不相干。在跳园场上,呈现出的是多种文化的“盛会”,是不同人群共同参与的地方盛典。此外,还有一处值得关注。当年的小贩摊子统一被规划到跳园场左边的一大块空地上,被规划的小贩摊子看起来整齐多了。在商贩摊子的旁边还有一个特别的摊点,后面挑着写有“草原计划生育宣传活动”的横幅,前面的一些纸箱子上摆着宣传册和围裙,后面两个工作人员也学小贩吆喝着;有妇女们过来看时,工作人员就将宣传册和一个围裙发给她们。跳园结束后,参加跳园的蒙白,被请来的红毡苗、海葩苗以及县文工团退休人员都能得到一些劳务补助。
(三)“申遗”成功后被搁置的跳园
2016年在开展“跳园”仪式的前几天,团结村干部多次到龙里县文化局申请经费,县里面拨了1万元作为支持。虽然没有2015年多,但还是得到了龙里县文化局的支持。村干部将从县里面申请到的1万元钱都交给了场主等鲊寨的两位组长具体支配。两位组长在买了“跳园”中要用到的帕子、烟花、红布等一些物品后,剩下的钱已经很少了。
2016年的“跳园”,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龙里县都没有领导来参加,可以说又恢复了传统的“跳园”形式:等鲊寨的中老年男性没有穿“披袍”,没有敲木鼓,没有端牛角,没有吹唢呐开道,没有整齐的“入场式”。但没有受到邀请的红毡苗“广场舞”队、县文工团退休人员队、海葩苗队仍然来了。他们依然像2015年被邀请来时一样,带着大音箱,穿戴整齐,光彩艳丽。他们到场后直接进场找到合适的场地,放好音箱,排好队列,在音乐的伴奏下欢快地舞了起来。2016年的“跳园”依然如2015年一样热闹,在跳园场上既有“广场舞”,也有蒙白传统的吹芦笙的跳园,总体呈现出的是不同人群共同参与的地方“盛会”。据说,2016年来参与跳园的人不论是红毡苗、海葩苗还是蒙白,每人都得到一条帕子作为鼓励。
三、跳园:多元的“表征空间”
在当下,把民族和民俗中的传统文化遗产化是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策略。跳园与“申遗”的关联也表现了这样的意义。三年的跳园与“申遗”成功前后的过程,反映了各方不同的关切,同时又把蒙白的跳园从传统的节日庆典聚会推向一种多元的“表征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蒙白跳园发展的可能性。
(一)作为蒙白自己的跳园
跳园作为“非遗”时,蒙白人民为了跳园发展需要,在适应性地理解国家“非遗”性质的跳园,但没有改变他们心中的跳园。近几年,在其他多方力量参与下,蒙白自己的跳园出现了不少变化。
在当地人眼里,他们的跳园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就像当地老人经常讲的:“不需要打广告,不需要通知,一到那几天,四面八方的人就聚拢来了。”一些老人在谈到他们年轻跳园的情景时显得非常激动: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跳园的人比现在要多十倍,跳的人是前面挨后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都要踩到脚后跟了。即使下雨天、下雪天,跳园场上有水坑、有泥巴,都快淹住脚了,也还是没能阻挡大家去跳园的热情,大家都还是会去跳。以前不仅跳的人多,看的人也多。看的人有上排的、中排的、高坡的、花溪的,甚至还有凯里的……可以说是跳园场两边的坡上都站满了人,有上千上万人,人山人海,数也数不清。以前我们跳三天不够,还要跳个第四天,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场。以前大家没事情做,不像现在有电视、有手机,来跳的人不如以前的多,看的人也不如以前多了。以前没有奖品、路不好,没有车子大家走着来;而现在路好了,车子也方便了,但大家都不愿意来了,要靠奖品大家才会来。如果在第一天和第二天就将奖品发到来跳园的姑娘和小伙子手里面,那第三天基本上就没有人来跳了……”
其实,跳园作为表征蒙白自己的空间,其意义比较纯粹和自然。对于老一辈的蒙白来说,跳园表达的是一种纯朴的乡土社会的感情,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记忆的延续。
(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跳园
我国自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现了法制化和制度化[9]。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制定评定标准并经过科学认定建立了国家级、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四级保护制度”[10]。“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11]国家根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级认定,相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他们的保护措施[10]。跳园成功申报成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参与跳园的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为了突显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跳园所应有的古朴性、审美性,龙里县文化局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跳园的空间结构,把一般不会在蒙白跳园中出现的人物(鬼师、鼓师、芦笙师)“包含”了进来,把属于家庭荣誉的“敲巴朗”的象征物——牛角“包含”了进来,把不能随意敲打的大木鼓也“包含”了进来。这一系列表现隐含的是祭祀祖先的象征表达,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实现与祖先的沟通和交流,祈求祖先神灵的保佑,以及表达一种“场主”寨子应有的权力。其实,蒙白跳园的神圣性是在一系列文化表达中早就存在的;即使没有以上内容加入,它的神圣性也自然存在。事实上,蒙白跳园所要表达的意义也自然存在,以下特点是为蒙白跳园参与者所共同认可的:上中下三排各有一个跳园场,每一个场都有一个场主,场主是每一个排举行跳园时的仪式主办者和主持者,场主寨上的人是跳园的“中心”,以及跳园作为“表征空间”表达的是年轻人的恋爱空间和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是蒙白的生产生活空间等。这些都不需要被讨论,也不需要特别显示出来,因为它们是蒙白社会历史延续的一部分。
(三)作为旅游资源的跳园
从龙里县文化局的旅游视角出发,“仪式在现代旅游活动中经常作为体现和展示传统文化和地域价值的一种活动载体”[12]。要使仪式这种文化资源服务于旅游或产生经济效益,就要适当地进行“传统的发明”,发明一些形式感的东西,就如同2014年和2015年的跳园一样。“传统的发明”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他认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13]。所以,对场主寨来说,跳园作为“表征空间”表达的“主与客”和“先与后”的关系空间,是一种公认的、不需要明示的“权力空间”,在当地文化局的参与下进行了“传统的发明”,从“后台”走到了“前台”。通过仪式展演方式,管理者的权力在蒙白苗人的价值和行为规范中由“内隐”变为“外显”。跳园中被发明的“传统”,是对当地蒙白苗人文化有一定理解的一位红毡苗(红毡苗聚居于高坡乡,在龙里县境内分布于摆省乡,在文献中与蒙白被统称为“白苗”)文化人士策划构想的,虽不能算是蒙白的一种“客观表达”,也可以算作格尔兹所谓的“经验接近”的理解。作为文化传统的蒙白跳园,受现代社会的影响,它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正如在上文中当地人对将葬礼上的木鼓抬到跳园场上来敲的解释——“即使敲鼓把祖先请来了,正月间我们也是有酒肉招待的”。
这种以显性方式展示跳园和更多外来群体融入跳园,可以说是“传统的文化仪式向群众活动场面的转换”[14],也可以说是一种保护跳园的更好的方式。因为这样的“建构”是想把蒙白跳园作为一个文化展示的平台,是将原本隐性的东西以舞台的形式,以更直接的方式让游客了解跳园,也使新一代蒙白对本民族文化有直观上的认识。可以说,这样的方式对他们起到教育、鼓励他们保护与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作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当地文化局在原来基础上增加跳园的神秘性和古朴性,不仅能使当地蒙白群众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跳园,而且还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对当地蒙白群众来说,跳园作为“表征空间”表达的是一种纯朴的乡土社会感情、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记忆的延续。但成为“非遗”的跳园则将当地蒙白、文化局、旅游局、商贩联系了起来,让各方能够运用相同的跳园符号表达各自的诉求。
四、跳园:多元“表征空间”中蒙白社会的变迁
在蒙白的三个文化空间(坐花园、斗牛、跳园)中,跳园是最外显、最具有形式感的一个,也最适合进行旅游开发。这也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重视蒙白跳园的一个原因。从“空间生产”的角度说,跳园作为生活的、感知的、象征性的、体验式的空间,它所“生产”出的社会关系空间、表达的社会结构空间,是与蒙白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互为表征的。随着时代发展,人与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会有新的社会关系产生。因此,跳园这一象征性的、体验式的空间也会依照人的各种活动不断建构出新的空间——作为蒙白自己的跳园、作为“非遗”的跳园、作为旅游资源的跳园、作为商品交易的跳园等。因关系空间错综复杂,跳园“申遗”成功后,在跳园空间中发生了一些利益诉求上的冲突;但经过协商调解,冲突得到了化解。从“空间形塑力”[15]角度看,新的空间会产生新的意念机制,会发挥对人的行为活动进行限制和调节的新的力。人们依照在不同的关系空间中所存在的力行事,表达各自的诉求。因为现代社会中的跳园是在原来的文化传统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需要建构出来的节日仪式空间,所以这一空间会反过来维护和塑造社会的文化和秩序。我们也可以说,跳园的多元“表征空间”展示了蒙白的社会变迁。
蒙白跳园原是当地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缅怀祖先、与祖先沟通的仪式空间,是有利于年轻男女寻找配偶、组成家庭的空间,也是人们进行交流、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空间。随着社会发展,不少人觉得祈求祖先保佑身体健康,不如到医院。随着在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田地多荒芜,养家禽和牲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城里买房子,不会再养家禽和牲畜,所以不再需要祈求祖先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平安了。男女寻找配偶也不需要正月间再到“花园”里去了,也不需要再通过跳园看姑娘衣服的“针脚”细不细腻,看小伙子腰间所系“腰带”评判其家里田地多少以此来决定选择的对象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通信和交通工具的发达而变得方便。因此,跳园原有的“表征空间”所具有的功能已经失去。用马林诺夫斯基的“需要—功能论”[16]解释,既然人们没有了这样的需要,那它也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但将其作为扎根于当地历史和自然环境的文化事象,跳园体现了蒙白的社会文化特性;与此同时,它有了新的“需要和功能”——作为传统文化被传承与发展,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蒙白跳园的这种转换,其实是将传统融入现代之中,成为地方社会变迁的象征。
五、结语
本文以跳园被“申遗”“申遗”成功以及成为非遗后的情况探讨跳园作为“表征空间”的“空间生产”,反映了蒙白社会的变迁。随着人们在跳园中活动的多样化,在原有属于蒙白自己的社会关系空间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构成元素。这说明了蒙白在通过跳园展示其族群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对其文化进行了创造,从单一的民族文化领域进入多元的文化共同体之中。这些变化反映了蒙白社会的变迁。通过蒙白跳园产生的经济效益改善村寨设施,以蒙白跳园的开展来促进其保护等,不仅有助于当地人民继承其传统文化,而且有助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