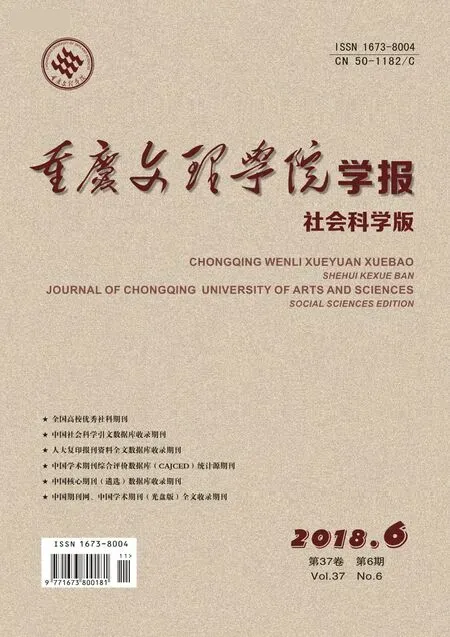突破禁忌的女性参与:浅析“撒尔嗬”传承中的嬗变
邓炜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北碚400700)
“撒尔嗬”是鄂西土家族地区特有的丧葬习俗,主要流行于西起湖北省建始县东至长阳县的清江中游一带,又以巴东县的野三关镇、水布垭镇和清太坪镇为核心传承区。2006年,“撒尔嗬”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撒尔嗬”的唱跳是禁止女性参与的,这成为丧葬仪式场域内的女性禁忌。我国本土对民俗禁忌的研究不少,但针对土家族丧俗禁忌的专题研究甚为少见,尤其是对近年来突破女性禁忌参与“撒尔嗬”的研究。在“撒尔嗬”传承区内,土家族文化观念的变迁构成了女性突破禁忌参与到“撒尔嗬”中的条件,在这一嬗变之下又有某些文化似变而未变。“撒尔嗬”中女性禁忌的突破断不止于表面现象的变迁,所以不仅要考察实现女性参与“撒尔嗬”的物质条件,还要从更深的文化层面进行分析。
一、“撒尔嗬”中女性禁忌的文化之源
传统土家族社会与“撒尔嗬”相关的禁忌较多,最为严苛的当属禁止女性跳“撒尔嗬”。关于此项禁忌的古训较多。这类禁忌在“撒尔嗬”传承区域为人所熟知,在土家族文化中有不容小觑的分量。
(一)维护神圣的社会分类
1.“撒尔嗬”中的神圣本源
有学者认为,禁忌是关于神圣或不洁的约定俗成的一种分类。玛丽·道格拉斯对其作用有过精确论述:其一,“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为的是保护宇宙中的清晰种类”[1];其二,“禁忌对含混带来的认知不适做出反思,含糊的事物看上去很有威胁”[1]。据此分析,“撒尔嗬”中女性禁忌的设置,可以先假设女性禁忌是为了防止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但“撒尔嗬”中的神圣性源自何处?可以肯定的是:在丧葬仪式过程中,有关神圣的观念其存在是具有普遍性的。丧葬仪式是亡人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即从生者的世界过渡到亡者的世界。这一过渡阶段的阈限状态是模糊不定的,“阈限或阈限人的特征不可能是清晰的……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2]。我们可以认为,丧葬仪式中的亡者既具有神圣性也具有世俗性,这在“撒尔嗬”唱跳中可见端倪。有的歌师唱词是即兴而作,其内容有时是对亡者加以调侃,方言中对这种调侃行为本位地称为“呵闲儿”。唱词拿亡者生前的事或就死亡本身进行“呵闲儿”。有时调侃尺度过大,观众会在一旁嬉笑着恐吓歌师:“你小心他(指亡灵)来找你算账。”歌师有恃无恐地回答:“他在生都那么个样,死了我才不怕呢!”这一情景中的恐吓和有恃无恐,所反映的正是土家人对于“神圣—世俗”二重性的认识,亡者本身就是具有神圣性的。
也有较多学者试图将“撒尔嗬”与土家族白虎图腾崇拜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从舞蹈起源来看,“撒尔嗬”极可能出自巴人的战舞,而巴人与土家族有渊源,巴人具有崇虎的原始信仰[3]。“撒尔嗬”中有“虎抱头”“猛虎下山”等一些模仿老虎的舞蹈动作,在“撒尔嗬”仪式的舞蹈动作和造型中更充满了极强的虎图腾崇拜色彩[4]。有人认为:“撒尔嗬”源于古时巴国人对祖先的祭祀活动,纯粹是一种反映图腾现象的祭祀性歌舞[5]。但不应忽略的是,“撒尔嗬”舞蹈中还有诸如“牛擦痒”“燕儿衔泥”等许多对其他动物动作的模仿。这使得“撒尔嗬”与白虎图腾崇拜之间的联系显得有些牵强。因此,欲建立“撒尔嗬”同图腾神圣性的联系,这一解释途径还有待探究。
2.社会分类的女性禁忌
女性具有一些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现象,有些现象超出了年代久远的人们所能理解的范围。这些现象使女性在其认知范围里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存在。这种存在难以用当时已有的知识去解释,从而被认为它一定附着一种神秘的未知的令人恐惧的力量。对古时人们而言,这种未知的威胁无法克服,只有规避。因此在“撒尔嗬”的神圣场域内,女性禁忌是传统社会中关于女性的一种分类,是对女性特殊生理现象的一种规避。在调查中,当笔者问及为什么会忌讳女性跳“撒尔嗬”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在这样的场合,她们跳就会使事主家走霉运,是不吉利的”。在“撒尔嗬”的传承地区,忌讳女性清洗水井,堂屋正楼上忌讳女性睡卧,当地人对以上女性禁忌有着与前面相似的解释。很明显,在当地多数土家人的认知里,女性禁忌观念印证了道格拉斯所论述的传统社会中有关不洁与危险的分类原则。那么在“撒尔嗬”这类丧葬仪式程序中,就会有禁忌秩序来维护洁净、维护神圣。每当丧礼中举行“撒尔嗬”,必有一次对女性禁忌的无言重申。这无疑强化了传统社会的分类认识。
(二)父权制及礼教权威
爱弥尔·涂尔干认为:“宗教产生了社会所有最本质的方面,那是因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因此,宗教力就是人类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6]神圣和宗教力的来源正是社会本身,是社会群体中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撒尔嗬”中女性禁忌存在的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属于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低位,加之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三从四德”在土家族社会同样被看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说法亦反映了传统权威在习俗中的存在。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差异有着具体又细致的反映,例如“撒尔嗬”仪式中的男性歌师是较受尊重的,有着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这种优越通过男性歌师的“掌鼓”技能获得。女性却是被潜意识定位到无技艺也无地位的一类。在土家族父权制的文化体系中,女性在诸多文化场域之中是缺席的,是毫无话语权的。父权文化俨然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影响着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作为文化主体的女性在“撒尔嗬”仪式中被剥夺了自由表达情感与欲望的权利。禁忌的存在维持和强化了社会认可的秩序,当换位审视时,可以发现禁忌在规避“危险”的同时也限制了女性应有的发展权利。“凡存在着禁忌的地方,就必然有潜藏的欲望。”[7]女性禁忌的背后,也必然潜藏着女性作为文化主体的必要欲望和权利。禁止女性参与“撒尔嗬”仪式,无疑将女性追求自我实现、文化娱乐等的权利掩藏。比如“撒尔嗬”本身具有娱乐功能,从前在农村,人们劳作之余可以载歌载舞的场合本就不多,但禁忌使女性无法直接参与这种娱乐,限制了女性追求这一娱乐的自由。在禁忌中,压抑女性权利的力量正源于上述神圣和权威。
二、突破禁忌的文化观念之变
在土家族的丧葬仪式中,传统“撒尔嗬”的唱跳及至“撒尔嗬”商业化班子的出现之初,都只有男性参与。21世纪以来,“撒尔嗬”除了在丧葬仪式中可见,更发展出一些去仪式化的表演形式。为了推动其传承与保护,“撒尔嗬”作为歌舞出现在诸多表演和比赛的舞台上,在此过程中女性便参与到“撒尔嗬”表演中来。这个过程脱离了丧葬仪式独立发展,这种有女性参与的“撒尔嗬”形式,又跟随商业化回归到丧葬仪式之中。这一变迁直接打破了传统“撒尔嗬”中的女性禁忌。
在传统“撒尔嗬”场域中,女性禁忌能够持续存在,在于当地土家族秉承了前述有关神圣或权威的文化观念。在当下,女性突破规避危险和维护洁净的禁忌,参与到充满神圣性的“撒尔嗬”中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诸如国家政策推动、去仪式化的场域出现、商业化“撒尔嗬”班子形成等一些现实条件产生了作用。从表面上看,女性参与跳“撒尔嗬”使得角色、场域、形式、内容等发生了较多变化,如女性参与唱跳甚至承担“掌鼓”角色,原在灵堂内举行的“撒尔嗬”现在外移到院坝中,内容上掺入女性专跳的花鼓戏,男女搭配成为常见形式等。这些都是传统跳法中所未见的。透过此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嬗变背后那些根植于当地土家族意识层面的传统观念的变迁。也正是当地土家人文化观念之变才突破了严苛的禁忌。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女性特殊的生理现象已有了科学认知。虽然表现到与女性相关的观念层面显得有些迟缓,但终究也从“撒尔嗬”中女性禁忌的突破中表现出来。前述有关神圣本源及社会分类的禁忌观念,在近四十年里已悄然发生变化。土家人出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认同,意识里逐渐对传统的社会分类知识产生怀疑,并不断从意识里对女性禁忌等观念进行消解。
同样,父权制和礼教的权威所代表的是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因素,更可以看成是构成传统政治体系的基础制度或观念。回顾女性突破禁忌参与到丧葬仪式中“撒尔嗬”的过程,其初始物质条件是有了去仪式化的场域——表演和比赛的平台。这一平台的出现、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及基层文化部门的实践是关键性的催生力量,使得女性有了作为文化主体而不再受到压抑的权利。这是一种对传统权威、对父权制和礼教权威等的消解。
三、突破禁忌的争议及其分析
当今,女性参与“撒尔嗬”所带来的变化正在发生,其带来的影响也正在扩大。但围绕“女性究竟能不能参与‘撒尔嗬’仪式”的话题尚有不少争议。当地民间对此存在着两种相对的见解:一是反对这种变化,认为女性参与“撒尔嗬”仪式是对传统的背叛;一是赞成这一变化,认为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新。
(一)破坏传统与否
认为女性突破禁忌参与“撒尔嗬”是破坏传统的观点亦可分为两类:从表面上看,他们认为这种变化破坏了传统“撒尔嗬”的唱跳内容和形式;从深层次来看,他们认为女性参与“撒尔嗬”是对禁忌的无视,破坏的是一种文化传统。
从表面上分析,比如对“女的跳丧,只能说是看着新鲜,但比起传统跳法并不正宗”的说法,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认为女性参与“撒尔嗬”仪式属于破坏传统形式的基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以前大都会跳且爱跳“撒尔嗬”,所以不难理解他们有着对传统跳法的偏爱。与此相对的观点是:“这是现在的潮流了,而且很多女的唱得跳得很好,比一些男的跳得好看些。现在大多数人家有钱且请得起班子,没钱的人家为了面子也会请一个,场面是越大越热闹。”我们可以从这些观点中提炼几个关键词:好看、面子、热闹。好看是因为有女性参与和商业化班子有现代化的表演设备,这无疑体现了当地土家族审美观念的某些细节变化,人们已经在关注抛却禁忌之后的现实美学。但面子观念及“面子”背后所代表的“里子”,这个“里子”就是在集体聚会场合下进行的社会竞争,实属久已存在的传统实质,形变而质未变。
从深层次来看,“有了女性参与的‘撒尔嗬’中掺入了许多现代歌舞,这是对其文化内涵的破坏。商业化的‘撒尔嗬’表演队不一定由孝家乡里乡亲组成,因此唱者与观者多不熟悉、缺乏互动,其表演所展现的内容地方性文化不足,形存而神散”[4]。这种说法似乎在表达“撒尔嗬”不再是一种集体欢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只有男性唱跳的传统“撒尔嗬”,还是有了女性参与的商业化“撒尔嗬”班子,“撒尔嗬”的参与主体是演员和前来悼念的人,作为亡人最亲近的那些人——孝子却没有参与到“撒尔嗬”的唱跳中来。所以,一些丧葬仪式的核心成员是游离于外的。在此嬗变中发生变化的是“演员”,演员中有了女性,甚至演员不像以前那样来自朝夕相处的邻里而是有“外人”。但调查显示,“陌生人”并不尽陌生,即使不是邻里,但至少完全是同一文化区域内的“熟人”。仅从对丧葬文化的理解来看,“演员”与“观众”并无二致。
(二)功能缺失与否
对“撒尔嗬”的学术关注中从来不缺乏功能研究的身影,此处有必要再次厘清这类研究的重要前提,即“撒尔嗬”的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近40年间,有的定义如“‘撒尔嗬’仪式是土家人为亡人举行的一种以歌舞为载体的丧葬仪式”[4];也有的定义如“跳丧,又叫跳‘撒尔嗬’,又叫‘打丧鼓’,是一种古老的丧葬礼仪”[8]。这类定义实为多者。总之不难发现此前研究中对“撒尔嗬”的定义几乎就等同于丧葬仪式,这俨然成为一种学术共识。
对女性参与“撒尔嗬”持质疑意见的人中有这样一种声音:“女性参与以来,‘撒尔嗬’变得泛娱乐化,其娱乐功能得到突出表现,但原有的教育、凝聚族群等功能却逐渐消解。”细加甄别,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可靠。首先,如果承认“撒尔嗬”确有许多传统的社会功能,而现在存在些许功能消解的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于“撒尔嗬”的商业化变迁,所以这一质疑有“迁怒”于“女性参与”之嫌。其次,学者论及“撒尔嗬”具有肯定人生价值、增强民族凝聚力、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娱乐、健身、交际、教育等多种功能,详加考察易见“撒尔嗬”不专有也不全有这些功能,如增强民族凝聚力更多是丧葬仪式的功能,而不是突出体现在“撒尔嗬”这一仪式程序中。
“撒尔嗬”的举行只存在于正常死亡的老人丧礼中,但丧礼是不分男女老幼的。一般而言,有人死亡自当有丧葬仪式。人生之大苦大悲必有这样一条——白发人送黑发人。诚如前述,这样的场合下当更需要举行“撒尔嗬”以悼亡慰生,发挥其控制生者的情感的功能,但父母尚在的青年人死亡一类的丧礼中却不见跳“撒尔嗬”。由此看来,“撒尔嗬”成为丧葬仪式中可有可无的一环。之所以可以存在于正常死亡的老人丧礼中,是因为当地土家人对老人去世持“顺头路”的豁达生死观,而“撒尔嗬”恰有娱乐的性质,女性参与与否对此都不造成影响。笔者认为,不可完全将“撒尔嗬”与丧葬仪式等同看待。
四、结语
女性突破禁忌参与“撒尔嗬”,不仅体现在“撒尔嗬”的表现形式上,更体现在传统的分类观念、社会权威等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中。通过分析现有对女性参与“撒尔嗬”的争议,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传统文化的审视不应当只关注表层的变,还需要关注内核之未变。研究“撒尔嗬”这一丧葬习俗,不应该离开当地土家丧葬文化乃至整个土家文化。正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述:“不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为土家族传统的丧葬习俗,尤其是丧葬仪式中至为特殊和重要的程序,“撒尔嗬”直接成为土家丧葬仪式的代称,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内有其学术可行性。但我们应注意到,“撒尔嗬”作为独立的文化事项在21世纪已有较多变化,去仪式化的表现形式可以作为典型。所以有必要对“撒尔嗬”与丧葬仪式加以区分,不可简单地将二者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