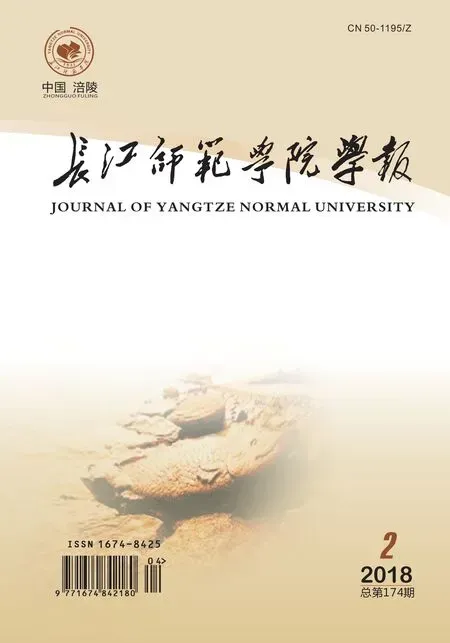羊士谔入蜀及其蜀中诗歌创作研究
李青青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羊士谔,字谏卿,泰山(今山东泰安)人,家洛阳(今属河南)。唐德宗贞元元年进士及第,授义兴尉,顺宗时累至宣歙巡官,因言王叔文政治革新之非,贬汀州宁化县尉。宪宗元和元年擢为监察御史,迁侍御史。后于元和三年至元和十四年徙巴、资、洋、睦四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入为户部郎中。羊士谔在诗歌创作一域颇有风采,《唐才子传》称其“工诗,造妙梁《选》,作皆典重”[1]363。孟简谓之“受气端劲,为文雅拔”[2]6221。《唐诗品》评价“士谔诗气格昂然,不落卑调”[3]1578。此外,《诗人主客图》还将其列为“广大教化”派的入室者之一。士谔诗收入《唐百家诗选》《唐五十家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石仓历代诗选》《全唐诗》等诗集,计存诗101首。
羊士谔一生仕途跌宕起伏,屡次遭贬,四十七岁被贬至蜀,滞留七载,创作了《郡楼怀长安亲友》《书楼怀古》《资中早春》等诗作。经统计,羊士谔现存诗中蜀中诗最多,近50首,几乎占全诗一半。且其笔下的蜀中诗题材广泛,既有咏物写景、登高题壁之作,又有酬答寄怀之篇,这些诗对了解羊士谔的诗歌风格以及其在蜀活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其入蜀后曲折的创作心路。
一、入蜀原因及时间
元和元年,羊士谔自谪地汀州返京,重登朝堂,然而好景不长,其再次卷入政治是非,由此远离朝阙,开始漫长的贬谪生涯。
考《新唐书·李吉甫传》,“吉甫本善窦群、羊士谔、吕温,荐群为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谔侍御史,温知杂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决,群等衔之。俄而吉甫病,医者夜宿其第,群捕医者,劾吉甫交通术士。帝大骇,讯之无状,群等皆贬”[4]4740。再结合《旧唐书》,知元和三年十月,因构陷吉甫一事,宪宗“乃贬群为湖南观察使,羊士谔为资州刺史,温均州刺史”[5]3769。羊士谔存诗《赴资阳经嶓冢山》,诗题下自注元和三年已授此官。则元和三年士谔被贬资州属实。
然而,元和三年羊士谔并未正式知资州。《旧唐书》记载同年与羊士谔一起遭贬的窦群、吕温均因“朝议以所责太轻”而被再贬,虽未见史书记载士谔再贬事,但二贬之罚其理当不能独免。考《建南镇碣记》,士谔“出为巴州刺史……再移资州,如巴之政”[2]6221。又时“巴州为中州,资州为上州”[6]281,是以知其虽被贬为资州刺史,然未到资州,便又再度被贬为巴州刺史。其在巴州担任刺史期间,“持逸群之才略,廖疲人之疾苦,理行居最”[2]6221,恐怕正是因为他关心民瘼,颇有政绩,其后才得以迁为资州刺史。
据《早春对雨》《在郡三年,今秋见白发,聊以书事》等诗,及《宝刻丛编》“巴州”条下所记元和六年羊士谔于石壁题《游西龛》等诗一事[7]446,知元和六年时,羊士谔仍在守巴州。至于其任巴州刺史与资州刺史的分界期,我们考订为元和七年稍后。
羊诗《梁国惠康公主挽歌词二首》。据《新唐书》:“宪宗十八女。梁国惠康公主,始封普宁,帝特爱之。下嫁于季友。元和中,徙永昌,薨。诏追封及谥。”[4]3667《旧唐书》又记载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上书宪宗“永昌公主准礼令起祠堂,请其制度”之事[5]3994。则梁国惠康公主当卒于元和七年或此前不久。羊士谔的挽歌词中诸如“玉殿中参罢,云輧上汉遥”“都人听哀挽,泪尽望寒原”等场景描写似为长安之况,又时人韩愈、窦常等均为公主作有挽诗,羊诗题下有注:“时诏令百官进词。驸马即司空于公之子。”[8]3707其挽歌诗中也明确说到“授册荣天使,陈诗感圣恩”,那么元和七年时,羊士谔等部分官员确实曾奉诏返回长安呈诗哀悼。虽然此年并无史料记载士谔受拔擢之类事,但此次回京极有可能是其仕途的转折点。《宝刻类编》卷四羊士谔条记云“《毗沙门天王赞》,撰并正书,元和九年,资”[9]118,则羊士谔至迟在元和九年便已任资州刺史。据上推断他应是在元和七年或八年由长安返蜀期间被擢升为资州刺史。《建南镇碣记》作于元和十年十月十日,其中记羊士谔“今复为洋州”[2]6221。再据羊诗《彭州萧使君出妓夜宴见送》,该诗所涉的萧使君即萧祐,而祐约元和九年为彭州刺史[10]2979,诗中又充满离别惆怅之意,可能正作于士谔迁升离蜀之际。由这两则材料,可以推知羊士谔是在元和十年左右由资州徙洋州。综上,羊士谔自元和三年十月被贬资州,至元和十年左右升任洋州刺史,其在蜀时间近七年。
二、入蜀路线
据羊士谔为数不多的入蜀纪行诗,可推断其主要沿褒斜道与金牛道入蜀。
《褒城驿池塘玩月》为羊士谔于褒城驿所作。褒城(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位于褒斜道上,褒斜道的开凿历史悠久,是古代巴蜀通秦川的主干道路。又由“夜长秋始半”知作诗时值秋,而元和三年羊士谔被贬正在十月,则此诗极有可能作于诗人由长安赴蜀经褒城之际。
士谔有诗《赴资阳经嶓冢山》,记其赴任资州刺史途经汉水之源——嶓冢山一事。《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兴元府南郑县:“汉水,经县南,去县一百步。禹贡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11]558秦州上邽县(今甘肃天水一带)亦有记载,“嶓冢山,在县西南五十八里。漾水之所出也,东流为汉水”[11]980。说明唐时有两座嶓冢山,且均被传为汉水发源地。时士谔自长安赴资州任,当在赴任期限内到任,若说到秦州绕一圈再入蜀着实不符常理,再则汉中的嶓冢山亦在入蜀的褒斜道上,推断羊士谔所经汉水之源当位于汉中一带。
《暮秋言怀》一诗作于羊士谔任巴州刺史期间,据“丘中只望还”一句,可感其思归长安之心切,而时贬谪官员若无诏令不得返京,则诗中“驰晖三峡水,旅梦百劳关”不过是他对踏上归途的一番憧憬而已,不过这也说明羊士谔入蜀时可能曾途经过诗中所涉地名。百劳关,即百牢关,位于今陕西宁强县境,乃金牛道上的重要关隘,唐时“自京师趣剑南,达淮左,皆由此也”[11]560-561,元和年间元稹入蜀就曾五次途经百牢关。三峡与金牛道相去甚远,且并不位于长安入蜀一带,诗人将三峡水引用在此可能仅为与百牢关作比。
羊士谔自长安赴蜀的大致路线可定,出长安,西南行,经褒斜道,至褒城,抵汉中,再一路南下沿金牛道入蜀。
三、谪蜀诗作及其创作心理
羊士谔在蜀的七年谪贬生涯,创作了不少好诗佳篇。正如《蜀中名胜记》所记:“唐元和中,羊士谔为资州守,风流文采,照耀一时。”[12]128-129其今存的蜀中诗作多属登临题咏、惆怅抒怀之类,情感真挚动人,集中反映了诗人的在蜀生活与心路历程。
(一)“闲似淮阳卧,恭闻乐职吟”——蜀中生活之闲
在蜀期间,羊士谔勤政爱民,以诗歌记录在巴蜀的生活体验。“守土亲巴俗,腰章囗汉仪。春行乐职咏,秋感伴牢词”(《酬礼部崔员外备独永宁里弊居见寄来诗云图书锁尘阁符节守山城》),该诗写出其亲身体验巴地风俗,赋诗吟咏的闲适生活。此外颇能展现巴蜀民俗风光的《上元日紫极宫门观州民然灯张乐》,一句“灯花助春意,舞绶织欢心”将州民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欢庆上元佳节的热闹场面勾画而出。然而即使在这种热闹情境下,诗人仍有一丝抑郁,“唯将圣明化,聊以达飞沉”,从朝堂跌落至偏僻贬所,其内心自然有强烈的落差感,加之时蜀地相对安定融和,士谔政务闲散,致使满怀一腔报国热情的他只能空叹“闲似淮阳卧”。
为了充实生活,排遣心中烦闷,他或于郡斋独坐,寄闲情于书本,聊以慰志;或徜徉于巴山蜀水之间。其有诗“岘首当时为风景,岂将官舍作池笼”(《登郡前山》),诗人感怀羊祜镇守襄阳登岘山事,自述效法先贤之意,颇有一番洒脱之气,但他主要是欲借山水美景忘却贬谪之痛。于是在蜀抑郁不得志的羊士谔,寄情山水,登临咏怀,在发泄内心忧愁的同时,亦留下了不少慨叹歌咏巴蜀人文的诗篇。
(二)“远目穷巴汉,闲情阅古今”——对巴蜀人文的歌咏
居蜀期间,诗人瞩目自然美景,借助诗歌描摹蜀地风光,如“月满自高丘,江通无狭流”即呈现出一幅幽静的蜀丘江月图。在创作这些蜀中景物诗时,羊士谔多用白描,其写景诗之所以出色主要基于他对景物特征的细致把握。“苔斑自天生,玉节垂云长”(《野夫采鞭于东山偶得元者》),诗人仅用寥寥数字便将布满青苔的山径、高入云霄的山峰以及青翠垂云的蜀竹勾勒而出。此外,士谔写景状物诗往往蕴藏遣词用字之妙,“南馆垂杨早,东风细雨频。轻寒消玉斝,幽赏滞朱轮”(《早春对雨》),该诗描写春景,所用的“垂杨”“东风”“细雨”,均为平淡之物,然诗中一“消”字点出早春雨频所致的轻寒噬骨,一“滞”字则从侧面展现出所赏景色惹人陶醉,可谓精妙。又如“柳意笼丹槛,梅香覆锦茵”(《资中早春》),“笼”“覆”将柳条之密、柳叶之绿、梅香之馥郁均展现得淋漓尽致。羊士谔将蜀地美景揽入其诗篇,尽情歌咏当地自然风光。然而作为秉持儒家济世思想的传统文人,诗人被贬居至蜀本就意味着其理想抱负受到严重打击,无处诉说愁闷的他便多将个人不遇之悲等情感寄托在山水景物之中,故而其笔下的写景咏物诗往往意境清幽,含蓄深婉。
诗人在登临游玩之际,对蜀地名胜遗迹与先贤亦有感怀。“何独文翁化,风流与代深。泉云无旧辙,骚雅有遗音”(《书楼怀古》),诗人感慨文翁兴学智蜀的风采,欲效仿文翁作出一番功业。除了感怀蜀地颇有政绩的前人,诗人也对昔日被贬蜀地之人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意。如士谔对自京兆少尹贬为巴州刺史的严武,便作有追怀诗两首,“玉帐空严道,甘棠见野花”(《题郡南山光福寺》)充满对严黄门政绩的景仰。《乾元初,严黄门自京兆少尹贬牧巴郡,以长才》一诗则是诗人在偶得严武当年的“浮杯之地”与赋诗高会犹存的文字后所作,诗歌感怀严武“几醉东山妓,长悬北阙心”的胸怀,从而联想自身正与当年严黄门一样,虽有“盛世当弘济”的胸怀,但却仕途坎坷,只得“无能愧陈力,惆怅拂瑶琴”。羊士谔所作的这些登临怀古之作,均古今作比,寄寓个人身世,抒发对政治失意的感慨或自我激励。
综上可见,在蜀地吟咏山水人文之际,羊士谔压抑不住的思想情感喷薄而出。壮志未酬,思乡怀归,年华易逝,归隐无期,这一系列矛盾复杂的人生体验构成了他在蜀期间的创作心路。
(三)蜀中情怀与创作心路
1.“淹留巫峡梦,惆怅洛阳人”——蜀中思归。诗人大量的抒怀诗歌承载了其思归之情,既有对故乡洛阳的怀念,对亲友的思念,也有对回归长安朝廷的期待。
“西园旧才子,想见洛阳人”(《郡中玩月,寄江南李少尹虞部孟员外三首》其一),“秋风南陌无车马,独上高楼故国情”(《登楼》)无不抒发的是对故土的思念。“愁鬓华簪小,归心社燕前”(《郡楼怀长安亲友》)蕴涵对长安亲友的深切怀念与思归之心,颇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之味。
导致诗人在蜀急切思归的因素颇多:首先是诗人只身在蜀的孤寂,“含情非迟客,悬榻但生尘”(《早春对雨》),其以“悬榻生尘”暗指在蜀久无知音作伴,“暮节独赏心,寒江鸣湍石”“飘荡云海深,相思桂花白”(《九月十日郡楼独酌》)则深刻体现出其独在异乡的寂寞与相思的无奈。其次,羊士谔居蜀期间由壮年迈入知命之年,漫长的迁谪生涯,令他愈发牵挂故土、亲友。另外,传统文人治国施才的抱负也强烈催生着他重返朝堂的欲望,不过也正是基于这种壮志不灭的心态,诗人才在被贬至蜀地后仍不断自我勉励。
2.“东山自有计,蓬鬓莫先秋”——自我勉励。“李白桃红满城郭,马融闲卧望京师”(《山阁闻笛》),东汉马融曾因得罪大将军梁冀而遭诬陷,被免职流放,羊士谔感想自身贬谪之遇,而以马融自况,可见其并不甘于久居蜀地。士谔在蜀早年恪守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在郡三年,今秋见白发,聊以书事》直言“承明那足厌,车服愧无功”,表明他并不嫌弃在朝为官,只是惭愧为官未有功绩,而无功绩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便在于“日日山城守”,好比“淹留岩桂丛”。诗人希望早日回到朝堂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面对政治打击与独在异乡的孤寂,纵然时有抑郁,羊士谔仍不断宽慰勉励自己。如被贬初期所作《酬卢司门晚夏过永宁里弊居林亭见寄》,首联“自叹淮阳卧,谁知去国心”,诗人以淮阳太守汲黯自比,这种自喻在他的诗中十分常见,多借以表达自身离开朝廷后的苦闷无奈。然而该诗尾联却一扫哀叹之风,“风蝉一清暑,应喜脱朝簪”即是诗人的自我安慰,颇具洒脱旷达的名士之风。又如在知巴州期间所作的《郡中端居,有怀袁州王员外使君》以及知资州时所作的《寄黔府窦中丞》,此二首赠答诗分别与同被贬官的王涯、窦群共勉。从诗中可以看出,羊士愕虽遭贬谪,但雄心仍在。“济物阴功在,分忧盛业馀”“满岁归龙阙,良哉伫作歌”不仅是对好友的勉励,更是对自身前途仍然满怀信心和希望的体现。
3.“无功惭岁晚,唯念故山归”——年华易逝与理想幻灭之哀。在数年的怀归与憧憬之中,诗人重返龙阙的期待随着年华渐逝而落空,诸如壮志未酬、哀叹岁月的情感也自然流露于笔端。
“自愧朝衣犹在箧,归来应是白头翁”(《郡斋感物寄长安亲友》),“病起淮阳自有时,秋来未觉长年悲”(《偶题寄独孤使君》),“报国得何力,流年已觉衰”(《燕居》)。这些诗句,字字诉真情,是诗人对年华老去、疾病缠身的哀叹,饱含了其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不得实现的无奈慨叹。
4.“迹似桃源客,身撄竹使符”——出世与入世的平衡。长期贬居蜀地以及知命之年的到来,迫使羊士谔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生,“平生信有意,衰久已忘言”(《山郭风雨朝霁怅然秋思》),正是在年华渐老与理想破灭的人生状态下,羊士谔所秉持的儒家入世思想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并在现实的打压下被逐渐消磨,正如其自叹“壮龄非济物,柔翰误为儒”(《郡斋读经》)。在这种人生理想幻灭而自我勉励徒劳之际,诗人亟需寻得一处心灵栖所。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形成儒释道共同发展的文化格局,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文人尤其迷醉佛道,这在大历诗人的身上便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生活在那动荡的年月,因避地、仕宦、贬滴,漂泊不定,因此诗的主题集中在羁旅、相逢、离别等内容的抒发,他们感叹战乱流离,自伤穷愁潦倒,厌倦宦游漂泊,渴望着归隐田园,过安稳舒适的生活,可迫于生计又下不了决心,内心也常充满矛盾,于是他们放浪山水,寄心佛老,希望在其中忘却时间苦难”[13]25。另外,诸如与羊士谔同时期的白居易、柳宗元、元稹等人的诗作也往往蕴涵佛老思想。可见崇佛慕道风气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已十分普遍,那些遭受政治打击、仕途坎坷的文人士大夫则更会倾向于在佛道中寻求慰藉。为寻求精神解脱,羊士谔流连于山水之余,也开始在推崇心性修养的佛道思想中寻求排解愁闷的方法。《闲斋示一二道者》一诗中,诗人从道家体悟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方可长久之法,从而直言“知止惭先觉,归欤想故侯”,同时亦得出佛家“唯有空门学,相期老一丘”的感悟。通过这些诗,不难发现羊士谔对佛道的学习主要在于对它们出世思想的吸纳与共鸣,“讲义得醍醐”最集中的表现便是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其实羊士谔的隐逸思想在早年就有流露,“早岁尝游女几山,有卜隐之志,勋名相迫,不遂初心”[1]363。官拜监察御史亦有诗云“谁问乌台客,家山忆桂丛”(《和窦吏部雪中寓直》),“幽抱想前躅,冥鸿度南山”(《小园春至偶呈吏部窦郎中》)。但是这些早期的归隐之志是诗人早年尚未受挫时所萌生的,并且他最终选择的仍是追求功名利禄,恐怕彼时稍有标榜清高之嫌。然而士谔在蜀地期间可谓饱尝人生风霜,仕途的打击、老病的折磨、无处可诉的愁闷使得其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激化至顶点,加上佛道思想的调和,与早期相比,此时的诗人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体验,因此其归隐遁世的心愿表现得更为真实强烈。
“南国疑逋客,东山作老夫。登朝非大隐,出谷是真愚”(《守郡累年俄及知命聊以言志》),该诗乃羊士谔五十而作,时已任巴州刺史多年,长期升迁无望。诗人自喻为官似“逋客”,登朝为官也并非真正的“大隐”,只愿学谢安隐居东山,不做那入世愚人。又有《郡中言怀寄西川萧员外》:
功名无力愧勤王,已近终南得草堂。身外尽归天竺偈,腰间唯有会稽章。
何时腊酒逢山客,可惜梅枝亚石床。岁晚我知仙客意,悬心应在白云乡。[8]3711
这首诗历来被认为情真意切,并集中体现了诗人的归隐之志。金圣叹评此诗前两联:“吐口便说‘功名无力’四字,此便是真心实意人,真心实意语也。盖‘功名’虽是每人初心,然‘无力’实是各人天分。如果力有不及,便应愧有不免,如何世上乃有腼颜素餐之夫,又有矫语高尚之夫也。‘已近终南得草堂’妙,言身虽未去,去计已成。”[14]250诗中“天竺偈”为佛教语,“终南”“白云乡”则是道家归隐之地,诗人晚年抱有“仙客意”乃基于其在宦海浮沉中对人生的彻悟,无论是身归禅门亦或隐遁山林,都体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厌倦。
羊士谔愿“用拙怀归去”,然而却“沉痾畏借留”(《晚夏郡中卧疾》),蜀地的百姓还需要他,他想离开官场却又无法舍身而去。这种去或留的矛盾心态基于其秉承的儒家思想与后期所接受的佛道思想之间的对立,解决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成为其在蜀后期着力思考的问题。其中最能表明羊士谔出世与入世观点的便是《资阳郡中咏怀》:
腰章非达士,闭阁是潜夫。匣剑宁求试,笼禽但自拘。
江清牛渚镇,酒熟步兵厨。唯此前贤意,风流似不孤。[8]3708
这首诗作于士谔在蜀后期,他主张既不能太过看重出仕,否则并非达士,同时也不可闭门自居作潜夫,而应向李白、阮籍这些前贤学习,饮酒赋诗,超然旷达,自得一番风流。这无疑反映了作为儒家文士的羊士谔在崇佛尚道的过程中已将儒释道的出世与入世思想有机融合,从而转化为个人的思想体系。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士谔最终选择将向往隐逸的超然出世情怀寄于山水与佛道经典之中,依然继续着他的仕宦生涯,过起了半隐半吏的生活,“迹似桃源客,身撄竹使符”(《郡斋读经》)便是他对自己这种人生状态的最佳诠释。
羊士谔一生抒发不遇之哀的咏怀诗几乎均创作于贬官在蜀期间,壮志难酬、孤独苦闷的心态下,他或寄情山水,或自我慰藉。在蜀七年,他由一开始郁郁不得志的悲伤,到对年老的哀叹,到为政理想幻灭后在山水与佛老思想中寻觅得出世归隐志趣,再到将出世与入世平衡于有机融合的儒释道思想中,羊士谔的思想情怀与蜀中诗创作心理无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真实反映了中唐贬谪文人普遍的创作心理。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刘呴,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中国唐代文学会,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7]陈思.宝刻丛编[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无名氏.宝刻类编[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1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曹学佺.蜀中名胜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3]吴庚舜,董乃斌,乔象钟,等.唐代文学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4]金圣叹.金圣叹全集(四):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等六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