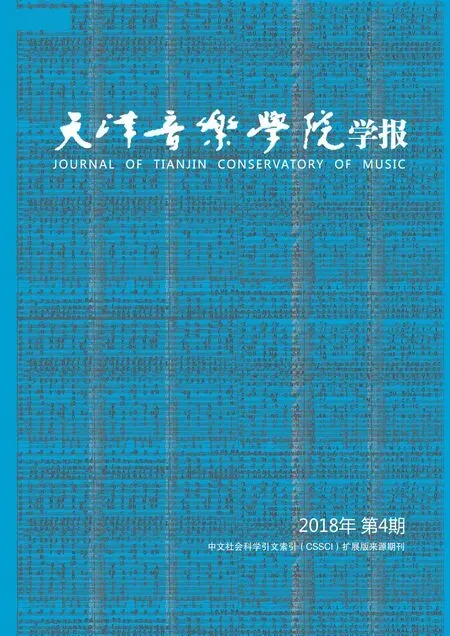《琵琶辞》: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孙志鸿
引 言
“文化自觉”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费孝通提出的世纪文化命题。费先生在1997年发表的《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生动地阐释了这一概念的命题。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它不是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①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1522页。。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对自己60载学术生涯进行“反思”的结果,它体现了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一代学术巨匠对中国文化脉轮的深切洞悉。所谓“一定文化中的人”是指在稳定的母语文化成长起来的知性群体;“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是指要熟稔母语文化:既要了解母语文化的历史,也要明了母语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既能明确母语文化的优势,也要承认母语文化的劣根;既要感受到自己与母语文化的鱼水关系,也要跳出母语文化圈,以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态势,对待他文化形态;既要厘清他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是母语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欠缺的,也要认识到他文化劣根性是什么,哪些是我们要坚决拒斥的东西。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基于文化比较、对话和交流基础上对母语文化所进行的客观评价,包括价值属性、历史渊源与发展趋势等。
作为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增强的中国中青年作曲家的杰出代表,秦文琛的许多成熟作品不但体现了基于对母语文化的高度自觉、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民乐创作进行的成功探索,同时也饱含着这位作曲家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丰富人文情怀、宽广的国际视野以及坚韧的开拓精神。
琵琶独奏曲《琵琶辞》正是这样一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的音乐作品,该作品体现了秦文琛对文化上的中西关系、古今关系、雅俗关系的成熟思考,是作曲家个体文化自觉基础上,东西方两种文化融合与创新,也是作曲家努力构建当代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成功尝试。这个话语体系,可以用作曲家自己的话来解释:“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去看待中国的传统艺术,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孕育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音乐的新的音乐”。①周勤如、郭赟:《与作曲家秦文琛谈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3—18页。
一、《琵琶辞》是基于传统文化基因的融合与创新
《琵琶辞》(Pipa word,2006),由旅居瑞士的琵琶演奏家俞玲玲通过瑞士电台委约②黄暐贸:《秦文琛<琵琶辞>之分析与诠释》,台湾“艺术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6页。俞玲玲,国际著名琵琶演奏家,2016年获瑞士国家音乐大奖提名。,由秦文琛创作于2006年,其初衷是为了回应好友于京君的一部以水为表现内容的作品,以此来表现二人之间的深厚友情③。2008年由青年琵琶演奏家兰维薇首演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该作品的CD由北京京文唱片传播有限公司于2010年发行,乐谱由德国思考斯基音乐出版社(Musikverlag Hans Sikorski)于2012年出版发行。下面是该作品的结构图表:

表1.《琵琶辞》作品结构图表
③ 同上注,第117页。
④ 本文中演奏时间的标记以中央音乐学院兰维薇的演奏版本为准。
⑤ 在该文中,采用字母体系来标记具体音级,即pitch,采用阿拉伯数字来标记抽象音级,即pitch class。
这是一部不仅仅是用耳朵听的,也是可以用内心听的非常“传统”的琵琶独奏作品。作曲家通过提取传统文化基因进行创新性编码,实现传统话语和当代审美相交汇和碰撞。
(一)将传统音乐中以单音作为独立表情单元的思维运用于创作中
该作品A、B、D三个部分的音高材料方面,运用了以四根空弦为基音的21个泛音,音域自b音至g3音。其中不包含八度重复的抽象音级共9个。在这9个音级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D音。如果将D音作为中心音高(不仅因为该音出现的次数多,还因其多出现在重要结构位置上,下面还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其音高组织的排列应该是如下形式:

谱例1.
除了中心音D音之外,其余8个音级分量也各不相同,B音仅次于D,其它如#F、E、#D、#G、#C等音也都属于比较重要的音级。这些音级之间的关系不是体现在其相互进行中,而是体现在结构功能上,形成了类似作曲家自己所说的“等级衍生”①周勤如、郭赟:《与作曲家秦文琛谈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3—18页。(由 D、B 衍生出 E、#F,再由 E、#F 衍生出其它音级)。在该作品中,这些音的选择运用、其音高关系是由四根空弦所产生的自然泛音决定的,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且也多作为单音性结构出现。这些泛音各有品格,从音乐的上下文关系上看,它们也较为独立,它们试图作为平等的一份子参与到音响结构的构建中,相互之间较少形成旋律意义的音的运动,因而不具有确定的调式意义。这是中国传统音乐中重视单音表现思维在该作品中的生动体现。
(二)以虚实相生作为内在音乐发展逻辑
该作品B部分(3'21″—7'03″)为承接段落,在音高方面运用了泛音组、实音组(包含微分音和不确定音高)的交替。首先,A部分的泛音音高材料大部分被保留下来,9个音级只有c音没有出现,且运用泛音与实音段落交替的方式出现,其交替的时间长短不一,较为灵活,形成虚实相生的音响结构。这种虚实相生的音响结构考验着演奏家的演奏技术,是作曲家刻意表现传统文化内涵的体现,对此作曲家曾说:“这些虚实之间就像山水画中跳跃的色彩”②黄暐贸:《秦文琛<琵琶辞>之分析与诠释》,台湾“艺术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9页。。
(三)以音色为结构力的内在时间性流体结构作为整体结构思维
该作品在总体结构上为起承转合式结构模式,③与本文作者结构划分相同的还有崔颖:《秦文琛<琵琶辞>的演奏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在该文中,虽然作者将该曲划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部分,但具体的划分与本文不同。除此之外,作曲家本人也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结构划分方法,即六段、四段加尾声和一气呵成的不分段,详见黄暐贸:《秦文琛<琵琶辞>之分析与诠释》,台湾“艺术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1页。这是一种较早在中国诗歌和音乐实践中被固定下来的结构思维,它与中国大型传统器乐曲中惯用的散慢中快散的结构大致相同,皆以强调渐变、以速度和音色作为统御全曲的主要结构力(该作品中还有一种结构力为音高因素,下面展开论述)。A部分全部为泛音奏法,具有初步呈示的结构意义。B部分泛音与实音交替出现,并加入了1/4音和不确定音高的滑奏,具有承接的结构作用。C部分全部为实音,有不确定音高的大幅度上行滑奏,各部分之间对比鲜明,具有不稳定的展开性。D部分全部为泛音,在音色、速度和音高上具有再现的意义。
(四)以数列思维作为微观结构力要素
该作品中运用的这些数列思维主要源于民间器乐,可以证明作曲家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具有高度智慧的。该作品中最为典型的序列结构有如下三种形式:
1.由“单一变量”构成的递增等差数列。如A部分的终止式,在d2、e2两泛音反复摆动的段落,其间的休止时值即是从1个十六分休止符开始,依次递增至8个十六分休止符。而苏南民间器乐中的“金橄榄”或者“螺丝结顶”则是先递增、后递减的等差序列,二者虽形有不同,但神相似,都是通过数列来形成结构力。
2.由“双重变量”构成的常数列。所谓的双重变量,即数列A和数列B都是以等差数列进行时值变化,只不过一个进行等差递减,另一个则进行等差递增,两个变量的时值总和不变,形成常数列(标为C)。此种数列在苏南民间器乐中也称为“鱼合八”。在C部分第三段(?=146)即有此种手法的运用:首先是琵琶老弦上以挑奏奏出渐强的8个八分音符(变量A),之后转换为扫弦奏出的三音和音,节奏为逆分形式,与A部分开始处遥相呼应,其时值为4个八分音符(变量B),两者时值相加为12个八分音符(常量C)。之后以此数列为原则进行发展,音乐具有粗犷的舞蹈性格。值得注意的是,变量B在以等差数列进行时值递增时,其演奏法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扫弦、不确定音高的上行滑奏等;除此之外,在音高方面,由中心集合(此概念在后文中有详细说明)及其子集的移位变形,结合非中心集合音高的装饰,产生了丰富多变的和声效果。该段数列到达2+10结构时,即转化为更加复杂的数列模式,以推动音乐向着情感的高峰发展。下面是这段常数列的基本参数表:

表2.
由上表可以看出,同样作为变量B,在做等差数列递增的过程中,通过中心集合的衍生,在音高上形成了既保持一定数量的共同音,又增添一定数量的新音级的音高设计,从而将这段音乐扩展至除了f(5)之外的其余11个音级,从中也可以看出作曲家对音高处理的精微和别致。
3.由变量和常量构成的等差数列的混合式。表面上看,这不是真正的数列,但当我们仔细研究其内部规律之后,发现这是作曲家将等差数列各项进行乱序排列的结果,是作曲家对数列思维的灵活运用的体现。如A部分开始,速度标记?=76处、C部分速度标记?=60处,以及C部分的结束处等片段,皆运用了变量和常量组合构成的混合式数列结构,使得这些段落更具有不稳定特性。这些段落都具有连接性结构功能。如在A部分的开始处,变量A(以十六分音符为基本单位)与常量C(1个十六分音符)构成长短不一的弹性节奏组合。在音高方面,变量A是泛音d2和#d2的交替,伴随着由pp到mp的力度变化;常量B为泛音#d2,标记以重音。变量和常量的四次结合分别为8+1、12+1、10+1、6+1,可以看出变量 A 是差数为2的等差数列6、8、10、12的混合排列。除此之外,在C部分段落二和段落三之间的过渡段以及C部分段落三最后导向高潮的片段,分别运用了差数为2和4的等差数列的混合排列,以便在节奏时值上构成更具伸缩性、更有弹性,起过渡和推动作用的结构片段。下面表格是这三个混合式等差数列的具体运用情况:

表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曲家对于数列的运用,其思维是源于民间器乐的,且在具体运用技术上比民间器乐中更为多样和复杂,其结构作用也更为突出,即展开和连接、过渡作用,表明作曲家对传统音乐文化基因的创新性转化和灵活运用。
(五)装饰性的微分音和不确定音高阐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声音
该作品B部分第一段是四条弦依次满轮奏法进入、并由滑奏的微分音加以装饰,后接一段泛音的片段;第二段为B部分的主体段落,以在持续音e音上的快速弹挑,辅以滑奏1/4音的装饰,间或插入泛音片段构成,状如水花,性格活跃;第三段为连接段,以e2、d2音为主,辅以装饰半音或微分音构成。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记谱的初衷是作曲家想回到民间音乐的原生状态,以此获得最真实的民间音乐的符号性声响。
该作品C部分第二段为连接句(?=60),是单音结构思维与数列思维的结合形成的“云式”音块(“它们就像天空中的云块一样,乍一看没有变化,过一会就会发现云块的形状和位置发生了悄悄的变化”①引自陈怡:2018年5月在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跨界与融合——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与分析国际论坛”——《传统与创新》学术讲座上的讲话录音。),也是运用微分音和不确定音高以准确表现民间音乐中奏不齐、唱不准的现象。
(六)以中国传统美学为参照,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丽精神
源自传统音乐的结构思维、音乐生成方式、特定音响逻辑、符号性音色等音乐参数的运用,使这部作品充满了传统文化韵味,成为一部有意味的当代音乐作品。概括的说,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总体结构方面,该作品以线性思维为基础,在起承转合的宏观结构中,通过微观组合的细致音响形成整体音响结构,就像一条条向着大海不停奔流的小溪,最后汇集成波涛壮阔的大河,涌向大海,归于平和和寂静中。
第二,在该作品中,既有境生象外、意境深远、发乎天地、止乎人文的意境与与旨趣,也有“诗言志”的中国文人传统的印痕和生机盎然的生命力量。对此作曲家曾说:“中国古代的艺术家都善于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刘长卿、李贺的诗最能体现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的音乐有写意感,喜欢大块的对比。”①周勤如、郭赟:《与作曲家秦文琛谈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3—18页。
二、《琵琶辞》是基于他文化因素的融合与创新
该作品在对传统文化基因进行编码和创新的同时,也以开阔的胸襟和气魄合理借鉴西方音乐等他文化因素,并将其与母语文化基因有机融合在一起。如通过改变传统定弦获得更多的泛音组合和泛音和声;运用中心集合技术加强乐曲的有机联系和内在统一性;作品中段落的对比较传统乐曲更为强烈,有些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展开性,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乐曲中较为少见的而西方音乐中常见的技术现象,等等。下面择其一、二略论:
(一)关于《琵琶辞》的特殊定弦
特殊定弦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泛音数和中心集合的移位,因而其思维中包含了西方音乐中的泛音列理论以及20世纪的后调性音乐理论的因素,受其精微性和系统化的影响而对泛音音色进行极致开拓的。虽然中国在很早的音乐实践中运用泛音了(如古琴曲《梅花三弄》和《流水》),但显然在该作品中对泛音品质的追求上超越了传统音乐中的两个例证,其最终目的也不相同,倒是与秦文琛另一部民乐重奏作品《阮组曲》之《向远方》中的泛音运用异曲同工。
为什么该作品会采用不同于常规的B—d—e—a定弦呢?有研究者从音色变化或其它的角度进行了解释,②黄暐贸认为这样的定弦“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泛音,采用此种定弦的目的是泛音的组成方式与更丰富的和声”,详见黄暐贸:《秦文琛<琵琶辞>之分析与诠释》,台湾“艺术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而崔颖认为这样的定弦是为了获得二度音程,因为“二度为整首曲子中最重要的结构力量,整首曲目都围绕着大二度、小二度的扩张而成”,详见崔颖:《秦文琛<琵琶辞>的演奏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但是本文作者认为,采用非常规定弦的动因是想获得更多的泛音以及更多的不同弦序演奏同一个泛音的可能性,以增加不同泛音间音的连续性。采用此种定弦所获得的全部泛音见表4,其泛音数比传统定弦多4个,不同弦奏同一泛音的数量比传统定弦多3个。

表4.
除此之外,采用此种定弦还有一个考量,就是最大化的形成中心集合以及其更多的移位形式。在该作品中,如果将B—d—e—a作为中心集合原形的话,分别以和音和旋律型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结构部分,承担着不同的表现功能。除此以外,以中心集合为基础,可以衍生出更多泛音和音组合的可能性,丰富了音响色彩。
(二)以中心集合和双基音高中心形成的高级调性场作为作品的音高结构力
四音列构成的中心集合源于特殊的琵琶定弦,其基本形态为B—d—e—a(标记为T0),由这四个音构成的集合在全曲中具有结构意义,称为中心集合,该集合基数为[0,2,5,7]。四音列以和音与旋律两种形式出现在不同的结构部位,因而具有中心和弦(音)的意义,全曲共出现了8种较为典型的移位的运用,这个四音集合由于其在全曲中的统御作用,因而可以称为中心集合。这些中心集合的原型和移位分布在不同的段落中,其作用和分量也各不相同,有的以和音为主,有的以旋律型为主,有的兼而有之。下面是中心集合及其8个移位的谱例:

谱例2.
双基音分别为B和D音,通过这两个音高在不同结构部位的强调,获得了具有传统主音的中心性意义。其中D音的分量更重,在重要结构位置上出现的次数也更多,如在A段结束之前,通过增盈节奏(主要体现在休止符时值的数列式增长上)的运用,强调了D音的终止作用;在B段第三段落中间部分,大片段的出现了被临音(先是E音,之后变为bE和E音,分布在低声部和高声部)装饰了的D音;在该段的结束处,则在低声部运用了D音作为持续音,并通过不确定音高的轮奏滑奏,接以满轮奏出了g2音,结束该段。C部分第一段落和第二段落之间的连接段,也是结束在高声部的d3音上,接以数列结构段落。在D部分的第一段落结束之后的连接段开始处,也是从D—E两音开始,且尾声也结束于D音。D音的中心性多使通过旋律层面的强调,辅以低声部空弦持续音的运用获得。而B音的中心性多是通过低声部的空弦持续音获得,如C部分中的数列段落。由此可以看出,双基音形成的手法不尽相同。为什么选择D—E两音作为该曲的双基音,恐怕和这首乐曲的写作初衷有关系该曲表现的是作曲家和朋友于京君之间的友情的。
由中心集合构成旋律与和音型等前景性内容,而双基音则具有终止的背景结构意义,二者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结 语
作曲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是其创作个性化、形成作品独特品质的基础条件。少年时期的草原生活,使秦文琛具有了敏锐的对自然和事物的洞察力,而他也往往是以纯净而饱含深情的姿态,仰望着云彩,踏着阳光,远望着伸向天际的草原,倾听着耳边的风声,若隐若现的歌声,牛羊的叫声,响亮的扬鞭声等。以上丰富的生活阅历造就了作曲家欣赏自然、表现天地的独特艺术禀赋。而自1987年开始的国内专业学习的经历使作曲家一步步具备了审视的勇气和力量。1998年留学德国的经历,进一步开拓了作曲家的艺术视野,同时也逐渐明白了坚守母语文化的意义,明白了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和价值,并用不同的声音形式表现着他内心中一个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阐释。对此他曾说:“作为亚洲作曲家我跟他的区别在哪,逼迫你自己思考,你跟他要不一样才是对的”。①黄暐贸:《秦文琛<琵琶辞>之分析与诠释》,台湾“艺术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4页。文中的“他”指的是秦文琛在德国留学时的作曲老师尼古拉斯·胡博(NicholausA.Huber)。
对于秦文琛的音乐创作,作曲家王西麟将其看作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他曾说:“文琛的创作是我国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结晶、艺术结晶和音乐结晶。把他的创作放在我国30年、60年或更早的近百年的历史中来看,作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我们音乐事业的过去、现在、将来,对我国当前的普遍的音乐创作,对往后作曲专业学生的进步,都有着很深远的意义”②王西麟:《从自我中寻找音乐语言的作曲家秦文琛的创作对我们的启迪》,《福建艺术》2011年第5期,第24—28页。。而秦文琛也是当代作曲家中具有历史使命、人文情怀,并沿着这一方向“上下而求索”的新生代作曲家。《琵琶辞》体现了作曲家致力于对当代中国民乐创作的不断求索,从而使当代中国音乐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从血统上看,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内涵源于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所有形态与观念,并有意识、有分寸的取自其他异文化。从影响力上看,她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散发着馥郁的香气,浸润着四野,被他文化所尊重、欣赏、感动、接受。从品格上看,她充盈着丰富的人文情怀,将人置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③出自《孟子》·《尽心上》。,追求着三者的协和并最终归于一体。这就是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融合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