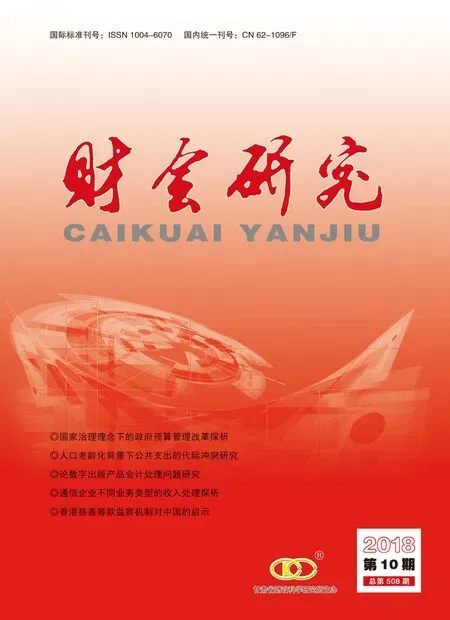税收遵从的社会成本形成机制及对策分析
■/陶蕾花 袁奋强
一、研究回顾
对税收遵从的研究最早始于美国国内收入署对纳税人遵从度的评估项目,而对税收遵从度的理论研究,A llingham和Sandmo(1972)通过运用个人所得税偷逃税行为的A—S模型,探讨了纳税遵从的度量问题。此后,众多学者对税收遵从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当前我国学者对税收遵从理论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制度、心理、法律等不同层面来探讨纳税遵从度问题。除了高培勇(2000),王玮(2008)等学者外,鲜有学者以征税人、纳税人和用税人为研究对象,更少有学者统筹考虑上述“三人”共同博弈下的公共收益损失,本文将其定义为社会成本效应(下同)。
二、税收遵从的基本概念明晰
当前,税收遵从的研究主要是以纳税人为研究对象,从税收征管的角度对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进行了研究,也就是对纳税人的“纳税遵从”的研究。所谓的“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要求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主要包括客观税收遵从度和主观税收遵从度两个方面。客观税收遵从度是以纳税人应纳税额与纳税人自愿及时申报缴纳税款的差额为衡量标准;主观税收遵从度则是:“在现行税法框架下,纳税人对税法遵从的自愿性和倾向性程度,或者说是对一国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等的心理认同程度。”(安体富,王海勇,2000)。那么,我国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究竟如何呢?刘振彪(2010)通过对广东、浙江、北京、吉林、湖南、贵州6省市的纳税人和纳税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税制的复杂性、征纳双方间信息传递、税率、税收征管以及纳税人的社会公平感等诸多因素均会影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同时,其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税收遵从度很低,税收不遵从造成的税收流失问题比较严重,税收流失率在进入21世纪后均超过了20%。
实际上,上述关于纳税人税收遵从度要涉及“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三个行为主体。其中“纳税人”是税收遵从的核心,“征税人”和“用税人”是“纳税人”是税收遵从的相关行为影响人。“征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是指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主体,其在税收征管中按照税收法律履行相关职责程度。同时,与“征税人”相对应的是“征税人”行为意识下的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所以,“征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相关的税收政策遵循程度下,“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另一方面是税务机关对相关的税收政策遵循程度。当前,虽然我国税务机关的税收遵从度相较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延压税款、有税不征、借税买税、中饱私囊等问题屡见不鲜。“用税人”则是指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公共事务的法人单位、法人或个人。与此相对应的税收遵从是指“用税人”为完成公共服务和事务经批准使用税款的行为。同样,“用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用税人”在完成一定公共服务水平的预算支出遵循程度下,“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另一方面是履行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和人,在相应的公共服务水平下,对预算支出的遵循程度。
三、“三人”动态博弈关系下社会成本分析
“纳税人”作为税收遵从行为关系中的基本主体,其行为方式既要受“征税人”和“用税人”行为影响,而且也受自身主体行为习惯或道德素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纳税人”自身主体行为所导致的税收遵从行为差异,又可以分为客观性税收遵从度和主观性税收遵从度差异。客观性税收遵从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程序性”不遵从和“无知性”不遵从所造成的成本。假设这种税收遵从度的差异成本为A,那么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损失同样为A。主观性税收遵从成本是指由于“纳税人”自利动机所引发的税收遵从成本。假设这种税收遵从度的差异成本为B,那么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损失则为B。“纳税人”的这种主客观税收遵从度必然要受税务机关的评价与监管。“征税人”由于完全评价和监管“纳税人”税收遵从度所引发的成本为C,但这种监管成本过高,其适用性不高。在“征税人”的实际监管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稀释,其监管成本则为ψC,其中:0<ψ<1。而“征税人”的监管效应是通过对“纳税人”税收不遵从情况进行处罚,惩罚收入为PR,P为发现概率,R为惩罚程度。“纳税人”税收不遵从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为A+ΓB,其中:Γ为税收遵从度的加强系数,0<Γ<1。
在“征税人”作为非自利人的前提条件下,“纳税人”税收遵从度差异下的社会成本要受“征税人”监管强度的影响,由其所引致“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的差异为A+ΩB,其中:Ω为税收遵从度的加强系数,0<Ω<1,且Ω=F(ψ),Ω的一阶导数是大于零。此时的社会成本损失:A+ΩB+ΓB+ψC-PR。
但是“纳税人”和“征税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其都具有趋利的本性。“纳税人”往往会进行寻租,“征税人”则易于与“纳税人”形成合谋。这种合谋在外部完全无监管的情况下,由二者所引致的社会成本损失为SC。但是,“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合谋行为必然要受到外部规制,假如外部完全监管的情况下,监管成本为JC,合谋成本为SC=0。当监管减弱时,监管成本为ΠJC,0<Π<1,则合谋成本就变为:∂SC,0<∂<1,且∂=F(Π),∂的一阶导数是大于零。此时的社会成本损失:A+ΩB+ΓB+ψC-PR+ΠJC+∂SC。
同时,“纳税人”和“征税人”都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社会的影响。从税收遵从的视角来看,“用税人”的用税情况必然会对“纳税人”的纳税遵从行为和“征税人”征税遵从行为产生影响。当“用税人”能够恰当使用税收,使税收能够真正运用到公共社会管理和福利中,提高了“纳税人”的纳税幸福感和“征税人”的征税成就感。但是,当“用税人”不能够恰当使用税收时,就会挫败“纳税人”和“征税人”内心满足感,使“纳税人”的主观税收不遵从感增加,使“征税人”和“纳税人”的合谋倾向更加严重。所以,在增加“用税人”用税效用的假设情况下,“纳税人”的主观性税收遵从成本就变为θ(Ω+Γ)B,那么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损失则为θ(Ω+Γ)B,其中:θ为“纳税人”的主观税收不遵从加强系数,同时θ>1。“征税人”和“纳税人”的合谋成本为β∂SC,其中:θ为合谋下的税收不遵从加强系数,同时β>1。此时的社会成本损失:F()=A+θ(Ω+Γ)B+ψC-PR+ΠJC+β∂SC。
在“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三个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和博弈关系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是实务界和理论界追求的目标。根据上文函数公式F()=A+θ(Ω+Γ)B+ψC-PR+ΠJC+β∂SC可知,我们可以通过二次线性规划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求解。
四、对策建议
根据上文对“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动态博弈关系下社会成本分析结果来看,纳税人的主客观税收遵从度、纳税人与征税人合谋下的税收遵从度、以及“用税人”在适度用税的背景下,纳税人的主观税收遵从度、纳税人与征税人合谋下的税收遵从度的变化都会对社会成本形成影响。如何降低这种税收遵从度对社会成本的放大作用,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根据函数F()=A+θ(Ω+Γ)B+ψC-PR+ΠJC+β∂SC的分析,提出如下的建议来加强“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的税收遵从度,进而降低由此引发的社会成本。
首先,由于客观性税收遵从成本主要是指“程序性”不遵从和“无知性”不遵从所造成的成本,而这种不遵从性并非是个人道德素养、行为习惯所引起的税收不遵从,而是个人对税收知识欠缺所造成的税收遵从度的降低。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损失进行控制。一方面要加强税收知识的普及以及后续教育,切实落实税收政策的再学习。另一方面要提高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知识水平,改善相关职业人员的知识层次和知识结构。
其次,在没有“纳税人”和“征税人”合谋的情形下,“纳税人”主观性税收遵从度所引起的社会成本为ΩB+ΓB+ψC-PR。但是,二者都具有自利性的倾向,二者的合谋是现实存在的。所以,除了加强对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情况监管外,还应该加强对“征税人”的监管,加强“征税人”个人素质修养的提高。只有不断的学习、教育,才能有效避免或者降低“征税人”和“纳税人”合谋条约的达成,进而能够降低“纳税人”主观性税收不遵从度所导致社会成本。
最后,通过对三方纳税遵从度的博弈分析可以发现,“用税人”的用税情况必然会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税收遵从度产生影响。“用税人”作为“纳税人”和“征税人”相互发生作用的基础,诚信、廉洁、高效的用税情况对于推进“征税人”的征税遵从度和“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和完善制度化、程序化、高效化的用税环境是推进税收遵从度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