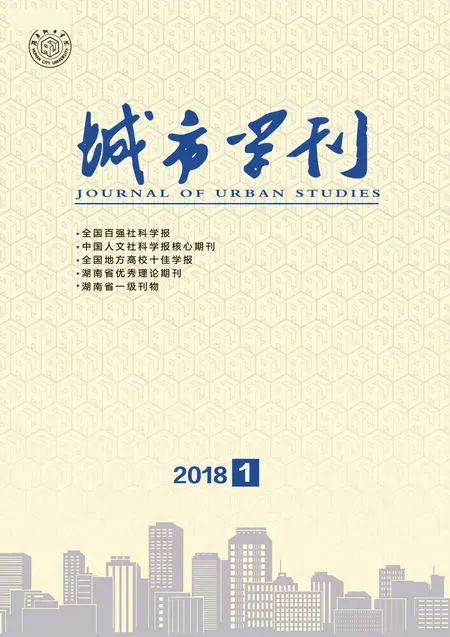图书漂流的开放性与新媒介时代的全民阅读
谭军武
(湖南大学 文学院 / 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长沙 410082)
一
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3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全民阅读列为“十三五”时期的文化重大工程之一,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为此,国家广电总局于2016年末颁布了《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要“不断提升全民阅读的质量和水平”,在十三五期间“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局面”。而“全民阅读深入开展、取得实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民既有参与感,又有获得感。”这意味着,经过十几年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在文化基础设施和前导“书香”观念完成了整体构建与布局之后,全民阅读的开展将要从客观条件的改造和阅读环境的营造,转向主体阅读意识的培养和内在文化素质的提升。《规划》指出,“开展全民阅读,每个人既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明确强调了阅读活动中读者主体性的丰富展开。读者从一个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变成了具有行动力量的知识传播者。这就打破了过去“自给自足”的阅读形态,意味着阅读方式的根本转变。全民阅读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全社会的文明水平。它的终极价值指向的是人,而非书。由书到人的支点转移,决定了全民阅读推广的重心摆脱了书的“可得性”,落到了人的“获得感”上。如果说过去全民阅读推广的主要成就在于解决了“读什么”的客观问题,那么下一步推广的目标则聚焦在“读到了什么”这个主体性的命题上。“全民参与,共建共享”,也应该从较低层次的物质性(图书和阅读场地等)互助,提升到知识传递和思想分享层面来。全民阅读的“参与感”,切不可沦为志愿奉献的道德快感,它是读者投入到以书为舞台的文化嘉年华中所获得的精神快乐。参与感的体验深度,决定了获得感的文化力度。
当前,全民阅读的“参与感”大多由国家主导、计划安排、免费配送,通常在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等公共机构的支持下,对阅读资源进行“运动式”聚集,营造读书节日的浓厚氛围、推出公益性的读书活动来实现。运动一来,熙熙攘攘;运动一走,冷冷清清。每年的四五月份,全国各地都会举办以“书香”为名的阅读推广活动,组织规模和媒体宣传奢华不减,但民众的参与感却并未如愿获得饱满升级。相反,缺乏连续性和自主性的阅读“快闪”,刺激了民众阅读参与的条件反射,在全民哄闹的图书聚会中,许多人各怀所求,竟至于伪装“参与”,而实质上不过是为配合活动现场嘉宾表演的“行为艺术”。这种日渐脱离阅读主体的任务式推广,造成了大量的无效参与;参与感打折,自然难以有效“获得”。与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主导的阅读活动不同,近年来各地由民间机构和学术组织倡导并推动的高端阅读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主动参与。它们选题独特、思想开放,善于抓住社会热点和文化动向,具有开创性与引领性,受邀嘉宾动辄成功人士、学术明星,自带强大号召力,因此颇受年青人的欢迎。但这些活动常囿于场地空间的限制与延展话题的深度,对参与人数和听众素养,有较为苛刻的要求,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私人定制的小型“家宴”,或者朋友圈相聚的文化沙龙,与全民阅读提倡的“全民”参与感相去甚远。加之这类活动有主讲嘉宾坐镇,话语表达的机会和权重并不平等,知识信息的传播依旧固守“一对多”的模式,致使读者参与的深度大打折扣,主动性受挫。另外,出版机构作为推广阅读的中坚力量,经常活跃于各大阅读活动现场。围绕热点出版物而展开的系列推广活动,虽然兼顾了公益性,但由于其初衷和目的常常是通过调动读者热情来激发市场,以创造高价值的商业回报,往往在推动过程中陷入资本的饕餮,阅读推广效果适得其反。2016年末上演的地铁“丢书大作战”,巧妙利用了全民阅读来“背书”,其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和强烈的营销色彩,引发了广泛争议,被吐槽是一次成功的商业炒作。[1]如此看来,全民阅读参与感和获得感指数的提升,并非易事。用心良苦、五彩缤纷的公益活动,装饰了社会的文化空间,却未必走入了读者的心灵;而大量同质重复的类型化阅读推广,主事者竭尽心力,民众反倒不买账,两生龃龉,费力不讨好。
毫无疑问,倡导“书香中国”,不是要引领现代民众复古到传统的门第秩序中去;全民阅读,也绝非出于对“万般皆下品”的陈陋偏见。阅读是时代主体自我身份建构的文化展开,也是思想情感与知识观念的历史性沉淀。全民阅读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是阅读主体的自我成长与建构特性的体现。以文化资源的等级化分配和垄断独占为基础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早已不适应当代社会主体的发展需要。静坐玄冥、孤独自省、封闭自律的阅读者形象,也与巨变了的文化语境格格不入,更不适应全民阅读的伦理要求。在一个马克·波斯特所言的“第二媒介时代”,人们渴求“一种的双向的去中心的交流。”[2]22富有互文特征的新电子媒介语境,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根本上带来了“身份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为广泛而全面的变化……电子媒介在促成一种同样深刻的文化身份转型。”[2]34如果说现代启蒙所强化的个体是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和稳定的,那么,“第二媒介时代中的主体建构是通过互动性这一机制发生的。”[2]45阅读作为主体精神建构的力量,正伴随着当代主体的自觉而不断深入展开,并且内化为当代人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要在“双向去中心”的时代语境里,促进阅读主体的深度参与,并将这种参与转换为文化获得,我们需要同时解放主体与客体、人与书在阅读过程中的封闭性,破除由书(经典之作)和人(知识精英)形成的权威结构,真正敞开阅读的文化空间,激发民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如此看来,深入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尚需转变思路,不断探索新方法。
从知识形态上来看,媒介的大数据和互文结构,颠覆了“百科全书式”的权威叙述,带来了“互动百科式”的知识表达。图书漂流,秉承“分享、信任、传播”的朴素理念,“倡导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开放的阅读方式”,[3]将图书从巍峨庄严的图书馆和个人藏书室解放出来,把个人阅读的孤独世界打开,以书为媒,不设防,不设限,既与他人共享书中的知识和智慧,也与人分享自己阅读的悲欢喜乐,为庋藏的图书重新注入情感的温度和生活经验。“它打破了阅读空间的限制,使人们不论在任何时候、地点都能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同时它区别于政府的有组织的阅读行为,是一种自发进行的活动,更能促使人们积极阅读,将全民阅读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营造阅读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3]图书漂流真正体现了“双向去中心”的知识传播形态,也应和了当代社会主体内在的心理需求,贴近“第二媒介”语境下的某些社群特质,能够激发新一代读者的阅读参与,重建网络世界的阅读精神。
图书漂流具有时尚的气质。自由,率性,毫无拘束,不设规范,有广场文化酣畅淋漓的恣肆狂放,却又不失思想的优雅与趣味的格调,赋予阅读超越一般大众文化娱乐的精神品味。它还带有些许理想主义,充满冒险与传奇色彩,又富有浪漫情怀。每次图书漂流,犹如一场说走就走的知识旅行,既是与书的相遇,也是与其他旅人的邂逅,真正有“诗与远方”的落拓不羁。没有终点的阅读旅程,激起人们对未知的无限好奇和浪漫幻想。“对未知的生产……对第二媒介时代中的传播很重要。”[2]52图书漂流从一个未知走向另一个未知,在互文游戏中激发读者的创造,始终维持着整个社会阅读过程的张力。这种阅读参与是热诚而饱满的,它召唤了当代人内心真实的情感渴望和生命体验。总之,图书漂流打破了以中心(不管是书还是人)为支点的被动阅读形态,解放了阅读的主体与客体限制,舒缓了权威(中心)与读者的知识等差所形成的阅读心理压力,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在一个敞开的公共阅读过程中,以社交式的阅读分享和广场式的知识交流,丰富了主体的获得感,实现阅读的全民共建共享。
二
图书漂流的阅读方式,自2004年引入我国,就因其全然不同于传统的阅读观念和时尚新颖的传播特点,受到读者的欢迎。[4]公共机构和出版部门也有效利用图书漂流的“民意”,组织形式各样的漂流活动,与全民阅读推广相互融合,得到了广泛认可。[5]甚至有人提出要实施全民图书漂流工程,搭建全民阅读网站平台,以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建设、全民收益目标。但总体来看,图书漂流对全民阅读推广的贡献率并不太理想,热闹了面子,抽空了里子。许多活动常常是虎头蛇尾,后劲不足,最终成了“烂尾工程”;有的是情怀满满,高开低走,终了不过变成新闻材料。究其原因,不一而足,但最根本的,是对图书漂流属性的理解过于简单、陈旧。众多论者多是从图书馆学的公共性角度,挖掘图书漂流的积极动能,肯定其在信息共享、图书管理机制创新,以及促进阅读和保障读者权利等方面的作用, 却未能考量当代媒介语境对阅读机制和读者行为的深刻影响,导致观念上存在着误区。因此,要真正组织好图书漂流活动,发挥其在深入推广全民阅读工作中的效能和价值,就必须从理论上澄清两个基本问题。
(一)作为图书漂流的主体,应该是动态、多元、自由、开放的人
这意味着,漂流阅读的主体既无空间限制,也不受身份职业的束缚,打破过去阅读的社会性区隔,释放每个主体的自由潜能。主体的流动性,才能保证图书漂流不至于落入到画地为牢的圈子主义或自设畛域的户外图书馆模式。漂流不能做成专题读书会的扩展板,更不能成为图书馆的附庸,尤其要避免沦为出版机构的市场工具。我们发现,以往的图书漂流活动,组织者总是作为强势权威、目标明确的主事者,掌控着整个进程,它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阅读过程的监管者,实际上就把开放的漂流又强行扳到了封闭的轨道上。主事机构管得过多过严,就挫伤了读者的参与积极性;目标诉求单一明确,也阻滞了民众对漂流阅读的介入深度。图书漂流的参与者像被人架着往前推,身不由己,自然就会看热闹一般,曲终人散,人走茶凉。主体的固化、中心化,有悖于开放交互的漂流原则,也破坏了图书漂流的阅读本性。
另一面,作为图书漂流的主体,不仅是活动的主导者、推动者与管理者主体,它首先是图书的阅读者与消费者。而当下图书漂流的组织者,常常以公共利益的承担者角色登台,只管把书送出去,却从不参与阅读和消费。它通常是图书的提供者、发送者和监管者,但唯独不是图书的阅读者、消费者。不管公共图书馆,还是出版机构,抑或是大学、社会团体与组织,他们主导了图书漂流的启动工作,但往往无法以书为媒与读者建立平等关系。毋宁说,我们的图书漂流是一场等级化的、不平等的图书击鼓传花活动。我们的公共组织是游离在图书漂流核心结构之外的,他们更多扮演漂流的技术维护者而不是知识与情感的传播者,这导致组织者与阅读者在价值诉求和阅读目标上的严重脱节。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常被诟病的图书“回漂率”问题,组织者在管理方式上的煞费苦心,就反映出根深蒂固以我为主的权威意识。国内图书漂流大多在固定地点设立漂流站,以便于图书的回收和中转,提高管理的效率。且不说这种管理手段有很强的空间局限性,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也与图书漂流的宗旨相背而行。用漂流站来架设监管网络的做法,实际上给读者设立了一个“心理图书馆”,构成了对漂流自由的威胁。甚至有论者主张,“高校图书馆是高校图书漂流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图书拥有者,拥有正在漂流图书的物权,可以回收图书或随时中断漂流过程。”[6]这无疑与图书漂流的精神背道而驰,已经远离了这一阅读形式的本质。图书漂流的价值核心在人,而非书。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图书漂流网站Bookcrossing,在自我说明中开宗明义提出,图书漂流“目的就在于通过书将人联系起来”(aim to connect people through books),书是媒介,人才是根本。不能把图书漂流视为一场图书的守恒运动,执念于如何把流出去的书能量守恒地漂回来。如何更好的解决图书“回漂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需要探讨。不能因现实的困境而毁灭图书漂流的自由精神,进而扼杀了民众阅读的真正参与感,这是理论认识上需要解决的。更何况,现在可以利用网络媒介技术进行社交式互动跟踪,解决图书漂流过程的轨迹标注,Bookcrossing就巧妙地实现了“以书聚人”的目标,也比较好地解决了回漂率的问题。
总之,图书漂流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全民阅读沙龙,漂流图书的主体既是图书的提供者、管理者和传播者,更是它的消费者。他不但阅读和传递知识信息,还要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参与到思想和知识的生产中去。这是一个所有人自我主体化和对象化(作为他人图书漂流对象的他者)的过程,而不是从中心出发又回归中心的循环运动。因此需要建立一种“自组织”的社群关系,[5]而不是围绕某个权威中心的价值目标来决定阅读的走向与轨迹。当然,我们也希望具有自组织能力的阅读者能够以知识共享为快乐,克服“藏而不用”的书香观念,抛弃“窃书不能算偷”的道德诡计,真正成为阅读社会的合格公民。
(二)作为漂流的客体,图书在整个漂流过程中,应该是具有成长性的公共资源
图书的成长性,一方面是指漂流的图书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应通过书来召唤书,挖掘图书自在的生长性,依靠知识的力量激发民众的阅读参与热情,推高读者的公共意识和互助精神,让漂流成为纳百川聚大海奔流不息的生命体。这是图书作为“物”的成长性,是漂流链条和阅读网络“物”的增长。基于此种观念,我们就无须始终忧虑投放图书的数量,也不要固执地守着回漂率指数喟叹。要保证漂流图书的成长性,与其殚精竭虑地向公共机构“派捐”,不如热情洋溢地向民间读者“众筹”。只要民众热度参与,图书漂流就能将全社会“变成一个流动图书馆”。由图书漂流引发的连绵阅读,必能成为“切实促进全民阅读的有力手段。”[7]
图书成长性的另一层内涵,意味着围绕图书展开的阅读行动,不但传播书中既有的知识内容和思想信息,它还将携带读者独特的个人体验、文化思考与情感温度,绵延接力,不断积累沉淀,增长丰富。这些内容,伴随阅读链条的延伸,不断丰富图书的知识信息,保持文化的活力。同时,读者的阅读思考与情感体验,融汇了个人的生命感悟与时代的文化精神,构成了对图书意义与价值的历史性阐释,为图书注入了新的时代性内涵,扩大了书籍的思想边界,凝聚了多元的情感蕴藉。读者不仅是历史智慧和经典思想的搬运工,而且是图书内容和文化信息的生产者,漂流图书的内容不断得到增殖。所有人都可以在漫长而自由的阅读旅程中,既与文化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又可以舒缓轻松地聆听当代邻居们的喜怒哀乐,阅读的至乐,就在参与过程之中,纷至沓来。
由此就引出一个与推广阅读相关的问题:放漂图书时,如何确定它们能成为具有成长性的图书呢?图书的可读性、思想性、时代性以及漂流目标读者的定位等,都是影响漂流图书成长性的技术指标。但关键之处在于,漂流图书的选择要秉持公共性原则。我们应该遵循开放、自由、自主参与的原则,以公共性为导向,服务于广大民众,避免把图书漂流变成功利追求的注脚——不管这功利是商业性的还是政绩性的。“图书漂流使个人书籍不再是藏书架上的固定资产,而是被赋予了明确的公共性,书籍的内在价值也因为被重复利用而得以充分实现。”[8]图书漂流的公共性,主要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实现了知识的全民化共享。分享知识与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特征。当那些能够为大众广泛共享的知识得到传播时,它往往能成为一时的文化兴奋点,形成全民对知识的热情追捧,激起参与的热情。但知识分享不是平铺直叙的等价交换或民主贸易,它是一个知识激荡和创造的过程。正因如此,图书漂流的公共意义,其实要远大于我们现在组织的各种漂流活动所预设的追求。一旦漂流图书变成某个特定主体能够配置的资源,“知识”在整个过程中就容易被利用,成为营销的情怀或文化的噱头。功利驱使,容易把知识公共性让渡给喧哗热闹的文化真人秀,读者被过度消费,易生拒斥,参与感与获得感就无从谈起了。图书漂流不是出版社做的慈善施舍,更不是商业机构操弄的高端行为艺术,他应该类似于全民参与的知识众筹。人人皆能以己之力,置身其中,有一种主体自觉感和自豪感。人人得而奉献,才能保持漂流永恒的动力。阅读分享和知识共建,不同于其他的社会活动,它以主体精神的丰富和涵养的增长作为回报,不断召唤所有人的奉献精神。既然是全民参与的众筹,我们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大众狂欢的假面舞会,而不是一场高端奢华的鸡尾酒会。只有如此,图书漂流才能成为促进全民阅读的利器。
总而言之,图书漂流(bookcrossing)重新建构了书与人的社会关系,符合多元异质、开放互动的媒介传播需要,也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体身份建构的文化要求,非常切合全民阅读的现代理念。阅读从书斋走向日常生活,从令人敬畏的图书馆走向车站广场,进一步置入了读者的生命体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持续性和成长性的主体建构过程,参与即获得,只有参与才有获得,人与书的关系在新的层面上得到解放。通过图书漂流,全民阅读被逐渐全方位推广,推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融汇到个体触手可及的亲切体验中,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乃是阅读广度与深度的提升,更是参与感与获得感的真正落地。
参考文献:
[1] 潘文. 地铁“丢书大作战”:是情怀还是营销[N]. 新闻晨报,2016-11- 18(A3)
[2]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范静哗,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 郭芹, 罗燕. 我国图书漂流活动的现状及发展策略探析[J].新世纪图书馆, 2011(9): 55-58.
[4] 刘颖, 董红霞. 图书漂流再思考[J]. 图书馆学刊, 2012(3):76-78.
[5] 郭丽梅. 图书漂流可持续发展与自组织管理机制探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4(1): 16-19.
[6] 马志杰. 高校图书馆“图书漂流”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3(5): 50-53.
[7] 罗爱静, 崔巧灵. 另辟蹊径的阅读方式[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2): 22-25.
[8] 刘秀平. 图书漂流与流动图书馆之比较与启示[J]. 山东图书馆季刊, 2008(2): 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