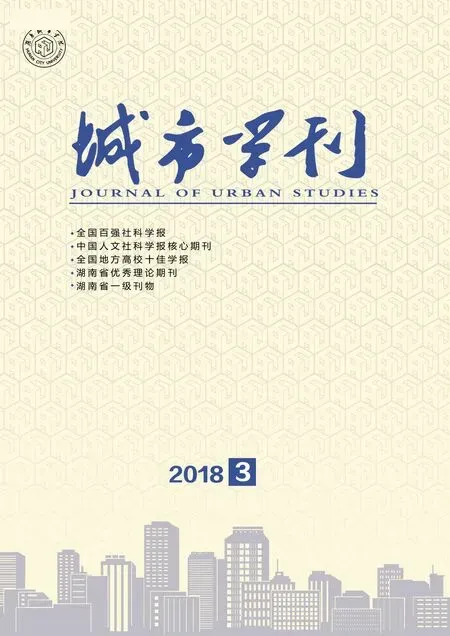论国学经典外译者应具备的素养
姚力之
论国学经典外译者应具备的素养
姚力之
(湖南城市学院 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由于我国传统国学经典常常是文有限而意无穷,集文学、哲学、音乐、逻辑、历史等要素于一身,这对国学外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优秀的国学外译者应当具备以下素质:对翻译的本质和机制有足够的认识;具备双语能力和深厚的国学基础;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涉猎的知识既要专又要博;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文化强国;国学经典;外译;外译者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习总书记强调,要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助力新时期文化建设,将中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他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8年5月2号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和北大的师生交谈时说: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扬全世界。
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明显提升,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要想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增强文化软实力。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没有翻译家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前外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曾说:“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翻译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
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思想、艺术的重要载体,是凝聚之学,是兼容之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国学经典外译。国学经典外译的目的,一是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到国外去,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二是要在文化传播中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国学外译者要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翻译既要保留国学经典的形,又要传达出其内在的神。因此,国学外译者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那么,国学外译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一、 认清翻译的本质和机制
通常意义上,按照翻译的形式和场合等,翻译分为同声传译(口译)、文本翻译等类型,国学经典外译属于文本翻译的范畴,同时,它也是文本翻译中独树一帜的一支。翻译学家雅可布逊将语际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1]国学经典外译某种意义上就是将以汉语语言符号为主要呈现形式的国学经典转换成外语语言符号,以达到文化传播的效果。但这一翻译过程又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换。源语向目标语的转换实际上是对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再编码,从形式到内涵都要完美地表达,不能有所遗漏或歧误。国学经典著作大多年代久远,主要以文言形式写就,即使是当代中国人也或多或少存在经典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这就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国学经典外译的难度,形译难,意译更难,兼顾形式与意义的翻译更是难上加难,国学经典外译者应对这项工作的重点、难点有清醒的认识。认识上的不足“不仅遮蔽了中华文化的神采而且造成了极大的误解乃至危害”。[2]翻译界有些通用的准则,有些在国学经典翻译中也是适用的,比如最基本的“信、达、雅”,但基于国学经典本身的独特性,有些常用的翻译准则就可能不那么适用了,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做些调整,比如直译的运用,国学经典言简义丰,多隐喻、典故等,直译很难传神。这需要译者对文本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内涵做深入透彻的理解,兼顾“音”“形”“义”三方面,做到直译尽其可能,意译按其所需,最大程度再现原文信息的同时又兼顾形式美,让译作和原文之间尽量语义相等、文体相谐、语效相当。
二、 具备双语能力和深厚的国学基础
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迁移活动,其作用在于将原语中体现的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3]翻译首先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这里面包含了两个语言向度,即源语与目标语,要想实现国学经典外译,译者不仅要精通汉语,还应具备较高的目标语语言水平。对源语与目标语的熟练掌握,是沟通中外,建立翻译之桥的基辅钢架材料。
基于此,我们说国学外译者应当重视双向语言能力的培养。这种双语能力,首先指语言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学习,就汉语而言,外译者应掌握尽量多的汉语字词、成语、谚语、歇后语等,还要学习汉语语法、句法结构,同样,外译者对目标语的这些基础语言知识也应熟练掌握。由于国学经典的一些字词现在并不常用,一些语法、句法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国学经典一些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其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可能会造成一些理解和翻译上的困难,简单根据字面意思翻译,读者很难读懂,而且容易出现谬误。这就需要外译者多学习、攻关和积累,只有把这些基础知识掌握好了,才有可能在翻译过程中把准脉、找对路,精准地找到目标语中与源语相对应的字词,同时又不出现因为“中式外语”等语言形式问题而造成目标语国家人民的阅读障碍。语言基础知识不牢导致的翻译“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如王宝童就曾将《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翻译为“And,Rong,only four,Picked the smallest pear,To leave his elders,The lion’ s share.”其中“The lion’ s share”出自《伊索寓言》,讲的是狮子霸道、贪婪,用于此处完全是歪曲原文,前后文语义不通,还容易引起误解。[4]双语能力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这里面还包含了内在的文化因子的熟识度,这种对语言内在文化因子的熟识度一方面关系到译者对源语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与目标语的“对等”翻译密切相关,这方面的能力不足就可能导致上文例子中那种形似而神非的错误。
三、 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
翻译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有专业知识的学科,它有自己的一套专业技术理论,这是翻译者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知识。只有拥有专业理论的指导和专业技术的支撑,才可能产出专业的翻译作品。这就好比插花艺术,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作指导,胡乱摆弄,费时费力,做出来的作品凌乱而不美观,有时甚至插花作品还不如一朵自然状态的野花更具美感。国学经典外译尤其是一项考验专业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工作,面对卷帙浩繁、晦涩难懂的古文经典,没有专业翻译理论的指导和翻译方式方法的帮助,要完成译介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翻译中涉及的翻译原则、技巧、方式方法等有很多,而且不同历史时期中外翻译学者所运用的翻译方法、技巧等丰富多样,要系统罗列整理,工作量极大。这里,笔者仅就国学经典外译这一研究主体对外译者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做针对性的论述。
国学经典外译人才应具备术语学知识和术语翻译能力,具备有效解决国学经典翻译过程中的术语问题的知识与技能系统。国学经典作为千百年来思想、文化、艺术等的典范,许多精简的表达逐渐成为一种范式,作为术语被后世沿用,这就需要外译者具备相应的术语学的知识,以应对国学经典外译工作中的大量术语难题。我们通过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翻译的陶渊明的《责子》诗就很能看出来术语学知识的重要性,诗曰:“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韦理将“二八”译作“eighteen”,又将“行志学”译作“does his best”,[5]我们知道,“二八”在中国古汉语中应指十六岁(或虚指正值妙龄),绝没有“十八岁”之意,而“志学”缘自孔子《论语》,《论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学”指十五岁,与“弱冠”“不惑”“天命”等一样,是特定年龄的代名词。再比如,李白《长干行》诗中“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也是很考验译者专业术语能力的诗句,“抱柱信”和“望夫台”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已经是术语化的表述了,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翻译呢?有的译家将其翻译为“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out?”前句省略了“抱柱信”没有翻译,而后句“climb the lookout”也没有传达出望夫台所蕴含的意旨,相对而言,“Rather than break faith, you declareld you’ d die/Who knew I'd live alone in a tower high?”则很好地将“抱柱信”和“望夫台”背后的典故及其意蕴表达了出来。[6]
除此之外,国学经典外译人才不可或缺的专业能力还应该包括网络资源使用能力以及文本审校能力、文献查找、利用、储备和管理能力、各类文体的处理能力等。这些能力多倾向于辅助性,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以网络资源使用能力为例,当今时代是网络信息化时代,通过网络可以获取古今中外海量信息,无论是翻译理论、翻译文本,还是翻译家的访谈,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还可以通过网络与千里之外的翻译家沟通、探讨翻译难题。网络资源的应用可以实现知识与智慧的集聚,对国学经典外译大有助益。
四、 涉猎专业而广博的知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文学、哲学、逻辑学等诸多西方学科分类。国学经典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容纳了文学、逻辑学、哲学、民俗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和先民智慧。这就要求国学经典外译者掌握广博的中文知识,同样,出于翻译的需要,译者对目标语国家的知识掌握也应该是既专业又广博,只有知识的“对等”才能实现翻译的“对等”。另一方面,掌握了广博的知识,才有可能跳出翻译陷阱和思维限制,在矛盾中找到平衡点,破解翻译难题。我们说翻译就是文化的再编码,“翻译如何编码,决定文化内涵能否保留。”[7]再编码的成败取决于译者文化背景的厚薄。译者没有贯通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文化体系,翻译工作就会阻碍重重,或流于形式而失了意蕴,或出现曲解和错误,有时还会闹笑话。
著名国学经典翻译家赵彦春先生认为,合格的外译者在学识上应当具有“八备”素养,即具备目标语的句法知识、文学知识、语义知识、语篇知识、逻辑知识、语言本体论知识、哲学素养以及翻译学本体论素养。“八备”中的部分素质笔者已在前文中有所论述,从赵彦春先生的表述可以看出,没有广博的知识,国学经典外译是难以收获实效的。赵先生举例说,比如翻译林徽因的“黄昏吹着风的软”,有的译者将其译为“Sundown is cafessing the soft”或“The dusk wind blows up and down”,遮蔽了原文的魅力。[8]诚然,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着逻辑和审美中介的角色,应当具备广博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做到既博又专,使自己能够超越文字的取舍和调变,达到不等而等、不忠而忠的辩证性高度,进而达到一个圆满调和的境界,实现国学经典形与意、哲与思、艺术与审美、逻辑与思辨的完美译介。
五、 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国学经典外译的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海外汉学家都已经有很多人走过,也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可能成为后来者前进道路上的指向牌,也可能成为阻碍前进的绊脚石。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外译者,一方面要善于向别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不迷信前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外译工作常常会遭遇困境,尤其是面对国学外译工作,很多国学经典由于历史久远缺乏科学权威的解释,这时候就需要外译者运用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众多的释义进行甄选辨别,必要时还可以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释,并根据这种释义进行翻译。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内含了创造性思维的运用。例如,赵彦春先生在翻译《道德经》时,对前人的很多所谓经典原文的汉语解释及外文译本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自己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道”翻译为“Word”,“道可道,非常道”译作“The Word that can be worded is not the Word perse”,之所以这样翻译是考虑到《道德经》中的“道”并不是指道路的道,而是万物之源,万物之始,这与赫拉克利特的《论自然》的“Logos”及《圣经》中“Word”极为相近,尤其与《圣经》中“Word”存在高度契合性,将“道”译作“Word”既做到了意思的完美诠释、译介,又容易被西方社会理解。[8]相比前人的翻译“The Dao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Dao”“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将“道”译作“Dao”或“Way”的做法相比,赵先生的外译版更契合原文,又易于理解。经典翻译中陷阱很多,这需要靠逻辑和语篇来推导,而不是根据字面来理解,比如“道常无名”通常的解释是“道永远是无名的”,显然这种解释不仅违背常识,而且不符合《道德经》的精神:没有“名”就无法言说。其实“道”就是“道”的名字,而且它另有别名。这种语序实际上是名词或名词词组之间插入否定词,是汉语的一种结构。“道常无名”实际上就相当于“道无常名”,类似如“菩提本无树”(本无菩提树)。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蕴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国学经典著作,这些国学著作不仅思想独特深邃,而且表达优美如诗。因此,国学经典外译是一项庞大、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鉴于国学经典自身的特点及翻译的难度,国学经典外译者首先应当是位文化学者,其次还要掌握大量的翻译专业知识。但是,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又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苛求每一位国学外译者都是博古通今、参互中外的大儒,只能希望从事这项工作的外译者,根据工作需要尽可能的去涉猎知识,增强本领,发挥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力争国学外译不走样,能传神,真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传播出去,使中华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传播中得以展现,中华优秀文化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秀立于林,为文化“走出去”战略作出重要贡献。
[1] 赵彦春. 中华文化外译缺失的学理叩问[J]. 中华文化论坛, 2017(7): 28-32.
[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43.
[3] 辛红娟. “国学重振”与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5(1): 136-139.
[4] 赵彦春. 三字经英译集解[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54.
[5] 赵彦春. 论中国古典诗词英译[J]. 现代外语, 1996(2): 31-36.
[6] 谢瑜芳, 张软前.殊途同归的译诗形式——《长干行》两种英译对比[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4): 153-156.
[7] 赵彦春, 吕丽荣. 国学经典英译的时代要求——基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J]. 外语教学, 2016, 37(4): 98.
[8] 王祖友, 赵彦春. 百花齐放总是春——赵彦春教授访谈录[J].翻译论坛, 2015(1): 72-79.
The Literacy of a Chinese-foreign Translator of Chinese Classics
YAO Lizh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The Chinese classics ar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s are often limited in character, while limitless in meaning, they are full of elements such as literature, philosophy, music, logic, history and so on. There is a high demand for a Chinese-foreign translator. A good Chinese-foreign translator should possess the following qualities: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bilingual ability and deep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mastery of certain professional techniques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both expertise and breadth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think in dependently and creative thinking.
cultural power;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foreign translator; out translation
2018-03-22
湖南省教育厅教改课题(湘教通[2015]291-433)
姚力之(1969-),女,湖南益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H 315.9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8.03.019
2096-059X(2018)03–0104–04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