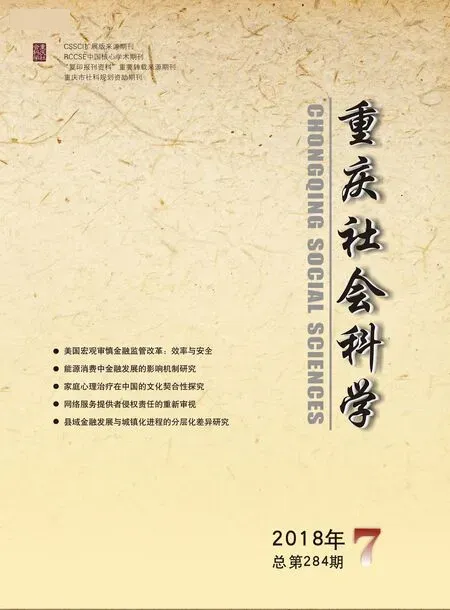痊愈的本能:创伤叙事下《被中断的女孩》的自由主题解读
张宇 石静
(兰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说:“自从弗洛伊德和皮埃尔·杰尼特的著作出现,创伤思想不仅仅使我们面对单纯的病理学,还一直使我们面对根本性的谜团。这种根本性的谜团就是精神与现实的关系。”[1]曾被诊断有边缘人格障碍的美国作家苏珊娜·凯森(Susanna Kaysen)于1993年出版了回忆录《被中断的女孩》(Girl,Interrupted),讲述了1967年4月至1968年10月,17岁的苏珊娜·凯森在美国有着悠久历史的精神病院——麦克林疗养院(Mclean Hospital)中18个月的所见所闻。书中,凯森以深刻敏锐的思考剖析着自我,也以诙谐辛辣的口吻审视着他人和社会。小说出版后久居《纽约时代周刊》畅销榜单7年之久,到2013年共再版了20余次。《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该书甚至会取代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钟形罩》①该小说第一次发表于1963年,是一部根据普拉斯早年经历发表的半自传体小说,也是唯一一部小说,主要反映了女性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桎梏。小说出版后不久普拉斯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0岁。随后小说风靡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校园,至今这部小说在美国青年女性心目中仍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当时美国高中和大学女生的必需读物,认为该作品游走于疯狂与洞察力之间,表现了灼热与敏锐的自我意识领域。《纽约时报》书评称回忆录痛心、诚实且饶有趣味,是一个引人入胜、令人心碎的故事。这部回忆录于1999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并由好莱坞著名演员薇诺娜·赖德与安吉丽娜·朱莉出演,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无数美国少女受到影片的启发与激励。电影的成功也引起了人们对该回忆录的进一步关注。国内鲜有对该作品的研究,仅见唐伟胜从疾病叙事与身体叙事的角度,探讨了自我身份建构的问题,他认为回忆录反映了凯森大脑中的“神经生物节奏”,并认为凯森在撰写回忆录时仍然是疯狂的[2]。国外对该作品及其同名电影的研究较为丰富。蒂莫西·道·亚当斯(Timothy Dow Adams)从自传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作品中的大量病例文件和信件对阐释传主及文本所起的作用[3]。伊丽莎白·马歇尔(Elizabeth Marshall)分析了作品中的批判性视角,对女性性别化的教育(gendered pedagogies)、精神疾患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探讨了回忆录中青春期女性对僵化的社会准则以及家庭、学校的期望呈现出的压抑性反抗,也批判了精神疾病医学话语中欠缺中立及性别化的判断标准[4]。
一、《被中断的女孩》中的创伤叙事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创伤本身指“身体受伤的地方”,又比喻“物质或精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创伤既可以来自自然灾难,也可以来自人类社会;既可能来自外部环境,也可能来自家庭内部;既可以是集体经验,也可以是个人体验;既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总之,无论是人类个体成长,还是人类总体历史发展,创伤作为“成长痛”从未离开过人类。
(一)位于故事与话语层面的“创伤”
“在文学作品中,‘创伤’是表达的对象,也是表达的工具[5]。”就小说的故事层面而言,创伤经常是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和主题。从话语层面来讲,创伤叙事的叙述方式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有的叙述方式可以实现并加强创伤叙事的效果。澳大利亚创伤理论家安妮·怀特海德 (Anne Whitehead)认为:“在创伤叙述的风格中,有大量关键性的特征一再出现,包括互文性、重复和一种播散与断裂的叙述声音。”[6]96但她认为这些文学技巧不一定必须在创伤作品中出现,它们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卡鲁斯也认为:“进入这些小说的入口不可能是唯一的。”[7]她同时强调接近文本时应力图停留在“创伤本身的天性上”[7]。
(二)体现在叙事结构与叙事内容中的创伤叙事
总体来看,《被中断的女孩》呈现出非线性与片段化的叙事结构。回忆录由34个章节构成,没有统一的情节,不按时间的线性顺序记叙,各个章节相对较为独立,关于某个人、某件事或话题展开。一些章节内部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则是关于自我或某个话题的分析。某些章节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连贯性,主要体现在某几个相连的章节就同一主题展开,或上一个章节末尾的词语作为引子引起下一个章节的讨论。例如在第四、五、六章,凯森通过记述三个人物的故事,展开对自由主题的思考。第八章凯森讲述了黛西的自杀,从而引出了第九章中对自己当年自杀经历的回忆。但总体上,叙事结构呈现非线性与片段化的特点。这是因为:首先,作品回忆录的文体决定了它主要呈现为简短故事、生活片段、场景描述与评论式的感受。菲利浦·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在《自传契约》中讲到:“自传首先包含一种非常经验化的记忆现象学。叙述者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过去,但是依靠的是无法预见的记忆的作用……记忆没有故事的结构,它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线性叙事无法传达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8]69-70凯森回忆录中的叙述如同一张正在打开的网,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思考交织其中,不断生发出丰富的话题。其次,创伤叙事的特点也决定了这部作品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一方面,创伤本身就具有回忆属性;另一方面,创伤不仅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事后影响。卡鲁斯在分析创伤的这种历史属性时指出,创伤的叙事结构与传统的直线顺序相分离:“创伤携带着一种使它抵抗叙事结构和线性时间的精确力量。由于在发生的瞬间没有被充分领会,创伤不受个体的控制,不能被随心所欲地重述,而是作为一种盘旋和萦绕不去的影响发挥作用。”[6]5在回忆录中,离开麦克林20多年之久的凯森,借助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经常将叙述闪回到当年被诊断入院时的情景,她难以释怀医生最初说的住院“几周”最终竟变成了“将近两年”[9]39。书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多年后当电子表发明时,凯森立即想到的是当年每天例行的频繁查房。显然,麦克林的经历已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创伤影响渗透在她的生活中。因此,从作品回忆录的文体特征和其创伤叙事的特点来看,该作品总体上呈现出非线性和片段化的叙事方式,而在回忆录的局部又体现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最后,从修辞角度来看,片段化的叙事方式巧妙地对应了禁锢于麦克林中年轻女孩们破碎的生命体验。
这部讲述疯人院故事的作品,汇集了诸多创伤内容与创伤表现方式,凯森以心理现实主义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和他人的创伤,同时运用反讽、黑色幽默、重复和片段化等叙事手法将创伤编织于叙述中。创伤,有时犹如暗流一般缓缓流动于凯森漫不经心的对周遭景物的描述和对病友自杀的简短记述中;有时创伤浮出水面,清晰地展现在凯森反复的思考与质疑中。对凯森来说,创伤既是自己的,也是他人的,是她目睹“病友”经历电击疗法后的痛哭、接受低温疗法①低温疗法指通过物理方法降低病人体温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几乎可以回溯到人类医药的最早历史,不同的低温疗法目前被广泛运用在医学领域。此处指的是在1941年由麦克林医院的医生约翰·塔伯特(John Talbot)和肯尼斯·提洛森(Kenneth Tillotson)设计的低温疗法:医生给精神病人服用镇静剂后,用特制的毛毯来循环冷冻剂,同时通过胃管给病人输送葡萄糖。后的颤抖和服用索瑞精②索瑞精又称氯丙嗪(Thorazine),是由法国科学家夏庞蒂埃(Charpentier)在1950年合成的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具有降低神经活动的作用,属于强烈的镇静剂,至今仍是精神病治疗的首选药物。后的呆滞,是她听到禁闭室里传来的绝望尖叫声。有时创伤被包裹在她对时间焦切的感受中,是每五分钟一次、十五分钟一次、半小时一次的护士查房带来的窒息与紧迫感;偶尔,创伤也势如火山爆发,携带着巨大的能量在非理性的自虐场景中,带给读者猝不及防的震惊与冲击,使读者一同经历凯森压抑的自我和自我崩塌的过程。根据马歇尔的分析,回忆录中的种种创伤与非理性行为,可以解释为“女性对创伤的内化方式”[4]。然而,理性与希望的光亮如星光点点,闪烁在凯森的叙述中。作为20世纪美国60年代的“精神病人”,凯森从未放弃过对理性自我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思考。
二、创伤下凯森的自由之路探寻
从古希腊城邦公民自由的存在方式到诸多哲学家关于自由的概念,从自由的概念史到历史进程中社会现实下的自由,从微观的个人到宏观的社会,由于时空、视角与范围的不同,关于自由的讨论纷繁复杂。而对于禁锢在麦克林的凯森而言,自由,无论是作为现实的存在还是意识的存在,都是她时常面对与思考的问题。聚焦于自己与病友被禁锢和剥夺的状态,她不仅要面对自己失去自由的创伤感受,也成为了他人创伤的见证者。
(一)莉萨的恶作剧——一幕追求自由的行为艺术
小说的四、五、六章较为集中地讨论了自由。第四章“火焰”讲述了一个名叫波莉的女孩18岁时用汽油点燃了自己,面颊和颈部严重烧伤。入院后,她平静、快乐、善解人意,没人知道也不敢问她为什么那样做。然而有一天,波莉从清晨开始一直哭泣,到了傍晚时分,她歇斯底里地喊道:“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9]18夜晚,波莉同样的话依然回响在医院走廊的尽头。对于几近毁容的波莉,这一章在凯森冷峻的口吻中戛然而止:“我们也许会在某个时刻出院,而她却被永远地禁锢在那个躯体之中。 ”[9]19
此时,题为“自由”的第五章也被开启了。这一章讲述了莉萨的故事,回忆录关于她的记述较多,她是医院里唯一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的病人,她倍受病人尊敬,在病人眼中,不羁的莉萨是她们的精神领袖,代表着“清醒、反抗与希望”。同很多美国60年代反主流文化青年一样,她吸大麻,用烟头烫自己胳膊,用各种方式与体制作对。莉萨从不睡觉也不看电视,她对着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大喊:“这就是狗屎!你们已经像机器人一样了,它正让你们变得更糟。”[9]21有时她干脆关掉电视,站在屏幕前挡住病人观看节目,她也时不时挑衅和捉弄医生护士。莉萨时常逃出去,称其为“休假”[9]22,每次回来后,她把所见所闻告诉病友。根据《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艾里克斯·宾恩(Alex Beam)对麦克林的记载,这种做法在当时大量涌入麦克林的青年中十分常见,病人们为了和60年代文化保持联系,经常策划逃脱,因为“大家都这么做”[10]220。对于莉萨,麦克林的人通常在一天内就能找到她,但这次她在外面待了三天才被发现。凯森写道:
这一次,当他们把她带回来时,他们几乎和她一样愤怒。两个大块头抓住她的胳膊,第三个家伙扯着她的头发,抓得很用力,莉萨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每个人都很安静,包括莉萨。他们把她带往走廊尽头,去往隔离室,我们就那样看着。
这一身体冲突的场面描写并不太符合我们对精神病院的想象——没有尖叫与咒骂,没有歇斯底里,而是“每个人都很安静”。此处,安静忍耐与激烈的身体冲突产生了一种张力,有力地表现出积聚在人物内心被压抑许久的愤怒。同时,该段与相邻的上一段对莉萨的描写形成了对比:
她很少吃东西也从不睡觉,所以她又瘦又黄,是那种不吃饭的人才有的样子,她眼睛下的眼袋很大。她用一枚银制的夹子将她那长而没有光泽的头发束了起来。
第一段中“两个强壮的男人”与第二段中莉萨纤细、面黄肌瘦的形象形成对比,同样,“第三个家伙扯着她的头发”已经破坏了莉萨别着银夹子时较为体面的形象。这些描写凸显了莉萨的弱势地位与她的无能为力,但也表现了她的倔强。之后作为惩罚,莉萨被关进了隔离室。比起凯森在麦克林见到的各种疗法带给病人的痛苦,她认为莉萨从隔离室出来后的情形最为可怕:
我们见到过很多事情。我们见过辛西亚在每周接受电击后哭着回来。我们见过波莉被冰冷的毯子裹起来后颤抖的样子。然而我们见过最坏的却是,两天后莉萨从隔离室里出来的模样。
莉萨从隔离室出来后和之前判若两人。她神情恍惚、不再和其他人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活跃有趣,而是一反常态地与其他病人一起看电视。病友们怀疑医院给她服用了索瑞精。索瑞精是20世纪50年代末被广泛使用的临床镇静药物,它能让极其骚动不安的病人安静下来,而它的副作用便是漫无目标的“索瑞精游走”(Thorazine shuffle)、不时松弛下垂的舌头以及“索瑞精日晒”(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皮肤很容易被晒黑)[10]211。曾住过麦克林的60年代美国著名歌手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曾这样评论这种至今仍广泛使用的药物:“这种强烈的镇静剂会让人变得迟钝,以这种方式处理精神健康问题,其实是非常粗鲁的,就好像有人拿我的头撞水泥墙。”[10]211服用索瑞精后,莉萨的主体性被机构的“治疗”剥夺了,先前那个有血有肉、精力充沛的莉萨变成死气沉沉、丧失了自由意志与反抗精神的一副空壳。在凯森眼中,这样行尸走肉般的状态最让人绝望,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两个月。
然而有一天,莉萨突然冲进厨房让病友们去欣赏她的“杰作”。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她用卫生纸将所有家具缠绕起来,包括电视机和天花板上的防火洒水系统。凯森描述道:“成米成米长的厕纸飘动着、悬晃着,打着褶皱包裹着每样东西,悬挂在每一个地方。这简直太壮观了。”[9]24此刻,莉萨“plot”了一场真正的行为艺术,她为自己和其他病人创造了一个新奇的白色世界、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甚至带给人一种艺术才能传达出的崇高感受。同时,这荒诞的一幕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白色卷纸缠绕着的房间摆设就像被裹尸布裹住的木乃伊,象征着被束缚、窒息和无生命的状态,这对应了病人们在麦克林的处境。但同时,这样一场行为艺术又“打破”了这种被禁锢的状态。莉萨并没有真正失去主体性,当她从药物的效力中恢复过来后,通过这种恶作剧的方式,她最大化地行使了自由意志,用艺术行为反抗着医疗体制的压制。根据宾恩的访谈,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的年轻病人涌入麦克林,类似的恶作剧时常发生。在凯森所居住的南贝奈普楼(South Belknap),女诗人普拉斯也居住过,青年病人喜爱的把戏之一是突然拉下火警铃,而当一堆消防队员冲进病房时,他们会发现那里有着一群没穿内衣的女孩悬在天花板管线上等候着他们。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用“战术”一词来形容弱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即弱者如何利用空间、时间、身体和各种资源等进行顺应或反转局势的“微小抵抗”,从而抵制强势的生产力量和社会秩序的压制与规范,这种抵抗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运作,在受限空间里寻求自我实现[11]。因此,尽管莉萨的生存环境受到控制,身体受到折磨,但她的自我意识是独立的,她仍然有选择回应方式的自由。这出乎意料、戏剧性的一幕展现了一次狂欢式的反抗,让莉萨重获了短暂的自由与尊严。
(二)凯森对自由的思考
1.自相矛盾的自由
凯森对自由的讨论并没有止步于莉萨这一次狂欢式的反抗。在同一章中凯森引用了莉萨的一段话表明莉萨对出逃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刻薄的世界,’她会说。通常她回来时已经心满意足了。‘在那儿(外面的世界)没人照顾你。’”[9]22此处,莉萨的行为与话语互相矛盾:一方面她愤怒于被禁锢在麦克林,另一方面她依赖着麦克林提供的“照料”,莉萨惧怕真正回到社会,而只是偶尔“度假式”地逃出医院,回来时已经“心满意足”。麦克林的区隔功能的确也扮演着庇护所的角色:
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所医院更像是一个避难所而不是监狱。尽管我们被隔离于这个世界和我们热衷于在那儿引起的麻烦之外,但是,我们也同样被隔离于将我们逼疯的要求与期望之外。
凯森的叙述揭示了出生于婴儿潮,被冠以患上“精神嬉皮症”[10]210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真正的困扰:他们“无法符合现在被自负地称为‘最伟大的一代’的期望。”[10]他们永远无法企及他们父辈的成就。这些有着各种精神危机与心理障碍的青少年大多来自波士顿上层社会的精英家庭。凯森在撰写这部回忆录时说到:“这是一次工程浩大的剑桥社会学实验”,意指麦克林疗养院是富裕人家问题子女的庞大收容所[10]204。而始建于19世纪初的麦克林疗养院(现今为哈佛大学教学医院)很长一段时期由波士顿当地贵族富豪资助,这些名门望族也将自己家族中有精神问题的人送至这里。麦克林逐渐成为了知识圈、文化圈与上流社会人士的交集之处,尽管麦克林有明显的社会区隔功能,但“基本上还是上流社会与文化的延伸与复制”[10]4。
麦克林风景宜人,拥有溪流与巨大的红铜山毛榉,甚至存有很多古董收藏与画作,散落各处的庄园式病房很难让人将它同精神病院联系在一起,而它更像一座大学校园,其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年代才对女性开放的宏伟建筑阿波汉姆(Upham)被昵称为“哈佛俱乐部”,据说有段时间几乎每间豪华套房住的都是哈佛毕业生。麦克林构成了它所在的波士顿的重要文化背景,而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波士顿一直是美国的知识首都,至今它仍是风头正劲的美国创新创业摇篮。麦克林曾接收过还未获得诺贝尔奖时的约翰·纳什、著名歌手詹姆斯·泰勒、灵魂音乐家雷·查尔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等众多名人才子。提供奢华静养疗法的麦克林成了他们逃避外界、缓解压力的绝佳处所。苏珊娜·凯森因为当年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而被父母送入麦克林。在回忆录中,凯森记述自己厌学并只乐意写作和交男朋友,而且她是当时所在中学历史上第一个不愿上大学的人。据凯森的社工回忆,凯森的父亲无法容忍她不上大学,认为她的脑袋一定有问题而让她住院治疗。而根据回忆录,凯森不仅不想上大学,而且在自杀未遂后和高中英语老师有染。
同时,凯森在回忆录中丝毫未提及自己父亲显赫的背景:肯尼迪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且曾掌管着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可想而知,凯森当年的混乱表现让父亲丢尽颜面,让整个家庭蒙羞。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越战战场的重挫和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将嬉皮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垮掉的一代”彻底否定了传统的理性规范,试图通过反主流文化的方式来回应充满变化和矛盾的美国社会,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在几乎为所欲为的放纵享乐中,青年一代们提倡个性自由与性解放,向往爱与和平,但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政府对嬉皮青年们的压制与打击、嬉皮文化的消极一面都使得这一代年轻人内心充满了难以自救的痛苦与迷茫。被送往麦克林的凯森正处于这个时代中,对其文本的解读也应该置于此时的历史语境中。凯森的文本暗指了当年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但若干年后,她并没有推卸自身的责任,当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回顾这段经历时,她与这段经历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在这段颇具哲学意味的叙述中,凯森看清了自己。从“奇怪”可以看出,凯森并不认同逃避外界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从“只要”“愿意”的选词上可以看出写作回忆录时的凯森认为沮丧是一种可由主体操控的选择行为。她认为当年的疯癫与偏离常规多少要归咎于自己的选择。在之后的章节中,她也写道是自己的“无能”[9]154导致了她的精神危机,自己也许没疯,而是在和疯狂“调情”[9]158,就如同对老师和同学一样玩世不恭。
2.凯森的选择
在第六章“生命的秘密”中,凯森记述了她的朋友吉姆·沃森①詹姆士·沃森(James Watson)出生于1928年,是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动物学家,并于1962年因为和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发现DNA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来医院探望她。沃森“发现了生命的秘密”[9]25:他当时和另一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当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想带着凯森乘上他停在医院外的红色跑车逃离麦克林,去英国开始新生活时,与上一章莉萨的不断出逃形成对比,凯森选择了留下。在这相邻的两章中,凯森和莉萨关于出逃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样的叙事安排显然是凯森有意为之。凯森写道:“‘你的意思是,坐上这车?’我感到困惑。这就是生活的秘密?逃走是生活的秘密吗?”[9]26“秘密”在这里一语双关,一方面指DNA的发现,另一方面指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秘密。显然,发现了科学的奥秘并不等同于发现了幸福生活的秘密,自然科学并不能彻底解决人类的心灵问题。凯森对沃森的话语充满了批判意味:“理性”的科学家也许比身在精神病院的凯森更加疯狂,医院外的红色跑车更暗示了这一点,它让人联想到明星、炫耀、激情、浪漫、危险与不受控制,而并非理性的科学家。因此,凯森巧妙地反衬出自己理性的一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疯狂。在短暂想象了逃出医院的生活后,凯森没有找到这样做的意义——她仍然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她说道:“这一切,事实上,是那样模糊不清。只有乙烯塑料椅,监控屏幕,护士工作站大门的嗡嗡声,那些才是清晰的。”[9]27自由的基本意味就是选择,凯森此时选择了面对自己的精神危机,面对内心的迷茫。她还没有准备好再次应付外面的世界,又或者,她希望带着尊严离开,正如弗洛姆所言:“自由不仅仅是个量的问题,而且是个质的问题。”[12]
终于,1968年9月的一天,凯森毕业于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朋友向她提出求婚,她接受了求婚并获准离开麦克林——因为婚姻,她“自由”了。她写道:“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求婚,他们让我出院了。在1968年,每个人都能明白求婚。”[9]133然而,凯森离开麦克林后,她的婚姻持续了不长时间还是结束了,凯森了解自己正是不愿进入婚姻生活的那类人。而从当时乃至现在的价值观来看,一个人有婚姻就足以证明她是正常的。当凯森再一次步入社会,麦克林的经历使她在找工作之初受到诸多冷遇,她试着去克服这些压力适应社会,然而她仍然在工作中频频出错。凯森讲述了在哈佛作打字员的经历。第一天上班时,凯森发现巡视员们边抽烟边监督她们工作,当凯森也点燃一支烟时,巡视员警告她不许吸烟,凯森反问“可你正在吸烟”,巡视员却告诉她:“打字员不许吸烟。”[9]131凯森打量着周围才发现:所有打字员都是女性,都没有吸烟;而所有巡视员都是男性,都在吸烟。十五分钟休息时,女打字员们纷纷涌入卫生间吸烟。当凯森想去大厅吸烟时,她被告知她们只能在卫生间吸烟。第二天,凯森又被禁止穿迷你裙工作。由于凯森还没收入添置新衣服,第三天时她便身着一身黑:黑迷你裙、黑丝袜,期待着情况有所改观。然而巡视员依然警告她不许穿迷你裙。听到又一次警告后,压抑的凯森疾步走进卫生间快速吸了根烟。回到座位后,巡视员又随即警告她上班时不许吸烟,只有休息时才可以。而从此时起,凯森便在工作中频频出错。第四天,她对巡视员解释道:“如果让我吸烟,我不会犯这么多错。”[9]132第五天,凯森离开了这份工作。在美国60年代的性别歧视和缺乏人性化的工作环境下,凯森仍然坦承自己确实不善于遵守规则。凯森分析道:“我的自我形象并非不稳定。我十分准确地看到了我自己,我跟教育和社会体制格格不入。”[9]155凯森不能长期地持守一份工作让她十分苦恼,她说道:“我可能真的疯了。”[9]157然而,在经历了拒绝和失败后,凯森没有绝望,而是决意成为一名作家。凯森的社工和护士却并不看好这个选择,凯森自己甚至也怀疑能否以写作维生:“就我当时所见,我并没有生活所需的技巧。结果是长期的空虚与无聊。”[9]156尽管如此,凯森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沉浸在自暴自弃中,而是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当她的作品获得成功,重返麦克林为书迷签售时,她说:“我一直很高兴回到麦克林,因为感觉能离开真好。”[13]凯森最终离开了原地,克服了自己的软弱,没有随波逐流或郁郁不得志,而是最终获得了独立与自由。
三、结语——理性的光芒与自我超越
凯森将关于自由的思考夹杂在创伤的裂缝与混乱中。与其说凯森被禁锢在麦克林,不如说她被放逐在自我迷失中。凯森最初的任性叛逆甚至自杀是她不愿取悦他人、追求个性与自由意志的体现,但这种缺乏至善标尺的自由观并没有带给她自由,而是难以自救的迷茫与困惑。这迷茫来自充满巨变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来自反传统文化对人们价值观的冲击,来自凯森无法满足父母期望而产生的内心冲突与无法自洽,来自青年女性步入成人世界时的焦虑与无所适从,抑或来自凯森所说的——自己的“无能”[9]154或软弱。
尽管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凯森的精神危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多年后的凯森清醒地认识到她的迷茫更多归咎于她的选择和无能。正如萨特突出主体性的存在主义哲学观所表明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自由选择,不断地自我创造,证明自己的存在。凯森从最初的迷茫无力到最终成为一名作家,从最初的消极厌世到后来在重压之下努力面对生活都是她选择的结果。在快离开麦克林时,她对自己说道:“振作起来!我跟自己说。不要再放纵你自己!”[9]157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凯森对理性自我的渴求与选择。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理性精神是通往自由的前提,是理想的人格。对人类个体而言,理性无疑是个体成长、获得独立与通往自由的钥匙。而作为劳动实践的“写作”对凯森寻求自由有着重大意义。正如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和自由的关系的论证所言:“劳动的过程就是人的内在本质对象化的过程。正是在劳动中、在物化的精神产品中,人才自觉到或看到包括自己的精神力量、自己的创造能力和审美情趣在内的自由天性。”[14]当凯森付诸行动努力书写时,凯森最终汇集了内在的理性力量,通过写作这一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治愈并连通了自己与外部现实世界。
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对人类的心灵苦难痛心疾首,提出了惊世骇俗、与当时哲学氛围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哲学的宗旨应是通过心灵治疗让人们在哲学中找回自我,实现个体精神的自由,哲学应该假理性之手医治人们的精神创伤和灵魂的疾苦,应该走出象牙塔成为一种社会事业。的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困境面前整合自己,而敢于直面人生最终站起来的人就是自由的。凯森最终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答案,通过写作重建了自己的生命。诚然,凯森的人格并不完美,对于“疯狂”,她仍然有着疑惑,然而,凯森对创伤的讲述和对自由的探索终究源于她对生命的热爱。在回忆录结尾,凯森借着荷兰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名作《被中断的女孩》①《被中断的女孩》(Girl Interrupted at Her Music)是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一幅名作,现收藏于纽约弗利克美术馆(Frick Collection)。维米尔善于在绘画中表现光线,这幅画中,一名贵族装扮的男子正在与一名年轻女子看乐谱,但女子却扭过头看着观众,似乎有什么人正进入画面打断了她。说道:“音乐中的女孩坐在另一种光中,一种断断续续、有些忧郁的生命之光中,透过这光我们偶尔看到我们自身的不完美,也看到别人的不完美。”的确,人性的复杂与身处的不同境遇使我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生命景观。我们不尽完美,在生命之洋里茫然浮沉,在黑暗中困顿摸索,甚至滑入非理性的灰色地带——任性、甚至疯狂。然而,人类永远不会停止对自我的寻找与重建,带着这种不完美,我们仍要发掘自我意识的内在力量,努力挣脱那些囚困我们的牢笼,从伤痛中获得痊愈,超越过去的自我,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也正是写作的意义所在,诚如勒热纳所言:“写自传是为了传诸后世,但也是为了发现自我……找到过去一生隐藏的意义,总结未来的生活之道,这就是继往开来。 ”[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