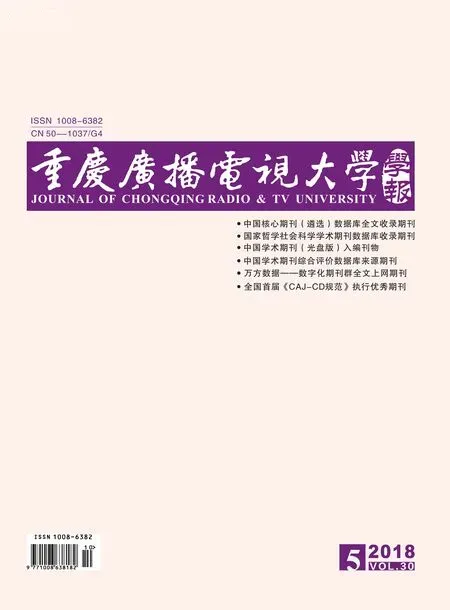徐訏《风萧萧》中的异国间谍形象
金安利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孙子兵法·用间》篇有云:“故唯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间谍活动无疑是战争谋略较量中最隐蔽、最神秘的领域,是任何样式的战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每次血与火的冲突对抗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用间踪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也不例外,中日双方在隐秘的谍报战线上展开了殊死较量。这些斗智斗勇的谍报活动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作家极好的写作素材,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风萧萧》以青年哲学研究者“我”与多位女性的交往为主线,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小说虽以“我”为故事轴心,但也塑造了几位栩栩如生的间谍形象——国民党间谍白苹、日本间谍的宫间美子和美国间谍梅瀛子。徐訏对后两位异国间谍形象的塑造是截然不同的,值得我们去探究。本文运用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分析这两位异国间谍形象,并从社会集体想象物和作家思想、感情等层面探讨其原因,借“他者”来反观“自我”。
一
根据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任何文本中的异国形象都不是对异国现实世界或人物的客观呈现,“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先存于形象”[1]157。这样的异国形象也可以视为“社会集体想象物”。所谓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对一个社会(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集体描述的总和,既是构成、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1]30。这就是说,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异国形象在历史、社会、心理以及哲学等方面的进一步拓展。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异国形象的纵向深化。根据让-马克·莫哈的理解,“社会集体想象物建立在‘整合功能和颠覆功能之间的张力上’,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间的张力上”[1]34。他强调异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功能,因为它是“集体记忆联接站”,是“被理想化了的诠释,通过它,群体再现了自我存在并由此强化了自我身份”。“意识形态较少由内容来定义,而主要由它对一个特定群体所起的整合功能来定义。”[1]32这就是说,“凡按照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1]35。从注视者主体立场来看,意识形态化的异国形象是要维护和保存本国现实的,而乌托邦的异国形象则在“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它具有“社会颠覆的功能”[1]33。
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中国作家创作了大量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相适应的文学作品,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徐訏笔下的日本间谍宫间美子,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一社会集体想象的两极来理解的话,无疑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异国人物形象。
日本间谍宫间美子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她的首次登场是在小说的第四十六章。当“我”应邀前往日本巨商本佐次郎家吃饭的时候,碰巧遇到了静娴幽秀的宫间美子姑娘。女主人对宫间美子意外的恭敬引起了“我”对她的特别关注:“宫间小姐个子不矮,坐在那里更不比我低多少,我从她衣领看上去,觉得正是图画中所见的日本美人,可是脸庞完全是属于孩子的活泼的典型,古典气氛并不浓厚。这样的脸庞应当有谈笑嫣然的风韵,可是她竟是始终沉静庄严,当她去夹在左面的菜时,我注意她的眼睛,睫毛很长,但眼睛永远像俯视似的下垂着,这印象,正如有许多照相师把人像的眼珠反光修去了的照相所给我的一样,是一种肃穆,也可以说是有点神秘。”[2]363这位初次会面的东瀛丽人,给“我”留下了肃穆和神秘的感觉。这也为下文叙述她的神秘行动埋下了伏笔。
她的第二次出场犹如幽灵鬼魂般飘逸而诡异,故事发生在日本军官梅武少将的密室里。正当“我”溜进密室准备下手窃取保险柜里的军事密件时,突然听见有人在推门,于是“我”灵机一动,赶紧躲到了房中的圆桌下面。透过台布的缝隙,“我”在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从密室门口溜进来的神秘女子。这位女子身穿白色晚礼服,戴着银色的面具,手中还拿着一包白色的东西。她持着手电筒向密室四周一照,很快就照到了保险箱。“她缓步过来,于是像下弦月一样,她身躯慢慢地被台布吞蚀,最后我只能看到她白色的衣裙在我桌前驶过……”[2]373“我”看见她用钥匙打开了保险箱的门,转动密码取出箱内的密件后放在写字台上,又从自己带来的白包内取出一件黑物放进保险箱。随后她就关好保险箱门,拿起写字台上的密件悄然离开。“我”直觉地感受到这神秘女子安放进去的是炸弹,于是在她准备离开时竭尽所能地在其衣裙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就在她驶过我的面前时,我放足了勇气伸手出去,把我笔管的墨水射在她曳在地上的衣裙上面。”[2]375随后,“我”目送着她那轻盈的身躯在密室门口隐去。
在这一连串的描述中,黑暗中突然出现的神秘女子完全具备了“鬼”的一些特性:带着银色面具,穿着白色礼服,走路毫无声息,动作轻盈飘逸等等,这些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幽灵和鬼魂。这位幽灵般的神秘女子,让“我”窃取军事密件的行动无功而返。“我”的失手而归让美国间谍梅瀛子大失所望,但是也并非一无所获。“我”偷偷洒在神秘女子身上的那串墨渍成为揭开谜底的唯一线索。
紧接着,“我”与梅瀛子在花园中的对话非常值得关注。当“我”担心花园中的那些人会发现我们时,梅瀛子笑着说:“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外,自然都是天使。” 但是“我”却有一种凄凉不祥的预感,意识中冒出了可怕的阴影,不禁打了个寒颤:“但是天使以外还有魔鬼。”梅瀛子低声告诉“我”,那魔鬼便是蛇,“就是沾着你的墨水的那位”[2]378。
在这段对话中,作者以《圣经》典故为叙事模型,借梅瀛子之口把那位沾着墨水的神秘女子喻为蛇,一种类似魔鬼撒旦般的邪恶形象。在《圣经》里,正是因为蛇的引诱,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开始了人间的苦难历程。
“我”留在神秘女子身上的墨渍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没有隔多少时候,就看到左首一个女子衣裙上的墨渍,很小,七八点像虚线似的,像……一条小蛇,不知怎么,我打了一个寒隙;……我注意她的面部,在银色面具下,她所透露的下颐似乎是属于很温柔的一类脸型,怎么她在干这一个勾当?我几乎不相信刚才在房内所见的女子就是她了。”[2]381那串墨渍在“我”的眼中变成了一条小蛇,神秘女子也就幻化为蛇意象。伊甸园中的蛇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因此这样的“妖魔化”意味着她有魔鬼般的阴险歹毒、邪恶善变等种种特性。
当“我”特意邀请她跳舞时,她自称朝村登水子,来上海前曾在满洲待过十年。随后“我”多次与其共舞,希望能打探到更多的信息,但她却始终忍耐与缄默,不露丝毫的情感与声色。“我”竭力想看清楚“鬼”的真实面目,“借着较亮的灯光,从面具的眼孔,看她乌黑的眼睛,再从面具的下面,望她温柔的下颐,我觉得她一定是很美的女子”[2]383-384,而此时她却又变回到了人的形象。
当假面舞会的所有人都撤掉面具后,“我”迫不及待地在舞池里寻找着神秘女子的踪迹。“我立刻在她衣裙上看到蓝色的墨渍,我急于细看她的脸。我挤过去,啊,果然是一个温柔的脸庞,嘴角似乎始终有悲悯的表情,下颐有可掬的和蔼,但是我忽然与她的视线接触了,我顿悟到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我在思想中探索,但怎么也想不出来。”[2]385打听到她就是宫间美子时,我简直吃惊得目瞪口呆了:“宫间美子!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会说上好的国语,又改叫朝村登水子。是那样一个古典闺秀般羞涩的姑娘,会就是房中干这样可怕勾当的女子,而又是具有这样温柔的脸庞与悲悯的嘴角的朝村登水子?但是这毋庸我怀疑,蓝色的墨渍明明在她的衣裙上,而她操着纯熟的国语,告诉我她是朝村登水子的声音,也明明在我的耳畔,人间真是这样的可怕与不可测么?我整个的心灵在那上面战栗起来。”[2]385-386
从舞会回家后的“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发现我在圆桌底下隐伏,好像是月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我忽然看见一条蓝色的蛇在桌边游过。”这蛇突然把头伸进桌下对“我”说:“我知道你在那里躲着,我都看见。”[2]388“我”在密室里的那段梦魇般的经历,最大的担心莫过于被人发现,而关键时刻这神秘女子突然像蛇一般地溜进来。尽管现实中“我”躲在桌子下并没有被发现,但这种担心和恐慌已经进入到个体的潜意识中,在梦境中以被发现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出色的梦境描写,充分地挖掘了人物的潜意识心理。
为了打探到宫间美子更多的信息,“我”登门拜访日本巨商本佐次郎,碰巧在他家里与宫间美子不期而遇。于是“我”坐在了她的斜对面,特别集中注意力地仔细观察起来:
在“我”第一个印象中,她有一颗孩子气活泼的面庞;后来“我”发觉她有柔和的下颐与悲悯的嘴角;现在“我”觉得这两种观察完全没有错,只因为她始终保持着沉静与庄严,使她的面庞,竟调和了两种不同的美点。这就是说,这样的脸庞如果太多嫣笑与表情,一定失之于轻佻;如果不是这样的脸庞,那么她的沉静与庄严就会失之于死板。“我”现在觉得我意料中她的年龄是很正确的,因为从这脸庞来猜,“我”可以少猜几岁,但从她这沉静与庄严来猜,“我”可以多猜几岁,而“我”现在所猜的正是二者的调和,“我”猜她是二十二岁,今天她又穿和服,“我”觉得比穿晚礼服要年轻。
就在我们随便谈话之中,“我”同她的视线接触。她避开了“我”的视线,“我”发现她面部的特点还是在眼睛,她的眼睛瘦长,似乎嫌小,但她睫毛很浓,而又略略上斜,因此“我”觉得所有她具有的神秘,就在那里面无疑,而这也凭空增加了她脸庞的高贵成分。昨夜在饭桌上所见到她面上的游涟,今天一点也不曾透露,而我所发现她嘴角悲悯的意味,则似乎在首肯一种意见时常常浮起[2]395。
在抗战文学里,如此具体细腻地描写日本人形象的作品实属罕见。这样一位东瀛美女蛇,究竟是何方神圣呢?“我”刻意地探到了她零星的信息:她从东京来了才几月,她只是来游历的,等等。在送她回家后的归途中,“我始终想不出宫间美子给我的印象里的异常之点”。“她今天在车上的谈话,还是用不很纯粹的国语,处处把话说得缓慢或者省略,以掩盖她对于中国话的拙劣。假如她有朝村登水子的国语修养,这样伪作的确是奇迹,她如果将纯粹‘会’装作纯粹 ‘不会’,可以不难,而装作半会半不会,则的确使我很惊奇,除此以外,我并不觉得她有特殊的魔力。我似乎很有把握来对待这个敌手,所以在自恃中得到了宽慰。”[2]399看来这美女蛇的确有很强的迷惑性,她竟然让男主人公“我”反省起自己对她的判断是个可怕的误会。
正当“我”自信满满地认为很有把握对付这个敌人时,她那神秘的面纱在美方谍报人员的密信里揭开了。这“鬼”背后的真实面目竟然吓得美方间谍梅瀛子花容失色,一副萎靡颓唐的样子:“宫间美子即郎第仪,随川岛芳子多年,在满洲国华北活跃,常乔装男子以秋雨三郎名驰骋军政各界。风流倜傥,矫健活泼。豪赌千金一挥,毫不动容。慷慨交友,人皆从之。一度回国,旋至南京,最近来上海,不知有何使命。”“宫间美子到沪后,立刻对梅瀛子怀疑,为梅事数度与梅武冲突。”[2]404
宫间美子真实面目的出现,也让“我”彻底惊呆了。正如梅瀛子所判断,她绝非一个无能的敌人。她对梅瀛子早有疑心,对她进行了秘密窥视而又不被其察觉,这不禁让“我”感到寒颤不已:“在这许多日子之中,梅瀛子竟毫不注意,也毫未想到背后有人在窥视她,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宫间美子又是个多么可怕的人物。”[2]405
在随后的谍报战中,急于获取密件的国民党间谍白苹中了宫间美子的埋伏而命丧九泉。仗义的梅瀛子替白苹报了仇,她设计用毒酒害死了宫间美子后便隐匿而去。“我”也踏上了去大后方的旅途,去从事民族的抗日工作。
由此可见,徐訏在《风萧萧》中非常具体地描写了日本间谍宫间美子的容貌和性格。比起那些概念化、脸谱化和“鬼化”的日本侵略者形象,宫间美子的形象的确要生动得多,但却是半人半鬼。
二
徐訏笔下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日本间谍形象,又是如何生成的呢?其实,异国形象的形成是比较复杂的。“异国形象应该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1]12那么,我们不妨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日两国间谍观的差异,进而探究其对异国形象生成所产生的影响。
在人们日常语言中,所谓“间谍”即指出于某种斗争的需要,深入侦察对象内部,秘密从事情报搜集、离间及破坏等特殊任务的人员。人们通常出于对自己国家、民族乃至集团安全利益的捍卫及其对外防范的意识,普遍对“间谍”一词持有反对和敌视态度,主观上很容易对这“人类第二古老职业”赋予“鸡鸣狗盗、男盗女娼、卑鄙无耻、阴险诡诈”等贬义标签。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用间行谍无异于鸡鸣狗盗式的诡诈与不义,有悖于讲求“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的正统经学。故中国人的传统间谍观是“只做不说”,用间行谍岂可公诸于世。
然而,日本人对间谍的评价却与中国截然不同,他们把爱国尽忠纳入了对国家至关紧要的谍报工作。理查德·迪肯曾这样评述日本人的间谍观:“靠爱国主义,不靠行贿,是日本谍报机关所有下属机构始终不渝的座右铭。日本人强调以爱国主义作为谍报活动根本出发点的做法,在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是不能想象的事。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从事谍报活动被看作是一件相当不体面的事,而且永远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官方否认他们和这种勾当有牵连,主要不是出于谨小慎微和保密的考虑,而是地地道道的伪善,感到谍报活动是见不得人的下贱事。……日本比西方高明之处,是在于他们有目的地给间谍活动以履行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地位,其荣耀并不亚于驰骋疆场的兵士。为了自己的祖国搞谍报,与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一样无比荣光,也许甚至比当兵冲锋陷阵更受人尊敬。因为,他们认为谍报活动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开路先锋。”[3]37-38
鉴于日本人在从事谍报活动方面获得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日本诸多民族主义者建立起了各种秘密社团,每个新加入社团的人都要宣誓为日本国的荣誉而收集情报。例如,日本第一个真正的国外秘密谍报机构隶属于玄洋社,于1881年在日本九州的福冈成立。尽管这个组织标榜自己以“光耀皇室”“尊崇帝国”和“捍卫人民权利”为宗旨,但是这些高调实际上不过是用于掩盖他们企图向海外扩张日本势力,从中国、朝鲜和俄国刺探情报的真实用心。随着谍报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展,成绩也日益令人鼓舞,于是日本陆军就暗中提供资金,帮助这些秘密社团。
日本人不仅把谍报活动当作一项光荣的爱国事业,而且还大肆炫耀,将其公诸于世。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评价“甲午日谍第一案”中被清政府处死的石川伍一的:“石川伍一,间谍。生于1866年,卒于1894年。受命赴中国活动,到过蒙古边境一带。中日战争中在华积极活动,后被中国人抓获,在天津被处决。……”[3]2
由此可见,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间谍观存在着天渊之别。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价值观对作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他们塑造异国间谍形象时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作用。《风萧萧》中的日本间谍宫间美子,在徐訏笔下幻化为蛇的形象。蛇意象隐喻着她有魔鬼般的阴险、残酷、歹毒、邪恶、善变等种种特性。这样“妖魔化”的日本间谍形象是作者在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按照本社会模式、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异国间谍形象。它符合了当时中国人对日本间谍的集体想象。
三
在小说中,除了日本间谍宫间美子之外,还出现了美国间谍梅瀛子。同为异国间谍形象,徐訏对梅瀛子的叙述却完全不同于宫间美子,对两者所持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对于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本文从形象学角度来揭开谜底。
异国形象的塑造过程,可以说是形塑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其进行操纵和控制,甚至欲望化,直至改塑成如其所愿的那种异国形象的过程。依照巴柔的总结,形塑者对异国形象所持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即狂热、憎恶与亲善[1]175-176。
以此来分析,徐訏对日本间谍宫间美子形象的叙述,明显地表现出了中国人“憎恶日本”的情感和敌对情绪。另一方面,作家则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将自身的价值进行正面化,使得其以美好的形象展现给读者。小说中的国民党间谍白苹形象,无疑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白苹是一个姿态高雅而又豪爽沉着的舞女,这位风尘女子身上有着许多善良和优秀的品质。她常露百合初放般的笑容,具有一种银色的凄清韵味,好像“海底的星光”。小说取名为《风萧萧》就是作者对她悲壮牺牲的一种赞叹!
若是形塑者认同他者文化的正向价值,就会对他者表现出亲善的态度,并进而与他者建构起一种亲善型的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形态之下,他者和形塑者都呈现为正面形象。徐訏笔下的美国间谍梅瀛子形象,呈现为正面形象,表现出了作者对美国的亲善态度。
梅瀛子是一个中美混血儿,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中国人,但她从小又是在日本长大的。这位兼具东西方女性之美的神秘交际花,有一种红色的热情和令人不敢逼视的特殊魅力,犹如太阳一样灿烂逼人。她的性格像变幻的波涛,忽而上升,忽然下降,新奇突兀,永远使人目炫心晃而不能自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我”在史蒂芬太太的劝导下加入了盟军间谍组织,这才得知梅瀛子原来也是上级。她机敏干练,咄咄逼人,为达到目的可以毫无内疚地把纯洁的海伦拉入谍海而使其不自知。海伦的母亲不知实情,逢人就夸赞她美丽、漂亮、聪明、能干,又夸赞她人好,为宝贝女儿介绍了工作。殊不知梅瀛子是为了自己谍报工作的需要,把海伦介绍到日本人的电台工作,还让她周旋于数位日本军官之间,有次险遭一位日本海军军官凌辱。
梅瀛子忠于自己的工作,十分看中政治搏击中的成功。她总是以全局来观照个体价值,一切都要服从于胜利这个目标。她的自我身份认同是美国人,这也使得她为了美国海军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她不惜牺牲无辜的个体,觉得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义而可取的。她阴险残酷却又肩负着伟大使命,这使得“我”对她爱恨交加。
虽然梅瀛子在“我”的眼中已经成了一个魔影,但这不妨碍“我”对她不时进行正面肯定和赞赏。在小说的尾声部分,深谋远虑的梅瀛子苦苦劝阻白苹不要亲自去取情报,而白苹却急于功成而执意前往。梅瀛子为此进行了诸多周密的安排,还和“我”亲自陪同白苹前去接头的地方。谁知还是宫间美子技高一筹,白苹中了埋伏而饮弹身亡。梅瀛子设计用毒酒让宫间美子香消玉殒,为好友白苹报仇雪恨,随后自己也隐姓埋名而去。
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作家笔下出现妖魔化的日本间谍形象和亲善的美国间谍形象,是不足为奇的。这与当时的中美、中日关系有密切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对战争的态度是暧昧的。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才对日宣战。美国参战导致了世界局势的大逆转,美、英、苏、中等国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美国是中国的盟友,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中国作家笔下的美国人形象大都呈现为美好亲善的形象。徐訏对梅瀛子形象也进行了完善式的加工,譬如小说结尾对梅瀛子仗义替好友白苹报仇的描述,使这一异国形象具有了中国人仗义豪情的品格。这样的美国间谍形象无疑是中美文化交融的产物。
然而,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远比中美关系要复杂的多。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半个多世纪,正是日本觊觎海外领土,加紧侵略扩张的时期。无独有偶,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日本的谍报活动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日本间谍的许多重大行动都是直接服务于它侵略中国、争霸太平洋的目标的。他们不遗余力地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政治活动的马前卒,是其扩张政策的重要帮凶。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更是向中国境内派遣了大量的特工间谍。他们秘密潜入各地,竭尽所能地刺探中国军事情报。譬如,日本侵华头号间谍土肥原贤二,在华从事侵略活动长达20余年。中国人称其为“土匪源”,西方媒介则把他与名噪一时的英国间谍“劳伦斯”相提并论。正如理查德·迪肯所评述的那样:“关于劳伦斯那些神出鬼没的谍报活动的神话,已随着近来披露出来的一些事实而消失殆尽,……而土肥原呢,作为日本在满洲有史以来最干练的谍报军官的形象,却是一如既往,不可动摇。”[3]158此外,日本还利用美人计为其刺探情报,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效果。这其中最活跃且最为有名的人物是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
由此可见,虽然日本间谍为日本的数次侵华战争立下了战功,但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因而,《风萧萧》出现“妖魔化”的日本间谍形象不足为奇,这类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准确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对日本间谍的总体认识和“他者”想象。
徐訏笔下的异国间谍形象之所以迥然不同,除了社会集体想象物、时代精神等因素外,也与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和人生经历有关。
这位曾被称为“鬼才”的作家,曾于1936年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徐訏曾一度滞留于上海孤岛,后来在内地到处辗转奔波。日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在战争中体会到了屈辱感和危机感,也爆发出了高昂的抵抗情绪。作家在《风萧萧》中将抗战的时代背景融化到具体的人物内心世界中来表达,这种从心理角度来反映社会的写法显得更有底蕴。因此,作者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在《风萧萧》中塑造出了“意识形态化”的日本间谍形象和“亲善型”的美国间谍形象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