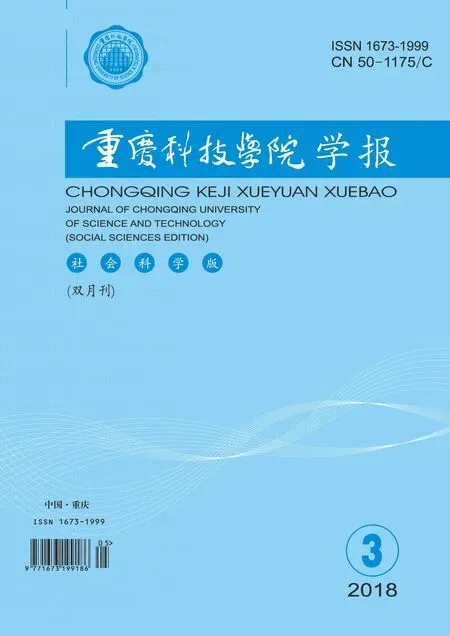酷儿理论的认知科学视角探析
——以《紫色》为例
杜 坤
早在20世纪70年代,“认知革命”所引发的多学科“认知转向”已经扩展到文学研究领域,但是,将酷儿理论研究与认知科学方法相结合还没有在英美文学界得到广泛认同。不过,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KosofskySedgwick)、迈克尔·穆恩(Michael Moon)等酷儿理论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认知科学能够为酷儿理论研究提供科学的解释和有用的模式,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尝试。2015年,《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在“认知酷儿理论”一章中,明确提出了认知酷儿理论。其中,文森特(J Keith Vincent)的 “心智上的性:酷儿理论与认知理论”(“Sex on the Mind :Queer Theory Meets Cognitive Theory”)一文,重点探讨了将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与酷儿理论如何进行有效结合。
一、认知酷儿理论研究概述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观点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主张心智和身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可以分离的事物,心智是一种不具有广延性的实体,其本质是思想,能脱离具有广延性的身躯的实体而存在[2]4。身心二元论涉及到一系列相关概念,如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者等。认知方法和酷儿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心智内外二分,主张克服身心二元论,以及自我和他人之间严格区分[1]200,反对性的“内在性”和性别“二元论”。
现代主流的价值观点认为,性别存在于我们自身内部,与个体身份紧密联系,从整体上决定着我们性格的不同方面。但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塞吉维克和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等人从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视角,运用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性别权力形式,质疑假定的“内在性”和性别“一致性”。《内外:女同性恋史和男同性恋史》(《Inside/out:Lesbian Theories,Gay Theories》)是最早讨论内外在问题的酷儿理论文集。该书的编者、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戴安娜·弗斯(Diana Fuss)在简介中写到: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哲学对抗像许多传统的二进制,一直是建立在一对相反关系的基础上:内和外[3]1。福柯在《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中认为,性别和性的形成是由外而内的。巴特勒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明确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塞吉维克在《暗柜知识论》(《The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不能用简单二分法来划分,这样不仅仅在束缚、限制同性恋者,更会对20世纪的西方现代思想和知识结构产生影响。可以说,酷儿理论研究者挑战传统两分结构不局限于性领域,还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常识。
认知酷儿理论研究着眼于对身心二元论以及“自我”“他者”区分的批判,致力于消解身心二元论观点,模糊“内外界限”。认知酷儿研究是对酷儿理论的继承、深化和发展。它运用认知科学关于人类心智、情感等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分析解读非常态题材的文学、电影等,主要涉及同性恋、双性恋、同性恋恐惧症(简称“恐同症”)等,消解文学的、心智的等一系列身心二元论观点,突破知识、权力、伦理等形成的“内外界限”,从而拓展了作品解读的深度与广度。
二、认知酷儿理论研究的不同角度
认知酷儿理论与酷儿理论的学科背景、方法路径有很大的差异。以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为代表的研究者,将研究分析视角转向了认知心理学视域;以迈克尔·穆恩(Michael Moon)、文森特(J.Keith Vincent)为代表的研究者,结合认知叙事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文学作品。
(一)酷儿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结合
赛吉维克认为,认知心理学中的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和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可以为酷儿理论提供新的研究模式。也就是说,与心智和情感结合的认知主义能够为注重精神分析的酷儿理论提供有用的模式。
赛吉维克利用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Silvan Tomkins)的情感理论分析羞耻和偏执狂,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羞耻的情感存在于大多数同性恋心中,因为他们耻于承认自己的身份。汤姆金认为,羞耻、惊喜、快乐、愤怒、恐惧、痛苦、厌恶、蔑视等都是情感的基本内容。对偏执狂的性取向研究在酷儿理论中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偏执”被汤姆金称为“强烈情感理论”(strong affect theory),是一个强烈羞耻或羞耻-恐惧理论,更是一个强烈的负面影响的理论[4]133。鉴于偏执与同性恋恐惧症的特别亲密关系,赛吉维克也希望为恐同症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在塞吉维克的著作中,“认知”这个词不断出现,如认知功率(cognitive wattage)[5]7、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5]97、认知优势 (cognitive mastery)[5]98、认 知 特 权 (cognitive privilege)[5]152、认知过度刺激(cognitivehyperstimulation)[5]25、认知间隙 (cognitive hiatus)[5]97等。尽管从这些冠以“认知”的词汇的使用不能直接推导出新的认知方法,但是,这样的“认知强度”表明,塞吉维克的酷儿理论的兴趣点在于“知道、有权知道、乐于知道、想要知道以及不想知道意味着什么,别人是怎样想和渴望的?”[1]201不仅如此,塞吉维克就性的“内在性”问题提出:“如何以及为什么我们自认为知道别人的欲望?为什么我们认为知道别人的欲望与我们的知识和自我欲望的无知有关?”[1]201她所讨论的不再是性的内容,而是关于“人类是否具有性别”这样的认知问题,超出了酷儿理论关于性别二分的范围。
赛吉维克晚年关注到心智理论。她希望通过认知科学研究成果能为《暗柜知识论》中提出的公理,即人与人之间不同,给予科学的解释。她探索了心智理论与情感理论的交互作用关系,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为文本分析对象,围绕叙述者逐渐产生的偏执,以及偏执产生的心智的多个原型的层次叠加进行讨论。通过结合不同的情感理论,以及对心智理论的阐释,展现出叙述者渐进的情感层次,使读者进入了叙述者难以预测的情感范围。在谈到心智理论时,赛吉维克认为,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的《我们为什么阅读虚构作品:心智理论与小说》(《Why We Read Fiction: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把对小说的讨论局限于心智理论本身。与丽莎·詹塞恩相反,她觉得自己的分析更像是一个精神分析移情。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这样做是否更有意义,即将心智理论嵌入其他理论或与其他理论结合,抑或是在某种意义上用平行理论概念化心智理论。但是,赛吉维克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对心智理论都还要进行再思考[6]144-165。她提出了6条评测标准[1]201,并明确讨论了认知文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阐释潜在心智理论的概念。然而,包括塞吉维克在内的众多酷儿理论研究者,在其早期作品或研究之初,都侧重关注同性恋者思想认知和欲望需要的消极方面。如果所有这些早期酷儿理论家能早一点对认知科学家的心智理论感兴趣,他们就可能会早一点看到对同性恋个体实行异性恋规范的这些操作是惩罚性的、投射的和偏执的[1]202,或许也就能早一点为酷儿理论提供一些认知科学的解释方法。
(二)酷儿理论与认知叙事学的结合
到目前为止,酷儿理论与叙事学及认知叙事学的交叉领域研究很少关注到性与性别的问题,尤其是酷儿叙事学领域内的文章和著作几乎很少关注。以迈克尔·穆恩(Michael Moon)和文森特(J.Keith Vincent)为代表的研究者结合认知叙事家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和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的研究成果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期开启“文学内在性”与“性的内在性”的关系研究。
赫尔曼指出,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经典叙事学认为,文学虚构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人的心智。也就是说,只有小说家才能看清其他人的心智,只有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才能让我们进入别人的大脑。例如,叙事学家多丽特·科恩(Dorrit Cohn)在《虚构的区别》(《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中描述的第三人称的虚构作品是“独特的认识论,允许叙事者知道现实世界中不知道的事情,并在叙述中把现实世界作为叙事目标表述人物的内心生活”。福斯特(E M Forster)在 1927 年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的第3章“人物”中,对虚构人物和真实人物最大的不同就进行了讨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从来不能相互了解……我们用外表的种种行迹使彼此大致有所认识,而且这些行迹足以用来让人们作为彼此社交往来、甚至亲密相处的基础了。但是,在小说中,只要小说家愿意,就可以让读者彻底了解小说人物。不仅小说人物的外在生活,还有其内心活动,都可以毫无保留的被作者揭示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小说人物看上去往往比历史人物、甚至我们自己的朋友,都更加轮廓清晰、形象生动。和小说中的人物相关的一切能够被人知道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知道”[7]123。但是,赫尔曼认为,经典叙事学家将“虚拟心智”和“真人心智”区分得太明显了[8]8,他将这种观点称之为“例外论”(exceptionality thesis),即当阅读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时,我们的心智活动是例外的,与我们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时的心智活动没有关系。这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我们阅读和分析小说时,以牺牲承载文学独特魅力的“内在论”为代价,陷入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思想,区分“自我”与“他者”、“内”与“外”。不仅如此,“例外论”还带来了2个假设性问题:第一,因为思想是“内部”的,世界是“外部”的,在日常互动的语境下,别人的思想依然在一个单独的内部域,与“我”分离;第二,这种分离的真实思想意味着,只有在虚构的语境中,“我”才可以直接进入另一个人的主体[8]8-9。帕尔默也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不能为研究小说中人物思想的各个方面提供更好的方法论,因为经典叙事学忽视虚构人物行为中的整个思想,过度强调私人的、被动的、孤独的、高度的内心思想,以牺牲其他类型的心智功能为代价[9]。
因此,赫尔曼支持心智“外在论”,反对“心智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他人心智的唯一的虚拟通道”这些说法[10]141-162。帕尔默在《小说中的社会心智》(《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中也说到,小说中,尤其是英语虚构作品中,意识不一定是锁在人物个体心智中的,而通常是散布在人物与人物的心智空间中的。并且,他们由于受认知心理学家心智理论研究的启发,认为我们阅读小说时和日常生活中是一样的,即通过他人的语言、表情、手势等途径了解他人想法是没有太大差异的。人类解读心智的能力是无法阻挡的,任何看似活着的或是被人化了的东西都能被人解读。因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心智理论既适用于虚拟的小说人物,也适用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时,虚拟心智外显,可进入而且使真人心智内化,不可见的“二分模型”就必须要让步于“梯度或渐变模型”(a scalar or gradualist model),或是让步于来自神经科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真实心智的“平行话语”(parallel discourses)[8]9。由此可见,赫尔曼等研究者对“内在外在”“虚拟真实”的二分模式的批判与酷儿理论对性的“内在性”的批判具有共同之处。并且,认知主义的“外在论”观点也使得一些研究者开始重新考虑性的“内在论”问题,以期认知科学的方法帮助我们超越“内在和外在”问题、超越心智和欲望的“内在性”问题。
波士顿大学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副教授文森特将酷儿理论与认知研究结合,分析了《源氏物语》中“欲望”(desire)的酷儿语法,从认知叙事学以及语言学的角度,帮助我们了解小说是怎样去个性化欲望的,挑战我们对文学的、心智的、性的“内在性”的理解。文森特认为,这种欲望机制被男性同性社交叙事(male homosocial narrative)调解,在这种特定的同性社交文本中,还可以发现对类似的“外在性”的强调。若是从认知视角进行解读,会大有裨益。在其他一些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森欧外(Mori ōgai)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性不是存在于个体内部,而是散布在三角恋中[1]209。酷儿理论家迈克尔·穆恩(Michael Moon)解读了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Tanizaki Jun’ichirō)的《少将滋干之母》(《Captain Shigemoto’s Mother》),即微缩版紫姬的故事。他谈到:“我们被迫认识到我们最深的和强烈的欲望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梦想和幻想只是他人欲望的副本、音频和录像带,我们的话语是假唱的循环,而是不断复制再生的欲望。”[11]21穆恩关于外化逻辑(externalizing logic)的描述就是酷儿解读和认知方法完美结合的例子:欲望似乎不是从内而外的展现,是从一个人物横向传播到另一个人物[1]214。因此,借用认知工具研究像《源氏物语》这样的文本,有助于我们超越“内在和外在”问题、超越心智和欲望的“内在性”问题。这与认知叙事学所主张的欲望似乎不是源于个体内部,而是散布在人物之间,这种联系通过认知的方式描述,体现了酷儿理论与认知研究的有机结合。
三、《紫色》中“酷儿”人物的思维(心智)解读
酷儿理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一种文化理论,强烈批判对性、性别等问题的二分法,不仅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12]。可以说,酷儿理论研究者挑战传统两分结构不局限于性领域,而包含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常识。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也是从挑战性别二分、消除异性恋霸权、构建和谐等角度解读作品。在此,从认知的视角解读《紫色》(《The Color Purple》),探讨作者在写作中是怎样挑战传统霸权制度并极力构建和谐的,个体如何突破性与性别身份的阻碍得以完善自我的,中心与边缘的界限被超越的,女主人公是怎样在抗争中成长的,即性别、身份二元对立的解构与重新建构。
依据丽莎·詹塞恩的“心智阅读”相关研究:我们根据他人的想法、感觉、信仰和期望来解释他们的行为[13]12。也就是说,基于人物的可观察的行为解释人物的特定心智状态。在这里强调的是叙述者和故事人物的心智阅读活动而非真实读者的心智。例如,读者在茜莉的叙述中,看到她可以用理性代替麻木的感觉,分析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她对于生活的认识已经不只是感性的描摹,一些细节的心理描述和自我感触有了逻辑的结构,她更多的是看到了生活的因果关系,还对事情有了自我的感受和判断。所以,文本通过心智解读可以展示人物人生不同阶段的心智状态和情感变化。例如,莎格为了安抚受伤的茜莉,她们之间有了第一次亲吻,从此确定二人的同性之爱[14]87。茜莉回忆起自己被继父强奸的画面,疼痛、悲哀的感觉似乎又被唤起,仿佛自己在重新经历当时的情景。顿时嚎啕大哭,泪流如注。莎格像母亲一般一把将茜莉搂在怀里,安慰她,一边亲吻茜莉的嘴,一边说爱她。认为不被人爱的茜莉第一次被人这样疼爱着,被歧视、否定与压迫已久的情感瞬间被激活,被释放,她回吻莎格,2个女人忘我地亲吻对方,直至精疲力竭,茜莉发现自己“像一个迷路的小娃娃了”[14]87。茜莉与莎格身体的触摸与爱抚,以及她们的话语,使得茜莉身心的极度舒展与愉悦替代了对性的恐惧,她变得平静了,有了安全感。从此以后,莎格取代了“某某先生的位置,和茜莉睡一个被窝了”[14]88。2 个女人宛如初恋情人,依偎在一起,享受二人世界灵与肉的完美融合。
茜莉和莎格从相识、相助到相知、相爱,缔结了同性爱、酷儿情,是对传统价值的挑战,不被主流文化接纳。这份特殊的“酷儿情”最终因为莎格的移情别恋而终结,虽然只持续了几年但是意义重大,因为这段“酷儿情”完成了对茜莉的救赎。茜莉在莎格的鼓励下离开家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朋友、有了时间和金钱,觉得自己很幸福。可以说,茜莉自我意识的开始和自我的完整性创造始于对女朋友莎格的爱。
从茜莉的叙述可知,最初,她用简单浅显的文字记录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与遭遇,倾诉自己的困惑与恐惧,很少触及内心的想法。后来,她能够叙述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大胆诉说自己的所感所悟。这些细节描述体现了一个备受压迫的黑人女性的成长,同时也是黑人社会的缩影。文本通过对细节的心智解读展示了小说人物人生不同阶段的心智状态和情感变化。
四、结语
目前,认知酷儿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理念和方法等成果较为分散,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不可否认,采用认知方法对酷儿理论研究具有极大的帮助:第一,有助于超越内在与外在的区分,冲破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第二,提供了一种方式,解读欲望是如何通过叙述传递或模仿的,而非简单地在文中“表达”出来的;第三,以去本体论的观点看虚拟心智与“真实”心智之间的差别,使二者都可以被接近和感知;第四,超越了性的真实与替代之间似是而非的区别[1]209。可以说,认知科学将酷儿理论引向新的方向,打开了新的探索空间,开辟了新的境界。当前,认知文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世界文学研究范围,因而,认知酷儿理论有待进一步探讨。
[1]ZUNSHINE L.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2]章士嵘.认知科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
[3]FUSS D.Inside/Out:Lesbian Theories,Gay Theories[M].New York:Routledge,1991:1.
[4]SEDGWICK E K.Touching Feeling:Affect,Pedagogy,Performativity[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
[5]SEDGWICK E K.The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25,97,98,152.
[6]SEDGWICK E K.The Weather in Proust[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144-165.
[7]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23.
[8]HERMAN D.The Emergence of Mind:Representat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English[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1:8.
[9]PALMER A.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133.
[10]Iversen,Stefan. “Broken or Unnatural:On 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 in Non-conventional First-Person Narration,” The Traveling Concepts of Narrative[G].ed.Mari Hatavara,Lars-Christer Hydén,and Matti Hyvärinen.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13:141-165.
[11]MOON M.A Small Boy and Others:Imitation and Initi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Henry James to Andy Warhol[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21.
[12]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2(2).
[13]ZUNSHINE L.Why We Read Fiction: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M].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12.
[14]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