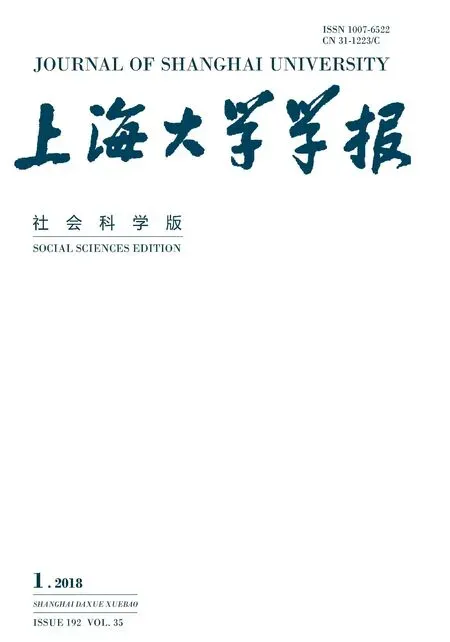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
——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田 瑞 文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阐释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它最先被班固收录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后被《文选》收录在卷四一中。这两个版本在字词上略有差异,而最大的不同则是《文选》比《汉书》在文章起始处多了一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①今之所见《汉书》景祐本(宋祁校本、庆元本、明监本、清殿本等)和汲古阁本(清局本等)两大版本系统中(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的《出版说明》、倪小勇《〈汉书〉版本史考述》,《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1期),均无此语;而《文选》五臣注卷二十一(朝鲜正德四年本)、六家注卷四十一(日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韩国奎章阁本)、白文本卷二十一(杨守敬过录本、九条本)等皆有此语,可知《汉书》之略与《文选》之录非后人转钞所致。由于《文选》的巨大影响,《文选》本《报任少卿书》也随之广泛传播,影响深远,《文选》本的这句异文该如何看待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 、“太史公牛马走”的学术史反思
关于“太史公牛马走”的解读,李善的意见是:“太史公,迁父谈也。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自谦之辞也。”吕延济也认为:“太史公,迁之父”,“言己为太史公牛马之仆,盖自卑之辞”。[1]宋吴仁杰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辨析,他认为“太史公”不是司马谈,而是司马迁本人,“迁被刑之后乃有此书,是时谈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为称耶?则知所谓太史公者,子长自谓也”。而关于“牛马走”的解释,他则认为是“先马走”之误,并征引文献以为正说:“《淮南书》曰:‘越王勾践亲执戈为吴王先马走。’《国语》亦云:‘勾践亲为夫差前马。’《周官·太仆》‘王出入则前驱’注:‘如今导引也。’子长自谓先马走者,言以史官中书令在导引之列耳。”[2]相对于李善、吕延济的注解,吴氏的这一解释更易为后人接受。钱锺书承是说,同样认为:“‘太史公’为马迁官衔,‘先马走’为马迁谦称。”“‘先马走’犹后世所谓‘马前走卒’,即同书札中自谦之称‘下马’、‘仆’耳。”[3]今人游庆学进一步论证了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中所言“前马”“先马”“洗马”为一事之观点。[4]范春义在对游氏观点补说时认为,“牛马走”在唐前的使用仅有此一例,只能说明唐前并无此用法,当为“先马走”之误。唐后人们关于“牛马走”的使用,“是后人沿袭了《文选》的错误写法,是以讹传讹的结果”。[5]以上诸家说法,大致认为“太史公”是司马迁本人,“牛马走”为“先马走”之误。但以往的研究中仍有一些问题未展开讨论。
首先是关于“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一句真伪的问题。以上所举诸家之说,都是在承认此句为司马迁原话的前提下展开讨论的,可见大多学者都以之为司马迁的原话。但也有学者认为:“《文选》本《报任安书》首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中之‘太史公’,当是‘太史令’之讹,很可能是后人据《史记》妄改,亦有可能这一句是编录《文选》的萧统所加。”[6]不同的意见认为:“萧统编选《文选》注重的是辞采,《报任少卿书》入选的原因也是由于它声情并茂,并非是为开篇首句,也就是说萧统断然不会去妄加套语。”[7]实际上,从《文选》书类文篇首自称语的成例上也可证此语非萧统所妄加。《文选》书类24篇书信中,除却8篇没有明确篇首自称语外,其余篇首自称语的基本成例为“名+白”,如“(曹)丕白”、“(曹)植白”、“(应)璩白/报”、“(嵇)康白”等,这种篇首自称语成例多见于魏晋时期。《文选》书类所选3篇汉代书信,《报孙会宗书》《答苏武书》皆无篇首自称语。照此看来,如果此句为萧统所加,按照成例,他要么如汉代书信无篇首自称语,要么如魏晋书信以“迁白”起句,但事实却非如此。还可进一步讨论的是,《答苏武书》以“子卿足下”起句,与《报任少卿书》篇首自称语下句“少卿足下”句式相类,如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为萧统所加,那么他也应该为《答苏武书》加上类似的篇首自称语。所以此句为萧统所加之说不能成立。实际上,“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的句式在汉代也是有成例的。如高帝五年诸王上尊号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8]又如文帝初立,群臣上议:“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朱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8]108又如汉文帝十五年,晁错等举贤良对策:“平阳侯臣窋、汝阴侯臣灶、颍阴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昆邪,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昧死再拜言”。[8]2291以上三条材料的基本句式是“官职+自名+‘再拜言’+‘××足下’”,《报任少卿书》起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句式正与之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牛马走”、“再拜言”二语在汉代的使用情况。“牛马走”为“先马走”之误已如前揭,文景之际的贾谊在《新书》中说:“楚怀王……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象使随而趋。”阎振益等注曰:“先马,《荀子·正论》:‘天子出门,诸侯持轮挟舆先马。’注:‘先马,导马也。’《字汇》:‘先,先马,前驱也。’”[9]《新书》中对“先马”的使用,也可证司马迁以之为自我谦称,不是凭空生造,而是有所依本。查考文献,可知“先马”“再拜言”二语主要见于汉初至武帝时,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之后几乎不见使用,这也可以说明,司马迁用“先马走”“再拜言”二语虽前有所承,却后乏回响,至于说后人妄纂此语以为迁言,似乎就更不可能了。因此,句式与句中语词的使用情况均可证明,此语当为司马迁所言。
其次是司马迁在书中自言“太史公”与作书时实际身份中书令之间的矛盾。虽然吴仁杰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矛盾,并以推测之辞说太史公为正职,中书令为加官,[2]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后人的回应,这一问题也没有被展开讨论。然而如果把这句话放到《汉书》本传中,问题就非常突兀地呈现了出来。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8]2725
班固在选录该书信时,可能就已经注意到了上言中书令与选文起始句中“太史公”之间的矛盾,但他也许未细究“太史公”一语的深意,在实录思想的指引下,如实记录了司马迁中书令的实际身份,而删去了书信中易使人疑惑的起始句。《文选》作为选集,可以不受史书上下文文意的限制,所以完整收录了该书信,因此就有了相对于《汉书》本的这句异文的出现。但无论是《汉书》的不录,还是《文选》的选录,都未能曲尽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以“太史公”自称的原意,特别是《文选·报任少卿书》对此句的补录,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司马迁的实际身份与言说内容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影响了后人对《报任少卿书》的理性解读,使司马迁阐释史的建构陷入到更深的迷障之中。
二、太史公与中书令:司马迁的自我身份体认
受《文选·报任少卿书》一文的影响,人们在解读司马迁的这封书信时,通常以为其身份就是太史公,而很少从他作是书时中书令的实际身份来展开对《报任少卿书》的讨论。实际上,在实际身份和书中自称身份的矛盾中,隐藏着司马迁更深的人生感慨。
“太史公”是谈、迁父子对太史令职责的历史性错位理解,侧重强调内涵其中的论著之义。传统关于“太史公”的理解,歧义纷繁,莫衷一是。张大可将诸多解释总为十说,“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曰尊称说;二曰官名说;三曰以官称为书名说。”[6]以上诸家在讨论时,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本韦昭、桓谭说而申论之,一是由当时制度推论之。韦昭、桓谭之说无史实可证,而制度之推论,也颇多皮毛不附之嫌。也许对“太史公”一语在《史记》中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是接近该问题的一种可行之策。在汉代,太史令是一种官职,其主要职责是“掌天官,不治民”。[10]从谈、迁父子的公务活动来看,主要是关于天文历法的,并没有体现出著述立说的内容。[11]太史令的这种职责特征还可从刘向校中书中得到进一步确证,《汉书·艺文志》载:“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太史令尹咸校数术。”颜师古注“数术”曰:“占卜之书”,[8]1701- 1702此说可证太史令的专业主要是体现为“占卜”的天官事。而谈、迁父子的著述成果《太史公书》则属于负责校对经传的刘向的工作内容,被列入“六艺略”下的“春秋类”。从刘向的这一处理可知,谈、迁父子的著述之事不在太史令的职责范围。但在司马迁的相关叙述中,作为太史令的父亲与自己,通常被称为太史公,如《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10]3319这一称谓的改变与谈、迁父子对太史令一职的独特理解有关。在谈、迁看来,其先人周室太史之职承流而下,即为汉代的太史令,而周室太史不仅“典天官事”,也内含着“论著”事,所以谈、迁父子虽职汉之太史令,但仍以先人“论著”为务,这就是司马谈在临终时切切之念“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的深层原因,而司马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0]3295的承诺也表明了他对此的认同。司马迁将太史令转称为太史公,意在强调汉之太史令与其先人周室太史之间的传承关系,尤其是“论著”层面的文化传承关系,凝聚着父子二人心血的《太史公书》正是这一认识的具象呈现。
《太史公自序》从重黎司天地起,写其后“司马氏世典周史”,这种叙事意在强调司马氏“典周史”的文化意义。然自“惠襄之间”司马氏的发展偏离了“典周史”的轨道,主要为武职(“以传剑论显”)或官吏(“市长”、“五大夫”),一直到“谈为太史公”才再次接续“典周史”的文化之统。对《自序》中出现十四次的“太史公”进行考察,可知其主要关乎天官与论著事,其中与论著事相关者有十条左右,可见“太史公”一语侧重指论著事,而如果把每卷序赞中的“太史公曰”也计算在内,这个侧重就更加明显。需要辨析的是《自序》中“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一语,表面上看似乎与天官、论著无关,但《报任少卿书》中已明言李陵之祸与《史记》写作之关系,据此可知“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语意在强调太史公的“论著”之意,这与书信开头所言“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一语正相呼应。
司马迁所言“太史公”虽有“典天官”与“论著”两层内涵,但却侧重指“论著”事,它承周之太史、周公、孔子等的论著精神而来。太史、周公、孔子的“论著”行为旨在尊礼则后,即司马谈临终前所言:“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而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10]3295司马迁向弥留之际的父亲所承诺的“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表明了司马迁的作书态度,他认为依事立义者是自周之太史而来的司马氏先人,依事立义的范例是周、孔,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执行者,这种认识与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及“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行为是内里相通的,也就是说司马迁假先人立义与经学家假周、孔而正经的套路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先贤往圣的光环来增强自我言说的价值意义。因此司马迁所言“太史公”,既包括依事立义的司马氏先人,也包括将司马氏先人所立之义具体书写下来的自己。先人与自己、立义与书写的对比中,显然先人立义是主要的,因此“太史公”一语偏指立义的司马氏先人,这也是称之为“公”的原因所在。司马迁理解的“太史公”虽与现实社会中的“太史令”一职有部分对应关系,但又远远超越了太史令的职责权限,更侧重于文化意义的建构与传承,这样去理解“太史公”,就能较好地解释“太史公曰”的价值评判意义以及《自序》中“太史公”的适用情况。其实无论是《报任少卿书》的直白还是《史记》写作的具体体现,都可见司马迁对个体荣辱得失的超越,以“作”者而自居的心态,这正是“太史公”一语的内涵所在。单纯职务之称的“太史令”不足以涵盖司马迁父子的这层认知,而“太史公”之称既涵盖了“太史令”职务层面的意思,更体现了“论著”者的文化立场。这便是司马迁以“太史公”作为《史记》叙事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之省称,少府属官。清齐召南《汉书考证》论之甚详:“唐六典曰: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司马迁为中书令,即其任也。不言谒者,省文也。洪迈曰:中书尚书令在西汉为少府属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虽典机要,而去公卿甚远。”[12]洪迈之言是就两汉中书令整体情况而言的,具体到司马迁为中书令,可谓“尊宠任职”,颇受武帝信任。
司马迁对太史公和中书令这两种身份实际上都是持认可态度的,只不过太史公是从文化心理层面上的认可,中书令则是现实人生成就获得感层面上的认可。以往学界多从文化心理层面,对太史公身份下的司马迁的行为进行阐释,而实际上,司马迁在写作《报任少卿书》时的身份是中书令,对这一身份的关注,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司马迁的身份与言说内容的深层关系。
司马迁虽遭宫刑,但旋即“为中书令,尊宠任职”,[8]2725甚得武帝信任,而司马迁也是以忠君的态度来对待武帝的。中书令秩虽千石,位却重要,“武帝晚年‘游宴后庭’,不去未央宫前殿朝会。由于百官包括尚书一般不能出入后庭,所以文书(有时是口信)上下要靠中书令传递。司马迁能任此职,虽然地位不算高,但这是枢机之任,必得武帝信任则无疑。”因此他早年宫刑所受的“损失已在随后几年‘尊宠’的中书令任上得到补偿”。[13]理解了司马迁写作《报任少卿书》时的身份和心态后,再来看书中所写“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8]2726等文字,就会发现这些描述正是他中书令工作的实录,他在对自己工作忙碌状态的叙述中特别强调了琐事的密度,这种表面上看似不经意的叙述,实际上想要给人传达的是武帝对其倚重的事实,而对此,他是引以为荣的。如果进一步联系到他在《悲士不遇赋》中“士生之不辰”的叹息,以及“恒克己而复礼”的人生持守,就更能看到中书令一职之于司马迁世俗人生价值实现的意义。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说:“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8]2736从司马迁的自述来看,他对自我“闺阁之臣”的身份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而不愿归隐岩穴不过是对这份世俗身份与地位的眷恋,这种观点与同时期东方朔“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10]3205的思想多所类似,因此,其所谓“从俗浮沉”就不过是不愿离开中书令之位的一个借口罢了。
以颂汉为主的《史记》的书写也可看做司马迁对武帝忠诚的表现。《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临终嘱司马迁以周、孔为榜样写作史书,“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的意见是史书的写作应以颂扬为主,对于父亲的遗训,司马迁的回答是:“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0]3295后来,在回答上大夫壶遂的质问时,司马迁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作史立场。他认为《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而汉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纵令“臣下百官力诵圣德,尤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10]3299这样看来,以《春秋》为模仿对象的《史记》的写作,既有“刺讥”,更有宣盛德。祝总斌认为在《太史公自序》、《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封禅书》、《儒林列传》等序中的论述以及“《史记》中所记史实,有关汉王朝、汉武帝伟大功绩的内容,更不胜枚举”,所以整体上看,《史记》对汉王朝、汉武帝是歌颂、肯定的。[13]58这种歌颂、肯定正是其忠君思想的体现。
《史记》在关于任安的叙事上也体现了司马迁为武帝讳的意图。戾太子事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北军使者护军“不仅为北军的最高检察官员,而且又是实握平时北军统兵大权的要职”,由此可以看出武帝对任安的倚重。[14]任安受节不出的心理是,既不愿与丞相刘屈氂一道镇压武帝的骨肉戾太子,也不愿与戾太子一道对抗武帝。武帝最初是肯定任安的忠心的,“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但后来因轻信钱官小吏的话,认为任安老吏奸猾,“今怀诈,有不忠之心”,遂“下安吏,诛死”。[10]2782- 2783武帝诛杀了对自己忠心的任安,显然是武帝的错。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与任安生平交叉甚密的田仁事,但在叙述田仁事时,只字不提任安事,后来褚少孙详细地补续了任安的事,更可见司马迁的有意不为。司马迁的目的显然是为武帝讳,反映了他忠于君主、维护武帝权威的观念。
以此来看,宫刑之后的司马迁并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言,因对武帝充满了怨恨而作“谤书”,实际上更多的是忠君思想的表现,是对待中书令工作的勤勤恳恳。问题是作为中书令的司马迁,虽身处实利,为什么却不愿言及中书令这一身份呢?这和他的士人情怀与当时社会对中书令评价不高的现实有着密切关系。
司马迁的时代,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宫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的盐铁会议上,御史认为:
今不轨之民,犯公法以相宠,举弃其亲,不能伏节死理,循逃相连,自陷于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御史主张以刑治政的观点,遭到了文学的反对: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夫何耻之有![15]
从代表武帝时代行政观念的御史的角度来看,“不轨之民”若“不能伏节死理”,那就应该“被刑戮”。以此来看,司马迁以“沮贰师”“下于理”而治罪,应属“不轨之民”,而他所谓“勇者不必死节”的说法,正是御史给“不轨之民”所指生路“不能伏节死理”的翻版,所以他也自然应承受着御史所言的“被刑戮”的结果。由此来看,将司马迁逼到宫刑的刑罚制度,并不是针对司马迁这一具体对象而设定的,它是武帝朝严刑苛法的一个部分。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对宫刑事件“事有大谬不然者”的性质判定,就把武帝朝普遍的宫刑制度说成专门针对他个人的刑罚设计,显然这种解释是不合客观事实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人对宫刑事件的理解,司马迁也因此成功地博取了后人对他“隐忍苟活”的理解与同情。
从文学的批评性描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无行之人”不仅不以宫刑为耻,反倒将之看做一种进身之路。不仅身残戮辱,而且捐弃礼仪,所求只是“恒于苟生”。“恒于苟生”的具体表现就是“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虽然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武帝朝除司马迁之外的中书令任职情况,但从武帝死后六年的盐铁会议对此的热议,也可以想象当时应有一些人是以宫刑作为进身之阶的。这样的一种仕进之路不仅伤身亏形,而且在文化层面上,也是品格低贱的,这一点可从司马迁给任安的书信中对自己中书令工作“又迫贱事”的描述中得以求证。因此,对于有着强烈士人情怀的司马迁来说,这恰恰是他最不能面对的一种身份,而问题正在于此,他的实际身份就是中书令。所以他虽因中书令而“尊宠任职”,但在文化心理上却是排斥这种身份的。
这种文化心理来自于“君子不近刑人”的传统观念,盐铁会议中,文学正是据此来批评那些以宫刑进阶的“无行之人”的。就文学所言的“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一语,郭沫若认为,“就刀锯”是司马迁“再度下狱致死”的明证,这显然是对“就刀锯”的误解,但他从文学言“载卿相之列”与《汉书》言司马迁“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来推断“就刀锯而不见闵”指的就是司马迁,是颇为可信的。[16]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等“久典枢机”,“用事专权”,[8]1427萧望之认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8]3284据萧望之所言,中书之选,本为贤明之士,只是到武帝朝时始用宦人。可以想见,在司马迁前,宦者为中书并未成为惯例,在士人一直是中书主角的文化传统中,以宦者身份为中书令的司马迁显然无法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认同,在“士人”、“宦者”、“中书”的三重角色里,司马迁想要的是“士人”与“中书”角色的组合,但集于其身的“宦者”与“中书”的角色组合却在“君子不近刑人”的观念中被特别凸显了出来。司马迁虽为中书令,却不愿提及此身份,因为与中书令捆绑在一起的是他毕生之痛的宦者身份。相对来说,司马迁更愿意以获得文化认同的太史公身份示于世人,这是他在给任安写信时,以太史公自称的主要原因。
三、《文选》本异文出现的背景考察
《汉书》在选录《报任少卿书》时删去的“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一语,在《文选》选录时被重新补出。《文选》补出是语与《文选》成书前司马迁接受史的演变有关。关于发愤著书的原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的阐释框架是:沮贰师——宫刑——作史,反映的是臣子之间的矛盾,不涉武帝;而自东汉卫宏已降的阐释中,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则被置换为武帝,新的阐释框架是:武帝——宫刑——作史,它反映的是君臣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是士人的知识权力与君主的世俗王权之间的矛盾。在这种逻辑关系中,《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显然成了试图规训帝王的士人代表,因此,其作史时的太史公身份也被看做批评世俗王权的符号而被特别强调。
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10]3321卫宏的这番言论将司马迁一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作史、李陵之祸、报任安书联系了起来,并构成了具有前因后果的叙事关系。在这个叙事关系中,司马迁对李陵之祸起因于“沮贰师”的怨言,①郭沫若:“《报任安书》是充满了‘怨言’的。”《关于司马迁之死》,《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导致了他最终的死亡结局,而李陵之祸的伏线却早在作《景帝本纪》时就已埋下,所以《景帝本纪》中直书景、武之短就成了司马迁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在这个解释中,作为直接原因的“沮贰师”仅仅只是宫刑的借口,深层的原因则是武帝与司马迁在《景帝本纪》书写上的矛盾分歧。这个解释建构了武帝因护己短而致罪司马迁的阐释框架。在这个阐释框架中,司马迁与武帝是矛盾对立的。因此,司马迁的宫刑之痛越是有怨言,对武帝的批判和谴责就越是猛烈。
但卫宏的理解与史实颇有不合之处,为后之学者所批评。《汉书》本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8]2737梁玉绳据此认为“明载本传,武帝安得见之”,[17]以之批驳卫宏所言武帝以《景帝本纪》怒司马迁之事不实。余嘉锡也认为:“考之汉书,迁之得罪,坐救李陵耳,未尝举以为将,亦无下狱死之事。则其言武帝怒削本纪,自属讹传,不可以其汉人而信之也。”余氏认为卫宏之所以有此认识,是因为“卫宏东汉初人……其时班氏父子书未成,杨雄等续太史公书盖亦传播未广,宏无所据依,故其所著书,颇载里巷传闻之辞”,“故其言无一可信”。[18]传言不实,是相对所传之事的客观性而言的,传言本身却真实地反映了所传之事的客观本相到叙事形象之间的转换轨迹。
卫宏这一观点的形成,与此前《史记》的接受有关。宣帝时,朝中郎官之属如褚少孙、杨恽等已经可以轻易地阅读到《史记》,杨恽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但官方仍禁止其在社会上公开传布,这恐怕与《史记》一书的性质有关。杨恽“始读外祖《太史公纪》,颇为《春秋》”。[8]2889虽然司马迁在给壶遂的解释中认为《春秋》“褒周室,非独刺讥”,但杨恽所言的“颇为《春秋》”应该是指孟子所言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即具有“刺讥”性质的《春秋》,也就是说,杨恽的阅读感受是《史记》以“刺讥”为主。成帝时大将军王凤关于《史记》的一段讲话,则进一步说明了《史记》不合于时的特点。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东平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成帝向王凤征求意见,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王凤对《太史公书》内容的解读固然是在天子与诸侯王利益对立关系的认知框架中进行的,但他的进一步解释则明确指出了《史记》与儒家经典的对立性质,“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8]3325《史记》所记内容与时代统治思想的冲突,是《史记》被限制流传的重要原因。但官方的限制无疑表明了《史记》与刘汉王朝的矛盾,这种观念就成了后来人们解读《史记》的一个基本认知前提。虽然自宣帝以降,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等“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19]以补《史记》自太初以来的历史,但在班固写作《汉书》时,《史记》却仍“十篇缺,有录无书”,[8]2724由此看来,“十篇缺”洵非一日。但十篇具体所指为何,班固却并未说明。魏人张晏认为“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等十篇,不过后人对张说多不相信,颜师古就认为“此说非也。”[8]2725就《景帝本纪》而言,是否在所缺十篇之内也颇多争论,余嘉锡根据自序中所述《景帝本纪》之旨要与纪中所载内容相比较后,认为“今景纪非太史公笔也”。[18]23回到卫宏的言论上,可以推测卫宏所谓武帝怒削景纪是要解释《史记》中何以没有《景帝本纪》的问题,本于刘向歆父子的《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十篇缺有录无书”可以为之佐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梳理出卫宏观点形成的逻辑思路:在《史记》旨趣与刘汉王朝统治思想矛盾的格局中,人们往往将两者的冲突落实到司马迁与武帝的冲突中,特别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对宫刑之痛的深度渲染,更形塑了人们的这种观念,《报任少卿书》与《史记》书写问题的相互作用,在此构成了一种互文性解读的接受场域。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卫宏就将景纪缺看成司马迁与武帝冲突的具体表现,并以此为叙事的逻辑起点,将李陵事件与《报任少卿书》的书写都勾连了起来,构成了一个看似自足的逻辑体系。
卫宏的这种认识在汉魏之际得到进一步强化,魏晋之际的讨论,进一步突出了《史记》写作与武帝形象建构之间的矛盾。东汉末年,董卓被杀时,蔡邕“闻之惊叹”,司徒王允怒欲杀之,蔡邕以“黥首刖足,继成汉史”为由,求王允放其一条生路,但王允的回答却是:“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19]2006王允的言下之意是司马迁《史记》“谤书”的性质形成于其受宫刑后。把王允的意思明言的是曹丕,曹丕在和王肃的一次对话中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汉武,令人切齿。”而王肃则认为:“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20]从王允到曹丕,他们认为“非贬汉武”作“谤书”是司马迁因宫刑而怀恨武帝的一种报复行为,而王肃的回答则强调司马迁的实录触怒了武帝,武帝怀恨在心,借李陵事件欲杀司马迁。这些讨论虽然与史颇多不合,却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史记》的认识,即《史记》的实录非贬了汉武,汉武在李陵事件中借刀杀人,司马迁虽以宫刑逃过死劫,却悲愤不已,加大了《史记》对当朝的批评力度。
从《报任少卿书》中因“沮贰师”而宫刑,到因“非贬汉武”而宫刑,宫刑之因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些转变的指向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史记》中的讥刺之言的。长期以来,人们在对武帝的独断专制进行解读时,也对遭受不公待遇的司马迁致以同情,这种正义与权力对抗的思路就构成了司马迁接受史的一个基本阐释框架,这一阐释框架也成了后人理解司马迁《史记》写作的一个基本认知前提。
《文选》选录《报任少卿书》一书时,《史记》已经成了司马迁人生的象征性存在,是司马迁精神世界的全部,是司马迁与社会历史之间最重要的一重关系。因此,《史记》作者的太史公身份也就成了司马迁的主要身份,所以在时人看来,用以控诉宫刑之痛,详述发愤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的主体也自然应是“太史公”。在这种接受背景下,《文选·报任少卿书》中补录“太史公牛马走”一语也就不显突兀了。因为《文选》的深远影响,后人几乎很少再去细绎《报任少卿书》书写时,司马迁自言的太史公身份与实际的中书令身份之间差异的隐曲。而单纯以“太史公”身份去解读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的血泪控诉,固然有助于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理解《史记》的书写,但也遮蔽了中书令身份下司马迁与武帝的微妙关系对《史记》书写的影响,使后人不能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史记》、《报任少卿书》的全面认识与正确解读。
[ 1 ] 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764.
[ 2 ]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 钱锺书.管锥编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25,624.
[ 4 ] 游庆学.走狗?牛马走?先马走?[J].汉字文化,2006(3):39- 40.
[ 5 ] 范春义.“牛马走”补说[J].汉字文化,2007(3):88- 89.
[ 6 ] 张大可.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J].人文杂志,1983(2):95- 103.
[ 7 ] 程远芬,等.“太史公”考释[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5):23- 25.
[ 8 ]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 ] 阎振益,锺夏.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249- 258.
[1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田瑞文.司马迁对太史令职责的理解与《史记》写作[J].史学月刊,2009(5):113- 120.
[12] 齐召南.汉书考证[M]//班固.汉书//文渊阁四库全书.
[13] 祝总斌.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M]//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53- 55.
[14] 袁传璋.从任安的行迹考定《报任安书》的作年[J].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2):138- 145.
[15]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584.
[16] 郭沫若.关于司马迁之死[J].历史研究,1956(4):26.
[17] 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278.
[18] 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M]//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17- 19.
[19]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25.
[20]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