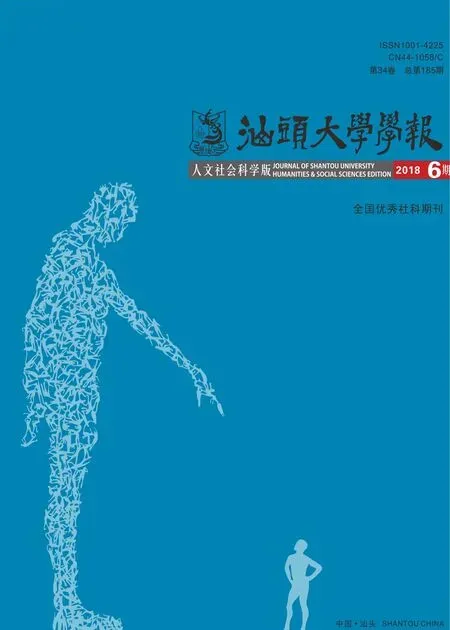《长祥嫂子》中的“鲁迅况味”
——兼及王富仁先生身心间的“鲁迅血脉”
彭小燕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富仁先生发表过两篇小说《长祥嫂子》(《上海文学》1980年8月号)和《集邮者》(《长安》1981年3月号,收入《小说选刊》1981年第4期)。这两个小说发表时的署名都不是实名,但据《王富仁著译目录》①这份著译目录在汕头大学文学院的部分硕士研究生以及网络平台上流传,据悉为王富仁先生生前亲手所定。的记载,两篇小说都是王先生所作,小说的语言初具风格——以洗炼、简劲见长,具“鲁迅风”,内涵上则人道主义色彩浓厚,透着一股浓浓的俄罗斯“小人物”题材小说的神韵,这篇小文拟对《长祥嫂子》一篇中几乎随处漫溢的“鲁迅况味”作一辨析。
《长祥嫂子》,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悲剧:是1949年以后的新社会了,一对原本幸福的长祥夫妇,再加他们善良、勤勉的父母,一个洋溢着活力、温暖的家庭,如何因为长祥嫂子被强暴,长祥哥哥冷酷地离掉妻子。其父母也无奈地接受这结果,整个家庭从此寒凉起来,幸福、温暖、活力不再,长祥嫂子则成了一个疯女人,音讯无闻,踪迹难觅。
《长祥嫂子》这标题就跟鲁迅的《祥林嫂》“长的神似”,小说文本亦随处可见样式各异、内质则具有某种整一性的“鲁迅痕迹”。小说一起头就呈现出一种近乎莫名的精神储势,长祥嫂子还没有出场,小说首先写的则是后来强暴长祥嫂子的三孬和长祥哥哥(数年后即为长祥嫂子的丈夫。)之间的一次惊险的“暴力冲突”。“敦实实的”“长得象头小黑熊”“打起架来又狠又辣,劲头又特别大”的三孬,“有一次,不知为什么,长祥哥哥碍了他的眼”,②本文所引《长祥嫂子》小说文本均出自《长祥嫂子》,《上海文学》1980年8月号,以下不再另注。于是这一幕就来了:
见长祥哥哥走过来,便照他一贯的“战法”,把长祥哥哥揍了个底朝天。长祥哥哥仰面躺在他的胯下,不挣扎,也不哭叫,也不喊爹求饶,任他怎么揍也不吭声。三孬实在打得累了,也只好破了惯例,站起身来。谁知长祥哥哥从地上爬起来,径直奔到他妹妹身边,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儿,把他妹妹的耳朵割了一个大口子,扭头就跑了。
小说写长祥哥哥干下的“这一件事震动了俺村的孩子界”,然而,“我”虽然其时年龄很小,却心情已经复杂得紧:
当天过午我便听说了。我到战地“考察”的当儿,地上的血迹还历历在目。但不知怎的,我颇有不满意长祥哥哥的地方,我也恨透了三孬,也同意他向三孬进行报复,但总还觉得里面有些不大带劲儿的地方。
那么,究竟哪里不带劲儿呢?其深度的隐义或者就在鲁迅的这段话里了:“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1]3卷49长祥哥哥抽刀报复三孬是可以的,然而,应该对着身为强者的三孬本人而非三孬的妹妹——一个女孩,一个弱者。可见,王富仁先生透过孩童之“我”的“不带劲儿”所暗示的内涵是极具鲁迅神味的,认同的是长祥哥哥拒不求饶、敢于愤怒,质疑的是长祥哥哥的愤怒找错了对象,也伤及了无辜。
再试看下面的一段:
别看二伯父整日价不言不语,心里可开通得很哩!他经常叫我讲说报纸上的事儿,提些有点好笑的问题。有一次,他郑重地问我:“毛主席到底坐了龙庭没有?”我向他解释,这是新社会,毛主席是为咱穷人办事的,和封建皇帝根本不同。他说:“这我知道。可是不管怎么说,反正毛主席不是个凡人,你看这几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天数哩!多少年一个真龙天子下凡,我看毛主席就是真龙天子!”他从心眼儿里喜欢新社会,因而也崇拜“进步人”。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的进步观念主要有两条:一是入党、入团、当模范;二是当干部,干部越大,当然就越进步。显然,这一幕令人很难不想起鲁迅的小说《风波》,虽则“龙庭”“真龙天子”等所引发的想象、心思并不同于《风波》,但是,百姓、民众内在的心思实无本质的差异,对于现实中的“上面人”:毛主席是最大的干部,最进步的、最可以崇拜的,是“真龙天子下凡”。入党、入团、当模范,也是足够崇拜的,词汇是变了,但是崇“上”(同时意味着驯服)、唯“上”(“上面人”“进步人”)是尊的“小民百姓”意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民人生活中的中古式、封建式“文化-精神”氛围在内质上基本未见大的变化。从崇尚独立思虑、自主判断的现代人、现代文化的视角看,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二伯父以及“在重要问题的观点上”“永远和二伯父一致”的二大娘都是并不知晓这问题的症结的。再看二大娘心中口里的旧式文化因子吧:
她会讲好多故事,好像永远讲不完似的,什么“牛郎织女”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了,“孟姜女哭长城”了,“郭巨埋儿”了,等等,她全会。有时还讲些轶闻轶事。记得她有一次重病之后,对我说:在她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两个鬼站在她炕前,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拿着绳子,要绑她到阴间去,她向他们哀求,但他们说什么也不放过她。待到二伯父醒了,喊上两嗓子,便把他们吓跑了。
这样的二大娘,在其精神实质上,与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那个阿长、长妈妈也是颇为相类的吧。很大程度上,二伯父、二大娘实在是“新社会里的旧儿女”,令人很容易联想起鲁迅在其众多小说中重度呈现过的历史图景:晚清王朝覆灭之后,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新民国下的旧儿女”们。短篇如《长祥嫂子》,其对“历史—社会—文化”的深沉解读意向明显地追随着鲁迅文学的轨迹,而独具某种虽短而意欲钻透“历史—文化”壁障的精神气势———创作出这类的富于“历史—文化”穿透意识的小说,对初中时代就阅读“鲁迅”,一生精神都深受鲁迅影响的王富仁先生来说是并不奇怪的。[2]11-15
因为儿媳妇正走在“进步人”的路上(入了团,当了小组长),二伯父夫妇对于儿媳妇“常要和男的在一起开会”虽然“有点点不满”,但也不表示异议了。但是,悲剧也正在这条同去“进步”的路上发生了,随着悲剧局面的尽显,《长祥嫂子》在形式乃至韵味上都离《祥林嫂》愈来愈近了。
看小说描写的长祥嫂子在其人生路上的系列神情吧:
叫她去医院看看,她也不去。神情也恍恍惚惚的,眼睛常常直瞪瞪地望着点什么,忽然又会涌出几串泪珠。
过了几天,她不再流泪了,只是神情更加恍惚,眼光直勾勾的,有点怕人。有时象要想对哥哥说什么,但嘴唇动一动,又不说了。
嫂子知道她没有挣得一丝希望,怔怔地跟他走到公社里,又怔怔地拿着一张离婚证回到家来。
这种种描写,恍惚那一位痛苦、绝望的祥林嫂已经转世投胎,行走在新社会,并且仍然在遭遇着生活的痛苦和绝望。长祥嫂子是被三孬,一个在新社会当着民兵连长的“进步人”强暴了。①小说里这位新社会的民兵连长三孬,后来“经常出入地主庞得贵家,庞得贵总是笑盈盈地送他出来,迎他进去,可庞得贵的十八岁的女儿庞小娟却有时眼圈哭得红红的。而三孬便也不再追逐长祥嫂子了。”新社会的这位民兵连长三孬并非二伯父心念间的可崇拜的“进步”人,而是一个依恃点滴特权动辄欺辱往往不敢声张的弱势民人的作恶者——新时代的伤人、吃人之鬼蜮仍是各种存在的。恶,绝没有那么容易地在人间收敛住自己的言动。小说告诉我们,这位民兵连长在后来的四清时期是被政府判刑了,但被强暴的长祥嫂子也被丈夫冷酷弃置、决绝离婚:
“你饶了我吧!这不赖我呀!长祥,我的好长祥呀!你就饶我这一次吧!”
长祥哥哥弯下腰,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拖出了院子,“嘭”地一声关上了大门。
是这对小夫妻原本就感情不佳,因而经不起生活的一点波折而弄到如此惨绝么?并不是。试看长祥哥哥在不曾知晓妻子被强暴之事时,对情绪极为低落、神情颇为痛苦的妻子的温暖安慰:
一天夜里,长祥哥哥主动躺在妻子身边。把她搂在怀里,从来不会说温存话的他,也不得不找点温存话说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爹,娘,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为什么不痛快,你就说出来嘛!闷在心里,不光苦自己!”
那么,这对夫妻的情义本是十分不错的吧,长祥哥哥也绝非一个寡情的丈夫。然而,这也抵挡不住因妻子被强暴而降临的残忍的离婚。悲剧的高潮还在延伸,小说继续写到:
伯父、伯母知道后,虽然伯父叹了几天气,伯母流了几天泪,但自然儿媳失了贞操,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四五天之后,二伯母正在北屋门口做针线,长祥嫂子突然撞进来,披散着头发,满脸污垢,飞也似地走到屋门口,噗通一声跪下来,在地上像捣蒜般咚咚地叩着响头:
“娘啊,我不能孝顺你了,我给你叩几个头吧!”
二伯母的眼泪也簌簌地流下来:
“儿啊,咱娘俩的命都不好哇!”
这里最经典的一个“鲁迅式描述”又出来了:“但自然儿媳失了贞操,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与《祝福》里的一个句子是极其神似的: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1]2卷12
没错,话语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是,话语间明显存在的对某种“既有规矩”“已有观念”的无条件驯服则十分神似——不仅仅一介平民的二伯父夫妇得驯服,威势如鲁四老爷也是要于此驯服的。实质上,如同并非恶、奸之徒的鲁四老爷(毋宁说,鲁四老爷算得上一个正经严正的旧式乡绅。)一样,伯父、伯母更并非恶、奸之人,小说中的他们足够勤勉、善良、温和,但面对儿媳被强暴、儿子与儿媳悲惨离婚的不幸结局,二老不仅无所异议,而且认定的就是应该没有异议。二伯母作为婆婆对长祥嫂子也并没有任何的恶意、不满,但即便如此,她也帮不了悲苦中的儿媳,她在心里就觉得没法子去帮什么,只落得一个悲叹婆媳俩共同的苦命的份儿。儿媳被离掉,疯了;儿子没人做伴,成了多年后“也没有再娶上一个人儿”的“够可怜的”的长祥哥哥,整个家冷清,没了活气,话极多、人也极活泛的二大娘变得“沉闷”而且“也真看得出老来了。”显然,这个家在不得不置长祥嫂子于绝境(一个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绝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的绝境。)的同时,也走上了其自身的毁败之路。这是真正的毁人兼以自毁,并且始终没有见到对此番不幸当负真正责任的强暴者“三孬”的愤恨情绪、惩罚意念。
不仅如此,在“我”姐姐家,五人参与(姐姐夫妇及父母及弟弟)的对长祥嫂子惨剧的议论中,有四人都绝没有异议的也正是:在强暴发生之后,长祥哥哥选择离婚是没有法子、不得不如此的事情。这四人说及此事的语气和内容尽管各个不同,但却没有一个人对长祥嫂子的被离婚生出过异议。这其中“我”姐夫的母亲这位旧时代的过来人就直接认为长祥嫂子的失身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女人,就得先守住自己的身子。老年间——”,她大概想表达的是:老年间,失身的女人是要自尽的。她的话被她活在新时代的丈夫打断了:“老年间!老年间!老年间你讨饭!”“我”姐姐则反驳自己丈夫所说的长祥哥哥“做得也太有点狠了”的话,争辩说:“狠不狠还不一样,反正都是一个‘离’!”值得深思的是,议论中的旧、新两代男性多少显露出某些时代的“进步”,而旧、新两代女性反而在不知不觉中见出了她们自身的驯服之“狠”、中(陈腐观念、文化)毒之深:女人被暴徒失了身子,在旧时代是要自尽的;在新社会不自尽了,那被离婚则是必须的——这是女性们自己说出的话啊,验证的则还是鲁迅的透彻之语:“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1]7卷82——敢说,这样的小说写法,王富仁先生是无意的么?考虑到先生在初中时代就沉迷的“鲁迅阅读”,其有意为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参与讨论的四人跟长祥嫂子的丈夫、公婆一样都无意在惩罚强暴者三孬的问题上有所用心——当“我”姐夫的胞弟,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表现出应当重罚三孬的强烈意愿时(值得注意的,即使是这位更多地长于新社会的年青人对于长祥嫂子被离婚的事情也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意见,毋宁说,《长祥嫂子》一篇是并没有展示他对离婚一事的直接态度的。)小说呈现了极具暗示意味的场景:
我姐姐讲完长祥哥嫂离婚的过程,我姐夫的十七八岁的弟弟便紧接着追问:
“三孬呢?”
“三孬被政府判处了五年徒刑,现在还在牢里。”姐姐说。
“我看该枪毙!”
可是没人回答他。年长的人都像在沉思一点什么,院子里静静的,只有西屋墙角下一个蛐蛐“苏苏苏”地叫着。
这是整个成人世界的死一般的沉默!因何会如此沉默?
仅仅因为三孬是一个身体壮、力气猛的“进步人”,而人人包括最相关的长祥哥哥都懦弱地不敢念及对他的重罚了么?事情恐怕并非如此。王富仁先生在小说的第一段就作了可以说与此相关的一点铺垫,前文讲到过,长祥哥哥自己曾被强势的三孬暴打过,但是,心中并不甘心的长祥哥哥一俟三孬松开暴打之手,便闪电式报复回去,用刀割伤了三孬的妹妹——没错,他的问题在于没有直接向三孬本人报复,但毕竟,胆敢当面割伤强势者三孬的妹妹多少也能够确证:如果长祥哥哥本人觉得必须的话,他至少是有可能并不忌惮三孬的威势而对三孬有点无论正当与否、匹配与否的复仇行动的。那么,残忍离婚自己的妻子而丝毫无损于三孬及其任何意义上的关联物的长祥哥哥也好,绝望、无奈地忍受妻子儿媳的离婚也一样无意于怒目三孬的二伯父、二伯娘也好,唏嘘长祥哥哥一家人的不幸而同样无意怒目于三孬的亲戚乡里也罢,究竟是笼罩在何种文化心理里而心安理得、处之泰然的呢?对此,半个多世纪前的鲁迅是有过深刻议论的:
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坟·我之节烈观》)
读完鲁迅的这段精髓议论,前文的疑惑或者可以稍解了:“观念—文化”的“吃人”是在堂而皇之的“伪道德”大旗下公行的,你即使真诚地为人的悲苦流泪(形如长祥嫂子的婆婆)也难以生出足够对峙整个恶性文化系统的个性化力量来!要对峙整个的“吃人”文化系统需要诞生新的思想精神之源、道德秩序之源;然而,这并非不可创造的事物,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是在这条创造之路上生成过新的关爱人间生命、对峙非人律例的精神果实的。鲁迅的“文学—精神”世界就异常饱满地储藏着丰富的中国现代精神之果。艰难、坚苦的是,诸多新的精神果实生成于知识层,却也大抵停留于知识层,尚未有效地抵达、触及更广泛的国人群体——尤其是处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
在《长祥嫂子》的故事里,新社会的“新”,是似乎离婚取代了自尽,似乎是有进步的,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此被离婚的,并无文化自觉意识的长祥嫂子在精神上自是入了死路,其整个生活也随之被判了“无期之死”,发疯几成必然。而经由鲁迅话语的引领,我们知道,正是一种文化痼疾(“贞操—节烈”观念),正是这一古旧的文化毒素——一个毁灭生命的“文化观念”,把长祥哥哥及其父母捆绑在毁人(于长祥嫂子的人生)自毁(于自家的幸福)的悲剧轨迹里,难以自拔自救,更难以去救助分明最需要他们的同情、帮助,他们也完全能够救得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长祥嫂子。长祥嫂子受暴徒之辱而没有去死,她本人也自感有罪而至于跪求饶恕,长祥哥哥竟直接判她:“贱女人,还有脸说,你给我滚!”可以说,王富仁先生创作《长祥嫂子》,他是自觉地藉着鲁迅的思想资源来完成对国人精神现状以及中国既有文化之非人毒素的深刻批判的。面对《祝福》中祥林嫂的悲苦终局,就有学者深锐地指出,祥林嫂的死“这一谋杀案没有真正的被告和凶手,因而全部是被告和凶手”,连小说中的“我”也难脱干系。[3]184而我要说的是,在一个被“吃人”之文化观念驾驭的众数世界,致死祥林嫂的“凶手”们甚至是包括了知识缺无、醒悟不够的祥林嫂本人在内的。在“寡妇不祥”、寡妇再嫁有罪的道德、文化氛围里,在“节烈”观念弥漫整个社会的时代里,虽不乏顽强生存意志,敢于出逃婆家的祥林嫂本人也是强悍拒绝再嫁,竟至于自杀式撞头的。而这只是祥林嫂“砍向”她自己的一处细节而已。比之祥林嫂,新社会的长祥嫂子的确是有所进步的吧,她已经并不像祥林嫂那样驯服于节烈的观念而不惜自残自死,对于所谓的“失了节操”,她也还能够自辩一句“这不赖我呀!”
当然,鲁迅的《祥林嫂》对众人于“祥林嫂之苦”的实质性茫漠和无所用心,对鲁四老爷夫妇、柳妈的助力“祥林嫂之死”,对新派知识分子“我”的无助于苦难祥林嫂,皆有深刻的、本质性的揭示。鲁迅所暴露、批判的旧时代是黑漆漆一片,难寻光亮的。王富仁先生发表于1980年的《长祥嫂子》,对新兴社会的阳光还是有多方展示的——那个虽则思想解放的时代,也还必须地要求着这样的展示吧。比之风格冷凝、悲风飕飕的《祥林嫂》,《长祥嫂子》多了几许暖意——很有留着眼泪讽刺的“果戈理风”。小说前半部分的叙述有一种轻松、温情的风格:不仅“我”对长祥嫂子纯洁、真挚的“爱”怜、牵挂,让人心里暖暖的;就是长祥嫂子出事前的家中氛围,也很有几分春日阳光的甜味儿,并不似《祥林嫂》几乎整篇冬日笼罩的风格:
在这时,我便一个人在旁边笑。但在这无穷无尽的拌嘴中,我感到一种温暖和谐和,它们象钢琴的各个音键上发出来的音儿,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异常协调,共同奏出了一曲和美的家庭幸福曲。我母亲也常对我说:“想不到你二大娘这么有福,娶了一房好儿媳妇。”
真是幸福、甜蜜的家味啊——甚至谐和到长祥嫂子的公婆、丈夫都已经能够并不在意结婚多年的她一直未能生下一儿半女,这是新社会的新谐和吧——然而,这“新”还是有限的,也是脆弱的,这一切,在长祥嫂子对丈夫坦白自己被三孬强暴过的那个夜晚遽然崩灭了。这样的“新”还不足以保护好中国人的生命、中国女性的生命。这里,还可以说《长祥嫂子》营造的家味愈是甜蜜,它后来的悲剧就愈令人唏嘘。
《长祥嫂子》在始终温情的叙述风格里也自觉地抵达了“陈腐观念”、文化毒素吃掉人之幸福,吞噬着生命而又令人们找不出具体的见血之手的深刻地带。面对长祥嫂子发疯、失踪的悲苦终局,当你仔细去搜寻某一个具体的唯一性的一步到位的加害者时,也是找不出来的。而当你去寻思哪一个环节(仅仅一个就够了。)足以斩断长祥嫂子的悲剧时,你会发现绝不止一个环节而是诸多环节都是可以独立地自足地对长祥嫂子实施地救助的:如果三孬不是那么一个无耻、恶性的暴徒;如果长祥哥哥已经不驯服于所谓的妻子贞操念头;如果长祥哥哥的父母也能够并不驯服于有关女人的贞操旧念,如果他们可以出面劝和几番;如果“新社会”的“新文化”足以让长祥哥哥一家在计较长祥嫂子的贞操问题时受到周围人群的非议而非认同;如果周围人群可以出而为长祥嫂子辩护一番……凡此种种皆未能出现。这在我看来,正是深受鲁迅影响、俄罗斯文学影响的王富仁先生有意为之、用心良苦的小说写法,他藉此要传递的深刻、彻底、独到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在他评价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是被表述得相当明确的:
《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他安分到了近于愚蠢的程度,对上司忠实到了近于奴隶的程度,对职守尽责到了刻板的程度,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摆脱掉悲苦的命运。他悲惨地死去了,但谁又是杀害他的凶手呢?是“某一位要人”吗?是“抢劫犯”吗?是嘲弄他的同僚吗?都不是,又都是,是他们综合起来的整个社会。[4]49
他(指果戈理—笔者)已经不满足于只揭露个别人的罪恶,已经不满足于只反映某些特殊的事件,而开始按照自己的认识来展示整个社会的沉滞和糜烂。他在谈到冯维辛和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的时候说:“……是社会原因,而不是个人原因,推动了我们的喜剧家。他们不是起来反对一个人,而是起来反对所有的罪恶行为,反对整个社会脱离开正直的道路。”(原注为:转引自新文艺出版社版《果戈里的戏剧创作》第8页。——笔者。)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他向自己提出了“切实而跟本地探索社会”的任务……[4]48
或者也可以说是受制于时代的言说边际,《长祥嫂子》虽秉持温情的述说风格却并不乏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审视与批判意图:
我听他们的谈话来回地兜着圈子,似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压在心上。我心里也有点乱,有点理不清头绪,似乎有好多话,但又没法表达清楚。我忽然想起二伯母说的那两个鬼。我想:解放后,广大农民走上了幸福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两个鬼,一个是像三孬这样的坏蛋们,这是一种有形的鬼。一个是几千年封建制度造成的农民的一些封建落后意识,这是一个无形的鬼。这两个鬼虽然不像解放前那么为所欲为了,但还有,还伏在农民的身边,一有气候,便出来伤人,吃人。当这两个鬼结合起来的时候,便更加可怕。就说长祥哥哥吧,要没有那可恨的“贞操观念”,也不至于把长祥嫂子和他自己一家害得这样苦哇!
在这样的小说文本里,是有着不可小觑的社会认知价值和值得记忆的文化努力的,其中也深有对鲁迅精神的血肉记取——其“吃人”二字彰显的“鲁迅印记”就是触目惊心的,在1980年代,这也是足够令有心人思绪纷纷的语汇。
令人瞩目的另一个议题是,《长祥嫂子》的基本情节结构极其类似于《祝福》《故乡》,乃至《在酒楼上》等小说,即悲苦主人公的身旁除了一群对其惨苦行状大抵抱以旁观态度的众人之外,还存在一位“我”。这个“我”最触目的特点就是在精神上与众人不同,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形如祥林嫂旁边的“我”、闰土旁边的“我”、顺姑故事旁的吕纬甫、祖母身世间的魏连殳一般,长祥嫂子的身旁也有一个“我”。长祥嫂子身旁的“我”的“新”与其众多“前身”的“新”,还携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信息:前者的“新”是时至20世纪后期意义上的“新”,这个“新”是已经相当程度上秉有后者之“新”的“新”,是双重的“新”,它是一种相当程度地秉有晚清以来直至20世纪诞生的中国现代新的精神传统的“新”。长祥嫂子故事之旁的“我”(或者说,《长祥嫂子》的显在叙事者)就有着很多鲁迅式的词汇、句子、典故和文学隐喻可以便捷地用来传递读者群中“你知我知”的精神信息——不仅“长祥嫂子”暗示着她与祥林嫂的血脉联系,此外的“龙庭”“吃人”等等语汇、句子也显示着《长祥嫂子》一篇有“鲁迅传统”可依而呈现的“言简意赅”、点到为止。同时,长祥嫂子身旁的“我”还是有新的历史经验、历史体验的一个“新我”:他眼中的历史既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还包括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历史。
然而,无论是祥林嫂、闰土、顺姑、祖母之旁的“新型知识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留洋归来者),还是长祥嫂子身旁的新社会的“大中学生”“大学生”(暑假归来者),由彼到此,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社会的表面变迁亦可谓剧烈,但世代更迭中的知识人对于悲苦者的同情更多的时候依然仅仅是同情,改变的意愿、心痛的情感尽管或隐或显的存在,但改变的路径——甚至,参与相关议论的路径都依然难见,先觉者依旧孤独,民众还是混沌,苦难照旧延续,那么,启蒙不正是很需要继续吗?!
甚至,这一“知识—文化”之“我”与小说中悲苦主人公及其身围现实之间的联系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称‘归乡’模式”(这也是尤为“鲁迅式”的一种叙事模式。)[5]37-39间生成的。换言之,在“知识—文化”之“我”与苦难生存现实之间,连实际有效的时空关联都是短暂的,那么,知识者启蒙群人的时空、乃至路径又何在呢?在不乏生活悲苦的群人世界中,秉承新的文化、现代意识、人道精神的知识者:在场,来了,看到了人的苦,感叹甚或沉默,而后离去;直至,再次的在、来,再次的看……再次的离去……。一次一次地轮回,一代又一代知识人“同情之眼”的更迭……。从《故乡》《祝福》之“我”,《在酒楼上》之吕纬甫,《孤独者》之魏连殳,到《长祥嫂子》之“我”,新型之“我”与依然旧式人间、老旧苦难之间的关联在内质上亦确乎不见怎样的大变。有心的人们,不禁要追问下去:意味新型“知识—文化”的“我”所“储蓄”的精神之光究竟如何实质性地影响、变异悲苦主人公所处的现实而带来国人生存处境、人生命运的真正改变呢?这是难的问题吧——中国现代知识人启蒙国民的道路于此依然任重道远,我以为。不仅如此,在这类小说里,意味新型“知识—文化”的“我”几乎都是孤单、孤独地处身在悲苦主人公及其所生活的现实之中的,新与旧,那力量的悬殊也是触目的。此中见出的是沉重的“历史—现实”话题,晚清以来,近两个世纪了,放眼今天的中国,出现在198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那一幕惨苦,那位“长祥嫂子”的命运,于今是彻底消逝了么?抑或,她(们)的命运转换着方式、变换了内容,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延续?那么,始于鲁迅文学的关注她(他)们悲苦命运的新型的人道之眼又在哪里、在哪些议题上延续着呢?
在这个意义上,探究《长祥嫂子》所引人想象的“鲁迅况味”,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某种基本的“人际—文化”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秉有“知识—文化”的“我”们如今又在怎样的“归乡—离去—归乡—离去……”的路途里?从城里短暂归乡的“博士们的春节随笔”又书写着怎样的欣慰、失望、绝望和希望?“我”们又还能够有怎样的对于“吾土吾民”的观察、记忆与“爱”情?还有怎样的改变之心,直至改变的路径?无论是更远处的鲁迅,还是刚刚离开我们的王富仁先生,他们携手在这样根本的中国问题上——至少的,不曾忘记,而只有不曾忘记,最终的改变现实才会可能的吧。
——《祝福》的文本细读与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