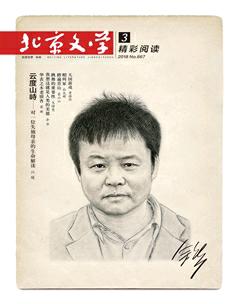书·记
海笑
风吹哪页翻哪页。
北漂的我,有点随遇而安。漂泊十年,北漂七年。痒。抓痒的方式,看书。前些天,还和多年不見的老同学争吵来着。他说: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我不信命。然而我相信人的孤独是与生俱来的。北漂,风起云涌,物是人非。许多人来了,又走了。一个厨师去法国做刀削面。一个网管回家去创业。一个编曲音乐人被家人洗脑搞直销。一个无名诗人自杀。一个大姐疯了。一个做兼职时认识的搬家的工友腰伤了没钱住院。一个玩玉的兄弟得了绝症,很久没有消息了……
“天下,暂时相聚,忽然云散水空流。”
北京似乎留不住我的兄弟朋友。唯有书,常相伴。可是我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一本《凡高自传》。还是借大学同学的。
淘书记忆
小时候淘气。长大了淘书。淘书,我上中学就开始了。周末赶大集,别的孩子买吃的,我淘书。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大厚小字本,黄土颜色封面。“人啊,忍,韧,仁”。五个字,写一生。
大学受红柯老师影响,更喜欢淘书。很多旧书店,是没有店名的。关门后,外面看,就像是工地房。有时偶遇红柯老师。红柯老师一看就是书店常客,操着方言向店主说,学生没啥钱,算便宜哈。红柯老师经常会引荐一些冷门的图书,《君王论》《热什哈尔》……“当古老的大海朝我涌动迸溅,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红柯老师后来写到了他的小说里。
和一些爱淘书的老同学,为了新的发现,经常走得很远很偏僻。一走就是一天。我是如此的喜欢走长路。老同学问我:路是没有尽头,以后你会去哪里?当时真没想过。毕业十多年,老同学们工作、成家。我一个人,自从淘了一本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竟然真的走远了。老同学问我何时“收心”,我竟无言以对。就像我《流浪猫》唱的:下一秒,我在哪儿?某街道?某荒郊?
曾经有一个笑话。一个人生病瞧大夫,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夜店,问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你那么无聊,何必活那么久?我心说这个大夫,一定不懂得有书的快乐。爱书的人,淘到好书,怎么会无聊呢?
前两年,北京有旧货市场,还有旧书的摊位。特价书店自不必说。每年更有一年好几次的地坛书市、朝阳公园书市,很是热闹。
说来我也是傻。第一次转地坛书市,因为要收门票,我自作聪明,把地坛公园绕行一圈,以为有围墙就有缺口,能逃票。就像顾城当年去老动物园,为了给蚕宝宝求桑叶,满处找翻墙地儿。地坛,是什么地方?结果,自然是没有。
一年年的书市,贵了。旧货市场,慢慢拆了,没了。旧书成了收藏书。盗版、翻印、电子版,加速了图书的消失。便宜还想有的看的,推荐潘家园旧货市场。市场边角处。不贴边儿走,不问熟人,不会发现。书市只有周六日两天开放。有多便宜?一两块钱。比如,卡内蒂《迷惘》就是我两块钱淘来的。
淘书,吃饭,钱从何来?
刚来北京时,不想找工作的我,只想兼职钟点工,自由。例如,我发过一个月送餐的传单,十元一小时。老板精明,几百张传单厚厚一沓,发完为止。于是两个多小时,领到十块钱。当时北京公交卡四毛钱起步,往返八毛钱。早餐一碗粥、一块饼,两块钱。有时老板心情好了,管一碗热汤挂面,不要钱。中午地摊,豆芽焖面三块钱。晚饭,一个戗面馒头、一包榨菜,一块钱。
每周六日,淘书钱,就是这么来的。
我平时不戴眼镜。日常,谁也不知道,不相信,我近视五六百度。公交潘家园桥西站下车后,淘书前,我会郑重其事地打开像是盛放金银首饰的、包裹着大红色丝绸的长盒子,取出我的金丝近视眼镜,斯文戴上。却不顾斯文扫地,蹲在每一个书摊前,眼睛逐行扫描每一排整整齐齐码着的书,手里扒拉着摊主故意放乱的,干脆从蛇皮袋子呼啦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堆书。挑所需,选所爱。有的书脏,只好如马克西姆《出埃及记》那样,拍落、吹落尘土。青蛙一样蹲着,爬啊爬啊,从头爬到尾,西排到东排。不知不觉,闭店音乐响起,那是萨克斯的《回家》。
地下人间
书越来越多。和许多北漂一样,为了省钱,我住地下室。半地下室有巴掌小窗通风透气。地下二层的纯地下室不见天光,白天懂得夜的黑,最适合看书。我这地下室,几年下来,不知不觉,书就堆了单人床那么长宽,儿童票那么高。没书柜,全在地上,辛苦了地下室的除湿机。夏秋季节,地下室除湿机大多在我屋里。轰鸣声里,盛放排水管的脸盆,魔术一样,无中生有。看不见的水蒸气,成水滴,成水流,滴滴答答,童子尿一样细细长长。学生时代,说某同学,麦当劳里就可以看书学习。我不行,嗅觉灵敏,餐馆看书会馋。不过地下室看书,机器响动,不影响我。我可以像《浮生六记》那样随时想象。我有聚斯金德的《香水》、有夏目漱石的《猫》、有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有米什莱的《山》《海》《鸟》《虫》……天下万事,尽在书中。
北漂书摊
不想当上班族,何不摆个书摊?
北京欢乐谷附近,我成了第一批摆地摊的人。
书摊简单,一个大妈买菜用的那种行李车,一二十本书,一张床单。卖几本,第二天加几本就是了。摆了书摊,知道了摆摊的辛苦。春有沙尘秋雨风,夏有蚊子冬有雪。
书摊没什么生意。一个文身哥们儿,代步车飞驰而过时,旁边手机贴膜大哥说话一针见血:有钱的不看书,看书的人没钱。
摆书摊,和其他地摊一样遭遇城管游击战。随时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自从有了我的书摊、几个袜子摊点后,欢乐谷附近的傍晚比集市还热闹:烤地瓜的爆米花的、假箱包的、假名包的、卖保健品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包治的、打底裤男女老少高矮胖瘦都能穿的……
垃圾遍地,吆喝大喇叭扰民。几经举报,城管几次突击围追堵截下,“欢乐谷集市”终于消失,只留想念。
围城姑娘
围城姑娘,是光顾我书攤最多的书客。
姑娘清瘦,短发整齐。简单黑色或素色调衣裤。不戴耳环项链。皮肤很好,剥了皮的荔枝一样。
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却有几分男人的大大咧咧。我书摊没有坐的地方,姑娘丝毫不介意地上干不干净,街头雅不雅观,铺书摊的床单一角,姑娘盘腿就坐。翻了这本看那本,看了品相看译本。经常聊天得知,姑娘是电力公司的。地摊邻居那里得知,姑娘有自己的黑色小轿车。除了我的书摊,其他地摊她从不光顾。
姑娘对我出手也大方,品相不是太差的,每次几乎打包全买,劝我可以早点回家。
我知道姑娘是在照顾我的生意。文学名著是普通家庭常备的,何况这样一位爱书胜过打扮的姑娘。我的反射弧一定太长。面对这么好的姑娘,我当时没有动心。每每想来,觉得没有进一步交流实在遗憾。姑娘一定是单身,因为现在回忆起来,我推荐的书,她从没有反对意见。唯有钱钟书《围城》,她坚持拒绝。她说她不想还没走进围城,就去念及围城外的好。我可能一再伤害了姑娘。我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我这本品相版本也好。另外我过分直接地说,我的藏书没有二十五史那样的成套系列古典。即使有,也不会贱卖。
围城姑娘,后来,再也没有相遇。
围城姑娘,如今你是否走进围城?如今你是否幸福安好?
白胡子大爷
白胡子大爷,胡子和洪七公同款。
白胡子大爷不是买书的。白胡子大爷说,他观察我好几天了。大冷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一边命令的口吻对旁边的儿媳说,把家里那个羽绒服拿来,我能穿他就能穿。
白胡子大爷转身进了京客隆超市,很快出来,提了一大袋馒头,和六连包大分量的方便面。
白胡子大爷儿媳住得不远,羽绒服很快拿来。接过馒头方便面,穿上羽绒服,我心里热乎乎的。我问大爷住哪里?以后好报答。大爷手一摆,说希望以后我能有出息,说以后记得垡头,有个爱管闲事的白胡子老头就是了。
惭愧我的倔强和不务实,一直也没出息。这些年,北漂人情冷暖自尝。虽然一面之缘,老大爷的白胡子一直在我脑海浮现。地下室搬离一次又一次,我曾去过垡头老地方念旧,旁边摆头花手套地摊的一个大妈认出我,聊天时说,也就送我羽绒服那两年见过,大爷儿媳有时还买她的小物件。可是大爷这些年没见出来了。我听到后心头一沉,不敢多问,不敢多想……
北漂,年年岁岁,朝朝暮暮。此时,又是一个冬天。我在读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这是我多次向认识的友人推荐的一本书。书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大雁随风而去,但愿我是那风。
阿沫曾经是个空姐,因为喜欢看言情小说,后来索性就辞职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到如今也出版了七八本书了。在影视改编日渐繁荣的时候顺势转型做起了编剧,因为这年头靠纸质书稿费养活自己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