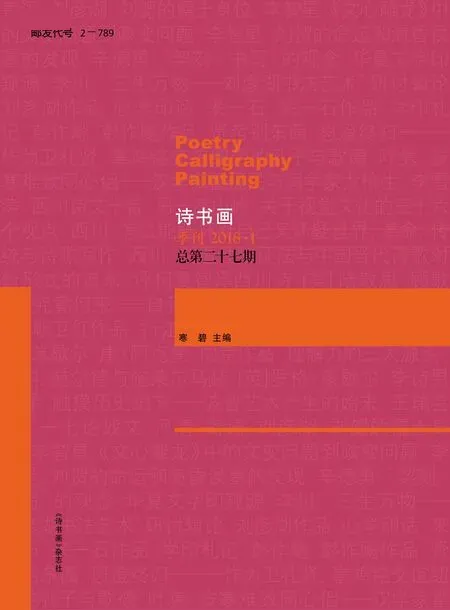刘勰的儒士身位
李智星
有“龙学”前辈指出,刘勰的思想属于古文经学家。《文心雕龙·正纬篇》也有助于确认刘勰之属古文经学家。《正纬篇》表明刘勰对纬书的排拒,这一姿态往往为历史上的古文经学家暨右派儒教士所共有,《正纬篇》亦流露出刘勰自视与此类经学家或儒士同道。联系《原道》、《序志》来看,刘勰的儒教士身位更明显。在历史各时代中,学人对刘勰的儒士身位抱有不同的态度,或重视之,或则倾向于强调其另一重身位,即文论家或文士的身位。正确看待刘勰文论,就应当不仅留意刘勰之为文士的面相,同时也当注意刘勰之为儒士的面相。
一、从文论家到儒士
对于六朝文风讹滥之病,刘勰《序志篇》明示其原因在于“去圣久远”,因而救治的方式就是征圣、宗经,文道合一。本来,文学的独立发展以文人个体的自主表达和文章自身的美感追求为前提,除非文道相分,否则,文道合一的结构使得“文”以及文人自身的价值伸展受到抑制。反之,当“文”的自觉意识产生后,正统的文道合一关系就有解体危险,六朝时代“文学自觉”引致的重大文变事件就是文道的两分。面对这一新变局面带来的文风时病,刘勰采取的救治方法就是重新弥合文和道,以道救文,故《通变篇》云“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然而,刘勰实际上远非满足在纯文章学的意义上谈以经补文。诉诸经典而求取典雅,以求文章的雅俗相宜,这完全可以在纯文章学的理路上谈,如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其中“文质彬彬”和“君子之致”都纯就文章学意义上论;最典型如清代王渔阳引《文心雕龙》来申发自己观点,但他发挥“本之《风》《雅》”之说则仅就文章写作、作家修养上,以使文章能“衔华佩实”、雅俗相济(《带经堂诗话·夏诀类》)。不可否认,《文心雕龙》确含把经书引导入文章学的意义,但另一面,刘勰又将文章引导回经书、甚至引回经书所载述的传统圣王文明上的意图。《文心雕龙》一开卷,就先从古远开始追溯,铺展开一幅宏大的传统圣王文明建构和圣王文明谱系的景观,如果刘勰只有王渔阳一般的用心,或如牟世金所以为,仅从文章家方式“宗经”,那么他完全不必以此构建儒家“文统”①参陈桐生《从中华文化发展史观到“文之枢纽”》,载《文心雕龙研究》(第七辑),文心雕龙学会主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126页。一般的气魄落笔。事实上,王渔阳在使用《文心雕龙》上追随明代性灵派文论家,明显偏重“剖情析采”的下篇文术论,其“宗经”便属文章家眼界的“宗经”,相应他也有意忽视开卷的“枢纽”论,从而回避了经的传统政教意义。所以如纯按文章家的方式“宗经”,其实完全不必正面顾及经的政教传统。反倒是与王渔阳在文论取向上相反对的大文学家钱谦益,则同时谨遵经的传统政教义蕴论文,故其论《文心雕龙》之“宗经”也相应充分地重视“枢纽”论。
如刘勰在文章之外别有一番文明的怀抱,其视野必超一般文论家的眼界。他煞费苦心,不惜“唐突而牵强”,也要“将五经视为各种文体起源”,甚至发挥五经极为有限的“含文”面相,也要“特意从‘五经’中寻求诗文艺术美的渊源”②冈村繁《冈村繁全集三: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陆晓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版本下同。,如果刘勰仅由治疗文章上的问题激发而选择“宗经”以求“矫讹翻浅”,那他毫不必要“唐突而牵强”地专门“改造”经典,冒此穿凿附会经典之患。冈村繁就观察到这点,故生疑窦:“(刘勰)真实意图是否真的在于‘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是否别有实际原因?”③冈村繁《冈村繁全集三: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陆晓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版本下同。或可做出解释:刘勰试图在一个文苑业已独立、文人与儒者明确分途且分庭抗礼的文学时代中,设法维系传统儒家经典和儒家圣王文明的权威地位,就不能不从经典的传统蕴涵中转生出“文”的全新义涵与脉络,尽管这样转换经书的操作“唐突而牵强”。当然,从文章家角度尊经,同样可以“改造”经典,将经典转化成文章的典范,即化经为文,但“化经为文”与“引经为文”是相区别的:前者从文论家的立场介入经,将经书演化成文学上的典范,目的在于让经学为文学张目;而后者虽亦引申经书为文学典范,却从儒者或经学家的立场出发介入文,目的是让文学接受经学的规范。两者移动的踪迹、进路与方向是不同的。然则在刘勰源初之处所发生的是从经学家的立场出发而介入于文的运动,毕竟,据《序志篇》,刘勰“敷赞圣旨”一开始就是选择经学家注经的方式,即一心想成为一名经学家,但后来自忖在经学上鲜有建树,才决意另辟蹊径,转向论文,但论文背后也许仍是原先经学家的抱负和情怀。甚至有龙学前辈明确指出,《文心雕龙》呈现出对作为一部集部之书性质的超逾,直至成了一部儒家的“子书”。①参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王更生《文心雕龙研究》(重修增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本下同。
其实关于刘勰经学家或儒士的身位,“龙学”前辈的专门阐论,主要是从不同角度议论刘勰之属古文经学家,例如提及刘勰在《序志篇》对同属古文经学大师的马融、郑玄表示钦敬(“马郑诸儒,宏之已精”)。杨明照“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一文中胪列过六大理由,支持刘勰从属古文经学家:
(1)《毛诗大序》的一些说法,书中多所运用(例多不具列);(2)《伪古文尚书》(当时还不知其为伪)的某些辞句,往往为其遣辞所祖(例多不具列);(3)古文经学家一般不为章句之学,《论说》篇“通人恶烦,羞学章句”的“通人”,就是指的古文经学而言。在他所举“要约明畅”的四个范例中,如毛苌、孔安国、郑玄都是两汉的古文经学大师;(4)《史传》篇对于《左传》极力推崇;(5)《诗经》的《毛传》《郑笺》,书中多本之为说(例多不具列);(6)古文经学家的旧说,闲或采用,如《宗经》篇“皇世《三坟》,帝代《五典》”两句,系用贾逵说……,《书记》篇“绕朝赠士会以策”句,也是用的服虔说。只此六端,就大可看出刘勰所受古文经学派的影响是很深的。②杨明照《杨明照论文心雕龙》:“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5页。上述“六端”,更详的分析可参羊列荣《〈文心雕龙〉与五经》,载戚良德编《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8-249页。作者认为刘勰因顺郑玄开辟融通今古之潮流,其文论亦不辨古今,涵通兼采,在经学上亦持“通脱的态度”。诚然,《文心雕龙》既取古文家说,亦采今文家说,但不能据此以为刘勰放弃了基本的古文经学家的立论立场。毕竟,即使郑玄融通今古,总体上也是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实行,不然便无法解释他与今文学家何休的论争关系。
台湾现代“龙学”界颇重《文心雕龙》的经学渊源及刘勰之为儒教士的身位背景,王更生即为代表。一九九五年,王更生参加北京《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以《刘勰是什么家》为题,对刘勰的儒士身位深入阐明,以提醒学界对刘勰儒教士身位的长久短视,并要重新评价。王更生往后的“龙学”研究工作仍不离此,继续对相关的问题进行钻研,可见其对刘勰的儒士身位极为看重。王更生在著作中也提到,刘勰排列五经的次序总是首进之以《易》经,这符合古文经学家们一贯以来的习惯做法。③王更生《文心雕龙研究》,第299-302页。除了上述的论据以外,笔者以为相对少受重视的《正纬篇》对于确认刘勰的古文经学家身份也不可忽视。
二、从《正纬篇》看刘勰的儒士身位
根据《正纬篇》,刘勰蔑弃纬书是因为其“无益经典”,最终认同纬书则是因为其“有助文章”,清人王鸣盛以为刘勰对纬书的取舍主要基于一个“文士”的立场:
余谓挚刘皆文人,故其言如此。纬虽无益于经,康成所注,皆有益者,学者宜研究之。(王鸣盛《蛾术编》)这个说法颇有问题。《正纬篇》篇终之际基于“有助文章”而认可纬书,或姑且可谓立诸“文人”观点,但刘勰批判纬书部分的议论却未必如此。
刘勰正纬是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认为纬学之盛引起“乖道谬典”(《正纬篇》),对五经之正典地位造成了破坏。《正纬篇》虽篇幅短小,却堪称一部考辨精详、论判入里的纬学研究著述,纬学研究大家钟肇鹏甚至认为其能与今人同类的纬学研究力作相媲美。④姜忠奎《纬史论微》,黄曙辉、印晓峰点校,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参看开卷钟肇鹏的序言。《正纬》绝大篇幅的内容俨然是篇精短的“纬学论略”,跟文论家论文已无多大关系。刘勰“正纬”是“宗经”的合理推延。但按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的观点,《宗经》非宗经学家的经,而是在文学上宗经,刘勰“宗经”论“不是儒家的五经论,而是文家的五经论”,“只是为了论文或为文而征圣宗经”。⑤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78、136页。如若“宗经”仅是文论家的“宗经”,则“正纬”也当是文论家的“正纬”。可是,刘勰如仅以文论家眼光来“正纬”,他完全不必花费绝大笔墨将《正纬》写成一篇精深的“谶纬论略”,且刘勰深入纬学的程度也明显超逾一个纯文士的怀抱与识见。
纬书兴于西汉哀平时,对纬书的攻伐则自东汉尤多,以其历经王莽、刘秀鼓吹,纬学风气盛极一时,攻纬书的儒士亦随之活跃起来,相为抗衡。对纬书的官方禁令在南朝刘宋时就有,但一直到隋朝,纬书作为官学之外的“异端”才正式遭焚禁,遂致散亡;随后,“纬学”曾一度成为影响王朝政治及儒生群体的暗流而长期存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季,其时官学对纬书仍态度反覆,但《文心雕龙》中的《正纬篇》已明确表达排纬立场,与前代的攻纬书家们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是一部论述文章写作的文论著作,后世目录家径直将其列之于集部,与诗文评齐同一类,为何却会跟儒士群体内部围绕纬书的争执扯上干系?
纬书在汉代起引发的争执,实是儒士群体内部围绕政教话语法权上的争执。自汉以来,纬谶和五经之间的地位消长,乃关乎争夺国家国教正典权位与王官学话语权位的纷争,纬谶学在其最兴隆的东汉之际,作为汉代显学,甚至一度占有“国教”之学的地位,属政制话语上的显论,“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隋书·经籍志·纬类序》)。在王朝高层的力推之下,“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正纬篇》),纬书大兴,纬学据位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刘勰也提到当时“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撰谶以定礼”(《正纬篇》),这说明纬学其时具备压倒性优势,已加入国家官方的政教建制之中,用以“通经”、“定礼”了。而对纬书加以挞伐的儒士则持有另一种政教建制构想,他们主张明确五经的国家法典地位,故力辟纬谶为妄诞。无论是支援纬书抑或攻击纬书,儒生集团内部的分歧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实取决于政制理念形式上的纷争。
对于纬书的态度将儒士群体划分开不同的两派。纬书家好假准圣人身位、代发孔子“微言”,垂青于纬书的一派儒士则喜借纬书原理影响政教秩序的建制,主要通过引申或转换出经典中的“微言”以迁就当下现实的问题状况,其重改制论,乃从出于齐儒“定位于历史未然的王道之治”的政教理念,故倾向“后王”;而判纬书为虚伪、为妖妄的另一派儒士,他们以持守“历史已然的王道之治”为任,乃从出于鲁儒的政教理念,故倾向“先王”、重循蹈发挥经典本身载述的古老义理以规导当下问题。①刘小枫《纬书与左派儒教士》,载《儒教与民族国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5、7页。版本下同。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张氏认为,荀子强调法后王的观念,对刘勰通变论影响颇深,“刘勰关于通变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来自《周易》和荀子”(第156页),毕竟,荀子“着重强调的是要法后王,而不是法先王。他认为先王之道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时代新形势要求,而后王之道则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对先王之道的灵活运用,是最能符合于新的形势要求的”(第157页)。凸出荀子哲学的影响是张少康“龙学”研究中的一项“新探”。不过,如果刘勰的理论禀赋如某些“龙学”前辈所言,是从属于古文派经学一脉,那么他强调的就应该是法先王,今文派经学一脉则往往强调法后王,或者换一种说法,鲁地儒学一脉强调法先王,而齐地儒学一脉强调法后王。刘勰固然深谙宗经与权变的道理,但懂得权变不一定就要从法后王而来,法先王论同样可以言通变,从《周易》中就能提取通变论的思想资源(《通变篇》中其实征引《易》经的比例是全书最高的);而实际上法先王者言通变与法后王者言权变又并不一样。刘勰文论当然积极响应“新的时势要求”,但却决不“认为先王之道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时代新形势要求”、从而把重点放在后王身上(对刘勰来说,这一位所谓“后王”只能就是屈原),其与荀子立论并不相同。且《荀子·儒效篇》释“法后王”为“以今持古”,与刘勰“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辨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中明显所持“以古驭今”的论调不一致。两派儒生之争自然属于“两大派儒教士的政制理念及其制度安排的思想之争”。②刘小枫《纬书与左派儒教士》,载《儒教与民族国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5、7页。版本下同。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张氏认为,荀子强调法后王的观念,对刘勰通变论影响颇深,“刘勰关于通变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来自《周易》和荀子”(第156页),毕竟,荀子“着重强调的是要法后王,而不是法先王。他认为先王之道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时代新形势要求,而后王之道则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对先王之道的灵活运用,是最能符合于新的形势要求的”(第157页)。凸出荀子哲学的影响是张少康“龙学”研究中的一项“新探”。不过,如果刘勰的理论禀赋如某些“龙学”前辈所言,是从属于古文派经学一脉,那么他强调的就应该是法先王,今文派经学一脉则往往强调法后王,或者换一种说法,鲁地儒学一脉强调法先王,而齐地儒学一脉强调法后王。刘勰固然深谙宗经与权变的道理,但懂得权变不一定就要从法后王而来,法先王论同样可以言通变,从《周易》中就能提取通变论的思想资源(《通变篇》中其实征引《易》经的比例是全书最高的);而实际上法先王者言通变与法后王者言权变又并不一样。刘勰文论当然积极响应“新的时势要求”,但却决不“认为先王之道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时代新形势要求”、从而把重点放在后王身上(对刘勰来说,这一位所谓“后王”只能就是屈原),其与荀子立论并不相同。且《荀子·儒效篇》释“法后王”为“以今持古”,与刘勰“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辨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中明显所持“以古驭今”的论调不一致。集中在经纬之辩、谶纬真伪之辩上的文献学争端本质上乃属于此政治争论的某种侧显。刘勰专立《正纬》一篇以主动介入经纬之辩、介入纬谶真伪之辩,实质其所介入的是一场儒生内部事关政制及文教建制的政治性论争,看来刘勰关心的事情远非纯粹文学之事那么简单。
刘勰《正纬篇》举了四个证明论“纬”为虚妄伪作,与经义不配,为攻纬书家一派的儒士提供学理上强而有力的支撑。他在概括了哀平以来、尤其是光武之后纬谶大为上下学者所趋的局面后,紧接着便举出四位批判纬书的代表性儒士,刘勰与这些前贤们深有共鸣:
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所列四贤张衡、桓谭、尹敏、荀爽,均是古文经学家,在政教立场上都抵制纬书③古文经学家多反谶纬,今文经学家则多好谶纬。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密切,周予同早有阐论,可参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的相关论述。今文经学家董仲舒作《春秋繁露》,清儒凌曙作注博引谶纬(《春秋繁露注》),晚清大儒廖季平亦谓“董子《繁露》,为纬书之祖”(《经话乙编》)。(其中桓谭更因反谶纬而在政治上遭贬),也绝然无法以“文人”等闲视之。刘勰一一列出四人论见,恰与自身辟纬之观点桴鼓相应,四贤论见无疑支撑了自己的观点,刘勰分享前人所论,并有意将自己置于与四贤立场相呼应的位置,示与四贤为同道,“对于桓谭之‘疾其虚伪’、张衡之‘发其僻谬’,刘勰给予了大力褒扬”④高林广《〈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22页。,这表明他自觉把自己的“正纬”论证接上该派儒士端正经纬关系的论证,无形中介入了事关经纬的文教政制论争。汪春泓论及《正纬篇》,便识出刘勰与四贤的密切关联:“在纬书可信与否的问题上,刘勰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汉‘疾虚妄’思想家一边,远绍中国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自然论’一派,这与其经学立场是相一致的”⑤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与影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426页。郭鹏《〈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和历史渊源》,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46-47页。,经学立场上刘勰与四贤实际同属古文经学派,但尚可进一步指认经学立场与政教立场的关联,如能透过古文经学立场辨别出攻纬书派儒士背后的政教关怀,则刘勰与四贤儒士便同在政教取向上相连属。由此可见,刘勰实有某种政治性的身位,倘若仅识其为“文人”、“文士”,恐怕将难免错过他文字中的政治抱负,进而也就无法恰当地理解《文心雕龙》这部书。
刘勰属古文经学家,《正纬篇》见出其归属于攻纬书派儒士,如前所述,此派儒士主张守持先王奠定的“历史已然的王道之治”。刘勰实际上也将这种政教观念转移到文论上加以贯彻。《原道篇》追溯经典的来源在于历史上诸先圣王的文章,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原道篇》),五经出自先古圣王世代文章累积。后世的文章本质上源于经典,故文章的性质也决定于经典的性质: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序志篇》)
文章之用立足于政治,盖文章的本源,即经典也同样立足于政治之用。经典是由历史上先圣用于政教的文章积累、凝聚而成,因此经典中也就必然承载着圣王王政的构建,也就是先圣王的王道之治,它意味着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的构建;文章必须“宗经”,就意味着文章必须以王道政治为关怀,作文章也要惦记着经典里的“历史已然的王道之治”。刘勰在《序志篇》表明自己撰写《文心雕龙》的心志所系,便提及自己曾经“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这是在比喻孔子为“素王”,而刘勰自己则是“素臣”,“南行”代指南面而王,手执丹漆礼器就好比托起王者的礼乐文教政治。《文心雕龙》谈写作文章之事,志向却在于端起王政文教事业,这已远非纯粹“文人”的眼界所能容纳的了。
三、作为儒家“子书”的《文心雕龙》
“文人”群体的形成是近人所谓“文学自觉”后的结果。“文学自觉”发生在魏晋六朝时期,其原因之一,据说离不开当时自汉末以来“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鱼豢《魏略》)的乱世风气,其景象仿佛战国时期,其时儒教文学散乱,“文以载道”的体统自然遭受破坏,于是文章也开始了突破传统经学精神的范围而独立发展的历史性变换。①参牟世金《雕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3-28页。面对文学变故背后的衰世,刘勰所作文论同时“有匡时救弊之意”、“怀有神州陆沉之忧”,亦不足奇,遂“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②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前言,第1页。
(彦和)眼见国家日趋危亡,世风日趋浇薄,文学日入于浮靡之途,皆由文与道相离所致,而曾无一人觉察,心怀恐惧,思所以挽救之而无权位,故愤而著书。所以他这部书虽则是专谈文学理论,虽则是总结以往文学的经验,虽则是评骘以往作家的优劣,然而可说是一部救世的经典著作,是一部诸子著述。③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第189页。
事实上从齐梁至隋,时俗文学主流皆以艳采华辞为好,进入初唐始对骈文的绮靡风气进行普遍批判和反思,急起八代之衰,其时,刘知几读《文心雕龙》也侧重其政道忧患意涵。刘知几可视为古代第一个《文心雕龙》思想的研究家,其《史通》自序中将刘勰《文心雕龙》与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齐同并论,显然《文心雕龙》被看做与这些子书同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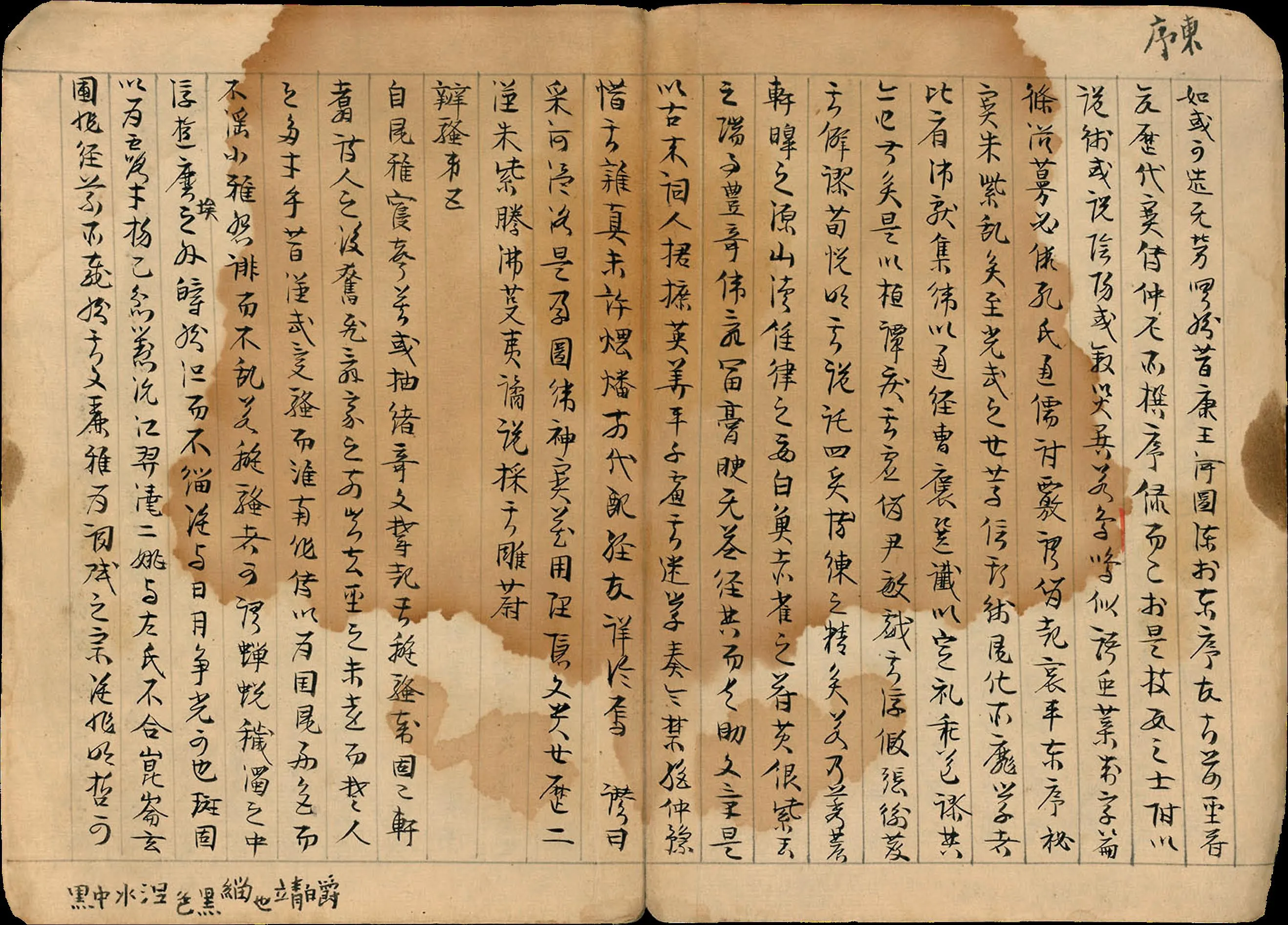
敦煌唐写残本《文心雕龙》
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世,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雕龙》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刘知几《史通·自序》)
刘知几对上述诸书均一视为伤时救世之子书,也把自己的《史通》看作接续它们而作,遂也自列诸子部。北宋黄庭坚在说到刘勰《文心雕龙》时,仍与刘子玄的《史通》相提并论:“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黄庭坚《与王立之》)。明人王惟俭、清人黄淑琳训注完《文心雕龙》后,又找《史通》来作训或补训,纪昀在黄淑琳注本的基础上评《文心雕龙》后,又作《史通删削》四卷,还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也“下该《雕龙》、《史通》”①章学诚《与严冬友书》,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人们“把《文心雕龙》与《史通》尊为文史著作中的双璧,并竭力使之显赫彰明”②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曹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页。亦参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444-458页。,看来亦都在《文心雕龙》和《史通》之间领悟到某种相通。在刘知几所列之诸子中,据说“扬雄对刘勰的影响十分显著”,《文心雕龙》和《法言》“两者的忧患意识实质上是相通的,救弊的思路也是何其相似乃尔”③参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版本下同。(值得留意的是,扬雄亦为古文经学家),而《法言》当然是一部子书,因而《文心雕龙》也应该可视为一部子书。其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其振文统、倡宗经也在继承刘勰的文道观①《文心雕龙研究史》,第124页。,譬如清人刘开便认为:
自韩退之崛起于唐,学者宗法其言,而是书几为所掩。然彦和之生,先于昌黎,而其论乃能相合,是其见已卓于古人,但其体未脱夫时习耳。夫墨子锦衣适荆,无损其俭;子路鼎食于楚,岂足为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其俳而弃其重哉。然则昌黎为汉以后散体之杰出,彦和为晋以下骈体之大宗。各树其长,各穷其力,宝光精气,终不能掩也。(刘开《书文心雕龙后》)
按韩愈的志向抱负在原道卫道,其胸襟自有同取于刘勰处,反之,则刘勰亦自未可以纯粹文士目之。进入明清两代,“文学自觉”可以说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明人曹学佺批点《文心雕龙》明显是从明代性灵派侧重纯文章学的审读趣味出发,但于《诸子篇》首句眉批亦承认“彦和以子自居,末《序志》内见之”②《文心雕龙汇评》,黄霖编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3、65、13页。版本下同。亦参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之《诸子篇》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清代纪昀评注涉及《诸子篇》时,亦提示说刘勰于其中“隐然自喻”③《文心雕龙汇评》,黄霖编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3、65、13页。版本下同。亦参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之《诸子篇》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言下之意,刘勰亦目己著为一“子”书,且评《原道篇》时谓彦和“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截断众流”④《文心雕龙汇评》,黄霖编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3、65、13页。版本下同。亦参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之《诸子篇》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把刘勰拔出于文人文士的一般萃类。这些仅为零碎评论。清代从文论大体上继承前人重视《文心雕龙》儒家襟抱面相的主张,代表者当推钱谦益和晚清的桐城派文论家。
《文心雕龙》学大家刘永济亦强调《文心雕龙》“以子书自许”⑤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前言,第1、175页。,并为古代目录书竟置《文心雕龙》入集部、“以其书与宋明诗话为类”、“以文士目舍人”的做法抱不平⑥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前言,第1、175页。。刘永济意欲把《文心雕龙》从集书提入子书。台湾龙学界的王更生追随刘永济,力申舍人的儒士身位,界定“《文心雕龙》乃‘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此说法又曾作“文评中的子书,子书中的文评”)。⑦转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0页。
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人社会流行不同的成见,受染乎其主流风气,对《文心雕龙》性质的界定就会发生变化。唐人侧重其子书性质,倡导“征圣”“宗经”的文学观,明清文人受新“文学自觉”的风潮波及,则多发其集书性质,凸显“下廿五篇”的文术创作论而忽视“枢纽”论。而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新的时代趣味嬗变又相继产生。现代文化意识一心为与西方现代的文教分科建制相接轨,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的文化相竞长,传统的经学系统被迫受到分解,划分成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原本的经学大道机体分崩离析,文学要摆脱经学的影响,成为独立的学科建构。在对传统经学和道统思想的普遍质疑中,自然又会开启文道分化的形式。在《文心雕龙》的解读上势必也受波及。例如,《原道篇》立说祖本《易》经,但《易》经作为神人圣王之书的神圣性由于受“新文化”精神的解剖而彻底瓦解(如顾颉刚《古史辨》所论“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⑧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亦参周春健《古史辨》第三册〈自序〉读剳》,载《经史散论》,台北:万卷楼,2012年,第251-285页。),影响及乎《原道篇》,于是鲁迅以为该篇的泛文论思想“其说汗漫,不可审理”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页。,徐复观也称其“将经推向形而上之道,认为文乃本于形而上之道,这种哲学性的文学起源说,在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意义”⑩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第179页。。在新的文道分离的历史思潮下,《文心雕龙》被逼从传统的经学精神背景中分离而出,随之难免不断被倾向于视为一部文艺理论的著作或讲授文学作法的修辞书⑪参戚良德《〈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63-177页。,舍人之系于传统王道抱负的政治性身位被忽略,而不断被凸出的是他的文学性身位。现代龙学在二十世纪延续这种理解方式,对于挖掘《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或文艺美学的义涵,前人耕耘所取得的成果固然蔚为大观。
结语
无论如何,要正确阅读《文心雕龙》,就必须同时注意到它的两种面相,不可偏废其一,王更生子书中的集书、集书中的子书的观点,无疑是兼顾了《文心雕龙》的双重面相。这起码说明刘勰本身既是一名传统的儒士,又是一名新兴潮流中的文论家。文章在刘勰看来是极高大深远(原乎大道、并乎三才)、极光辉灿烂(昭明军国、辉晓生民),如果仅受限于新兴的纯文士眼光,这种极高远昭明的文章境界是无法被容纳的。文章写作担负起开创王政天下的襟抱(“文心”),这样的文章才可能接近自身最高尚开阔的精神格调,与此同时又能兼配雕缛美好的文采(“雕龙”),则才堪当圣王“尽善尽美”的理想。从刘勰的文论思想来看,王政志向奠定文章的精神底蕴,这一点本来在任何时候都不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