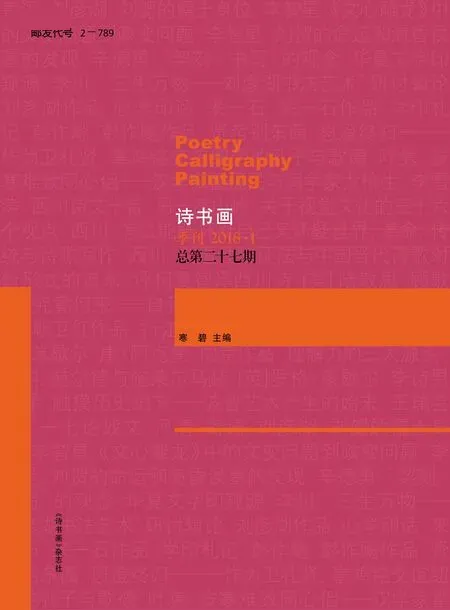《文心雕龙》中的文变问题到政变问题
李智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赵岐章句以为“王者,谓圣王也”,《诗》与圣王的命运休戚相关,“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班固《两都赋序》)。王者迹熄意味着王政消亡,王政政体跟《诗》血脉相联,王政政体的衰变伴随整个礼乐制度与文治文明的衰变,也就必然伴随《诗》的衰变。更早时正风正雅衰变为变风变雅,亦源于圣王政制的衰变:“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故国政衰落而有亡象者,先起“桑间濮上之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而晓各国政象,杜预注曰“季札贤明才博,……依声以参时政,知其兴衰也”(《春秋左传集解》),声诗之变也必是国政兴衰之变的反映。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显然遵循以上儒家传统的政变文变平行论。六朝文风遂讹滥而去古之风雅,中间经历的文变事件引人瞩目,在刘勰的理解里,仍然能回溯于政治之变在文学上的反映。对此有必要先着手对文变的历史本身做一大致的梳理。
一、讹滥时文
白居易总结诗文自周及盛唐历有四变:周衰时,“于时六义始刓”;骚赋起,“于时六义始缺”;至六朝,“于时六义尽去”;及李杜,“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白居易《与元九书》)。六义的损失有个过程,六朝之前六义虽已残缺不全,但仍有所存依,六朝时则六义尽去,这跟刘勰对文变趋势的判断有一致处。刘勰认为屈骚为文之一变,起自“风雅寝声”之后,但毕竟又“去圣之未远”,古义犹存(《辨骚篇》);《通变篇》叙述九代文章自古至今,其文变即循“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之势,去古愈邈,离本愈甚,盖“竞今疏古,风昧气衰”,变至宋时则“讹而新”,荒废尤甚,刘勰亦慨叹一句“文理替矣”(《时序篇》)。
刘勰所处时代是个文章相当盛行的时代,“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萧绎《金楼子·立言》);但刘勰所处之时代亦是文章流于淫讹的时代。时文以丽辞奇采等雕琢为美,从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论文》里对文的描述可见一斑:“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追求文采靡曼的宫体也在梁代兴盛,《梁书·徐摛传》云“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昭明太子所编《文选》即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选文(《文选序》)。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归纳当时之文章: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讬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此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南齐书·文学列传》末作赞亦以“文成笔下,芬藻丽春”总结齐时文章。《宋书》无文苑传,《晋书·文苑传》末赞语也说“子安、太冲,遒文绮烂。袁、庾、充、恺,缛藻霞焕”,可见主流文风也呈类似趣尚。
巧绮、繁缛,是六朝文风的主要特征,而衍至宋齐则确然至于讹滥淫靡,其中尤以俳赋为盛。赋于汉初已兴隆,至建安时期始又变体,俳赋这种赋体便于其时初萌,及至刘宋,精熟自成,逮梁时尤靡丽,去古义已远。虽汉代大赋已尚辞采雕饰和用典对偶,刘勰评价为“侈而艳”(《通变篇》),但也未及六朝俳赋刻意求之,而丽辞排偶,固俳赋之所尚,其俳对、声貌、藻饰,自呈铺衍,已与前汉异,而汉赋之始侈而终正的行文特征,至六朝俳赋更也殆不复见。①参盛源、袁济喜《六朝清音》,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3-319、321-338页。作者总结六朝俳赋的主要特点为“对偶精工、用典繁巧、声调谐畅、丽辞藻绘”。
二、汉赋侈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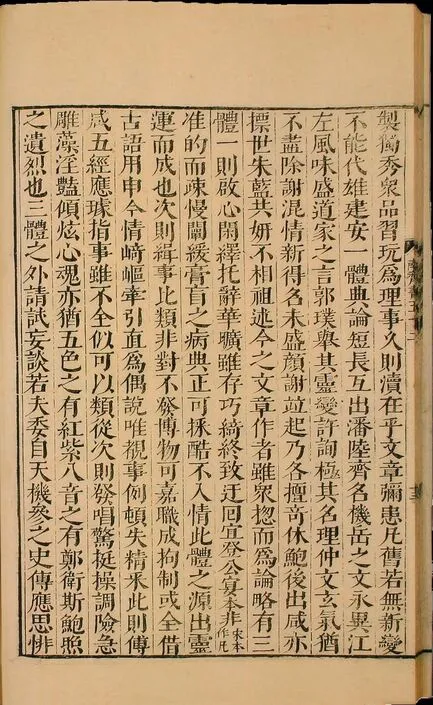
《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

《文选·序》
文章发展到汉代固然以辞赋为宗,六朝讹滥的风气也是从汉赋的“侈而艳”转出、发展过来,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谓汉赋“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违;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违;丽靡过美,则与情相誖”,刘勰亦称“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通变篇》),又称“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比兴篇》),即谓汉初赋已极具奇伟侈丽的特点,要理解六朝的文风就必须首先追溯汉代辞赋文风的兴盛。
西汉赋分为散体大赋及骚体赋,后者源溯屈骚,前者主以铺排,又往往篇末言志,微露讽旨。汉大赋盛于铺排跟汉朝泱泱大国的文物昌明与盛世气象分不开,作为“大汉天声”,“汉赋的雄壮宏丽,诚可谓是文风与国势同盛,辞彩与天威共辉”,①王旭晓《大风起兮》,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版本下同。特别“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鹜”(《时序篇》)。大汉王室本身就极赏识辞赋家的文才,汉武帝喜好司马相如赋即是例子。但长期以来辞赋家们的地位并不高,“贾谊抑而邹枚沉”就说明当时“辞人勿用”的状况(《时序篇》),毕竟文学写作不过一技艺而已,于经世治国无用,自不登大体,与倡优歌舞类同,《汉书·严助传》即谓帝“倡优蓄之”,传统儒生对他们亦颇鄙夷,《扬雄传》记录扬雄谑称之为“俳优”,刘勰亦提及灵帝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时序篇》),“无论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等方面,以枚皋为代表的一批不长于‘政事’的辞赋家自诬‘俳优’是情理之中的。……都是在宫中娱乐君王的”②曾祥旭《士与西汉思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版本下同。。那时候辞赋家自己也还未懂得重视自己的文章,司马相如的赋纵写得出色,但直至死后汉武帝还得命人替他蒐汇作品。③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汉代官方正史《史记》、《汉书》里为西汉的经学儒者专立《儒林传》,而文人辞人只被安排在一些散传里,备受旁落,此类“文学家”之传,“与经学家之传便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与经学之士、儒学之官名正言顺跻身史传不同,‘文学家’入传却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确实与‘文学家’得到认可、文人得成《文苑》之传尚还有很大距离”。5可见,自觉的文人作者群落西汉时并未真正产生,与文人得入《文苑传》尚有距离,所谓“文学自觉”还是晚后的事情。
一般的说法会称魏晋六朝时期为所谓“文学自觉”时期,魏帝《典论·论文》即在文论上发其先声。彼时对文章创作渐形成自觉意识,纯粹之文人群体也共文集文论之夥出而建立起来。但是“文人”或“辞人”自觉观念的出现,最早可能自东汉即已开其端,《文苑》之传就开始出现在《后汉书》。在西汉司马相如尚属“俳优”而已,但到了东汉,一个文人被认为有相如之风,却有可能得以晋身高位,例如《后汉书·李尤传》记载“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可见局面已产生变化。其时儒生们评价属文之士的口风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譬如班固《答宾戏》里已表达出对文章技艺的肯定,对此龚鹏程认为:
班固这位学者,已从瞧不起技艺、以别人把文章写作视同技艺为可耻的情况中,转换到自觉地以文章写作为一种技艺,而且是可以安身立命、表现自我的技艺。到王充,更直接地认为儒者必须为文著作。①龚鹏程《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0-81页。版本下同。
王充在《论衡·超奇篇》夸赞“繁文之人,人之杰也”,更一改董子《春秋繁露》里“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鸿儒”②龚鹏程《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0-81页。版本下同。的传统经生见解,而提出:
通书千篇以上……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者为鸿儒。
分明已把文人的才能上升到鸿儒的身份水平相论,王充还说“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篇》),文人的地位已超一般的儒生、经生或通人了,而惟一超越纯粹文人的鸿儒,按王充的标准也必须“能精思著文、结连篇章”、亦有文才才可以,萧帝所谓“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鸿儒也”(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亦如龚鹏程所述:
儒者不能只述不作……不论是王充的期许,还是班固的说词,都显示“文人”已正式出现了。述而不作的形态,彻底打破,儒者必须擅长文章写作这种技艺,才能成为文人、成为鸿儒。《论衡·佚文篇》说得好:“文人宜遵五经六义为文、造论者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文之德大矣哉!……从此之后,《儒林传》与《文苑传》开始分立,刘劭《人物志》中也正式把“文章”视为“人流之业”十二种之一,说:“文章家,能属文著述,司马迁、班固是也。”③徐彦疏尝引此语,并谓今本《繁露》已脱,见刘盼遂《论衡集解·超奇篇》,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80页。
可见文人作家心性的建构完成于六朝(文集“实盛于齐梁之际”)④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李春伶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页。版本下同。,却开始出现在东汉文人群体之中,就此而言,较早时西汉辞赋家陆贾、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人,便相当于中国古代文人的前身,文人是通过感染汉赋侈艳的写作特色而开端的。
三、战国诡俗
但是,汉代辞赋家群体的出现也有自身更远的历史渊源,“楚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源头,……汉皇室对赋的喜好,与兴起于战国末期楚王宫中的赏赋之风,实有着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⑤王旭晓《大风起兮》,第235、237页。,以此,“作为楚文化流绪,汉初文人多习辞赋”⑥王旭晓《大风起兮》,第235、237页。。汉高祖九年,因从西域归朝的娄敬献言,朝廷下令将齐楚两地的豪族名门十多万人迁徙至关中,齐楚两地的文化风尚也由此充斥于关中一带,首都的街市、汉室的宫廷,都流行起“楚国男性爱好的辞赋文学或妇女间流行的五言歌谣”⑦冈村繁《冈村繁全集三: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陆晓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0-581页。,影响所及,致使汉代的文学审美趣味都为楚地的辞赋文学所支配。刘勰在《诠赋篇》说“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明谓盛于汉家的辞赋文体,其产生可追溯到战国楚时。刘永济也认为:
汉承秦火之后,周文久坠,楚艳方零。立国之初,王伯并用。大氐政承秦制,文尚楚风。故辞赋之士,蔚然云起。彦和所谓循流而作,势固宜矣。⑧参刘永济《文学通史纲要》,载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附录一,第613-621页。版本下同。
刘勰评价汉家辞赋亦往往楚汉相提,如《通变篇》“楚汉侈而艳”,《宗经篇》“楚艳汉侈”。楚时赋已采富辞腴,夸饰侈丽,而且当时的辞赋家也只比俳优,比如宋玉为楚王作赋,亦不过娱君王之兴而已。对于汉辞赋家与楚辞屈赋的关系,刘勰在《时序篇》也有精当概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屈原被看做汉辞赋家的始祖:“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辨骚篇》),可知汉人辞赋一开初,其侈丽尚奇、“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杂文篇》)的特征便沿自屈赋“艳溢锱毫”、“夸诞”、“谲怪”之作风(《辨骚篇》)而来—《诠赋篇》追溯至“灵均唱骚,始广声貌”—或者更准确说,乃是延伸了整个战国楚地流行的文章风气:“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夸饰篇》)。所以说,要追究汉家辞赋侈艳文风的源头,就要溯回至战国楚时的文风。
战国楚地多辩士,好饰其辩说,以投君好,楚时赋风大致从出自此。①王旭晓《大风起兮》,第235页。恰恰“辞赋家在西汉往往被看作浮辩之士,枚乘、邹阳、陆贾、司马相如等前期辞赋家莫不如此,所以有辞赋起于纵横家之说”。②曾祥旭《士与西汉思想》,第156页。枚乘以《七发》赋名闻,为赋家文宗之一,据说其上书君主,便“纵横奔放,有战国说士之风”。③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上)》,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67页。战国时的纵横家就属这一类辩士说士。刘师培就把词章之家的“侈陈事物,娴于文词”也“溯源于纵横家”④转见钱基博:《古籍举要 版本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版本下同。,鲁迅称纵横家“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系波流衍,渐入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质朴之体式所能载矣”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3页。,这是说文苑里“繁辞华句”的作风是从纵横家的“竞为美辞”流衍而来。钱基博论之益详实:“吾则见为辞赋家者流,盖原出诗人风雅之遗,而旁溢为战国纵横之说。纵横家者流,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扺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赋者,古诗之流,而为纵横之继别。比兴讽谕,本于《诗》教。铺张扬厉,又出纵横。故曰‘赋者,铺也’。铺张扬厉,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故曰古诗之流。铺张扬厉,乃见纵横之意。”⑥钱基博《古籍举要 版本通义》,第85-86页。钱说实袭章学诚《文史通义剳诗教上》,第16页。刘勰素以屈原为“词赋之宗”。钱基博引《史记屈·原列传》所叙屈原之“娴于辞令”“从容辞令”,以说明屈赋之出于纵横家、行人出使之官,又引《诠赋篇》“赋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以示赋家之出儒家、为“儒家之支与流裔”,⑦钱基博《古籍举要 版本通义》,第85-86页。但钱同时称刘勰虽能穷其源于儒家,却未悉其流变于纵横家,此说则实在误解了刘勰。刘勰评论屈赋“风杂于战国”(《辨骚篇》),又以为其“出乎纵横之诡俗”(《时序篇》),刘永济对刘勰此说评价甚高:
“故知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二句,深得屈宋文体流变之故,与实斋章氏论战国文体出于行人辞命之说,可谓旷世同调。屈子主连齐抗秦,与子兰上官之主秦者异趣,故遭贬斥,是屈子亦近纵横家也。汉初人士多习纵横长短之说,而赋家如贾谊、司马相如、枚乘、严忌、邹阳之徒,皆有战代驰说之习,但高祖已厌纵横,文景务崇清净,故贾谊抑而邹枚沉,于是纵横之士,无所用之,乃折入辞赋;及武帝之世,此风已成,而赋人亦渐为帝王所重,其间因缘,固甚明白;舍人二语,已足窥见本源。实斋演之,遂成名论。⑧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54页。刘永济直将汉代辞赋家之习溯至战代的纵横文辞,无异于将汉代辞赋看作是汉代的纵横文辞。事实上纵观《后汉书·文苑列传》的记载,可以观察到其时文士们仍然遗传了上述辩士式的辩才,例如《刘毅传》“毅少有文辩称”、《刘珍传》“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边韶传》“韶口辩”、《刘梁传》“著《辩和同之论》”、《边让传》“少辩博,能属文”、《郦炎传》“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候瑾传》“有才辩”、《祢衡传》“飞辩骋辞”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在汉代以后历代史书的文苑传里,还能找到有关于文士辩才的记载。
周振甫评《时序篇》,亦以为刘勰观点独到,指出了“楚国辞赋受纵横家学派的影响”,“屈原宋玉的创作受到纵横家游说夸张的影响,像《招魂》写东南西北各方的怪异,同纵横游说夸张东南西北各方的形势相似,就是《离骚》的上天下地到处流转,也受到纵横游说夸张讽喻的影响”。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94-395页。但刘勰所说屈赋“出乎纵横诡俗”不必仅指纵横家之诡俗,而主要是指整个战国时各家异说飚盛、言辞繁盛的诡俗与世情,“战国者,纵横之世也”。⑩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16页。对比挚虞《文章流别论》描述纬书的奇辞华采,亦称之“纵横有义、反覆成章”。所以《时序篇》此处不但言及屈宋,也与邹衍驺奭并提,谓其分别出于齐楚之风,齐楚之风正涵盖了战国时期主要的“文学”之势,如此自与“风杂战国”构成呼应。
战国纵横家的产生本身便与当时整个诡俗时势分不开。比如说纵横家亦属“名家之支与流裔”,阐之于学则为名家,施之于用则为纵横家,“惠施、公孙龙,庄生称之为辩者。而范雎、蔡泽,亦世所谓一切辩士。大抵名家之出而用世也,出之以谨严,则为申韩之刑名;流入于诡诞,则为苏张之纵横。”⑪钱基博《古籍举要 版本通义》,96页。此处在战国百家辩说蜂起的这整个诡俗世情的背景下,把纵横家与名家、法家视为同宗同源、难解难分的时世之“一切辩士”、“辩者”。值得一提的是,名家“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恰好就跟辞赋家的文章面目雷同。

《太平御览》
钱基博以赋变出自纵横家,又言其“出入战国诸子”,也把纵横家与诸子百家同归铺衍辩说之士一类:“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教,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①钱基博《古籍举要·版本通义》,第97-101页。纵横家辞风与战国诸子整体上的言辩风格归乎一辙,整个诸子辩说甚而早已集中具备了后世辞人之讹滥风气,辞赋家者流既由“出入战国诸子”,难免亦染习上铺排夸饰、事丰奇诡等文学特征,这跟刘勰“风杂战国”“出乎纵横之诡俗”的判断完全一致,从而认为,刘勰所批判的辞人之讹滥文病正始战国诡俗而来。
钱以辞赋文章家上溯到战国诸子,实祖章学诚之说,钱引《文史通义·诗教上》语,
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②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第18-19、19、15页。

《太平御览》
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也把诸子兴与文集盛相连接起来:“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章说以为后世文章家承续诸子而来;而“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③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第18-19、19、15页。,正是通过诸子文章之变出,周代王制下的声诗之文得以转移出后世文章家之文,“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第18-19、19、15页。战国诸子之诡俗,流行横议驰说、奇辞华句,后来集部之作即接续子部之书而出(“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这也决定了文辞家之初起即接上诸子文士的诡俗风貌,难免“染乎纵横之诡俗”。
章说实际继承了刘勰的观点,刚刚刘永济的引文里也明言“实斋演之,遂成名论”,清代谭献也以为“章氏云:‘战国文体最备。’此言亦开于彦和”(《复堂日记》)。刘勰《诸子篇》的确也在战国诸子文学和后世文人文学之间建立“血缘上的联系”:
《文心雕龙》)列诸子为辞章的一体,其间不仅述流别,评优劣,而于诸子辩雕万物,智周日月的丽辞秀句,更览华食实,为后来操染翰者辟一习作的知识宝库,使百氏的情采与文学体式发生了血缘上的关系……⑤王更生《文心雕龙研究》(重修增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267页。
刘勰以为近世文人讹滥之病每每过乎“绮丽”“藻饰”,而实又以同等语形容过诸子杂说:《情采篇》谓:“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又云“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刘勰认为庄韩的文辞固“过乎淫侈”,其时战国文辞之“绮丽”、“藻饰”,本身已足为文辞之极变(“于斯极矣”),这跟章学诚“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的说法相当。至于观其《诸子篇》列述百家的辞气华采,如“气伟而采奇”、“辞壮”、“博喻之富”、“泛采而文丽”云云,可与“绮丽艳说”、“藻饰辩雕”相比。刘勰以为后世文辞之变以“变乎骚”为代表,实则也变自战国“艳说”、“辩雕”的诡俗。《序志篇》尝以“讹滥”一词概述文人流弊,以为时下文人的文病主要在此,然而何为“讹滥”?其据刘勰意,讹与奇诡奇巧近、滥与华采淫侈同,而奇诡与淫采不待“近代辞人”,于诸子文章已早有体现,所谓“诸子杂诡术”、“百氏之华采”(《诸子篇》),毕竟“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荀子·乐论》)①梁启雄《荀子简释》训“匿,读为慝,邪也。言文章邪慝而多采饰”,参见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5页。,—诸子杂说之奇异邪诡、饰采淫靡,就是政道乱离的必然征象。如此一来,刘勰面对当时“近代”讹滥之文弊,其实亦是面对战国诸子以来便已开始的讹滥奇艳之风。
四、王者之迹熄
据《时序篇》说法,“纵横之诡俗”产生于“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之季,《才略篇》也称“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都把诸子屈宋之诡俗文风置于“战代”背景下;刘勰在《诸子篇》历数诸子华采辞气,之前也先摆明“七国力政,俊乂蠭起”的政治现实背景,也就是说诡俗文风是在春秋战国诸侯任力使霸的政史背景下形成,其时六经泥蟠,表明王政官学破落分散,诸子得以飙起,王道分裂,典章散、声诗变,是王政政体衰败的表现,即又是一个“王者迹熄”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而辞赋本身就生出于《诗》之后,班固所谓“古诗之流”,刘勰所谓“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诠赋篇》),刘勰以政变现象譬喻文变现象:赋挣脱掉先王时代诗六义传统的大一统统治,蔚然而成一独立大国;甚至乎日后“文之敷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丘故都,而大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②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第20页先祖故国崩坏,后生竞维新政。紧接“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正是“《诗》亡然后赋作”。《诗》亡而赋作的文变事件,紧系在王政声诗散而乱世慝采生的文变事件之中,也紧系在王政解散而乱国力政的政变事件之中。其中屈赋就是此中间转折的代表,勘察屈赋有助于考察这一转折。屈赋作为“词赋之宗”即临此《诗》亡赋作之间,也就恰届上述文变-政变之间,谓之“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谓之“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辨骚篇》):“轩翥诗人之后”故有王政时代文章“典诰”一面,“奋飞辞家之前”而有战国时代文章“夸诞”“艳侈”一面。因此谓其“去圣之未远”、“《雅》《颂》之博徒”而又染乎纵横诡俗、出入战国诸子,也就是说它处乎周代王政和春秋战国之间,一者离周代王迹不远,二者又已蹈乎乱代之征,用刘勰自己的话说就是:
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③他本有作“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大意亦一致,考虑到《时序篇》“出乎纵横之诡俗”的说法,故取“风杂于战国”。或参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第10页。
三代代表王政,儒家素以三代先王政治为王政典范;战国则代表王政政体衰亡。从三代到战国,提示的是政体的迁变,屈赋文体的形成也端在于三代与战国之间,说的是文变乃在政变之间。刘勰针砭讹滥文弊,笔者追讨文变之源流,从六朝上溯至汉赋,从汉赋上溯至楚赋,又以楚赋回本于百家诡俗,诡俗生于“七国力政,俊乂蠭起”的战国政象,从而最终将文变溯本于从三代到战国的政变。刘勰暗示追本文变于三代战国之间,系依循儒家文变系乎政变的传统观念,也表明刘勰面对文变问题,其心所惦念已落在王政命运上,刘勰对王政政体的衰息与变迁、及其所带来的文道衰息与变迁保持基本的敏感和关顾。这些其实在《时序篇》里表达得很清楚。文章的典范就是以扶助王政为义归,假如后世文人一路沿着王政破落后的乱代风气走,“竞今疏古”,文章就会离王政关怀愈来愈远,其精神品质也会愈来愈远离三代时礼乐雅正昌明的崇伟而溺于战国时礼乐分崩离析的卑败。刘勰倡“宗经”,以为治文病首赖于宗仿王者的经书,也就是要挽救战国以降的文人群体,以使文人们的心性回归三代王政时期的精神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