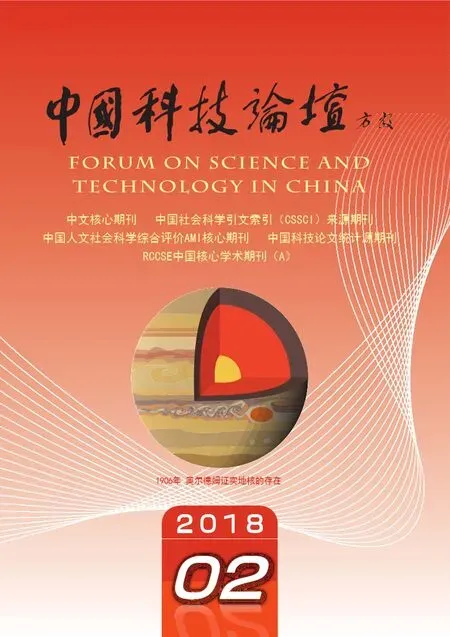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研究评述:从个体属性向网络关系演进
孙玉涛,国容毓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
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量高技能人才和科学家流失到美国,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现象开始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1-2]。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和高技能人才迁移的经济影响才又重新回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议事日程[3]。OECD高技能人才跨国迁移研究报告重点强调了科学技术人力资源(例如科学家、工程师和IT专家),以及跨国迁移对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趋势和影响[4]。很多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科学家等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性,开始担心大规模高层次人才流失再次出现,并出台相关政策挽留和吸引科学精英。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已经逐渐成为新兴国家深度参与科技全球化、全面实现科技追赶的重要途径。积极探索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理论和经验,对于新兴国家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目前,国外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才环流”论、“人才外流”论和“人才流入”论三个方面[5]。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一方面面临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的高层次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承受着规模居世界前列的高学历人才流失,海外高层次学术人员全职回国工作成为学术界和管理层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学术人员的工资收入水平已经显著提高,学术职业的发展空间日益拓展,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吸引海外高层人才政策(特别是 “千人计划”项目)有效地促进了人才回流,已经逐步形成了人才循环[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与海外学术市场收益的差异[7]。但是,高层次海外学术人员全职回国工作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6-8],迫切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
学术人员是知识的重要载体,学术人员跨国迁移不仅涉及劳动力迁移,还涉及跨国知识流动,是移民研究、人才循环和科技管理等领域重要的交叉研究议题。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科技大国,学术人员回流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重点关注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特别是中国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相关研究,评述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个人决策模型、人才循环理论和“中心-外围”结构,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推-拉”动力机制,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知识和社会网络效应,以及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特征等,为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理论研究和吸引高层次学术人员回国工作政策制定提供支撑和借鉴。
1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理论:从个体决策到国家循环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研究需要跨学科交叉,整合不同的视角、框架、理论和方法。以劳动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理论等为基础,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理论的早期研究主要专注人才流出国劳动力市场的建模,后来逐步转移到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研究,并运用中心(人才净流入国)-外围(人才净流出国)模型解释跨国人才流动的均衡[9],近年来大量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模型和观点(见表1)。

表1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基本理论
1.1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个人决策模型
个人决策模型认为学术人员跨国迁移行为是个人决策的结果,通过相关要素的调节可以改变学术人员的迁移决策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假设下,Stark等[10-11]构建了机遇、激励和信息三要素模型,研究结果认为人才流失实际上可以因祸得福,移民也可能给母国带来更多的人才;Stark[12]的扩展模型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移民概率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模型的主要贡献是区分了人力资本最优水平与实际水平之间的差异。
Dustmann等[13]以动态Roy模型作为基本框架构建了一个解释移民决策的模型,在作为学习中心的国家,个人可以更有效率地学习技能;个人学习的技能如果可以运用到自己的母国,回到母国运用他们的技能可以获得较高回报,那么个人则倾向回到母国。王培根等[19]指出流动净收益是国际人才流动的决定因素,高技术人才普遍具有年龄小与受教育程度高的优势条件,是国际劳动力流动中最富有流动性的一个群体。总体而言,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很大程度上由其流动净收益决定,或者说个人决策更多地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净收益。
1.2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人才循环理论
个人微观决策很大程度上会呈现在国家宏观层面,学术人员跨国迁移一度成为很多人才流失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人才流失理论也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Ackers[14]和Saxenian[15]等学者认为人才流失理论并不完善,在政策措施方面存在不足,建议使用人才循环理论。人才循环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学术人员不同于其他迁移者,跨国迁移的根本动力是他们的职业,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机会、交流思想和丰富知识;同时强调这些迁移可能是暂时的,通过一个更有效的跨国劳动力市场和跨国知识转移机制能够形成正向效应[20]。
冯慰容等[16]以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人才资源跨国迁移的行为模型,结果显示:人才资源跨国迁移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也有流动,发达国家还有人才向发展中国家回流,逐步形成人才循环模式。基于950名德国学术人员的样本,Edler等[21]考察了科学家访问母国之外研究机构的频次对知识和技术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流动的科学家既在东道国又在母国参与知识和技术转移,表明国外的知识和技术转移并不会替代或者挤出而是互补国内的知识和技术转移。上述经验研究为人才循环理论提供了非常直接的经验证据。
1.3 学术人员跨国循环的CP结构
虽然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在国家之间形成了迁入与迁出的循环,但是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在地理上仍然具有显著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简称CP)结构特征。Maier等[4]的研究表明,明星科学家或者高被引科学家的地理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只有很少的国家具有吸引科学人才的能力,其中教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明星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陆根书和彭正霞[17]对2636名高被引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有784人移民到别国工作;在高被引学者跨国流动的过程中,人才流失问题非常突出;只有7个国家是高被引科学家跨国流动的纯受益者,美国则是高被引学者迁入最多的国家。Beine等[18]基于127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具有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水平和移民率的国家能够从人才流失中获益,相反的国家则会有更多的人才流失,失去的比回流的多。Beine等[22]运用1957—2000年1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低收入国家技术移民能够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如果技术移民比率不高,可以获得净人才回流;相反地,没有发现中高收入国家存在这样的激励机制。Rapoport[23]提出,人才的流失会刺激输出国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使未迁移学术人员从中获益。
2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动力:双边“推-拉”机制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动力机制是学术界和管理层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吸引海外高层次学术人员回国工作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的“海归”经验更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吸引国际学生回流的例证。
2.1 动力模型
劳动经济学中的人口迁移推-拉模型是解释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动力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在推-拉模型中,“推”的因素主要是国内不利于学术人员发展甚至迫使学术人员离开的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教育结构、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个人发展机会等方面;“拉”的因素主要是发达国家鼓励个人学习和工作以及留在这些国家的因素。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人才循环逐步形成了国家双边关系,为双边引力模型的建立和运用奠定了基础,逐步成为迁移动力研究的基准模型。引力模型应用于模型化跨国迁移动力研究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近年来由于迁移数据的可获取性,特别是二值数据(例如,迁出地和迁入地有人员迁移即为1,否则即为0)格式的运用,使得跨国迁移双边引力模型重新获得青睐[24]。其中,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属性要素包括收入、移民政策、环境要素等,二值要素包括网络关系、双边迁移政策、语言和文化距离等。Beine等[25]在最新的研究中指出,双边数据在跨国迁移中的分析既有优势又有挑战,优势是运用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二值数据可以阐明大量之前没有回答的问题;挑战在于由于数据的特性,如何解决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

图1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推-拉模型
2.2 环境因素
在传统推拉模型分析框架下,自然环境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政策等社会环境因素也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选择。
Beine等[26]采用1960—2000年双边迁移面板数据分析得出,长期的气候因素对跨国迁移并没有显著性直接效应,并且在控制来源国特征、考虑回到母国和迁移网络潜在内生性的情况下稳健,自然灾害则促使人口迁移到城市郊区。Backhaus等[27]运用迁移引力模型扩展到平均温度与降水量,并采用1995—2006年142个迁出国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温度与迁移具有非常强的正向关联,较强的降水量变化能够引起迁移的小幅度变化,气候变化主要通过农业和内部斗争对迁移产生影响。
孙健等[28]、Weinberg[29]指出,人口规模、人均GDP、民主化程度和城市化率与重要科学家的数量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新研究还从文化和语言等方面更深层次地解释了跨国迁移行为。Fu[30]通过对加拿大学术界14位中国迁入科学家的深度访谈研究指出,文化因素已经渗透在“离开-留下”决策形成和中国科学家跨国迁移循环行为中,他们经历艰难的新文化构建过程;从迁移的角度而言,这些学术迁移者牢牢地坚持新文化的信仰、态度和行为;同时,他们又显著地受到中国文化价值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群体倾向、层级喜好、自谦、追求和谐和爱面子。Adserà等[31]从语言临近性、语言使用广泛性和以语言为基础的移民政策需求等方面考察了语言在跨国迁移中的重要性,结果显示迁移率随着语言临近性和英语目标地而增加,迁入地柔性的语言要求和目的地更大的语言社区鼓励迁移者进入,本地语言网络越大,语言临近性作用越小。
Cao等[8,32]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吸引到一流海外人才最重要的是制度因素。谢勇等[33]指出,高等教育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存在诸多方面的制度环境问题。显然,制度因素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海外人才回流不可小觑的因素。
2.3 个人选择
对综合高收益的追求是影响海外人才迁移个人选择的重要因素,高收益涵盖经济和精神两个维度,包括个人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发展前景、个人价值实现等多个方面。
一个强大的科学共同体对于国家产生和留住科学家非常重要,但是经验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大量精英科学家,但是却经历大量人才流失[29]。Tian[34]研究表明,国外学术市场具有非常显著的选择机制,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术人员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马万华等[35]通过“千人计划”学者访谈指出,千人计划学者选择海归是将个人价值实现放在重要位置,追求学以致用、竭尽所学;通过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精英科学家的流动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精英科学家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可以通过迁移找到更高效的科研环境,但是受到迁移成本的制约。高子平[36]基于2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大型实证调查发现,理工科留学人员群体的科研选题的持续性(前相关)、师承关系(纵相关)、职业发展目标(后相关)、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横相关)均对其回流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广泛的职业生涯相关因素,例如个人收入水平,将会对高技能人才跨国流动决策产生重要影响。Zweig等[37]调查显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海外人员转移新技术和传播新知识提供了经济激励。谢荣艳等[38]对组织层面的研究表明,科研机构的管理制度、职能机构、文化氛围以及科研经费的分配体制都会影响学术人员流动意愿。Zeithammer等[39]调查也显示,中国学生留在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
2.4 环境与个体互动
Qin[40]通过宏观层次推拉因素的结合和个人层面选择考察了受过高等教育人员迁移的动态性,结果显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驱动人口双向迁移,东道国的需求对于向外迁移的影响比回国迁移强;在个人选择层面上,顶尖的学生更喜欢迁移并且不喜欢海归,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是迁出国最好和最显著的迁移人口,回国选择受到能力、迁移后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等影响。具体而言,Alberts等[41]通过群体访谈识别了学生留在美国或者回到母国的动力因素,具体包括职业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三类;职业因素通常鼓励学生继续留在美国,中国政府提供职业机会鼓励海归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力,社会因素(例如语言、情感交流和社会交流)和个人因素(家庭、朋友等)更倾向于把他们拉回母国。高子平[42]认为全球经济波动导致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群体的专业技能发挥受到限制、心理压力加大,使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回流意愿也明显增强,建议将“人才抄底”作为先行先试的策略性选择,为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战略的转型与重塑积累经验。
3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效应:知识与社会“网络”
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知识“网络”实实在在存在,迁移网络中的连接具有和其他网络类似的路径依赖特征和知识扩散效应。
3.1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知识“网络”
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管理层都已经达成共识,学术人员是最重要的知识载体,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将会形成跨国知识流动,进而形成跨国知识网络。Coe等[43]定义跨国知识网络是企业研发网络、个人社会网络、教育和政策等公共网络领域相互重叠运行的结果,其中企业与其他非企业组织构成的知识网络是主体。在实践中,很多国家正在试图建立和强化他们与国外学术人员的网络,进而吸引和帮助国外学术人员回国。移民网络政策通过各类专项计划和工具(例如基于互联网的社会网络)保持与海外研究人员的联系,为人才流出国提供人才回流机会。
经验研究表明,海归科学家是知识技术转移的中坚力量。基于德国的经验,Jöns[44]指出通过人才循环形成的跨国知识网络已经超越了国际论文合作等范畴,人才循环开启了随后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积累过程,非常有利于德国在二战之后重新融入国际科学共同体,让德国在21世纪成为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来源国。太平洋小岛国调查数据研究显示,海归人员是国际研究人员和本地研究人员之间知识转移的主要渠道[45]。
3.2 学术人员迁移知识网络演化的路径依赖
虽然目前“网络”在学术人员跨国迁移中还是一个隐喻,很少有经验证据表明“网络”的真实存在,但是学术人员跨国连接“网络”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非常突出。Baruffaldi等[1]考察了海外研究人员的国内联系对海归选择和科研生产率的影响,具体考虑移民网络、广泛非正式知识网络、商业关系、专业团队、国内科学期刊和短暂交流等关系。以意大利和葡萄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指出,与国内保持高度联系的研究人员回国工作概率高,国内联系直接有利于扩展科学网络。高技能人员回国有助于建立母国和东道国科研系统之间的联系,Jonkers等[46]运用阿根廷的数据研究发现,国外工作经验有助于解释国际合作发表倾向,学术人员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与之前东道国系统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建立的学术联系具有很强的正反馈效应,学术联系具有路径依赖。
3.3 人员迁移知识网络演化的学术效应
学术人员跨国网络连接对于学术人员及迁入国的效应问题也是关注的焦点议题。陈代还等[47]以中国首批“青年千人计划”143位海归科学家为研究对象,指出国际合作网络对海归科学家的科学产出具有显著影响,国内关系纽带对海归科学家科学产出的作用呈倒U型曲线。Li等[48]以长江学者为例,考察了校友联系(即校友教研人员和母校之间的连接)对于海归学者个人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校友联系对学术人员国际合作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研究文化中非常强的本地网络导致海归学者难以呈现他们倾向的合作行为。杨张博等[49]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指出“千人计划”学者归国后通过“三元闭合”机制,将国外学术社会资本转移至国内。不难看出,上述研究主要通过建立合作网络而不是迁移网络研究归国学者迁移的学术效应——提高科学产出、改善研究质量、转移学术社会资本等。
4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特征:流失与回流博弈
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量高技能人才和科学家流失到美国,人才流失问题逐渐开始引起关注,如今,科学家和高技能人才迁移的经济影响又重新回到了OECD国家的议事日程,并且重点强调了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很多发达国家开始担心高层次人才流失再次出现,后发国家逐渐开始意识到人才回流可以让国家在世界系统的边缘位置变成核心位置,出台相关政策挽留和吸引科学精英,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特征可能会给理论和政策带来新的启示。
4.1 跨国迁移学术人员特征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群体特征群体性显著,其中教育是重要的区分因素。Adams等[50]通过对24个劳动力输出国的数据研究得出,高层次人员更倾向于迁移到美国和OECD国家,并且更愿意迁移到与母国临近的国家。刘俊婉[51]对五个领域高被引科学家的流动现象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高被引科学家的机构流动频次在2~5之间,半数以上的高被引科学家有过国外工作经历。每经过6~7年高被引科学家更换一个工作单位。Saxenian[15]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通过对由硅谷回流至母国的高技术人才研究发现,回流的高技术人才与硅谷持续保持紧密联系,并为母国的本地化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做出了巨大贡献。Gibson等[45]发现当前的移民人员比拥有相似技能的海归人员和非海归人员业绩更突出,但是海归人员与非海归人员在母国产生的学术影响并无明显区别。可见,迁移学术人员的国际联系对母国的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4.2 中国“流失”学术人员特征
学术人员特别是高质量学术人员流失,似乎一直是中国科技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对美国100所大学的3776名华人教授的地域、机构、性别、职位和学科数据进行分析,Wang等[52]指出,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华人学者最多;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埃默里大学和德州农机大学是华人学者最主要任职的三所大学;男性教授与女性教授人数比例悬殊,约为7:3;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比例是2.7:3:4.3;生物、医学和计算机科学学科是华人学者最主要从事的三类学科。张松涛等[53]通过对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教育经历进行研究,发现杰青群体从硕士开始呈现国际化求学趋势,主要流向国际主要科技发达国家。高子平[54]对27个国家1123名海外华人科技人才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海外科技人才回国发展的意愿较高,总体上达到了68.9%,明确表态不考虑回国发展的仅占9.1%。然而,Zweig[55]、曹聪[56]、Zweig等[6]指出,中国政府的努力成功吸引了创业人才和专业人士全职回国发展,但是高水平学术人员全职回国工作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4.3 中国“回流”学术人员特征
虽然高水平学术人员回国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回流”学术人员归国后的发展状况总体良好。中国的教育和就业系统非常国际化,中国政府派遣出去的学者主要靠国外的资助完成研究。Tian[34]研究表明,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的回国率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董洁林[57]的案例分析发现,顶级高科技海归创业团队呈现较明显的M型能力双峰,即“创业能力”和“技术能力”都较高。
赵卫华[58]通过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指出,虽然海归博士和本土博士在职业生涯上有很大差别,但是就发表论文、获得专利、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等职业成就指标看并没有显著差别。鲁晓等[59]运用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査数据研究指出,一般而言海归科学家在学术和创新表现上显著优于本土科学家;早期回国的科学家较近年海归潮中回国的科学家有较好的学术和创新表现,拥有国外博士学历的科学家相对本土科学家在学术和创新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余广源等[60]通过对国内985高校和211财经类高校的882位经济学科海归教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外任职的时长和研究成果对海归教师的论文发表数量有重要影响。
5 基本结论及研究展望
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已经成为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学术人员的流失和回流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层关注的焦点。学术人员跨国迁移作为新兴的交叉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系统梳理和评述了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研究特别是中国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研究的文献,以期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1)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理论研究具有显著的从个人决策研究向国家间人才循环研究转移的趋势。个人决策模型研究主要关注影响学术人员迁移决策的因素,而人才循环研究则拓展到国家得失以及国家层面因素对学术人员迁移的影响。尽管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存在循环,人才流失国可能因“祸”得“福”,但是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在地理上仍然具有显著的CP结构,少数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学术人员。
(2)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动力的机制仍然遵循人口迁移推-拉模型的原理,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或者迁出国与迁入国的差异促进了学术人员的跨国迁移,所以双边引力模型成为定量研究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动力机制的基准模型。现有经验已经表明,气候、自然灾害等自然环境,文化、教育、语言等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对环境的感知和环境对个人的影响等是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基本动力机制。
(3)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研究的关注重点已经从个人决策和国家循环变成了知识和社会网络,可以说“网络”本身就是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直接效应。换句话说,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网络是跨国知识网络的一种,具备一般跨国知识网络的基本特点。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学术人员跨国连接“网络”演化具有非常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的国际化联系有助于后期的跨国迁移;学术人员迁移形成的网络有助于提高科学产出、改善研究质量、转移学术社会资本等。
(4)学术人员流失与回流的博弈成为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制胜关键,学术人员的迁移频次、偏好等特征得到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共同关注,成为人才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中国作为全球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例如,在美国100所大学就有3000多名华人教授,虽然海外学术人员回国发展的意愿较高,回国工作学术人员的整体状况良好,但是高水平学术人员全职回国工作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应该看到,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研究正在逐渐从个体向网络演进,在向迁移网络或者跨国知识网络演进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继续进行深化或拓展的问题。
一是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机构层面理论薄弱,“网络”仍是有名无实的隐喻,迫切需要理论探索和经验证据。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学术人员跨国迁移逐步形成了知识“网络”,但是 “网络”仍然停留在隐喻层面,缺乏经验研究证据,可以通过构建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机构网络模型,解析科研机构间多边关系矩阵、搭建跨国迁移数据平台,让“网络”从隐喻变成现实。
二是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结构特征研究主要关注国家结构和个体特征,缺乏中观层面科研机构的特征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微观和国家宏观层面,学术人员跨国迁移的核心是“人员-机构”匹配,经验研究需要超越两国双边分析框架,在科研机构之间建立迁移关系,阐述科研机构的关系结构和组织结构特征[61]。
三是学术人员跨国迁移动力机制研究以推-拉模型为基础,主要关注国家和个人层面影响跨国迁移的“属性”因素,“关系”因素的关注较少。实际上,学术人员跨国迁移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术人员和科研机构的双向匹配,且是否连接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属性特征,还取决科研机构之间、学术人员之间以及科研机构和学术人员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从人员和机构两个层面揭示网络中学术人员连接科研机构、科研机构连接学术人员的机制,才能为吸引海外高层次学术人员全职回国工作政策制定提供足够的理论和经验支撑。
[1]BARUFFALDI S H,LANDONI P.Return mobility and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ers working abroad:the role of home country linkages[J].Research policy,2012,41(9):1655-1665.
[2]CERVANTES M,GUELLEC D.The brain drain:old myths,new realities[J].OECD observer,2002(230):40.
[3]OECD.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he highly skilled[M].OECD Publishing,2002.
[4]MAIER G,KURKA B,TRIPPL M.Knowledge spillover agent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obility of star scientists[J].DYNREG(Dynamic Regions in a Knowledge-Driven Global Economy),2007(17):1-34.
[5]朱军文,李奕嬴.国外科技人才国际流动问题研究演进[J].科学学研究,2016,34(5):697-703.
[6]ZWEIG D,WANG H.Can China bring back the best? Th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es China’s search for talent[J].The China quarterly,2013(215):590-615.
[7]孙玉涛,张帅.海外青年学术人才引进政策效应分析——以“青年千人计划”项目为例[J].科学学研究,2017,35(4):511-519.
[8]CAO C.China’s brain drain at the high end:why 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failed to attract first-rate academics to return[J].Asian population studies,2008,4(3):331-345.
[9]COMMANDER S,KANGASNIEMI M,WINTERS L A.The brain drain:curse or boon?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M]//BALPWIN R E,WINTERS L A.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analyzing the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235-278.
[10]STARK O,HELMENSTEIN C,PRSKAWETZ A.A brain gain with a brain drain[J].Economics letters,1997,55(2):227-234.
[11]STARK O,HELMENSTEIN C,PRSKAWETZ A.Human capital depletion,human capital formation,and migration:a blessing or a “curse”[J].Economics letters,1998,60(3):363-367.
[12]STARK O.Rethinking the brain drain[J].World development,2004,32(1):15-22.
[13]DUSTMANN C,FADLON I,WEISS Y.Return migration,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brain drai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95(1):58-67.
[14]ACKERS L.Moving people and knowledge:scientific mobi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1[J].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5,43(5):99-131.
[15]SAXENIAN A L.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upgrading in India and China[J].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CID),2005,40(2):35-61.
[16]冯慰容,冼国明.人力资源国际流动的趋衡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3(10):101-105.
[17]陆根书,彭正霞.高引学者跨国学术流动及对其成长的影响[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1):62-67.
[18]BEINE M,DOCQUIER F,RAPOPORT H.Brain drain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inners and losers[J].The economic journal,2008,118(528):631-652.
[19]王培根,牛敏.浅析高技术人才的国际流动[J].科学学研究,2002,20(3):262-265.
[20]MEYER J B.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brain drain’s changing face[J].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2003,3(213).
[21]EDLER J,FIER H,GRIMPE C.International scientist mobility and the locus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J].Research policy,2011,40(6):791-805.
[22]BEINE M,DOCQUIER F,ODEN-DEFOORT C.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the brain gain[J].World development,2011,39(4):523-532.
[23]RAPOPORT H.Who is afraid of the brain drain?A development economist’s view[J].Law,ethics and philosophy,2016(4):119-131.
[24]ANDERSON J E.The gravity model[J].Annual review in economics,2011,3(1):133-160.
[25]BEINE M,BERTOLI S,FERNNDEZ-HUERTAS Moraga J.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gravity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The world economy,2016,39(4):496-512.
[26]BEINE M,PARSONS C.Climatic factors as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15,117(2):723-767.
[27]BACKHAUS A,MARTINEZ-ZARZOSO I,MURIS C.Do climate variations explain bilateral migration? A gravity model analysis[J].IZA journal of migration,2015,4(1):1-15.
[28]孙健,纪建悦,王丹.海外科技人才回流的规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8):6-10.
[29]WEINBERG B A.Developing science:scientific performance and brain drai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95(1):95-104.
[30]FU M.A 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a’s scientific brain drain:the case of Chinese immigrant scientists in Canadian academi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2014,15(2):197-215.
[31]ADSERA A,PYTLIKOVA M.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2015,125(586).
[32]CAO C,SUTTMEIER P R.China’s new scientific elite:distinguished young scientists,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hopes for Chinese science[J].The China quarterly,2001,168:960-984.
[33]谢勇,陈念宁.我国高等教育涉外引智工作的发展、问题与对策[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7):67-72.
[34]TIAN F.Skilled flows and selectivity of Chinese scientists at global leading universities between 1998 and 2006[J].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China,2013,4(2):99-118.
[35]马万华,麻雪妮,耿玥.“千人计划”学者回归的动因、学术优势与挑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1):94-97.
[36]高子平.学术相关性维度的海外理工科留学人才回流意愿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30(6):74-81.
[37]ZWEIG D,FUNG C,HAN D.Redefining the brain drain:China’s diaspora option[J].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2008,13(1):1-33.
[38]谢荣艳,葛鹏.基于组织层面的科研机构人员流动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7(1):129-135.
[39]ZEITHAMMER R,KELLOGG R P.The hesitant hai gui:return-migration preferences of U.S.-educated Chines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3,50(5):644-663.
[40]QIN F.Global talent,local careers:circular migration of top Indian engineers and professionals[J].Research policy,2015,44(2):405-420.
[41]ALBERTS H C,HAZEN H D.There are always two voices:international students′intentions to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5,43(3):131-154.
[42]高子平.全球经济波动与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战略转型[J].科学学研究,2012,30(12):1810-1817.
[43]COE N,BUNNELL T.‘Spatializing’ knowledge communities:toward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J].Global networks,2003,3(4):437-456.
[44]JÖNS H.‘Brain circulation’and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s:studying long‐term effects of academic mobility to Germany,1954—2000[J].Global networks,2009,9(3):315-338.
[45]GIBSON J,MCKENZIE D.Scientific mobility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high emigration countries:evidence from the pacific[J].Research policy,2014,43(9):1486-1495.
[46]JONKERS K,CRUZ-CASTRO L.Research upon return: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n scientific ties,production and impact[J].Research policy,2013,42(8),1366-1377.
[47]陈代还,段异兵,潘紫艳.二元关系网络对海归科学家产出的影响[J].中国科技论坛,2015(9):143-147.
[48]LI F,MIAO Y,YANG C.How do alumni faculty behave in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 analysis of Chang Jiang Scholars in China[J].Research policy,2015,44(2):438-450.
[49]杨张博,高山行,刘小花.近朱者赤: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归国者跨国社会资本转移研究[J].社会,2015,4(35):177-198.
[50]ADAMS Jr R H.International migration,remittances,and the brain drain:a study of 24 labor-exporting countries[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3069,2003.
[51]刘俊婉.高被引科学家人才流动的计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1,29(2):192-197.
[52]WANG X,MAO W,WANG C,et al.Chinese elite brain drain to USA:an investigation of 100 United States national universities[J].Scientometrics,2013,97(1):37-46.
[53]张松涛,关忠诚.科技人才的教育经历研究——以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15(12):132-137.
[54]高子平.海外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科研管理,2012,33(8):89-105.
[55]ZWEIG D.Competing for talent:China’s strategies to reverse the brain drain[J].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2006,145(1-2):65-89.
[56]曹聪.中国的“人才流失”“人才回归”和“人才循环”[J].科学文化评论,2009(1):13-32.
[57]董洁林.“天生全球化”创业模式探讨:基于“千人计划”海归高科技创业的多案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4):26-38.
[58]赵卫华.海归博士与本土博士职业成就比较:基于全国博士质量调查的统计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0(11):47-50.
[59]鲁晓,洪伟,何光喜.海归科学家的学术与创新: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数据分析[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4(2):7-25.
[60]余广源,范子英.“海归”教师与中国经济学科的“双一流”建设[J].财经研究,2017,43(6):52-65.
[61]SUN Y,LIU F.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related technology spillover:a composite approach of network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theory[J].Scientometrics,2013,94(3):963-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