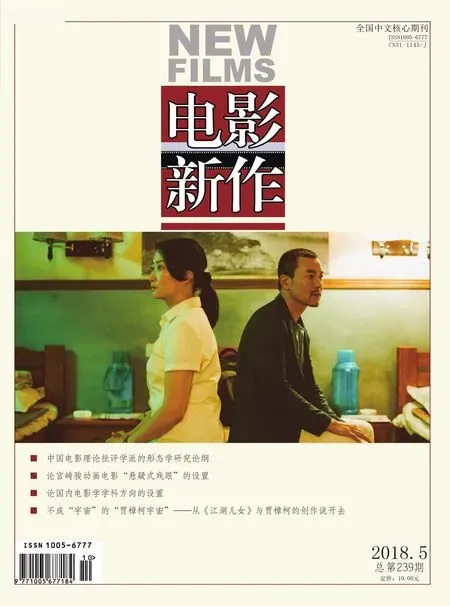论《燃烧》对跨国际文本的有效改编
王作剩
小说,特别是本土小说,素来是民族电影的重要改编素材,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国际文本的共享性、普世价值的共识性、异国风情的审美性、全球市场的占有性等目的,包含小说在内的跨国际文本越来越成为民族电影青睐的改编对象。在全球视野下,鉴于对文化亲缘性、改编成本等方面的考量,目前跨国际文本电影改编大致形成了欧洲、欧美、亚洲等几大重要板块。近年来,由于东亚文化的接近性等原因,属于亚洲的东亚跨国际本文电影改编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现象。中国将《犯罪嫌疑人X的献身》《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等日本小说改编成了《犯罪嫌疑人X的献身》《妖猫传》等电影,韩国将中国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改编成了同名韩国电影,并大量改编《父女七日变》《白夜行》《金色梦乡》《现在去见你》等日本小说。在此环境下,《燃烧》作为李沧东的第六部电影作品,同样改编自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并借鉴了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小说《烧马棚》。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对时空的调整、主题的位移、风格的承继等方面的努力,《燃烧》成了一次对跨国际文本成功而有效的改编,它既保留了原小说的叙事骨架,又实实在在地将其本土化,并巧妙融入了李沧东的作者元素,使之成为一部具有李沧东独特风格的韩国影像作品。

图1.电影《妖猫传》
一、时空的调整:由对时间的执念到对空间的重视
故事、影像皆具时空属性,即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内。而作为其重要载体的小说与电影,由于时代审美的变迁、艺术形式的固有差异、创作者的自我偏好与主题、风格的功能需要,时空在同类或者不同文本中往往具有不同的侧重与意蕴。诚如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所说:“有些艺术媒介的叙事只重视因果及时间关系,很多事件并不强调动作所发生的地点。而在电影中,空间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图2.电影《许三观》
由此观之,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自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开始,便在重视空间的同时,更加突出对时间的书写,折射出对时间迷恋的特质。写至第四部短篇小说集《萤,烧仓房及其他》时,时间更是萦绕于文字间,将读者拉入回忆或者当下的情境中。例如《萤》中的“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十四五年前”,《盲柳与睡女》中的“十四岁”“十点十分”等等。而在《烧仓房》中,作者通过“三年前”“两年前”“三个月后”“十月间一个周日下午”“去年的十二月中旬”“又一个十二月转来”等时间的提示,按照从过去到现在的线性顺序讲述了“我”“她”与“他”间的故事。作者对于时间的明确指认与反复书写,除了满足叙事需要外,更饱含着情感意味。时间于作者或者小说中的主人公“我”而言,是自我存在的明证与情感寄托的载体。“我”清楚地记着“三年前”与“她”的相识,又在时间的流转中结识“他”与失去“她”,并在日复一日对附近的仓房的查看中迎来“又一个十二月转来,冬鸟从头顶掠过,我的年龄继续递增”。流逝的时间正好是自己生命存在的证明,而时间的流逝恰恰给“我”带来了难以消除的伤感,让“我”沉湎于过去的记忆,生活在现实的孤独中。时间被寄予了不动声色却又缠绵悱恻的深情。
与迷恋时间的村上春树相反,李沧东具有非同一般的空间意识,且在《燃烧》之前的五部电影作品与一部《道熙呀》监制作品中,一如既往地承继着对空间的书写。与之一脉相承的是,在对跨国际文本《烧仓房》的改编中,李沧东便承继了过往的空间书写经验,增加了原作中不曾有的多重空间,且置换了原作中的时间之维,将原本三年的故事浓缩在短时间内的李式空间中,其情感也转向更加丰富的社会议题与心理结构之中。纵观李沧东的电影作品,家庭空间是典型的李式空间,而与温情的家庭伦理剧中的家庭空间不同的是,电影中的“家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避寒的港湾,而是成了又一个悲剧衍生的伤心地”。比“绿色三部曲”《诗》《密阳》更残酷的是,《燃烧》中的家庭空间由之前作品的杂居变为独居,由之前的情感疏离变为彻底破裂,被抛弃的孤独感更加浓重;更丰富的是,《燃烧》通过主角在三组家庭空间的迁移,悄无声息地凸显了韩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和贫富差距的形成。其中,身陷卡债的惠美被家庭拒之门外,租赁的房间是其暂时的寄居之地,钟秀的房间坐落在朝鲜与韩国的交界处,偏远而贫穷,时常听到朝鲜对韩国的政治宣传广播,此空间的设置尽显巧妙与荒谬,为钟秀自己的遭遇、母亲的离家、父亲的暴力做了无声而有力的政治解释,也反映出导演对钟秀家何以至此的深切同情与对时局的控诉。本居住在江南区的高级公寓内,面积巨大、厨房精致、厕所豪华。正是通过对三处家庭空间的对比与钟秀所感慨的“韩国的盖茨比太多了”而完成了“年轻人为何愤怒”的社会议题。而在非对比的情境中,也就是在自家或者具有亲密关系的家中,愤怒、焦虑的个体开始走向自由。在高档场所中,钟秀一般处于失语状态,话语权被自我放弃,而一旦回到自家与惠美家时,他便恢复了说话能力,甚至在喂牛与找猫时,快乐而自由唱起歌来。这便折射出阶层的空间所赋予钟秀的心理结构。其实,作为《燃烧》的共同编剧,李沧东虽然加入了惯有的家庭空间,但相较前五部作品,《燃烧》减少了对家人关系纠葛的描摹。
另外,自然空间、车内空间与餐饮空间也是突出的李式空间。李沧东电影中的自然空间向来是不幸的发生地,《薄荷糖》中田野上的铁轨是金永浩的自杀地,《密阳》中的荒野湖边是儿子抛尸的地方,而《燃烧》中的雪地是钟秀杀害本的场地。这种发生在自然空间中的不幸事件的设置,折射着导演对自然的敬畏态度。火车、汽车、货车、电车等车内空间,也是李沧东无比青睐的,这些空间除了完成叙事功能外,也同样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燃烧》中破旧货车与高档轿车的对比,揭示了贫富的差距所带来的阶层的隔阂。而餐饮空间也是李沧东电影常有的,《燃烧》正是通过咖啡馆、肥肠店、酒吧等餐饮空间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与阶层间不可打破的壁垒。此外,言语中的非洲与中国空间、电视中的美国空间、梦中的童年空间,都共同丰富着《燃烧》的空间语言。

图3.电影《白夜行》
二、主题的位移:由对消失的失落到对存在的焦虑
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名气大、受众广的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保持主题的延续性往往是至关重要的,这同样适用于对跨国际文本的电影改编。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电影改编与创作者都在主题上进行冒险,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同样作为作家的李沧东在与村上春树等人共同改编《烧仓房》时,便在原作主题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将对消失的失落的主题转为对存在的焦虑的主题。
众所周知,村上春树小说的主题往往为个体的孤独、人生的无奈、情感的疏离、周而复始的寻找与失落以及暴力,而且面对这些困境,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持平静、淡然接受的态度,并异常珍惜过往的记忆、青春岁月、昔日故乡,而非采取过于悲观或乐观的极端行为。《烧仓房》中的“她”是美好的象征,虽然无固定的收入,“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几个男友的好意接济”,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但“她”学哑剧、去非洲旅行、交新男朋友、保持单纯,且凭“无遮无掩不拘一格的单纯吸引了某一类型的人,在她的单纯面前,他们不自由自主地想把自己心中盘根错节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正是这样美好的人,在一次黄昏聚会后却凭空消失了,任“我”在宿舍寻找、电话联系、去哑剧班询问而不得。在寻找“她”的同时,“我”还在寻找被“他”烧的“仓房”。“他”为了保持“道德的均衡”而选择以两月一次的频率去烧仓房,“只消十五分钟就烧得干干净净,简直像压根儿不存在那玩意儿。谁都不伤心。只是——消失而已,忽地”。震惊的“我”从此走向寻找被烧仓房的道路。这里的“仓房”俨然是一切美好却无关紧要的事物与人,是《且听风吟》中家乡往日那片填平的海滩,是消失的1973年的弹子球机,是“偶闻牧歌余韵的60年代”,是消失的“她”。“对失去的东西满怀共鸣或者同情感”的村上春树,借“烧仓房”想表达的或许便是对滥用权力者、通过非法暴力“使这些美好往昔一个个消失不见的某种势力”的批评、对美好消失不见的无奈与失落。
而对于《燃烧》,李沧东想要呈现的是年轻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正如他所解释的:年轻人看待现代社会,可能觉得这个世界难以理解,甚至连自己的人生也无法掌握,就好像这是种谜一样。我希望通过电影来展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因此在电影改编中,加入了原作不曾有的惠美黄昏独舞、关于猫与井的存在的追问、雪地杀人等情节,延续了原作中个体的失落主题,并进而推广到群体的存在焦虑的主题,主题通过形象来阐发,形象即主题支线。《燃烧》主要塑造了三位阶层不同却困境类似的年轻人形象,以及其他同样深陷困境的群体形象。在“剥橘皮”这一段,通过惠美对非洲布希族舞蹈关于大饥饿与小饥饿的讨论,电影开始点题,并在酒吧展示饥饿之舞组合段、钟秀家黄昏独舞长镜头等中得以延续与深化。惠美本身便集小饥饿与大饥饿于一身,她身负卡债、无固定工作、靠当肢体模特为生,是为肚子饿的小饥饿之人;她去非洲旅行,追问人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何意义,畏惧死亡却又渴望像晚霞一样消失,希求最初自己不存在,是为灵魂饿的大饥饿之人。深陷何谓存在、存在何为泥沼中的她,将孱弱的希望投射在钟秀身上,却也无法得到钟秀的理解,最终在遭到自身意识局限的钟秀“你怎么能那样当众脱衣服,妓女才这么脱衣服”的身体否定与人格侮辱后消失了。与惠美的追问相比,钟秀遭遇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之苦、生理之苦、身份之苦,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之苦。大学毕业的钟秀靠搬运货物等零工为生,租“马桶就在洗手台”的便宜房子,餐后付账都将账单看得异常认真。身处物质困顿的人,性是稀缺的,爱人更是可望而不可求,钟秀只能靠在惠美的房间内,通过自慰来解决生理之需。他无法确认自己与惠美的关系,即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他渴望通过写作来实现自救,却不知道写什么,短时间内无法确定自己作家的身份。多重困顿将钟秀逼到了精神死角,他对惠美爱恨交加,他嫉妒抢走惠美与拥有巨大财富的本,并最终杀死了本。虽然本生活优渥,衣食无忧,但不会流泪的他同样遭受着存在的痛苦,于是他为了摆脱单调而选择旅行、厌倦酒肉朋友而选择容易流泪的惠美、通过寻找有趣和深刻的人与执行隐秘和暴力的事而获得“骨骼深处响起贝斯低音”的僭越法律的喜悦,以缓解自己的存在焦虑。但他的存在焦虑是无法治愈的,只能通过反复换女朋友、不停烧温室而得到暂时缓解,直到死亡来临,流下泪的他仿佛获得了最终的解脱。

图4.电影《燃烧》
拥有现实主义底色的李沧东,向来将个体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考察,其主题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燃烧》不仅要呈现个体的孤独、失落和存在的焦虑,更要揭示出存在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正是因为被父母抛弃、被社会遗弃、被男权控制,惠美才最终消失;正是因为身处朝韩边界贫穷地区、母亲对自己的抛弃、父亲对自己愤怒的管理无能、严重的失业问题、巨大的贫富差距,钟秀才走向极端暴力;正是因为身处食物链的顶层,本生活在浮华的物质表面,无法得到精神的抚慰,本才只能寄托于隐藏的暴力。不管是钟秀、本,还是钟秀的父亲、销售女郎,他们都拥有着共同的愤怒,而这种普遍的愤怒情绪与韩国社会息息相关。
三、风格的承继:由对现实的幻化到对真实的诗化
杰出的文艺作品流淌着创作者独特的气息与个性,反映着创作者的意趣与美学追求。因此,自有气息与风格的作品或者作者是很难被别人完全模仿的。那么,在对小说文本的电影改编中,能够承继原作中的风格自然是好的,但能够在承继中拓展,甚至打破之后又自建风格则是更妙的。比较《烧仓房》与《燃烧》便会发现,后者的风格是对前者的成功承继,同时又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拓展,融入了李沧东独特的审美韵味。
作为风靡世界的村上春树,其创作的小说既有匠心独运的语言风格,也有感同身受的现代性精神困境,即林少华所说的“作品的现实性包括非现实的现实性”。阅读村上春树的小说,读者会产生岛森路子一般的错觉:是我又不是我,是现实又非现实,是虚构又非虚构,精神视野中有而现存世界中无,但却又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作者本身便怀着这样的创作观念。认为“现实的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同时又是现实的”村上春树,一直在小说中构筑这样的世界。《烧仓房》便是一篇具有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相融风格或者说对现实进行幻化的作品。
整篇小说是偏现实的。人物是实在的、情感是真实的、情节是合理的、情境也是存在的,但这种现实感又掺杂着某种神秘。这种矛盾感受从小说开篇将“无”视为“有”并“剥橘皮”的哑剧便开始了,哑剧充斥着一种禅意,将读者的现实感从阅读中吸吮掉。三者的关系也让读者既觉得真实又匪夷所思,在“她”与“他”是情侣关系的情况下,却与“我”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且并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干涉,“我和她约会,他甚至开车把我送到约会地点”。当“她”消失,身为男朋友的“他”居然能够安然地生活而非焦虑地寻找,相反“我”却在寻找中焦虑并逐渐接受她消失的事实。最令人感到如梦如幻的是“他”竟然喜欢烧仓房,而烧仓房给读者带来的冲击恰如小说中给“我”造成的影响。“我”无意识地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当读者将剥橘皮、她的消失与烧仓房联系在一起时,“她”与仓房、消失与剥和烧便产生了紧密的关系,现实的周围弥漫着神秘的气息,不存在的存在感与存在感的不存在相互交织,是真非真的虚实世界融为一体。
正是《烧仓房》这种现实的幻化与神秘特质吸引了李沧东,让李沧东认为“可以将之扩充为一个层次丰富的故事”,而且令人喜悦的是,《燃烧》不仅承继了原文本现实幻化的特质,而且通过对光、猫、井、照片、火等意象符号的运用,通过黄昏独舞、寻找温室与钟秀全裸走向卡车等情节的设置,通过对乡村晨景深蓝色色彩与配乐《Generique》的选择等,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乃至创作的界限,呈现出了谜一般的影像世界,使电影有了一种真实的诗意。

图5.电影《密阳》
首先,意象让真实披上幻影。在承继“剥橘皮”情节基础上,电影又加入了猫与井的相似情节,使无与有的关系强化,让观影者堕入真实存在与否的谜境之中。猫粮、猫屎与本家突然出现的猫证明猫是真实存在的,但猫的不见踪影与房东的确切否认又印证着猫的不存在。抛却对猫存在与否的追问,情节设置本身富有某种游戏意味,能感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禅意与诗意。与猫相比,井在电影中的功能与意义更加丰富,它连接了钟秀与惠美、虚构与真实、过去与现在、存在与虚无。惠美幼年掉入井中并被钟秀救出的确认过程也是如此,毫无印象且视惠美为救赎之神的钟秀,唯有往返于惠美的亲人、邑长大爷、母亲之间,询问真相且在存在与不存在的回复中,才能获得某种痛苦而又自由的救赎。光对李沧东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绿洲》天花板上的光影、《密阳》结尾处的光影都有着了特殊的含义,而《燃烧》中的一抹光束,达到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境界。它是折射入屋而非直射的,是瞬间出现而非经常的,因此它于惠美而言是珍贵的,也暗示着惠美与美好生活之间渺茫的希望与巨大的距离。而它在钟秀与惠美做爱之时出现,并使钟秀停止做爱、深情凝视,乐中有悲却哀而不伤,达到了极佳的审美效果,产生了难以言说的诗意。
其次,惠美夕阳下裸舞、钟秀雪夜杀人让影片笼罩在无限诗意之中,堪称经典。朝鲜的扩音器声、牛叫声、夏虫低吟声、归鸟鸣叫等自然声音此起彼伏;风吹树摇,牛粪味飘散,三人屋前相聚,惠美率先进入梦幻时刻:脱去上衣,在朦胧夜色中开始起舞。在长达四分钟的裸舞长镜头中,中镜头下惠美腰部以上的肢体起舞在淡淡的夜幕近景中,而远景中还残留着红色晚霞,情景完美交融,惠美交叉的双手形似飞鸟,仿佛自由之鸟展翅而飞。起舞的惠美由背对摄影机到斜身的刹那,突然情不自禁地哭泣,继而滑出镜头;此后出现从左到右横摇的空镜头,镜头中近有草木、远有移动的如豆一般的车灯,丰富而静谧。整个裸舞长镜头实现了摄影、音乐、舞蹈、情感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统一,节奏舒缓,情感动人,韵味十足,堪称摄人心魄的天才影像。随后惠美进入屋中睡觉,屋外的钟秀开始对本诉说自己对惠美的爱,本说出自己“烧温室”的秘密,一切惊人的冲突都在静谧中呈现,静中有动,隐而不发。而电影结尾处钟秀雪夜杀本的镜头组合段,由夜幕、旷野与飞雪所组成的场景充满寒意,血染衣服的钟秀,选择将衣服脱掉并扔进汽车内一起点燃,自己全裸着、踉踉跄跄地走向卡车。此时移动的全裸着的身体,散发着某种决绝的冰冷诗意,冷酷而有力量,仿佛与过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告别,在摄影机前发表着某种宣言,带着一种意料之外的坦诚,宣告他们除此之外彻底一无所有。“尽管被无力和绝望包围,他们依然是支配自己身体的主人”。
此外,舒缓、迷幻、浪漫的配乐—《Generique》让影片充满韵味与诗意,而洪庆彪的摄影更是让影片拥有了神秘的质地。
结语
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燃烧》,可谓实至名归。由《烧仓房》改编为《燃烧》的有趣之处除了时空、主题与风格的变化外还在于,它不仅将一个国际小说文本改编成了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韩国电影,而且是将一个国际小说文本巧妙地改编成了另一个“跨国际”电影,在某个层面上李沧东这部电影超越了以往自己的作品,将韩国与世界进行了有效连接。首先,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对原作进行了继承,同时选择了韩裔美国人史蒂文·元作为主演;其次,电影中虽然没有出现一个外国或者外国人形象,但却通过语言出现了,比如惠美与本的旅行地非洲、钟秀家中电视台出现的美国特朗普演讲视频、聚会中本的朋友所言说的中国与中国人等,这些言语中的国家与外国人不是无关紧要的形式符号,而是精心设计的内容符号,与电影的主题有着紧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影片将韩国年轻人的困境与全球失业、贫富差距等所带来的世界年轻人的愤怒、精神的孤独、人生的虚无等对接起来。因此可以说,村上春树写出了国际化的小说,李沧东同样拍出了一部国际化的电影。
《燃烧》的国际化既归功于村上春树及文本的积极影响,也归功于李沧东监制的电影《道熙呀》等实践活动并从中获得的宝贵的国际化经验。因此在对跨国际文本的改编中,特别是对文化亲缘性国家文本的改编,应该像《燃烧》一样,既承继原作中的精华,又能有效将之本土化,符合本国的现实与审美,同时也要注入创作者的个人元素,更要兼顾国际化与本土性,使之成为一部国际化的民族电影或者具有民族性的国际电影。而这一点对目前的中日、中韩、中印等中外合拍片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注释】
1[美]大卫·波德莱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8.
2韩亮亮.悲歌一曲——李沧东电影的悲剧性初探[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08:16.
3林少华.村上春树作品的艺术魅力[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02):87-90
4林少华.村上春树作品的艺术魅力[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02):87-90
5[美]杰·鲁宾.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M].冯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91
6黑犬、Peter Cat.深焦x李沧东:为什么年轻人总是很愤怒?[E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 MjMzNTEzNg%3D%3D&idx=1&mid=2652286757&sn=773a06 8f863fb9c2105b2053b13a22dd,2018-5-19
7雷米.《燃烧》:世界静默如谜.[EB/OL].https://shimo.im/docs/7dsJUORi6z8jEb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