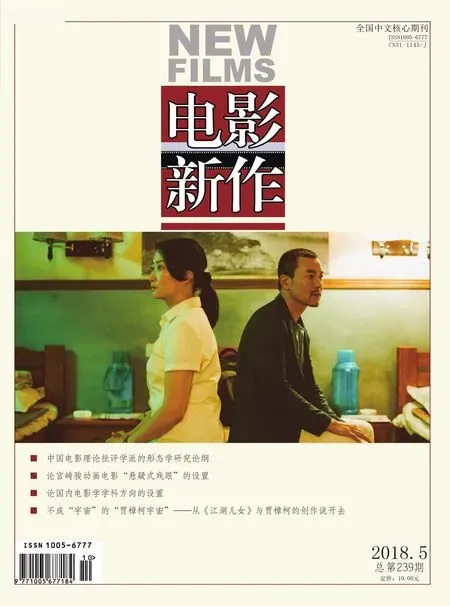被互文本建构的形象:章子怡明星研究
张 峰
明星是什么?理查德·戴尔指出,“明星乃是一种由电影和大众传媒等媒体文本一起参与建构的‘被建构的个体’,充满了历史的、美学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涵。在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图像时代后,电影明星早已渗透进大众文化的诸多层面,从书刊的封面、插图,到电视、网络的影像,明星不停地为商品,同时也为自己做广告,其‘广而告之’的特殊魅力似乎无处不在。”

图1.电影《卧虎藏龙》
章子怡作为华语电影最为重要的明星之一,她的成名之路似乎与21世纪之前的电影明星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巩俐是作为东方想象的视觉载体呈现在电影银幕之中,那么21世纪初的章子怡则是一个被互文本所建构的符号。章子怡成名的时代恰好是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时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随着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和《卧虎藏龙》在世界各地陆续上映,各大媒体都开始争先恐后地报道这位亚洲女性的新面孔,章子怡这个名字也开始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银幕内外形象的巨大反差,银幕内的章子怡不段尝试不同的角色类型以拓宽在电影表演中的可塑性,银幕外的她却得不到国内观众的认同,负面社会事件让章子怡备受争议。明星形象并非仅仅是由电影文本所建构的,而是被包括了电影文本在内的互文本共同建构的。本文借助理查德·戴尔在明星研究著作《明星》中所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方法为切入路径,研究被互文本建构的章子怡明星形象。
一、银幕内的形象:从单一到多元角色类型的探索
纵观章子怡塑造的各种形象,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角色类型的演变,可以将其在电影文本中的角色类型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呈现在银幕上的是清纯的女性形象,代表作品为《我的父亲母亲》,这一角色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对90年代巩俐银幕形象的延续。第二阶段主要以侠女形象为主,随着电影《卧虎藏龙》在国际电影节上的成功,章子怡也找到了这一新的银幕形象定位,随后连续出演了《尖峰时刻Ⅱ》《英雄》《十面埋伏》等影片。章子怡的“侠女”形象深受国际电影节评委和国外媒体记者的青睐,不仅帮它打开了通往国际舞台的大门,还摆脱了延续巩俐银幕形象的嫌疑。章子怡深知光靠“侠女”形象难免会戏路过窄,所以在成功将自己推向国际舞台后,她开始注重多元化银幕角色类型的探索。陆续参演了《2046》《茉莉花开》《狸御殿》和《艺伎回忆录》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似乎已经看不到“侠女”的身影。章子怡近几年所主演的作品,如《一代宗师》《非常幸运》《太平轮(上)》《太平轮·彼岸》《奔爱》《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问西东》等,似乎也并没有拘泥于某一种角色类型,而是在不断拓宽“戏路”的同时,去尝试演绎更多角色类型的可能。

图2.电影《茉莉花开》
章子怡首部出演的电影作品是《星星点灯》,她所饰演的角色“陈薇”是一个因身患癌症而截肢,被迫终止舞蹈事业的坚强女孩,银幕上的她显得十分青涩且稚嫩,坚强独立的品格让观众疼惜。但这部作品并没有给章子怡带来多大的影响力,让更多观众知道她的还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凭借在这部作品中出色的表演,章子怡还获得了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章子怡所饰演的“招娣”成功刻画了一个崇尚自由恋爱的女孩儿,她身穿粉色印花棉袄,扎着两个麻花辫,脖子上围着红色围巾,这一形象是章子怡早期在银幕内最先开始塑造的形象。理查德·戴尔在《明星》一书中认为,建构影片中的人物的三种方式,分别是“选择性使用”“完全匹配”和“非议的匹配”。在《我的父亲母亲》这部作品中,章子怡明星形象的所有方面同“招娣”特征完全吻合。年仅20岁还在上学的章子怡将“招娣”这一角色塑造得十分成功,观众也将其等同于章子怡真实形象的复现。“章子怡终于穿上了花棉袄和抿裆裤,带着青春而又浓郁的乡土气息,融进了张艺谋用摄影机演绎的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她爱上了到山里来任教的骆老师,但又不敢大胆、热烈地追求。整部电影中她跟骆老师说不上二十句话,炽热而又细腻的情感历程,全靠她的形体语言去做哀怨凄美的倾诉。”但也有媒体记者指出,章子怡早期的银幕形象似乎是20世纪90年代巩俐银幕形象的延续。随着《我的父亲母亲》在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荣获评审团大奖,章子怡开始被广大观众所关注。
不过,真正让国际电影节评委注意到章子怡的其实是《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一角。李安导演曾坦言,“老天爷赏饭吃,给了她这张脸”。根据李安的说法,章子怡的眼神十分具有杀伤力,这使她赢得了这个角色。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章子怡也是吃尽了苦头,原本就瘦小的她经过高强度的拍摄,显得更为消瘦。但也正是因为出演“玉娇龙”一角,奠定了她在后续影片中的“侠女”形象,更有媒体记者直呼她为“东方娇龙”。根据理查德·戴尔所提出的三种被用于建构影片中人物的方式,“侠女”形象可以看作是“非议的匹配”。这种成功的个案是靠选择性使用明星形象和明星形象同影片中人物完全匹配才做到的,但戴尔认为,明星形象的表意功能如此之强烈,常常会在建构人物时制造问题。“非议的匹配”所带来的结果是中外媒体和观众评价的巨大反差,中国观众并不认可“玉娇龙”这一角色,但在国际电影节和国外媒体报道中,这个角色却大获成功。“玉娇龙”在影片中体现为一个具有叛逆色彩的独立女性,她不接受父母安排的婚约,选择勇敢追寻自己的爱情。“玉娇龙”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大获成功,是因为这一角色背后所隐藏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十分符合国外观众的审美。《英雄》和《十面埋伏》等一系列影片再次强化了章子怡银幕内的“侠女”形象,例如章子怡在《英雄》中饰演的“如月”和《十面埋伏》中饰演的“小妹”。这些电影作品多为知名导演执导,而且在各大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例如《英雄》获得了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十面埋伏》则获得了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等。
对比《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英雄》中的“如月”,以及《十面埋伏》中的“小妹”,这三个角色除了共同塑造了章子怡“侠女”形象之外,还可以发现,这些故事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角色都是古装扮相,因此也就具有了浓厚的东方色彩。例如“玉娇龙”身穿轻薄的白色麻纱衣夜盗青冥剑的一幕。“玉娇龙”的造型和角色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符合国外评委对东方女性的想象,无论是电影节评选结果还是国外媒体记者的评价都是最好的证实。章子怡本人也深知“侠女”形象会束缚自己对角色的塑造,因此在之后的几年中,她开始尝试不同类型角色的塑造。随后章子怡便在《2046》《狸御殿》和《艺伎回忆录》等影片中开始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在这一阶段中,章子怡建构的银幕形象可以归纳为“选择性使用”,这是理查德·戴尔所提出的明星形象被用于建构影片中人物的第三种方式。“电影通过运用人物的其他符号和电影的修辞手法,能够让明星形象的某些特征呈现出来,同时又把其另一些特征略去。换言之,应该从被建构的明星形象的多元性中提炼出一定内涵,以符合影片中人物的首要特征。”《2046》中性感且倔强的“白玲”,《狸御殿》中美丽可人的“狸姫”,《艺伎回忆录》中坚强勇敢的“小百合”,章子怡在这几部作品中的表演张弛有度,一方面获得了很多观众和评委的好评,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无论如何,章子怡所建构的银幕形象丰富了她在银幕内对多元角色类型的探索,从单一的“侠女”形象中成功跳脱了出来。
二、银幕外的形象:媒体文本中的负面形象
理查德·戴尔认为,“建构明星形象的不只是视觉符号,更是视觉、话语和声音这三种符号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既可构成明星的共同形象,也可构成特定明星的形象。它不仅呈现于影片,又呈现于所有媒体文本。”章子怡银幕内的形象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角色类型的探索,从她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的结果来看是成功的。但银幕之外的章子怡在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中所建构的形象与之形成的巨大反差成却为许多观众诟病章子怡的症结所在。
《东方早报》于2009年12月25日刊登了一则新闻,“海报被泼墨章子怡报案,经纪人声称有人精心策划”。“泼墨门”硝烟未散,又一条关于章子怡的新闻,在互联网上引发网民热议,“网名为‘善款去向’的网友在天涯社区发帖称,章子怡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宣布过的多宗捐助善款,只兑现了一部分。随后,网民们启动‘人肉搜索’,通过对当时章子怡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的捐款数额,与目前搜索到的实际金额进行比对,质疑其善款是否完全到位以及善款去向”。
银幕内的章子怡坚强勇敢、对爱情执著追求的形象与银幕外的负面形象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引起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各大娱乐媒体网站也对其进行跟踪报道。可疑之处在于,章子怡似乎已经受到这些负面新闻的影响,但却仍然继续出席各种活动。2010年4月20日,章子怡参加“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募捐活动特别节目”;上海世博会志愿者部也正式授予了章子怡“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宣传大使”称号;12月1日,章子怡作为红丝带基金形象大使出席“爱与艾的相连”公益慈善晚会。
章子怡作为明星,代表着社会中的典型美女形象,但她的明星形象远比这种社会典型所要复杂和特殊。章子怡银幕之外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影片宣传有关,在经纪公司和媒体的合作下,一次次被将章子怡送上各大媒体网站的头条,以博取观众眼球、获得流量与关注。她的形象由媒体文本制造,观众成了“明星现象”消费的潜在对象。中国观众对章子怡的态度几乎没有涉及她在银幕内所饰演的角色,更多是针对银幕外媒体文本中的负面形象。如果观众能够认识到章子怡的明星形象是被电影和大众传媒等媒体文本一起参与建构的“被建构的个体”,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章子怡明星形象在不同文本中会呈现出巨大反差。因为各种文本累积的形象并不足以构成章子怡的明星形象,明星形象其实是复杂的整体,是暂时的,也是一个被建构的多元性的概念存在。银幕内章子怡所塑造的角色形象与银幕外的形象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章子怡在银幕内外所建构的形象并非她一个人促成,而是由影片制作者、经纪公司和媒体共同建构的结果。
三、互文本的产物:明星形象的符号建构
本文所考察的章子怡明星形象并非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章子怡,而是考察互文本中章子怡的明星形象。章子怡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电影工业体制的完善,她的成功与其说是银幕内角色塑造的成功,不如说是互文本的产物。章子怡的明星形象作为互文本的产物,与时尚杂志、广告代言,以及大牌导演合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章子怡曾三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两次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影杂志《世界银幕》,一次单人登上《新闻周刊》封面,同时她还是首位登上意大利高端杂志《MUSE》的华人女星,至于登上《VOGUE》《ELLE》《BAZAAR》《COSMOPOLITAN》等各类时尚杂志封面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与此同时,章子怡还代言了众多国际品牌,2009年4月,Armani宣布章子怡成为亚洲区代言人并请她拍摄了广告大片;2009年9月,章子怡成为瑞士知名钟表品牌欧米茄的全球代言人;2012年11月,章子怡成为宝格丽与救助儿童会合作项目的国际形象大使。除此之外她还曾代言VISA信用卡、奔驰汽车等国际品牌。细数章子怡的成名之路,可以发现她的成功似乎与西方国家电影明星的发展模式一模一样:与大牌导演合作拍片、携带影片亮相各大国际电影节、通过走红毯获得国外媒体关注,接下来便是应邀时尚杂志拍摄封面人物和永远接不完的国际品牌代言。此外,明星们还会通过关注慈善事业来继续扩大影响力,维护公众形象。
“正如电影在中国并非纯粹的艺术,也非纯粹的商品,电影明星也非单单与电影相关,在他们身上也往往纠结着多重社会文化元素的复杂构成和多重权利关系的复杂运作。”大众传媒时代下的今天,明星现象既是一种生产现象,也是一种消费现象。作为生产现象,投资方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当然,这同时也是市场和媒体操纵的结果。占据新闻头条的不再是商业大亨和政要人物,明星包揽了各种大众传媒的头条版面,媒体愿意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去报道他们,观众也愿意贡献流量和点击量去关注他们。观众关注的点甚至不再是电影本身,明星的生活、爱情、社会事件都成为观众关注的对象。明星的形象早已不再局限于电影文本中,他们的形象还存在于电视、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等各种大众传媒的互文本中,他们不停地向观众兜售意义和情感。观众消费明星其实是对明星形象的喜好和自我认同,明星出演的电影、代言的商品和登上封面的时尚杂志都成了观众消费的产品,比起电影制作者和媒体而言,似乎消费者才是促成明星存在的重要力量。
结语
考察章子怡的明星形象,不能简单地局限于考察电影文本中的形象,而应将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如今的章子怡也不仅仅只拥有演员这一个身份,她还成了多部电影的制片人。章子怡明星形象是被互文本建构而成的,只有通过对各种互文本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才能够深刻剖析章子怡明星形象背后所隐藏的多元的意识形态内涵。
【注释】
①[英]理查德·戴尔.明星.[M].严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总序.
②丁亚平,张斌宁.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34-51.
③[英]理查德·戴尔.明星.[M].严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0.
④陈阵.跨越冬季——小记章子怡[J].大众电影,1998(12):21.
⑤[英]理查德·戴尔.明星.[M].严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2.
⑥[英]理查德·戴尔.明星.[M].严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9.
⑦[英]理查德·戴尔.明星.[M].严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3.
⑧东方早报.海报被泼墨章子怡报案经纪人声称有人精心策划[EB/OL].http://ent.ifeng.com/idolnews/mainland/detail_2009_12/25/226840_0.shtml
⑨羊城晚报.章子怡“泼墨门”硝烟未散又陷入“诈捐门”[EB/OL].http://ent.sina.com.cn/s/m/2010-01-28/14352859538.shtml
⑩陈晓云.电影明星、视觉政治与消费文化——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明星[J].文艺研究,2007(01):12-18+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