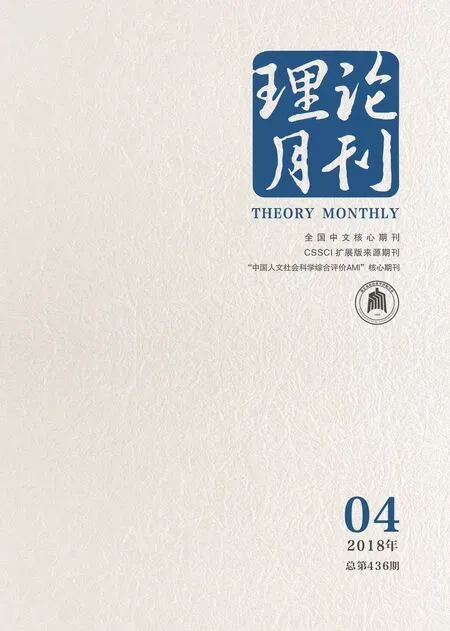论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筛查制度的构建
□ 孙海涛
(1.河海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2.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我国家庭暴力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调解制度具有诸多优点,例如节约司法资源、彻底解决社会纠纷、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等等。然而,调解制度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应用却凸显出诸多问题,通常表现为案件已了但事未了。调解制度的适用未能确保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结构的平衡,这就使得调解制度的适用前提即平等自愿荡然无存。这样的调解结果表面上使得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实质为受损社会关系的危机维持,并存在危机扩大的现实危险,被施暴者的权利损害进一步扩大,而施暴者的权力得到维护并成为调解制度最大的“获利者”,调解对于家庭暴力案件解决的实效全无[1](p43-69)。基于此,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家庭暴力案件调解适用的“度”是什么?调解是否可以不假思索而直接被强制适用于任何家庭暴力案件?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适用能否最终实现修复受损社会关系和保护被施暴者权益之间的平衡?
一、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问题性特征
(一)当事人之间的权力结构不平衡
调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为双方自愿。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才合法有效。我国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因为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结构不平衡,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而2015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则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即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的案件中规定了行政案件调解制度,这说明了无论何种性质的案件,调解均具有不可触碰的底线即当事人自愿。家庭暴力案件的调解是指施暴者与被施暴者双方平等地对未来行为进行协商。然而,在家庭暴力案件中,施暴者基于控制欲通过暴力手段确立自己的权威,施暴者绝对权威的确立意味着被施暴者的绝对服从。基于这种“控制”和“被控制”的情势,施暴者的一举一动均可能成为对被施暴者的一个暗示或警告。一旦被施暴者违背施暴者的意愿,可能导致十分可怕的后果。权力的悬殊或极度不平衡使得被施暴者无法也不可能基于自己的意愿主张合法权益,只能一味服从。权力结构的失衡使得家庭暴力案件的调解不具备平等自愿的前提条件,如若坚持调解结案,不但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之产生一种新的不公平。
(二)被施暴者的拒调解
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维护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的稳定。调解可以被简单理解为双方妥协,各自就自己的权利做出一定让步,但是对于受害人来讲,其根本没有可以放弃的权益。施暴者基于控制欲的享有当然不希望被施暴者脱离自己的控制,而基于修复社会关系的调解正迎合了施暴者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施暴者的不当权益。但是调解只是应用于私人领域的规则,并不能作为解决人权侵害的手段[2](p52)。被施暴者求助于司法的目的是通过断绝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来摆脱施暴者的暴行,维护自己正当且合法的权益。显而易见,被施暴者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拒绝调解的,调解违背被施暴者意愿且侵害被施暴者权益。然而,可能由于施暴者的施压,加上调解员或法官对调解的大力“引导”,唯一拒绝调解的被施暴者最后也只能无奈接受妥协,以表面上接受调解的形式替代了内心要求与施暴者脱离关系的强烈意愿,以极度恐惧的心理继续维持着随时可以产生“暴风雨”的社会关系。
(三)案件解决的非彻底性
调解与判决相比,其优点之一在于调解能够更为彻底地解决纠纷。然而,家庭暴力案件的调解可能建立在被施暴者非自愿的基础之上,被施暴者未能平等地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力结构的失衡导致拒绝调解的被施暴者被迫接受调解,调解的平等自愿已经荡然无存。这也造成了案虽了事却未了的现象频频发生,经过调解结案的案件,当事人在两年内再次提起诉讼的比率相当高。案件解决的不彻底性与调解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调解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更为甚者,法院被视为施暴者的“帮凶”,造成短缺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形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平。施暴者在控制欲再次得到满足之后,通常会变本加厉,进而引发刑事案件的发生或被施暴者的自杀。基于此,科学合理适用调解制度解决家庭暴力案件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和探讨的问题之一。
二、美国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筛查制度的缘起与演变
(一)产生与发展阶段:调解制度的确立与强制调解模式的形成
美国学者认为传统的诉讼方式解决家庭问题的诉讼成本较高、解决时间较长、矛盾易激化。与审判程序不同的是,调解的重点在于创设一个可行的中立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决定谁对谁错。在调解中会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协调和促进纠纷的解决。调解员并没有强制力或权力来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要求当事人同意[3](p467-471)。调解是当事方根据自己的意思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解决冲突的过程。调解的目标包括:减少法院的案件量、减少对司法资源的需求、加快案件的处理速度、降低解决争议的成本、提高当事人对法院的满意度以及改善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4](p304-306)。基于家事法的独特性,调解对于家事纠纷的解决具备独特效用。家事问题不仅仅涉及法律和事实,而且涉及情感。由于离婚和非婚生子女数量的增加,政府努力寻求诉讼之外的解决涉及包括子女探视、财产划分等家事纠纷的替代方法。而调解正是这样的一种方法①U.S.Bureau of the Census,U.S.DEP'T.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table 80(112th ed.1992).。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法院发起的调解盛行于美国。大部分案件进入调解程序,大约70%案件的通过调解会议得以解决[5](p1029)。而剩下30%的案件通过审判予以解决,这可能是基于程序起始于调解的原因。据美国佛罗里达州报道,其所调解结案的数量从1989年的34 000件上升到1991年的近50 000件。这个调解运动反映了佛罗里达州司法体系相对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6](p701-702)。同时在美国,超过150家律师事务所已经在一份声明中承诺鼓励他们的委托人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这些事务所承诺负责具体案件的律师将会与委托人讨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可用性,进而委托人能够在争议解决方面做出明智的选择[1](p43-69)。依据传统观念,调解一直被视为一个自愿的平等协商过程。最初,美国的一些法院采用了强制调解,要求双方当事人欲解决争议需先行调解。鉴于调解中的固有自我决策理念,强制调解的说法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但是,这些法规只是对调解程序进行了强制要求,而并未要求必须达成调解协议。1981年,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第一个实行强制调解制度的州[7](p64)。之后,许多法院颁行了类似的法令。不管是法律要求调解或者授权调解,一旦法院要求进入调解程序,那么各方当事人必须进行调解,除非法律有除外规定①Hendricks,Rule 1.740 of the Florida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expressly authorizes a trial court to refer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issues to family mediators.。
(二)改革阶段:家庭暴力案件免于调解制度的形成
虽然并不是美国所有的州在遇到家庭暴力案件时要求进行强制调解。但是,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发现调解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弊端,进而认为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免除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配偶之间的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所有已婚夫妇的30%。大部分家庭暴力的被施暴者是女性,调查显示只有5%的被施暴者为男性[8](p303-316)。家庭暴力案件的调解引起了人们对于安全的关注,因为研究发现在案件得到调解之后,家庭暴力情况进一步加重。调解也可能不能获得成功,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力量不均衡以及一方当事人的力量较弱而无法为自己争取权利或保护自己的权利[9](p2110-2120)。
基于学者的呼吁,美国一些州的立法机构也对家庭暴力案件免于调解做出回应。新墨西哥州颁布了第一个免除法令,许多州也跟着效仿。随后,加利福尼亚州修改了法律,规定家庭暴力案件免于调解②California Family Code 3181(West 1994)(exemption where party claims it has been victim of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abuse by the other party).。这些免于调解的措辞和免于调解所需家庭暴力程度的证据要求在各州之间存在差异。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当任何一方成为家庭暴力、身体虐待、精神虐待、情绪困扰、配偶虐待、性虐待、家庭虐待、吸毒或者酗酒的被施暴者时或者具有正当理由包括对方具有酗酒、吸毒、或者具有严重的心理、精神或情感问题时,当事人可以免于接受调解。新罕布什尔的法律规定,当一方当事人声称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时则可以免于调解,除非被施暴者请求调解。俄亥俄州要求法院对家庭暴力情形进行考虑,但是假如法院认为案件适合于调解,那么则允许对案件进行调解。在伊利诺伊州,法院可以对探视纠纷进行调解,除非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北卡罗来纳州法院对于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免于调解。北卡罗来纳州提供了一个免于调解的正当理由,包括对家庭暴力或者忽视未成年子女、酗酒或者吸毒的指控。犹他州规定免于调解的情形主要有调解会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一方或双方的子女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或者精神或身体健康或安全受到威胁。缅因州的儿童监护立法要求调解员考虑家庭暴力的所有历史。佛罗里达州免于调解的情形为假如存在较为严重的家庭暴力史,那么这会阻止调解的进行[1](p43-69)。
从对调解的批评我们可以观察到调解只有在双方讨价还价的权力相对均衡时才是可取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后,一些州开始规定当调解不符合案件事实时或者当一方当事人反对调解且提出很恰当的理由时则免于进行调解。在各种免除条文中,州立法授权参与者主观判断的权力。当参与者有权力决定家庭暴力是否已经达到排斥调解的一定水平或者满足正当理由的标准,那么他们就拥有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来确定是否适用调解。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律师、书记员、法官和调解员必须具有做出此决定的能力①Lorraine A.Rimson,Divorce Mediation and Partner Abuse,Newsletter(Florida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Tallahassee,Fla.),Spring 1992.。两个州的立法警示了所有强制进行调解的州。新罕布什尔州规定免于调解,除非提出控诉的被施暴者请求调解。新墨西哥州规定如果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那么法院应该停止调解,除非(1)调解员在家庭暴力影响方面接受过大量的培训;(2)一方当事人在权力失衡的情形下能够进行谈判;(3)调解过程包括适当的规定能够防止权力的失衡②Annotated Statutes of New Mexico.40-4-8(b)(1)(1994).。
(三)深化阶段: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筛查标准的确立
识别施暴者的危险程度以及被施暴者的安全可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由于担心受到威胁或者伤害,被施暴者在回答审查者问题的时候存在困难,从而可能会存在隐瞒家庭暴力行为的情形。因此,审查者应当尽量避免提及暴力行为,即使是暴力行为的个别事件[10](p24)。审查者需要了解一方当事人所要面临的暴力情况、避免暴力的策略、以及暴力行为在心理、身体、经济和社会方面对对方造成影响的方式。审查者应该明白,家庭暴力是一个不可避免地改变亲密关系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模式。这种暴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仅仅发生在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内的两者之间为了决出胜负的格斗。通常在他们的关系情境中,双方都能够理解特殊行为和言语的含义。一句简单的话例如“记得上次的感恩节吗”可以被视为一种控制暗语,代表着过去这个时间殴打的暗示。被施暴者必须遵从或者接受这样的后果[11](p113-123)。虽然先前存在暴力行为或者处于“暴力文化”之下的关系,但是审查者在提出每一个调解建议之前,必须确认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仍然能够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调解。虽然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调解人员来讲可能会发现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调解标准的确定与适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存在“殴打文化”,那么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免于调解就是必要的。如果暴力不是很严重,而仅仅是存在家庭暴力的个别行为,并未达到一方完全控制另一方的程度,那么双方之间可以进行安全且公平的调解[12](p50-64)。与“殴打文化”存在关联的有三个要素:首先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暴力行为,要么存在于身体、情感、性,要么存在于经济方面;其次,存在一种打人者支配和控制的系统模式;最后被施暴者存在隐藏、否认并淡化暴力的情形。一旦对暴力量化进行了定义,那么案件参与者必须确定暴力行为是否已经影响到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判定不适用调解解决问题。为了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当事人各方需要对当事方进行审查。审查者的提问涉及各种层级和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性、经济和情感虐待[1](pp43-69)。
三、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筛查制度构建的模式演变规律
(一)单轨制演变为双轨制
单轨制与双轨制的划分依据是调解制度的运行过程。我们以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为例来进行阐述。所谓单轨制是指被施暴者基于家庭暴力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首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也不判决离婚,被施暴者再次向法院起诉,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判决离婚。双轨制是指被施暴者基于家庭暴力向法院起诉离婚,法官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或直接进行判决,如调解成功,被施暴者再次起诉离婚,则法院根据实际案情进行判决;法官结合代理律师等各方是否适用调解的意见认为案件不合适调解,则径直判决离婚。单轨制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大局的结果,更多地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利益与价值,牺牲了个人即被施暴者的权益。正是基于对个人权益的侵害,导致被施暴者个人权益保护与社会整体权益保护之间的失衡,美国人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站出来对单轨制予以谴责和驳斥,提出应该废除单轨制,构建双轨制。双轨制基于单轨制的弊端应运而生,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裁量权即可在调解和判决之间进行选择,对于法官认为不适合进行调解的家庭暴力案件,其可径直进行判决,这种判决意味着对被施暴者权益的保护,保护其脱离家庭暴力的侵害,真正发挥司法的救济与保护作用。
(二)强制模式转向可选择模式
强制模式与可选择模式的划分标准是调解是否为前置必要条件。所谓强制调解模式是指对于所有家庭暴力案件必须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行判决。可选择模式意味着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进行调解,也可以不进行调解而径直判决。不难看出,单轨制、双轨制与强制模式、可选择模式一一对应。适用单轨制的国家通常会伴随着强制调解模式的应用,应用可选择模式的国家也基本适用双轨制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强制模式限制了法院的权力,同时也给公民行使诉权设置了障碍,阻碍了公民裁判请求权的实现。强制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而这种弊端在家庭暴力案件中显得尤为突出。被施暴者行使诉权的目的是为了在第一时间逃离施暴者,对于家庭暴力较为严重的受害者来说,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然而,强制模式使得法律对被施暴者无法进行帮助,反而可能被受害者视为家庭暴力的“维护者”。为了弥补强制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需要通过其他制度或程序来对强制模式进行补缺,例如需要增加调解适用的审查程序,将严重家庭暴力案件排除在调解之外,补缺之后的强制模式就演变为可选择模式。在此大背景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成立了专门会议对案件进行评估,比如1996年英国《家庭法》规定家事调解程序须由强制性的案件评估会议开始[13](p80)。
四、我国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筛查制度的构建
行文至此,可以对文首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从国外调解制度的演变与重塑路径来分析,我们可以将家庭暴力案件调解制度适用的“度”的要件划分为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为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双方当事人自愿,实质要件为切实保护被施暴者的合法权益,此实质要件也可以被视为确立调解筛查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调解制度的适用必须在满足形式要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实质要件的实现。不难发现,调解制度并不能够被直接适用于任何家庭暴力案件,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和加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员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审查,对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解,实现修复受损社会关系和保护被施暴者权益之间的平衡,而对不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家庭暴力案件可以不进行调解而径直判决。
(一)问题反思
我国一直重视并致力于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于2015年12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本法的亮点之一在于借鉴国外相关的规定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即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追求的是一种事前保护或者适度的事中保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美国防范家庭暴力、保护被施暴者的重要行政司法手段,美国法律规定施暴者一旦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即可构成刑事犯罪,警方认为违反保护令行为发生后必须对侵害一方进行逮捕。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既没有能够明确警察对违反保护令的强制逮捕权,也未对具体的操作程序予以规定,因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效难以保证。对于保护令的实践操作无法发挥实效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被施暴者会转而求助寄希望于司法救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出台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将调解确定为审理家庭暴力离婚案件的重要方式,并对案件的调解程序和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审理指南》对司法领域中家庭暴力案件解决的指引作用不言而喻。我国2015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但不应久调不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九十九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对家庭暴力案件调解实行的是强制模式。对《民事诉讼法》和《婚姻法》的规定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强制调解模式下双轨制的存在,即人们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必须先进行调解,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调解成功结案,另外一个是调解不成功则进行判决。其实,这是一个“隐性”双轨制,在现实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单轨制,即对于离婚案件,法院对于初次起诉通常不判离,再次起诉即判离。这是司法过程中对立法规定具体实施的偏离,但是欲通过司法改革改变现状难度极大。我们可以通过修法将“隐性”双轨制变为“显性”双轨制,通过立法的明确规定对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以实现调解制度双轨制的适用契合立法规定,促进适用效能的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款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这对于家庭暴力中被施暴者意味着,他们在“现实单轨制”的拘束下又加上了一副沉重的时间枷锁,即强制调解达成和解后,被施暴者在六个月内不能起诉离婚。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调解制度具备超越国界的特性与优点,对于大多数民事争议解决的可行性与实效性,调解制度在解决家庭暴力案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调解制度“繁荣”发展的背后,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家庭暴力案件调解所带来的问题。我国针对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没有规定在调解开始之前对家庭暴力进行审查。事实上,尽管审查表明存在较为确切的暴力史,但是我国法律规定对离婚案件首先应该进行调解,法律只规定了在存在家庭暴力且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才应准予离婚,而这个规定仅仅是“可选择模式”的表象,在实际司法实践中鲜有适用。因此,尽管存在家庭暴力,而法院在没有对案情进行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基于法律的规定仍然会对此案件进行调解,我国对于家庭暴力案件实行的是强制调解和单轨制,调解筛查制度缺失。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解已经形成一种“定势”,更成为一种习惯,用统一的方式或手段解决具体情况各异的家庭暴力案件,并不能够触及家庭暴力案件的本质问题所在,家庭暴力问题也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对调解之后可能存在的危险也无法预测和解决,调解员还通常被误解为施暴者的“帮凶”,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损害司法公正的形象,更为严重的还会引发刑事案件。因此,不难发现,调解制度不是完全可以不假思索地运用于家庭暴力案件,需要专业人员在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把握调解制度适用的度,在调解制度基础之上增加家庭暴力案件的筛查制度,重塑契合家庭暴力案件的调解制度,并借此检视和反思我国现有的家庭暴力案件调解制度。
(二)制度构建
1.确立筛查标准。筛查者指出针对家庭暴力案件调解无法掩饰的热情的最初冲击波和整体上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已经让位于清醒之后的再决策[14](p177-179)。家事案件并非都适宜于调解解决,过度依赖调解存在危险,因为强势当事人一方会利用调解制度来侵蚀弱势当事方的权益[15](p59)。同时由于调解不确认对错,更不对施暴者实施惩罚,进而无法避免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受害人在诉后遭受更为严重的暴力伤害,严重情况下受害人会选择自杀或引发恶性刑事案件[16]。女权主义者和受虐妇女倡导在发现任何家庭暴力时反对调解的适用,并认为调解对女性有害。家庭暴力证明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存在。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存在于众多离婚案件中,它可能会对双方当事人能否进行有效调解产生影响。部分家庭暴力基于其性质可能永远无法调解。一旦发现暴力,参与者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案件进入调解程序[17](p717-721)。但是,如果各方当事人明确排除一方控制对方,而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即使存在或多或少的暴力行为,家庭调解包括的子女监护权、探视、资助等问题均可进行协商。如果家庭暴力并未造成权力的不平衡,那么许多家庭问题可以成功调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习惯性暴力案件与偶尔发生的暴力案件进行区分,习惯性暴力通常不适合调解,而偶尔发生的暴力案件双方当事人能够平等地谈判。由此可见,筛查标准之一即是家庭暴力是习惯性还是偶发性,同时不得不纳入考虑的是家庭暴力造成的伤害程度,家庭暴力是否已经严重威胁到被施暴者的人身安全。不幸的是对于习惯性和偶发性暴力状态并无明确的划分界限。然而,我们可以由程序中每个参与者进行筛选,将不适合调解的案件剔除出调解范围。
综上,我国应该在现有的家庭暴力案件调解制度之内确立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筛查制度。筛查制度是由家庭暴力案件的参与者包括代理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人民调解员、书记员和法官等对案件进行调查与评估,依据筛查标准及家庭暴力是习惯性还是偶发性、家庭暴力是否严重威胁到被施暴者的人身安全等,结合案件事实做出案件是否适合调解的判断。然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简单地问及当事人是否虐待他人或者被虐待,那么这往往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筛查工作的承担人员应该进行严格的筛选努力发现家庭暴力。被施暴者可能会将存在严重的言语、心理障碍或者会视家庭暴力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筛查者应该在所有参与者共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地调查。当然,筛查制度的实效无法离开筛查者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因为一个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能够掌握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度”,往往更能够通过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访谈来发现案件事实并做出较为精准的判断。因此,在多层次的筛查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需要接受家庭暴力以及由于家庭暴力而导致的权力不平衡方面专业知识的培训,使每个参与者在对家庭暴力进行调查与分析,将案件事实与筛查标准进行结合,做出案件是否适用于调解的决定,对家庭暴力案件是否适合调查进行专业“过滤”。
2.明确筛查程序。程序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即家庭暴力的筛查者参考家庭暴力案件免于调解的标准基于案件事实做出案件是否适用调解的判断过程。审查程序在确保各方安全的前提下必须足够简单以确保广泛使用和统一应用。案件的参与者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会发现家庭暴力的存在,他们应以具体案情为依据对此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做出初步判断。案件参与者并非指当事人,而是家庭暴力案件法律程序的参与者:人民调解员、代理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法院书记员和法官。法官必须对家庭暴力进行审查,来确定案件是否适用调解。然而,这个决定的做出并不仅仅是法官的责任。因为在法官处理案件之前,其他参与者应该通过向当事人询问家庭暴力的情况等手段或方式来对家庭暴力情况进行初步审查和判断。人民调解员作为最初的案件调解人必须对其解决范畴之内的所有家庭暴力案件进行筛查,如果经过筛查发现家庭暴力案件不适合进行调解,那么应该向当事人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政府要不断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18](p155)。作为法律援助工作者或代理律师,应在最初的诉状中提供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以及提出案件是否适合调解的建议。当家庭暴力案件到达法院书记员手之后,书记员应该确认家庭暴力是否已经发生与严重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决定家庭调解是否应该适用。在决定是否对案件进行调解之前,法官必须对家庭暴力是否存在以及案件能否成功进行调解做出结论。假如在多层次筛选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参与者认为案件不适合调解,那么免于调解即可能成立。
3.完善相关立法。家庭暴力案件具有不可调解的特殊性,我国立法虽然通过“隐性”方式进行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却出现了偏离,这就需要我们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中汲取经验,即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相关立法如《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需要将家庭暴力案件划分为两种类型:可调解和不可调解,对不可调解家庭暴力案件的类型予以明确规定,以限制法院在适用家庭暴力案件调解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屡次实施家庭暴力、情节严重的,公权力的干预必须从适度干预变为主动干预[19](p162)。对于不可调解的家庭暴力案件,法院无需进行调解,而可径直判决。对于可调解的家庭暴力案件,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再予以判决。基于此分类,针对家庭暴力的案件,立法应该规定案件的参与人员在各个层面进行审查,当参与人员发现存在家庭暴力时,那么根据家庭暴力的具体情况确定是否排除调解制度的适用。立法也应该要求所有参与者尤其是人民调解员需要接受必备的培训和掌握必备的知识来识别家庭暴力的存在与严重程度。参与人员必须了解家庭暴力,审查每个案件是否存在暴力,审查是精神暴力、身体暴力还是两者兼有,审查暴力的严重程度。在立法中体现出对家庭暴力的思考,由于家庭暴力尤其是精神暴力通常具有隐蔽性,立法机关应该通过对可能存在的暴力类型进行定义来提供指导,案件参与者可以依据立法规定在筛查过程中证实这些暴力的存在。
进一步分析,立法需要对《民事诉讼法》和《婚姻家庭法》中调解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改变现有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单轨制与强制模式,确立双轨制与可选择模式,即在现有的调解制度基础之上增加家庭暴力案件调解的筛查制度,要求各个层面的案件参与者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筛查,当参与者发现存在较为严重的家庭暴力的证据时,那么可以建议或判定案件不适合调解。立法应该赋予法官是否启动调解程序的自由裁量权。具体修改意见为:第一,将强制调解模式修正为可选择模式,可以通过修法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将针对家庭暴力案件法院应当进行调解的规定修改为可以进行调解,具体到《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应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九十九条应修改为:不适合调解的案件、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应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可以进行调解。第二,将单轨制修正为双轨制,《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应增加规定:人民调解员、代理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书记员等案件参与人员应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筛查,对有证据证明存在家庭暴力且达到比较严重程度的案件,应建议免于调解,并最终由法官进行决定。立法还应增加规定对案件参与人员的培训,以增加他们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识别家庭暴力的能力。在规定调解的免除时,立法必须建立详细的指引,也即立法应该尽量明确调解适用应当考虑的基准。这些指导原则应针对能够决定是否免于调解的参与者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执行保护措施的方法。通过修法对权力失衡不适用调解的案件确定明确的适用标准。所有参与者都要负责任地对家庭暴力案件需要实行多层次的筛选程序。更为理想的情形是,立法者会从严重程度的变量方面对家庭暴力进行定义。该变量应该被纳入识别家庭暴力的工具及其严重程度。同时可以对家庭暴力的定义进行扩大,在身体攻击之外,还应包括经济、情感和性攻击。
五、结语
不是所有的家庭暴力案件都可以进行调解,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筛查以确定家庭暴力案件是否能够调解的根本目的在于切实保护被施暴者的权益。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对家庭暴力案件不完全适用调解达成共识,因为他们认为调解只能够发生在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且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达成,而家庭暴力案件中对施暴者“狼”与被施暴者“羊”的调解是无意义的,法律不能够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将被施暴者禁锢在家庭暴力的境地之下。因此,在我国家庭暴力案件调解制度之内应该增加家庭暴力案件的筛查制度,将单轨制转换为双轨制、强制模式转换为可选择模式,将超过调解之“度”的家庭暴力案件拒于调解之门外,重塑家庭暴力案件调解制度,实现修复受损社会关系与被施暴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Gerencser,Alison E..Family Mediation:Screening for Domestic Abuse[J].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5-1996(23).
[2]周安平.《反家庭暴力法》亟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分析[J].妇女论丛研究,2015(2).
[3]Joshua D.Rosenberg.In Defense of Mediation[J].Arizona Law Review,1991(33).
[4]Elizabeth Koopman et al..Professional Per⁃spectives on Court-Connected Child Custody Mediation[J].Family Courts Review,1991(29).
[5]Sharon Press.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a Statewide Mediation Program:AViewfromthe Field[J].Kentucky Law Journal,1992-93(81).
[6]Robert B.Moberly.Ethical Standardsfor Court-Appointed Mediators and Florida's Mandatory Mediation Experiment[J].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4(21).
[7]George Ferrick.Three Crucial Questions,Me⁃diation Quarterly[J].Fall 1986.
[8]Kathleen O.Corcoran&James C.Melamed.From Coercionto Empowerment:Spousal Abuseand Mediation[J].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2010,7(4).
[9]Karla Fischer et al..The Culture of Battering and the Role of Mediation in Domestic Violence Cases[J].46 SMULaw Review,1993(46).
[10]Mary Ann Dutton.The Dynamics of Domestic Violence:Understanding the Response from Battered Women[J].Florida Bar Journal,1994(10).
[11]A.L.Cantos et al..Injuries of Women and Men in a Treatment Program for Domestic Violence[J].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1996(9).
[12]Holly A.Magana&Nancy Taylor.Child Custody Mediation and Spouse Abuse:A Descriptive Study of a Protocol[J].Family Court Review ,2010,31(1).
[13]吕锋,王琼雯.调解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选择及规范[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2).
[14]Penelope E.Bryan.Reclaiming Professional⁃ism:The Lawyer's Role in Divorce Mediation[J].Fami⁃ly Law Quarterly,1994(28).
[15]汤鸣.家事纠纷法院调解的范围与限度[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16]陈敏.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不宜调解结案[N].法制日报,2009-7-17(3).
[17]Mary Pat Treuthart.In Harm's Way?Family Medi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Attorney Advocate[J].23 Golden G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3(23).
[18]朱渝.从法律援助角度审视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与实践[J].湖北社会科学,2006(5).
[19]陈苇,石雷.防治家庭暴力的地方实践研究:以重庆市某区2009-2010年防治家庭暴力情况为对象 [J].甘肃社会科学,2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