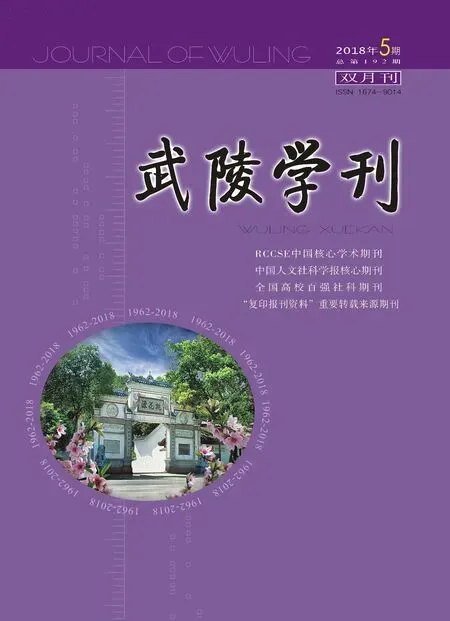在孤独中走进心灵深处
——评吴投文诗集《看不见雪的阴影》
王 颖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有一段名言:“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又马上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1]如果不为稻粱谋的话,这种生活会是很多作家渴望的生活。有的人生活在世间,他的种种身份只是外衣,而他努力进入的则是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是真正的自我的呈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诗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一种是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2]。的确如此,诗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描写经验世界的,他们也描写喜怒哀乐,但这种喜怒哀乐却是由现实生活引发,他们与具体的现象世界紧密相连。还有一种诗人,他们在人世间游走,作品却不是映照现实之“镜”,而是表现心灵之“灯”。他们的心灵世界过于强大,甚至于压过了世俗生活的能力。诗人吴投文恰好可以归入后一类,他在孤独中走进了心灵深处,他的诗歌呈现的是心灵的图象。
一、疏离与退守
吴投文的诗歌呈现出与现实世界的强大的疏离感,描写现实的诗不多,大部分是分析内心。他似乎是退缩的,总是要退回到内心深处。在《自述》中诗人被夜里的冰雹震醒,披衣起坐,在黑暗中接近黑暗。“实际上我没有倾诉/我只是爬出自己的洞穴/把孤独重新找回。”[3]32
在夜晚,披衣独坐,为什么诗人执意要把孤独重新找回呢?他不愿意像普通人一样选择世俗的繁华人生,而是执意退守内心世界,与孤独为伴。在《空白》一诗中,诗人表达了对空白洁净的癖好:
我对空白有一种洁净的癖好/我喜欢一本书中/突然出现的一页空白/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信仰
我在前世的日记中/留下一页空白/里面埋伏着我的一生/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贞操
我对空白有一种洁净的癖好/我喜欢一首诗中/天使为孤独者的爱好折断翅膀/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陷阱
这一生的空白太奢侈/我喜欢在午夜的祈祷中/面对辽阔的虚无/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死亡[3]35
这首《空白》是吴投文诸多诗歌中著名的一首。在这首诗中,读者看不到任何现实的色彩。或许,无论多么热闹繁华的俗世,也无法吸引诗人留驻。诗人热爱的是宗教的空白与虚无。
在《养狗记》的最后一节诗人写道:
要理解一只狗并不容易啊/当我受困于自己的内心/它领着我慢慢往回退/退回到原始的空白之中[3]41
类似的诗歌还有《围城》《壳》《山魅》《山中遇隐士》等,中国传统诗人的隐逸风格现于其中。
这些诗歌都呈现出一种虚空的色彩,逃避现实,沉浸于内心,并且有一种宗教的意味。他的诗歌是有禅意的,诗人并不留恋世俗的繁华,甚至对现实生活产生了一种厌离心,所以诗人执意要退回到“原始的空白之中”,如诗评家段晓磊所言,吴投文是一位“行走于信仰与虚无之间”的诗人[4]。
如何看待这种疏离感呢?应该说,这是不少诗人艺术家作品传达的内容。文学致力于描写内心世界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特征。事实上,从前现代主义也就是象征主义开始,西方文学就开始了“向内转”。从波德莱尔、马拉美、韩波、艾略特,一直到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无一不是如此。特别是卡夫卡,他小说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传递了与世界的疏离感。他对这个世界始终是陌生的,“这世界是我的迷宫”,他热爱孤独又害怕失去孤独,一直努力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从小说《美国》里面尚显宽阔的世界一直到《地洞》,世界在其小说中的分量越来越小,有时外面的世界甚至被他关闭。
如果继续向前回溯,除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以外,很多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也体现出了对尘世的厌倦。例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有一首诗叫《我从未爱过这世界》。这位行游广阔、极具反抗精神的摩罗诗人宣称自己没有爱过这世界,这个世界的肮脏与黑暗让诗人不忍直视,产生了强烈的厌离心。
值得一提的还有英国浪漫主义先驱威廉·布莱克,这位伦敦的雕刻匠诗人,4岁时声称自己看到过上帝,9岁时声称见到一棵树上栖满了天使,虽然结了婚,妻子凯瑟琳却抱怨:“布莱克先生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他总是生活在天堂里。”[5]布莱克的诗歌充满了宗教幻象而不是生活中的具体事物,不为时人理解,被称为“神圣的疯子”[5],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叶芝等人重编了他的诗集,人们才惊讶于他的纯真与深刻。而叶芝,也像布莱克一样是一位神秘主义者。
这样的诗人还有美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爱伦·坡、艾米莉·狄金森,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等等。他们的作品,无一不体现出疏离与退守的特征。
那么原因何在呢?首先,来自于诗人的个人气质。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此岸诗人,一种是彼岸诗人。前者的诗歌是经验的,后者的诗歌是超验的,具有丰富的哲学与宗教色彩。吴投文属于后者。尽管他在生活中看起来是一个乐观的人,但表象并不能掩盖他忧郁的思想者的特质。其次,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某些黑暗。出于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失望,诗人转而进入内心世界,沉溺在艺术的象牙塔中,精心营造“美”的殿堂,以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中国古代诗人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作为时代的清醒者,诗人不愿意同流合污,努力保持着精神的纯粹。第三,则是出于对艺术“游戏”的痴迷。德国美学家席勒和康德都认为艺术是一种“审美游戏”。艺术是非功利的,无涉利害,诗人在内心世界里获得了自由,摆脱现实的羁绊,沉浸于精神的游戏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吴投文的游戏世界中,却没有狂欢与欣喜,而是充满了宗教意味。《圣经·传道书》上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6]这种虚无主义的因子在吴投文的诗歌中时有体现。吴投文的诗歌十分克制与内敛,对物质世界充满了防御,他一点一点后退,最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在孤独中开始了严格的自省。
二、孤独与自省
如何看待孤独呢?从某种角度上看,孤独是创作的必需。诗人做不到随波逐流,拒绝融入世俗生活,即使勉强进入世俗人生,也始终会有那么一点“隔”。电影《梅兰芳》有一句台词:“谁毁了梅兰芳的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这句话充分诠释了孤独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吴投文在孤独中完成了对艺术的独创。在《自述》一诗的结尾,吴投文写道:“实际上我没有倾诉,我只是爬出自己的洞穴,把孤独重新找回。”[3]32可见,诗人多么离不开孤独。
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说:“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然后,把门关闭。”[7]那么,这个“自己的伴侣”是谁呢?应该就是存在本身。艺术家们往往在孤独中谛听存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的存在本质上就是孤独的。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个人内心中的存在,是人的个性、人的内心体验。它们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亦即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就是最基本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存在”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存在”就是“烦、畏、死、绝对毁灭”等个别性的精神状态。可以说,吴投文的很多诗歌都体现出形而上的存在之思,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存在主义者。个人的孤独、绝望、痛苦、对于死亡的迷恋,这些主题在他的诗歌中大量存在,并且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忧郁悲观的氛围。在不断的思考中,诗人似乎经历了“自我的分裂”。请看《一个人的影子生涯》:
我喜欢远游,在旅途上和一个影子对话/对近处的生活我保持忍耐,宽容它的放纵/和贫乏,却不能和它达成默契
在夜晚的灯光下,我遁迹无形,而在远方/我作为一个影子出现。我始终未曾达到过我的身体[3]49
这个“影子”是谁呢?它应该是诗人的本质存在。诗人千方百计地逃离近处的生活,因为无法达成默契。在旅途中和影子对话,就是和存在本身对话,那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而当我沉默,影子替代我活着,并说出生存的真相。生存的真相被揭示、去蔽、澄明。诗评家张清华说:“从所在境界与精神品位上说,当代诗歌的主题衍化经过了四个层面的爬升,这四个层面依次是生活—生命—生存—存在。”[8]吴投文的诗歌,就抵达了本质的存在。
在无限的孤独中,诗人不断地进行自省。鲁迅和卡夫卡是吴投文喜爱的作家,他们对吴投文有很深的影响。卡夫卡小说《审判》的形而上意义就是对所有人的原罪的审判,甚至透露出一种罪感。吴投文在诗歌中也不断地审视自身。在《自画像》里,诗人决定:“我不能再沉默了/开始了审判”[3]20。诗人要审判谁?是审判社会还是自身?没有明言,而像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一样,自画像已经明了了一切。在吴投文的诗歌中,以“我”开头的诗句特别多,诗人努力分析自我,体现出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剖析自我,反省自我,从中可以看到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影子。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把人的存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感性的物质享受,只顾个人与眼前;第二层是理性存在,让自己的人生合乎社会伦理与道德;第三层是宗教性存在,是人所应追求的最高层次。宗教性存在是一种祈祷和爱的生活,是对神的自觉和崇敬,是使精神有所寄托的存在。“人可以忍受饥饿感,却不能忍受无意义感。”[9]诗人吴投文感觉“这人世的繁华难以留下我的栖所”,“灵魂如何转身”[3]43是诗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诗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诗歌中的宗教色彩却是很明显的。有几首诗歌描写了诗人在教堂的感受,如《生命中的意外美好》:
在唱诗班的音乐声中,/这一对母女如此安详/她们洁净如浮雕的灵魂/充满上帝的爱情[3]97
再看《洗浴》:
很多年了,我独自到河边洗浴/黄昏的光芒照亮河水,露出/我赤裸的身体。清澈的岸草/在微风中抖动,隔着尘世的隐秘
我独自到河边洗浴,很多年了/我一件件退去衣物,看清了/身体里的废墟,又一件件穿上/终于露出了破绽。[3]135
这首诗的“洗浴”不禁让人联想起英文baptize。诗人努力洗掉的是尘世的污垢。“我一件件退去衣物,看清了/身体里的废墟”,作者对自我进行了严格的审视和剖析,努力追求宗教般的圣洁。这种自省意识,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罪感,与卡夫卡、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达成的高度有一致性。而其中,又透露出几许对信仰的寻求与渴望。
三、神秘、含混与不确定性
英国新批评理论家燕卜逊曾经提出过“含混”的诗学概念,认为一首诗可以是多义的。吴投文的诗歌也呈现出这一特点,诗义神秘,含混而不确定,这也使他的诗歌具备了一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像《乌鸦造访之夜》《吃雪》《亲近狼》《我信任一只黑色的乌鸦》等诗都很难说清诗的具体含义,读者的诠释只是猜测。在笔者看来,这些诗歌隐隐地传达出一种对自然的亲近,渴望充分释放被现代文明压抑的天性,所以诗人才会与狼“像久别重逢的兄弟/我们抱头痛哭流涕”[3]84。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臆测。这是诗歌的“空白点”,是未完成的,其意义需要读者去填充,不同的读者也会做出不同的阐释。以《我信任一只黑色的乌鸦》为例:
我信任一只黑色的乌鸦/在盛装的客人们中间/它裸露于水晶灯下/我突然陷入沉默
我感到一种触电般的震颤/体内的牢笼突然松懈/我涌起出走的冲动/悄悄煽动隐秘的翅膀
我有一颗乌鸦的心/已经习惯黑色的预言/当我发出乌鸦般的叫声/幸福的生活向我抗议
我信任一只黑色的乌鸦/它却抵抗我的灵魂/当我安静下来/它又拼命啄食我的肺腑[3]91
乌鸦在民间据说是一种不祥之鸟。在盛装的客人中间,诗中的乌鸦裸露于水晶灯下,“我”突然陷入沉默。诗人一定是预感到了某种危险。诗人有一颗乌鸦的心,习惯于传达黑色的预言,所以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警醒,不能安静。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的担忧与焦虑,悲伤的因子隐隐可见。但也许现实并非如此,“当我发出乌鸦般的叫声/幸福的生活向我抗议”。大家都在享受美好的人生,诗人却生活在巨大的不安之中,发出乌鸦般的黑色预言。诗歌并不一定说明某个具体的道理或者描述具体的事件,不一定要有明确意义,但是一定要对读者有所触动。这首诗就是表达一种不安且焦虑的情绪,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之后讲述了家人的种种冷漠。这种故事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但作者写出来,一种无安全感,一种生存的危险性的悲观情绪却感染了读者。
《我听见有人在月亮上哭》更是一首非常让人费解的诗。诗中写道:“我抬起头/月亮的光明照着我的眼睛/它是一块纯粹的玻璃/切着梧桐的枝条”。月亮被比喻成玻璃,挂在梧桐枝上。这种清冷的意境我们在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里读过:“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但是作者为什么会听到有人在月亮上哭呢?没有答案。
一定有人在月亮的背面哭/有人深夜独自打坐/我用指甲掐进我的肉里/我听见我的安逸在哭
月亮透过梧桐照着我的眼睛[3]95
月亮审视着我,使我不能安于安逸的生活。一定有人在月亮上哭,只能说是作者的一种幻听,作者似乎进入了神秘、直觉之境或梦境。而这,不正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么?西方现代派文学主张描写人的心理真实,而不是客观现实。这首诗歌描写的就是诗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仍然是不安与忧虑。一首好的诗歌,意境与意象的营造是很有必要的。《我听见有人在月亮上哭》借用梧桐、月亮、“我的眼睛”三个意象营造了一个悲哀而清冷的意境。读者被诗歌中弥漫的忧郁、悲痛的情绪感染,与诗人一样不能自拔。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曾经掀起“朦胧诗”运动,现在看来,当时很多朦胧诗也还是能解读出意义的。吴投文的很多诗歌,意义含混而不确定,但又有强大的吸引力让人深陷其中,宛如李商隐的《锦瑟》,至今无人说清到底是一首自伤诗、悼亡诗,还是感怀诗?但无人能否定它的艺术魅力。事实上,达·芬奇、卡夫卡、威廉·布莱克、爱伦·坡、梵高、瓦雷里、毕加索的作品莫不如此,伟大的艺术永远值得人们去探索。
这里有必要提及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世界被理性控制,人的很多本能和欲望受到压抑,能够展示人的心理真实和本来面目的是超现实的世界,也就是人的深层心理和梦境,冲破理性与意识的桎梏,追求原始冲动和意念的自由释放。吴投文的这些诗歌恰恰体现了超现实主义的特征。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概念是“纯诗”。爱伦·坡在《诗歌原理》等著述中指出,诗歌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既不同于理性的科学,也不同于道德的说教,它必须有属于诗歌自己的效果。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雷里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纯诗是一种“绝对的诗”,没有任何道德、说教和雄辩的意味。诗的本质因素在于语言。纯诗的语言是一种纯粹、绝对的语言[10]。笔者认为,单单从语言本身来说,吴投文的诗歌也体现了一种语言的形式美,从而接近了纯诗的境界。
四、现代性的隐痛
英国当代诗人奥登在评价卡夫卡时用了一个短语“现代人的困惑”,也许是因为卡夫卡的作品讲述了现代人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力感。吴投文的诗歌也传达出一种担心、忧虑,无安全感的心理,诗评家邹联安用“隐痛”来形容[11]。笔者认为“现代性的隐痛”这个短语更适合吴投文的诗歌。
1863年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评论同时代的画家斯当丹·居伊时写道:“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寻找什么?肯定,如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这个富有活泼的想象力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视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2]漫游在19世纪下半叶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巴黎,波德莱尔深刻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冲击。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诗人吴投文,从乡村到城市,在车水马龙、瞬息万变的城市里,现代性的隐痛也同样无可回避。他看到了什么呢?请看这首《埋伏之夜》:
这些幽暗路灯下的女子/把浓妆艳抹的阴影涂在脸上/她们仿佛刚从自己的身体中醒来/用迷一样闪烁的眼神抓住空洞的果实
已经习惯滥用夜的激情/随身的药丸却比法律还严谨/沉溺在深渊的狂想里安慰着自己/青春是一场盛宴,在背叛中挥霍爱情
光束像铁链从高处落下/她们在城市飞越故乡的屋顶/赤裸着翅膀,旋风在伤口里刮起/打开的身体在浩劫中盖住一世的贞洁[3]30
这是诗人眼里的现代化的城市,很容易让人想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伦敦》一诗里所描写的景象:
更不堪的是在夜半大街上/年轻妓女瘟疫般的诅咒,/它吞噬了新生婴儿的哭声,/把结婚喜塌变成了灵柩。[13]
很多诗人描写过城市的罪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里充满了腐尸、乞丐、妓女等不堪的景象,艾略特的《荒原》里描写了现代人空虚的生活。吴投文不可能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他看到了看性病门诊的女人,看到了埋伏在午夜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女子,看到了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看到了端上桌子被吃得只剩骨架的鱼,于是,诗人感叹:“哦,繁华的都市,我容纳你/你却不能容纳我的愿景/无数的邂逅都使我感到失望/我独自吞咽内心的寂寞”[3]67,“我的目的地/始终没有到来/我迷恋的那些事物/像爱人一样消失”[3]59,“在黄金时代/我选择素食/被逐出天堂”[3]25。这是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找不到合适的食物。“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也走了/我看见他们的背影/多么相似/像两个逃亡者/在惊恐中失去了方向/我独自留在了悬崖上/在那么高的位置/我感到了寒冷和孤独/同时感到了真实和存在/我终于腐烂在这里了,留下了一堆白骨”[3]21。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吴投文的诗歌体现了一种对高洁人格的追求[14]。为了绝对的纯粹,诗人选择了坚守理想的悬崖,曲高和寡,孤标傲世。
从审视社会到审视自身,诗人遍体鳞伤。于是,医院、伤口、发炎、感冒、咳嗽、生命垂危的病人、火葬场、墓园这样的意象出现在诗歌中。请看《伤口》:
伤口是皮肤上的一张口/它一张口/就流着唾液/它说:我是伤口/它不张口/是藏在某个位置/等着一只手拍醒/如果位置更深/它就在身体里面张口/听不见它说话/只听见它在咬着什么[3]18
这是一首很悲哀的诗,伤口没有愈合,一直在吞噬着诗人的心灵,一直在疼痛。这首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医生在大雪之夜出诊,历经艰难,终于到达病人家里。刚开始怎么也找不到伤口,后来却在病人的腰间右侧找到了。“可怜的小伙子,你没救了。我发现了你这个大伤口。你将带着你侧面这朵花逝去。”[15]身患肺结核的卡夫卡对疾病与伤口有切身的体会。病人渴望救赎,医生却束手无策。吴投文的诗歌也是如此,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样,是城市的罪恶土壤里的一朵病态之花。于是,救赎成了渴望,信仰之痛不可避免。
伤口如何愈合?唯爱可以疗救。诗人怀念父亲、母亲、爱情、乡情、友情,这些主题是吴投文诗歌中温馨明媚的亮色。如小诗《母亲》:
像从前那样/我坐在小院里/吃刚摘下的黄瓜/母亲在旁边/她说:/这一只是母的[3]8
这是一个小小的生活镜头,记录了日常生活中温馨的瞬间。小院、母亲、母鸡、黄瓜,几个意象连缀,颇有美国后现代主义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风格。
《合谋》这首诗没有说明是写给谁的,但理解为爱情诗应该没错。“我在你的梦中埋伏得如此之久/为漫长的等待感到孤独/你守着贞洁的黑暗/把梦做得尽量简单”[3]23,这些诗句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思念之情。
此外,描写亲情的诗歌还有《父亲和他的拖拉机》《梦见小弟》等,描写友情比较出色的诗歌有《湘潭桐子坳中秋望月,想起周瑟瑟》,描写乡情的诗歌则有《麻雀》,这些诗歌显示出来的温暖与爱,让读者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就像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在《荒原》的结尾,在描写了一番人情冷漠、信仰虚无等西方现代人的真实生活境况之后,荒原上终于盼来了雷霆的话,人们要“舍己为人。同情。克制”[16],荒原上才能有雨,荒原才能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对爱与救赎的祈盼,是绝望中的希望吧!在“看不见雪的阴影”下,迟钝的根茎在发芽,桃花即将开放。
如果想用某种“主义”定位吴投文的诗歌,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诗歌有少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有一定的人民性和时代性。大多数诗歌是描写彼岸世界的,兼具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其中,象征主义的成分和比重更大一些。象征主义深受唯灵论的影响。唯灵论把存在分为可见的物质存在和不可见的精神(灵魂)存在,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象征主义诗人主张透过可见的现象世界去洞观、暗示、显现本体世界,他们崇拜直觉,反对理性,走向神秘。诗人吴投文的大部分诗歌就是对个人心灵图景的描绘,他留给此岸世界很多神秘的符号与密码,等待读者去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