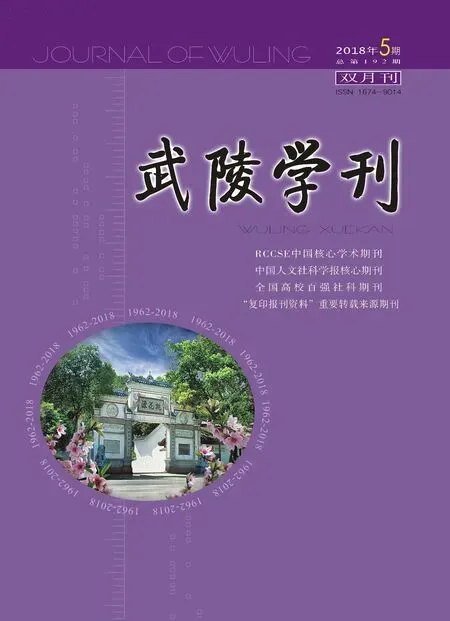挖土豆的人
——王单单诗歌的精神姿势
景立鹏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中国素有“文如其人”的古训。就王单单的诗歌而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挖掘者”的精神形象。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半开玩笑地说云南素来盛产两种东西:一是诗人,二是土豆。虽有玩笑的成分,但无意中透露出诗人的某种诗歌密码和精神基因。土豆,作为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之一,既可以是主食,又可以当蔬菜;既可以生长在干旱、贫瘠的北方平原,也可以生长在南方荒蛮、寂寥的高山,其包容性、适应力、生殖力和暧昧性以及沉入黑暗泥土中甘于忍受阴冷、寂寞的特性,无不塑造着一个典型的大地之精魂。而这又何尝不是一个诗人、一首诗歌所具有的品质。对王单单而言,写诗就是一个“挖土豆”的过程。土豆在阴暗、潮湿、孤寂的土层下潜滋暗长,不断积聚着来自山间的雾霭晴岚,收集着大河、深涧的流水清音以及透过森林的阳光雨露;同时,土豆的生长还构成对诗人的一种生命与语言的召唤。于是,在诗人的持续挖掘中,隐藏的不是理性支配下的精耕细作,而是一种大地内外情感的共契与召唤。诗人通过挖掘的动作语言为诗歌的土豆命名。正如夏可君所言:“诗意语言其实来自于命名和召唤,是召唤和命名产生了语言。语言是在召唤和命名中产生的。命名是对事物的第一次规定,是给出事物第一次到来时的惊讶。或者是,把语词召唤出来,召唤需要名称,因此需要名字,需要命名,是召唤的渴望导致了命名。”[1]5王单单的诗歌很大程度上就是埋藏于云贵高原深厚土层中的诗歌土豆召唤的结果。他在持续的挖掘中逼近生命土层的深部,捡拾着爱与疼痛,收集着来自故乡的山川花木的骨殖,倾听着身体挥动语言之锨时骨骼的脆响。
一直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混血身份,使其合法性遭到种种质疑并造成了在话语实践层面的种种困境。一方面,对于古典诗歌传统的某种背离,使现代汉诗在文类秩序、艺术特征和美学接受上遭到极大挑战。旧的标准被抛弃,新的标准难以建立,再加上读者阅读趣味上的传统惰性,使得现代汉诗一直在质疑声中筚路蓝缕。另一方面,现代汉语在语法上的欧化倾向使其成为一种更具叙述性、实用性和逻辑性的语言,导致其在诗性表达上的弹性大大降低(事实上这些特征未必就会造成诗意的蜕化,因为西方印欧语系的这种特征,并没有影响其伟大诗篇的产生)。面对这种困境,王单单的写作不着力于艺术、美学、语言上的实验,而是选择一种后撤、一种回归、一种指向大地与自身的虔诚的挖掘方式。他似乎要回到诗歌发生的原点来思考现代汉诗的当下困境。他关注的重点不在诗艺,而是诗歌如何在我身上、在我口中、在我笔下发生。以退为进,我们在王单单的诗歌中看到了一种淋漓元气与朴拙沉实。
一、挖掘:一种精神动作
马铃薯地里的冰凉气息,潮湿泥炭沼中的/咯吱声和啪叽声,铁锹锋利的切痕/穿透生命之根觉醒着我的意识。/可我没有铁锹去追随像他们那样的人。
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我将用它挖掘。[2]8
[爱尔兰]西默斯·希尼《挖掘》
语言,从发生学上讲,与动作、身体、姿势有着原初联系。语言,作为身体动作的一部分,沟通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人类通过语言来命名世界、创造世界,回应世界的召唤,并通过交流成为一个认识和存在的共同体。人类在通过语言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创造了自身。而这一切都是在语言的动作性中完成的。语言的规范、流动、运用引导着人类的身体、姿势、呼吸……人类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引导、塑造过程中,形成各种规范、程式、礼仪、风俗、制度。而诗歌只不过是个体语言动作在探询人类存在可能性过程中的姿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夏可君指出了身体姿势与现代汉诗写作的秘密:“汉语发生的礼仪教化与呼吸的转换调节,都实现在身体的姿势上。汉语诗学,这是身体姿势以诗性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语言表达,语言即是姿势,姿势即是语言。”[1]3王单单的诗歌写作也正是在挖掘者的精神姿势上创造了一处独特的诗歌风景。具体而言,王单单的挖掘动作既不指向古典传统,又不指向西方诗歌,而是指向诗歌最初的身体,那带着生命的温度与生存粗粝感的“内在体验”①。他把语言的铁锨挥向自己,朝向身体里的故乡和世界,切近诗歌的关节。
(一)挖掘与流浪:故乡的消逝
在当代汉语写作中,乡愁似乎成为一个时髦的文化显词,它与怀旧共同构成现代化语境中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时间的意识幻觉。庸俗的乌托邦化,并不能使诗人占据美学道德的制高点,反而在平面化的众口一词中湮没个人的音调与姿势。故乡的形象只有回到个人的体验中与舌头上才具有诗学意义。王单单对故乡的书写正是遵循了这一“舌头的管辖”②。他对故乡体验的挖掘既没有将其过度乌托邦化,也没有把故乡的“共同体”简单地放入现代挽歌的情调中,而是从个人家族史和对亲人、朋友的个体感知中挖掘诗歌的根茎。例如《雨打风吹去》:
我老爹,年近花甲,在地里/仍想着去远方,劫回落山的太阳/我叔父,孤家寡人,在家里/自言自语,等那些多年未归的子孙/我族兄,携妻带子,在广东/一家人内心的荒凉,被机器的轰鸣声震碎/我大哥,埋骨他乡,在天堂/投掷石子,此时,母亲是一面伤心的湖水/我内弟,单枪匹马,在浙江/犹大的门徒,用罂粟花擦亮尖啸的枪声/还有我,身无长计,在故乡/找故乡,二十九年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一个家族浮沉千年/就这样,被在生活的礁石上/撞击得/七/零 /八 /落[3]20
故乡,某种程度上就是亲人的代名词。一个家族的浮沉伴随着故乡的浮沉。当亲人们出走故乡时,故乡也就变得支离破碎。所以,“在故乡,找故乡”成为一个悖论性的宿命。诗人正是通过一个家族的经历来展开对故乡的认识与书写。对故乡的挖掘与寻找,成为一个具有西西弗斯式的过程,在诗人笔下反复出现。挖掘动作的重复出现使得这一精神动作获得了某种宗教性的仪式感与神圣感,而这正是诗歌作为语言宗教的本质所在。当反复的挖掘不能获得情感的慰藉时,挖掘这一动作本身就成了一种情感的流浪,一种不断重复的偏执。这一点在《滇黔边村》得到印证,“官抵坎”的变迁,伴随着家族的“创业史”,逃难、躲避计生结扎、农事、民俗,包括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流失等大量元素共同建构了一个个人化的历史暗箱。但当诗人试图挖出那个被时间掩埋的故乡时,得到的仍是在故乡小道上无望的徘徊:
阔别十六年,梦回官抵坎/曾经滇黔交界上的小道/我从云南找到贵州,又从贵州找到云南/都找不到我少时留下的尿斑[3]27
茫然的情感流浪与精神彷徨,最终获得的也许只是故乡的一抔抔骨殖,故乡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的精魂,抑或这挖掘本身承载着诗人对流淌在个人血液中的故乡体验的宗教般的祝颂与召唤。
从古典式的“在他乡思故乡”,到现代人的“在他乡找故乡”,再到后工业时代的“在故乡找故乡”,故乡在一代代诗人的诗意挖掘中,成为一个空转的能指,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时间迷宫。而挖掘这一动作本身则成为了故乡宗教仪式般的隐喻,或者说挖掘的过程即还乡。诗歌与还乡具有某种精神同构性。诗歌成为对精神故乡的不断挖掘、探询、翻检过程和可能性的揭示。正如希尼所言:“诗是占卜;诗是自我对自我的暴露,是文化的自我回归,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因子,带有出土文物的气味和真确感,在那里被埋葬的陶瓷碎片具有不为被埋葬的城市所湮没的重要性;诗是挖掘,为寻找不再是草木的化石的挖掘。”[2]253王单单的诗歌在挖掘与乡愁之间,除了一种现实层面的情感伦理承担之外,更在一种隐喻的精神动作中达到本体上的呼应。
(二)挖掘与对称:介入的诗学
作为诗歌的一种精神动作,挖掘又是介入的。但对诗歌而言,单纯的社会伦理、道德伦理上的要求并不能确证诗歌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如何介入,如何获得现实与美学上的对称与平衡才是诗歌的根本任务。王单单对现实的精神挖掘,主要体现在对生长在他周围的社会底层群体的诗意发现与书写上。如《卖毛豆的女人》:
她解开第一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二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三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四层衣服的纽扣/在最里层贴近腹部的地方/掏出一个塑料袋,慢慢打开/几张零钞,脏污但匀整/这个卖毛豆的乡下女人/在找零钱给我的时候/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就像是做一次剖腹产/抠出体内的命根子[3]25
对于一个“卖毛豆的女人”这样一个底层形象,诗人没有挖掘她身上的血泪史(作为一个陌生人,诗人很难了解,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了解,因为他不是社会学家),而是抓住了“找零钱”这个细节,通过她“解扣子”这一镜头的慢动作和长镜头把握,含蓄地暗示出生活的艰辛。前四句反复“解纽扣”的慢动作暗示着她对血汗钱的极端珍视,我们仿佛能在这一颗一颗的解扣子的动作中,听到诗人那一锨一锨向卖毛豆的女人的生命深处掘进的声音。纵向动作的反复与诗歌言说句法、语调的横向展开获得了诗、思与情的高度共振与平衡。接着,这一点在“最里层贴近腹部”“掏出”“慢慢”等一系列纵向推出的慢镜头中再次得到强化。“脏污”“匀整”这一特写镜头又使得一系列动作和诗意挖掘的铁锨终于触及到了埋藏地下的诗歌土豆。但是,仅仅有挖掘镜头的展开还不够,抖去修辞的泥土,找零钱的动作露出“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就像是做一次剖腹产/抠出体内的命根子”这一最后底色。王单单把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故事和心酸的妇女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一个“找零钱”的具体动作,再转化为一种“剖腹产”的身体修辞,这双重的转换与挖掘,使得“卖土豆的女人”获得的不仅是情感伦理的道德力量,更是诗人个人性的、发现性的诗意言说的胜利。
经验与道德伦理的胜利如何在发现性的诗意挖掘下获得美学的胜利,这是一个合格的诗人能否有效介入现实的标准。这种介入不是建立在修辞学上的封闭运转,而在于词与物之间、内容与形式之间和道德与美学之间,亦即深埋地下的诗意土豆与挖掘动作之间的相互召唤。生活的自性展开与诗意挖掘的自然生成过程的协调、互补、共生才是真正的介入的诗学。
(三)内在体验:朝向自身的挖掘
在经验贫乏的时代,如何保持词与物、精神个体与时代生存之间的张力是每一个诗人必然面对的命运。机械复制时代的祛魅使得现实生存在理性的训导下只会做规范动作,人的经验向内极度收缩。因此,对于外在生存的反应与挖掘,只有通过内在体验充分展开,才能获得持久、内在而有效的动力。这也意味着,诗人除了要有走向“远方”的跋涉之外,更需要有朝向自身的挖掘。这种内在体验是一种摆脱了理性、伦理、规范等因素的牵引(而这也许难以绝对二分,但至少后者不是一种经验之前的预设),精神主体自由的绝对在场,强调体验与生存的瞬间反应,直接抵达。对此巴塔耶的讨论颇为精道:“我把内在体验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神秘体验:迷狂状态,出神状态,至少是冥思情感的状态……内在体验回应了我——以及随同我的人之生存——所处的一种必要性,那就是永无休止地质疑(追问)一切的事物……我要让体验随性而行,不要通向一个被提前给定的终点。并且,我马上就说,它不通向任何的避风港(而是通向一个困惑之所,一个无意义之地)。我要让非知成为它的原则……”[4]8-9这种自由、出神与对自我的追问使得王单单的写作并没有局限于个人经验的兜售,而是增加了个人语调。自我追问的自觉性使他既摆脱了对具体经验的过度依赖,又远离了陷入神秘主义迷狂的危险。因为他的内在经验源于外在经验的本能激发,或者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因此,他的自我挖掘显得潇洒而从容,清醒而自然。例如《一个人在山中走》:
一个人在山中走/有必要投石,问路/打草,惊蛇,向着/开阔地带慢跑。一个人/站在风口上,眺望/反思,修剪内心的枝叶/看着周围:树大,招风/一个人走到路的尽头/还可以爬坡,跳埂子/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一个人/攀上石岩,抓住四处蔓延的/藤条,给远方打个电话/告诉她,真的有种东西/割不断,也放不下/一个人爬到最高的山上/难免心生悲凉,这里/除了冷,就只剩下荒芜/一个人在山中走,一直走/就会走进黄昏,走进/黑夜笼罩下的寂静[3]62
“一个人在山中走”本身就暗示了一种个人生存的本质性孤独。王单单通过这种隐喻性的行动来实现对自身的纵向挖掘。诗人行走的过程(投石、问路、慢跑、眺望、反思、跳跃、攀爬)看似理性、自觉,但实质上都是现实生存经验的某种隐喻,是外在体验的内化。这种内在体验的展开是一个充满了外在行走过程的精神映射。“一个人在山中走”是贯穿整首诗的行动线索,并且将一直延伸下去,沿着这个线索诗人一步步追问着存在的可能性,直至“走进黄昏,走进/黑夜笼罩下的寂静”。“黑夜的寂静”指向的是一种可能性的尽头,是空,是道,是“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③,是一种内在体验超越外在世界的自由、畅快。所以,我们又能经常在王单单对自我内在体验的挖掘中发掘其轻松、畅快、洒脱、豪爽的一面。如《滇中狂想曲》中,他既可以“落草为寇,隐身百草岭/积木成屋,窗口向南”,又可以“削发为僧,六根不净/昙华山中点青灯,睹佛思人”;既可以“采菊东篱,见枯木/死而不朽,朽而不倒/……/借山中木叶,吹一曲《梅葛》/替它还魂”,又可以“饮酒成鬼,囚于大姚堡/黑夜之中写反诗”。这种自我的狂想与其说是“找自己”,不如说是对在自我挖掘中超越各种理性常规牢笼束缚的“迷狂”。
虽然王单单的诗中充满了各种疼痛的经验,但是其书写从来不是悲观沉痛的,而是在从容、节制的词语的流淌中显出强大的内在控制力,这种控制其实来自内在经验的超越与对个体生存的持续追问与叛逆。《叛逆的水》就是最好的写照:“很多时候,我把自己变成/一滴叛逆的水。与其他水格格不入/……/我就是要叛逆/不给其它水同流的机会。即使/夹杂在它们中间,有一瞬的浑浊/我也要侧身出来,努力澄清自己。”这“澄清”的过程、不断地朝向自身掘进的过程,就是“在狂热和痛苦中追问(检验)一个人关于存在之事实所知道的东西”[4]9的过程,它需要耐心、坚韧,与话语和存在进行持久的搏斗。
二、疼痛的结构:错位、矛盾、重复
挖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语言的铁锨与生存肌体接触时骨骼、顽石的阻挡和惰性、钝化的枯草乱根的缠绕。精神挖掘的过程是一个词与物在内心擦枪走火的过程,是一个个体心灵与现实生存之间钻木取火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疼痛感、灼烧感、撕裂感。而这也为重新认知、打磨、梳理自身的经验结构提供了某种契机,在这种矛盾性的词与物的反复争斗中揭示出个体生存内部的冲突。
王单单的诗是一种“疼痛之诗”“经验之诗”。在我看来,其疼痛经验的诗意生成,来自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性生成。它不依赖于漂亮的句子、缠绕的句法和想象的腾转挪移,而来自对经验结构的精确塑型和对疼痛的骨骼的准确触摸。具体而言,这种结构是一种矛盾性结构,包含着情感的冲突、对立、突转,虚与实、经验与认识、宿命与叛逆、绝望与调侃、故乡与他乡、记忆与现实、此在与远方等诸多矛盾,诸如《卖毛豆的女人》《晚安,镇雄》《叛逆的水》《采石场的女人》等,无不如此。
疼痛,既来自于经验,又来自于个体生命与经验之间的某种张力关系。疼痛不论是来自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源于两种力的“背道而驰”。具体表现为时空经验的错位和逻辑的矛盾。首先来看时空经验的错位带来的疼痛,以《母亲的孤独》为例:
家里电话无人接听/或许,她正扛着锄头出门/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身子移出/长满荆棘的篱笆,独自走向/一片旷野,那里/杂草死而复生
过了很久,还是没人接听/或许,她刚回到家/钥匙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像往常一样,刚进屋/就给墙上的遗照讲述/瓜秧的长势,或者玉米成活的情况
她根本不知道,出门这段时间/遗照里的人,内心着急,试了很多次/都没能走出相框,接听儿子/从远方打回家的电话[3]108
诗中存在三重时空的错位。“我”打电话,但无人接听,这是第一重时空,“或许……”对母亲的猜测构成第二重时空,二者的错位造成交流的落空;而对母亲的两种可能性猜测又包含着两种交叠的时空经验,即母亲独自劳动的情景——这是第一重虚拟经验,母亲向遗像里的父亲讲述农事的情景——这是第二重虚拟经验,两种虚拟的情景更加衬托出母亲的孤独。第三重时空则是遗像里试图接电话的父亲的时空。“我”与“母亲”的交流,“母亲”与“父亲”的交流,“父亲”和“我”的交流,都因为时空的错位被切断。多重时空的顺向错位造成每个个体的情感流浪和绝对孤独,而作为这一链条中心的母亲则承受着来自“我”和“父亲”交流断裂造成的双重孤独。诗人的疼痛在这种对时空错位带来的矛盾性经验的一步步掘进中一点点增强。这种时空错位的矛盾经验带来的疼痛在《寻魂》《路边的理发匠》《冬夜,一匹马死在城市的街口》同样得到很好表现。而且,更加注重时代经验的矛盾带来的撕裂感,比如《路边的理发匠》。理发匠的手艺是属于特定历史情境的,在当代现实语境中,理发匠并不能从中获得主体的价值感:“这个在别人头上开荒的男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春天”。而这是时代的快速发展与技艺的陈旧之间的错位:“沧桑的手上,剪刀飞舞的速度/赶不上生活的浪潮”。被时代甩出历史轨道的命运使得这份坚持具有了一种挽歌情调,“或许他剪的不是头发/是自己所剩无几的光阴”。矛盾性经验的错位与撕扯带来的是个人生存经验的阵阵疼痛。但时空经验的错位使得事物本身又获得了一种新的被观看的视角,这种视角的变换往往造成诗意的产生。因为诗意本身即是对经验的陌生化感知与挖掘。
另一种矛盾性经验表现为一种逻辑上的矛盾与冲突。如果说时空经验上的矛盾性错位还可以通过个体努力矫正,那么逻辑上的矛盾性冲突则是根本性的死结。最典型的如《病父记》:
你说毬事没有,我说不可小觑/你说没做亏心事,我说与生病无关/你说从不打针,我说这次例外/你说祖上无病,我说并非遗传/你说看病花钱,我说花钱看病/你说休息就好,我说好再休息[3]96
父子二人的辩驳,即是两代人、两种身份的冲突导致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的交锋。这种激烈的冲突与错位使得“我的心/才像一架制造痛苦的机器/没日没夜地运转着”。诗人将这种关于疾病的矛盾态度通过简单、集中、尖锐的并置,将其推向不可调和的境地,最终使父亲生理上的病痛,转化为“我”的精神体验上的剧痛,二者在“疼痛”的经验上获得某种一致性:
你喊疼的时候我正喊拳/你吐血的时候我正吐酒/你呻吟的时候我正K歌/你想我的时候我正想你/其实啊父亲,因为你/我也身患不治之症[3]96
由观念、经验的矛盾性到病理经验对理性逻辑的战胜,由父亲的生理疼痛到“我也身患不治之症”,充分展现了疼痛在诗人身上逐渐累积、加深的过程。父子二人之间的矛盾性经验的博弈建构起诗人逐渐清晰的疼痛的结构。
另外,如果从诗人精神挖掘的形式特征来看,疼痛的结构伴随着一种经验的平行(或递进)展开方式与重复性的精神动作和语调。经验的疼痛不会自然成诗,它在诗人朝向自身的不断挖掘中一点点出土、成形,抖去多余的泥土,剩下的即是诗意的土豆,是精神、情感、记忆、语言凝结的核。所以,诗歌的展开方式与疼痛的经验是协调统一、二位一体的。在王单单的诗中,这种或平行、或递进的整饬节句的展开方式很常见。这种展开方式从容不迫、克制谨慎、有条不紊,与其对疼痛经验的虔诚挖掘、抚摸、探询,保持着诗与思的统一性,仿佛能够听到语言的铁锨有节奏的挖掘声。诗人在《哥》中写道:
哥,那年你少小离家/我蒙头大睡,没送你/若泉下有知,莫介意
哥,他们用纸包住火/你死后,走漏的风声/杀伤蒙在鼓里的家人
……
哥,老房子已成废墟/若回来,竹林边有路/故园沧桑,人心荒芜[3]94
整首诗都是在这种沉重、克制的节奏中展开对夭折的亲人的回忆,每节的一个“哥”就像沉重的鼓点戳中读者和诗人的情感死穴。回忆、倾诉的徐徐展开过程,也是诗人揭开伤疤,精确塑型、追问的过程,这种语调、经验、言说的彼此放大,使疼痛感获得一种听觉上、触觉上和视觉上的多重冲击。而在王单单的诗中,这种展开方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灵活、平行的复沓语式,比如“你儿子没回家过年/你儿子在外面发了/你儿子是溺死的/你儿子掉在工地上时/像一块土在墙上脱落/……”(《祥林嫂外传》)“许多姐姐流落在四川、浙江、安徽/……/许多姐姐带着伤痕替人生儿育女/许多姐姐用贞操夹紧硬币/……”(《姐姐》)“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十三岁的卢金花经常发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十四岁的卢金花扎着羊角辫/……/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十五岁的卢金花含苞待放/……/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十六岁的卢金花不知去向/……”(《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在这种语式中,或是经验的横向展开,或是现实的纵向追问,都是诗人疼痛的挖掘一步步展开的过程。内在体验的阵阵疼痛的节奏决定了这种话语方式的展开,而这种话语方式又使个人疼痛体验在秩序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个人化的语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促成同时也是诗人追问和自我追问、挖掘和朝向自我挖掘的过程。由是观之,王单单的疼痛书写,不是以“我”为中心,让外物在自我的谋划中运动,而是内在体验与外在生存的相互激发与敞开。此时,诗不再是抒情言志的外在媒介,而是诗人抵达存在和自我的话语和精神场域,诗人则成为体验和挖掘动作展开的通道,正如帕斯所言,“作家不是说话的人,而是那个让话说出来的人”[5]。王单单没有像罗兰巴特那样“杀死”作者,而是让作者与诗歌同时在场。
从某种意义上讲,疼痛的结构构成王单单的一种精神结构,它在个人体验与话语表达之间实现了一种自然的对称,通过精神挖掘实现了词与物的交流。王单单是一个在不断挖掘的劳作中和不断对疼痛的骨骼的触摸中劳作的人,因此,对他而言,诗歌是一种命运,一种信仰④。在不断的精神挖掘和阵阵精神疼痛之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诗歌自然生长的过程。也就是说,王单单的这种疼痛的挖掘不是一种理性、谋划支配下的诗艺操练,而是现实生存与个人体验召唤下的本能回应。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一种朴拙、沉实,包含着大地温润的元气淋漓的诗歌土豆。那是在“非知的黑夜”⑤中埋藏了很久结出的时间果实。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单单的写作回应了一种自然诗学、生长诗学的传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歌最初发生的遥远年代。
三、自然诗学:一种诗歌传统的回归
所谓自然诗学,意指一种诗歌发生学的古老传统,强调个人心灵与现实生存之间的一种本能的个性感发,是现实世界在个体经验内部激起的一种不可预见的创造性生成。《毛诗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强调的就是这种情志不得不发的发生机制。这种诗歌发生机制建立在存在与言说的一种迫切性之上,保证了诗歌言说的个体真实性。王单单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在一种看似简单的存在言说中直达经验和情感的根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疼痛经验在语言中的迫切性抵达,它只有在诗人的挖掘中转化为一种个人化的呼吸才能被疏导和释放。王单单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诗歌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灵魂的罹难。……我一直感觉不是我去写诗歌,这些诗歌早已在宿命中生成,它们像一支支浸着毒液的箭镞,时不时地射中我,当我感到疼痛的时候,其实就是诗歌从汉语的子宫爬出的时候。”[7]这一点在其对亲人、故乡和社会底层等对象的书写中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在持续的行走与挖掘中感受着生命的疼痛与大地的泪水。
如果自然诗学的呼吸是古典诗歌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的话,那么对于现代汉诗写作而言,自然诗学还有一个换气的过程,它更加强调对现代汉语可能性的探索。自然的生长本身即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过程。王单单的精神挖掘过程必然要在呼吸与换气的过程中发现言说的新边界,这是保证其创作活力的前提,正如德勒兹所言:“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8]这种转变在王单单的创作中已经初露端倪,比如在《手持火把的人》《醒来》《山行》《手套》《午夜的农场》《短章》《后将进酒》等作品中,其话语方式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新的句法、语调、气息融贯其中,逐渐形成对个体生存新的感受、发现与提问方式。具体而言,表现为更加注重对语言本体可能性的探询,个人话语范式的创设,语调更加简隽、流畅,思想的张力加大。如《手持火把的人》:
手持火把的人,在草地上行走/像一株石斛兰掰开坚硬的岩壁/如果,把他从人间突然拿走/黑夜中,会不会留下一个/人形的空[3]169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与空间、存在与虚无的寓言。前两句,动与静之间构成的明喻,使二者之间构成形而上的互文性启示,暗示了一个探索者的形象。而后两句通过一个假设和疑问的双重否定抽空了前两句中“人”的肯定性基础,以此提出对存在的质询。“人形的空”这一悖论性的存在包含着诗人对于有与无、现实与可能的思考。表面上看,诗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有时这一提问本身正是诗歌的意义所在。这一提问不仅是对这一问题的探求,更是对语言与存在、诗与思的深入质询。这种冷静、沉默的换气方式足以看出王单单的诗歌写作正在不断的精神挖掘中从经验与情感抵达语言与存在的深部。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王单单这种挖掘过程中呼吸与换气的转变,同样是生长诗学的自然延伸,它不是一种理性推导、牵引、规划的结果,而是一种在对诗歌经验不断地重临过程中获得的技艺,一种建立在手与土地之间的默契,就像农民不需要在每一次劳动中刻意学习耕种一样,种植、收获的动作已经融入他的无意识中,并在不断地耕耘中演变、发展。如果说诗歌的阅读是用感觉的话,那么诗歌写作过程中的呼吸与换气同样是在不断的精神和诗意挖掘中形成的自然感觉。总体而言,王单单的写作及其变化实践了一种向自然诗学传统的回归,他通过继承诗歌在原初阶段的真诚、朴拙、自然、真实的诗学传统,为现代汉诗写作新的可能提供了某种方向上的启示:前进,有时候是从回望开始的。
注 释:
①”内在体验”是法国哲学家巴塔耶在《内在体验》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巴塔耶继承了尼采、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传统,反对理性的谋划与训导,强调个体的一种出神、迷狂的精神体验,通过非知交流、戏剧化等抵达可能性的尽头。用他的话说,“体验就是在狂热和痛苦中追问(检验)一个人关于存在之事实所知道的东西”。参见[法]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第9页,尉光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强调“诗歌作为证明自身正确性的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这个范围内,舌头(既指诗人说话发声的个人天分,也指语言本身的共同根源)获得管辖的权利。诗艺具有自身的权威。……诗人具有一种在我们的本质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的本质之间建立意料不到和未经删改的沟通的本领。”参见[爱尔兰]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第235—236页,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版)。
③引自苏轼《送参寥师》:“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吷,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雪,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参见苏轼《苏东坡全集(上)》第193页,邓立勋编,黄山书社1997年版。
④帕斯在《写与说:在大学的对话》中说:“诗歌是一种命运:也许有一种天生的素质让我们去写诗歌。但是诗歌也是一种信仰。信仰什么?语言。诗人之道就是语言之道:忠于词语。诗人可以是一个醉汉,一个放荡者。……词语是诗人的情人和朋友,是他的父母,他的上帝和魔鬼,他的铁锤和枕头。也是他的敌人,他的镜子。”参见[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批评的激情》第78页,赵振江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
⑤巴塔耶所说的“内在体验”强调一种赤裸的个人的非理性体验。“非知的黑夜”即指那种超越了理性、规划牵引的可能性的边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