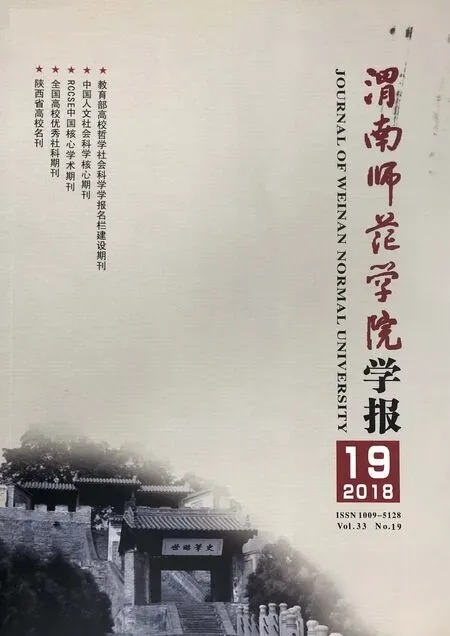论现象级影片《战狼2》的成与败
——兼论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
孟 丽 花
(渭南师范学院 丝绸之路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2017年,吴京导演并担任主演的电影《战狼2》刷新了国产电影的诸多纪录,影片以56亿8千万的票房登顶国产影片票房冠军,同时还创造了单部影片观影人数新纪录、单部影片单日票房新纪录等骄人的成绩。从商业片的角度来看,《战狼2》毫无疑问是成功的。“电影制作从一开始首先并且首要的就是一个商业性的企业。”[1]11这不仅是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基本理念,也是电影界很多生产者秉持的电影观。影片商业上的成功一方面有赖于作品叙事层面对动作片、战争片叙事范式的遵从,另一方面与外围的档期选择、国产电影保护月政策等因素密不可分。高票房意味着居高不下的观影人数和炽热的社会关注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战狼2》无疑是大片时代中国电影的翘楚。但电影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商业价值不是衡量一部电影的唯一标准。作为一部带有主旋律色彩的主流商业电影,在表达爱国主义情怀、塑造孤胆英雄形象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叙事逻辑上的不严密、叙事立场上的不理性,尤其是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区分上暧昧不明、在暴力与血腥场面处理上的不节制等等问题,都是值得反思与警醒的。对于电影艺术工作者来说,高票房、高利润回报与高口碑、高艺术质量之间的平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探究《战狼2》在艺术层面上的得与失不仅有助于形成对这部影片的深层认知,更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电影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边界。
一、《战狼2》的成功之处
《战狼2》选择2017年7月末上映,适逢国产电影保护月,在档期的选择上规避了海外大片尤其是好莱坞大片的强力竞争。在暑期、建军节前后上映,对于提高影片的关注度和票房而言都是有利的时机。当然,“天时地利”更需“人和”,影片能否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才是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关键所在,因此《战狼2》的成功首先源于故事层面的类型化叙事与高强度叙事。
(一)践行类型化叙事范式,满足观众的类型预期
从类型样式上来看,《战狼2》属于战争题材的动作片,影片较为完满地践行了类型化叙事的规范,符合观众对战争题材动作片的心理预期。作为电影市场上流通已久的“硬通货”,类型片有成熟而稳定的叙事范式。按照罗伯特·麦基在《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一书中的观点,可以用几个术语来界定类型片的叙事范式: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激励事件、进展纠葛、危机、高潮和结局五部分构成。激励事件打破人物生活的平衡,并在人物心目中建构起欲望对象、在观众心目中投射出必备场景。在矛盾冲突发展过程中,正反面角色相互较量,即进展纠葛。危机时刻与高潮紧密相连,此时正反面角色进行巅峰对决,对决的过程是整部作品最具备观赏性的场景,即必备场景。之后故事走向一个闭合式的结局,通常是正面人物历尽艰辛战胜反面人物,正义得到伸张,主人公的欲望对象变成了现实,被激励事件所打破的人物生活的平衡获得恢复。
《战狼2》的激励事件是非洲某国爆发了战乱,侨民被困,出于对同胞的强烈责任意识,前特种部队士兵冷锋请缨独自前往战乱地区营救包括医护人员陈医生在内的同胞。此时的反面角色是滥杀无辜的红巾军以及雇佣兵群体。随着矛盾纠葛的进一步发展,红巾军首领被雇佣兵首领斩首,以“老爹”为首的雇佣兵成了冷锋的敌人。由于此时瘟疫肆虐,“老爹”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陈医生的女儿萨沙,以掌握瘟疫疫苗制作的主控权,这是叛军在击败政府军之后顺利执掌国家政权的关键。冷锋受陈医生临终所托,誓死保护着萨沙以及众多侨民。作品的必备场景就是冷锋与“老爹”的巅峰对决。双方在一番激战——枪战、坦克战之后,进行近身肉搏。按照动作片高潮部分的叙事惯例,正面角色在交锋中一定会占据下风,在力有不逮险些丧命而观众为之揪心之时,受到某种强大精神力量的召唤,奋起反抗,力挽狂澜于既倒,最终反败为胜。冷锋杀死了“老爹”,在战舰的火力配合下,围攻华侨的雇佣兵被消灭殆尽,冷锋带领着侨民和萨沙安全撤离,人物生活的平衡获得恢复。
(二)双线并置下的高强度叙事,缝合主旋律与商业片的缝隙
除了宏大的家国层面的叙事情节的构建之外,本片还巧妙地设置了另一条线索,即个体层面的私人恩怨,家国情怀与私人恩怨双线并置,有助于缝合商业片与主旋律电影之间的缝隙。
离开特种部队后,冷锋之所以在非洲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是为了寻找杀死未婚妻龙小云的凶手。如果说战乱爆发是家国层面的激励事件,那么龙小云的死就是个人层面的激励事件,这一事件在冷锋心目中建构起了一个明确的欲望对象,那就是找到真凶,让他血债血偿。巧妙的是,剧作者让家国层面的敌人与个人层面的仇人合二为一——雇佣军头目“老爹”正是杀死龙小云的凶手。因此,在作品的高潮段落、必备场景中,“战狼”与“老爹”的对决就具有了双重的看点与多元的价值。这种把个人层面的恩怨情节与家国、民族层面的正义非正义的斗争并置的叙事技巧能够进一步强化作品的矛盾冲突,增强情节的戏剧张力,构建高强度的叙事,从而营造更跌宕的情节,创设更富有吸引力的故事氛围。从作品的思想层面来看,讲述一个前特种部队士兵在国家力量的支撑之下勇救侨民的故事,塑造忠诚爱国的英雄形象,展示冷锋为首的三人小组浴血奋战的场面,这些元素的铺陈对于完成作品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对观众的询唤而言,已经较为充分。正如片尾字幕所言,影片用鲜活的案例、恢宏的场面昭告所有的观众或曰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从“人人爱国”,到“国爱人人”,从个体为国家奉献、为民族牺牲到国家为个体遮风挡雨、民族珍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这种变化表面看源于创作者询唤技巧的转换,深层来讲是电影艺术工作者价值理念上与时俱进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战狼2》与2016年的主旋律电影《湄公河行动》异曲同工。除了宏大叙事层面的家国情怀、忠肝义胆,在个人层面上,冷锋又是一个重情重义、痴心不改的好男人形象,这种形象在《魂断蓝桥》《廊桥遗梦》这样的经典的好莱坞爱情故事中屡见不鲜。为了给心爱的人报仇,他枕戈待旦,始终没有忘记和龙小云相守一生的誓言,最终亲手终结了仇敌“老爹”的生命,这一线索的设置让主人公的身上在英雄特质之外又附加了浓郁的人情味与食人间烟火的凡俗气息,进一步促成观众对冷锋这一形象的强烈认同感。
作为一部有着主旋律叙事诉求的作品,《战狼2》巧妙的借助于双线并置的高强度叙事,塑造了冷锋这样一个既英勇伟岸又魅力四射的英雄形象。一方面借助于英雄的故事完成主旋律影片的主题传达与意识形态诉求,另一方面借助副线上的爱情故事以及复仇故事,形成高强度叙事,加上充满技巧性的打斗动作设计、复杂多样的战斗场面圆满实现了观众对于商业片可观赏性的心理预期。
从剧情结构上来讲,《战狼2》属于中规中矩的类型片叙事,与好莱坞大片《第一滴血》、经典的007系列电影有着明显的结构上的同构性:讲述一个有一定背景的独行侠,只身前往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遭遇劲敌,最终以强大的意志力、不凡的身手与超人的智慧战胜敌人、伸张正义的故事。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中规中矩的类型片已经能够很好地吸引观众。这是类型电影与艺术电影由目标受众群体的差异带来的叙事范式上的不同之处。毋庸讳言,类型片带有明显的趋利性,创作者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走进影院完成影片的消费为目标。影院的主流观看群体是审美趣味趋同的普罗大众,他们带着以往观看战争题材动作片的审美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期待走进影院,在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与炫目的特效镜头前,自愿自觉地放弃了对故事剧情的质疑与反思,沉浸在富有冲击力的视听元素营造的英雄故事中。艺术电影的创作与鉴赏过程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以年度艺术片《冈仁波齐》为例,影片以淡化情节、消弭戏剧性、消除艺术加工的痕迹为原则,既不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也不追求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艺术电影往往带有创作者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没有必须遵循的叙事范式,也不迎合普罗大众的审美喜好,艺术电影的创作者不以商业上的高回报为创作的核心目标,这是商业片与艺术片分野之处。
一言以蔽之,《战狼2》通过规范的类型化叙事以及巧妙的双线并置的高强度叙事,完成了主旋律作品应有的对观众价值理念的引领,实现了类型片自诞生以来就蕴含的商业诉求,是一部成功的动作片。《战狼2》的成功也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内香”,据统计本片99.7%的票房来自国内,在国外市场遇冷的同时,影片在国内热映之后引起的评论与争议之声也不绝于耳。商业上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可争议之处在影片的艺术质量与价值立场层面。
二、《战狼2》的缺陷与不足
(一)暴力与血腥:渲染还是克制
动作片必然涉及打斗,军事题材的动作片除了人物的近身搏斗之外,势必会出现枪战、爆炸、炮击等血腥的场面,如何处理影片中的暴力,如何表明创作者对血腥的态度,这是军事题材动作片绕不过去的议题。以同为动作片、涉及枪战与爆炸等血腥场面的影片《湄公河行动》为比较对象,可以映照出《战狼2》在暴力与血腥的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对暴力缺少克制,对血腥过分渲染。
影片《战狼2》中出现了车辆落入堆满拉曼拉病毒死者的尸坑的镜头、坦克碾压人体的镜头以及大量的枪械爆头、炮弹轰击人体、血腥的杀戮等镜头,尤其是作品的高潮段落,冷锋与“老爹”对打时,反败为胜的冷锋用当年杀死龙小云的子弹连续十余次的猛射“老爹”的头颅以及眼睛……充满血腥色彩的各种暴力镜头贯穿了作品的绝大部分场景。在任何影片中,暴力都不是值得宣扬的内容。“暴力只有工具意义,是不得已而采取的除恶手段。暴力的合理性只有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的合理性,暴力永远不可能成为合理的目的本身,不可能成为人类追求的价值本身。”[2]作为一种影响面广泛的视觉直观的艺术形式,电影作品在满足观众的正当欲求的同时应注意规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暴力在本质上对人的生命及其尊严构成威胁,因此在影片中应该审慎地表现暴力手段与血腥场面,以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化手段来展现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暴力与血腥。
在暴力与血腥的处理上,电影《湄公河行动》以及《敦刻尔克》显然要高级得多。
《湄公河行动》中,面对困境主人公首先采取智取的方式,智取失败,才转为强攻。在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解救人质时,警察们选择使用“低速橡胶子弹”,把伤亡降至最低。面对持枪开火的稚嫩孩童,警察的本能反应是停止射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避开要害部位开枪射击。捉拿毒枭糯卡时,面对荷枪实弹的“娃娃兵”,队长高刚命令大家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甚至在毒枭们火拼时,冒着生命危险拯救这些被控制的孩子。缉毒警方新武在战斗中抓住了毒贩刑登,与“老爹”相似的是,刑登也是导致方新武相恋十年的女友死于非命的罪魁祸首。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方新武一枪将其毙命。与《战狼2》不同的是,这一场景创作者未作任何细节的渲染,而是采用以声音代替画面的方式传达相关信息,规避了暴力血腥的镜头。之后方新武为自己逾越规则和纪律的行为感到自责。显然,这部作品中的暴力因素被理性框定在具备明确正当性的范围内。《敦刻尔克》一片也涉及众多的暴力镜头,但导演并未刻意强化任何的暴力场面或血腥镜头,而是通过视听元素的巧妙结合以克制的镜头语言营造了充沛的恐怖感——战争、暴力是恐怖的,因此也就势必引发观众对暴力的反思与警醒。
(二)情节与人物形象:弱化与扁平化
《战狼2》整体上呈现出情节的弱化与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影片通过高频率的打斗营造了激烈的场面,但作品的情节铺陈较为简单:冷锋临危请缨,只身前往战区及疫区,拯救受困者,遭遇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以“老爹”为首的劲敌,通过枪战、坦克战、肉搏等各种形式的对抗,全歼敌人,完成救赎任务。有人统计过,“贯穿全片123分钟的4077个镜头(国内一般的电影镜头是1000个左右),大量的战争场面和特效画面的连续、快速剪辑应用”等等恰恰说明本片重视的是动作场面的营造而非情节的交代,因此影片的剧情失之单薄。把讲述撤侨故事的《战狼2》与讲述撤军故事的《敦刻尔克》并置,就会发现后者的情节设置更丰富、叙事线索更多元。诺兰导演通过岸上、海上、空中三条线索,展现了陆地上等待撤退的士兵们、海面上赶来救援的普通英国人、空中坚守战斗岗位的飞行员们等多组人物,以类似于昆汀《低俗小说》一作中首创的“旋回”式叙事结构呈现出大撤退的恢宏画面。剧中人物的姓名被淡化,但形象却很鲜明。
弱化的情节与扁平的人物形象构成了这枚“硬币”的正反面。冷锋与“老爹”作为本片的正反面核心人物,在形象塑造上都出现了性格单一、形象扁平、缺少变化与发展的问题,通篇下来,给人一种这两个人物就是为了相互厮杀而生的观感。人物缺少发展与变化,这是叙事性作品创作中的禁忌。以冷锋为例,这一角色一出场就是战斗力爆棚的形象,人物自始至终都保持这样饱满的战斗热情与无惧生死的超然态度,不可否认这样的英雄的确形象伟岸,但很难唤起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与亲近感,因为他生来就是高大的英雄,除了对龙小云的思念,观众在冷锋的身上感受不到多少凡夫俗子的气息。
通常来讲,大多数作品会让主人公随着故事进展不断成长,将自身的潜质变成现实的品质,在追求欲望对象的过程中,主人公找到真正的自我。故事情节的铺陈与人物特质的显现同步进行。显然冷锋与“老爹”都没有这样的发展和变化,两个人物被纯化为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好人和一个邪恶的唯利是图的坏人——两个特别能打的人遇到一起,打了很久,最后好人胜利了,坏人被打死了。表层的热闹的打斗、炫目的特效镜头背后是如此单薄的剧情与简单化的人物设置,这是本片在赢得高票房之后无法获得相应的高口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镜头语言是一部影片的血肉,内在情节和人物形象是它的骨骼,那么作品表达的主题、价值观念就是它的灵魂。《战狼2》之所以行之不远,症结在于灵魂层面。
(三)立场与态度:丛林法则与“新东方主义”
“丛林法则是自然界一切生物生存竞争的基本法则,是维护自然秩序的规则。无论陆地还是海洋,除人之外的一切生物的进化过程都是生存竞争的过程,所有的生存竞争都要遵守弱肉强食的规则。丛林法则是自然界的伦理。”[3]显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不同,不适用丛林法则。本片从情节设置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一丛林法则核心律令的遵从与认同。不论是叛乱的红巾军与政府武装针对国家权利展开的争夺,还是以“老爹”为首的雇佣军与以冷锋为首的三人小队之间的殊死搏斗,由于创作者把笔墨集中在惨烈的战斗场面、炫目的近身搏斗等的展示上,对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缺少足够的交代。尤其是“老爹”和冷锋之间的争斗,在双方的行动过程中缺少明确的正与邪、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自证。换言之,冷锋的行为具备目的的正义性,但行为过程过于铺张扬厉,暴力、武力在这里因过度膨胀而走向了对自身作为工具性存在的否定,暴力只有作为工具,而且是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不得不使用的工具时才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否则,影片就走向了对丛林法则的认同——强者消灭弱者。任由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就会返归没有理性遑论现代性文明的蛮荒时代。
此外影片在呈现非洲国家时秉持的是对某些司空见惯的刻板印象进行进一步强化的态度,制造“新东方主义”视野中不断被他者化的非洲形象。
“东方主义”是由著名学者赛义德提出的重要理论术语,他认为,“在各种各样的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4]51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东方与落后、愚昧、保守、不开化、羸弱、阴暗等负面的本质性特征相连,从而成为现代、文明、开化、强盛的西方的对比对象,东方在西方的文化构想与话语实践中沦为西方这一主体的他者。
借用赛义德的上述理论及其分析方式,反观中国导演近年来创作的涉及亚非拉其他国家的电影作品,如《人再囧途之泰囧》以及《战狼2》,可以看出,创作者在他国形象的呈现上存在着类似于“东方主义”的倾向,即通过渲染相关国家在经济上的贫瘠、文化上的落后、社会秩序上的混乱,描绘政府在面对违法犯罪、叛乱暴动等社会问题时的无能与溃败,展现他国国民在思想上的愚昧、行为上的不堪,来制造一种“我们的世界”优于“他们的世界”的观感,这显然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包含着偏见的文化想象,暂且称之为“新东方主义”。徐峥导演的《人再囧途之泰囧》把泰国标签化为一个以真假难辨的人妖、地下非法交易、混乱的交通、脏乱差的环境、穷街陋巷为特色的国家。影片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显然与真实的泰国大相径庭。
《战狼2》中的“非洲某国”在形象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影片中这个不具名的非洲国家爆发了叛乱,面对红巾军的武力挑衅,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表现出的只有无能,武器弹药落后不说,毫无战略战术和政治智慧可言。拉曼拉病毒肆虐,被隔离的民众缺衣少食,感染瘟疫的人少数幸运者能够得到华资医院的救治,大多数病人只能坐等死亡的降临。镜头中的非洲景象除了广袤的富有自然美的草原之外,社会图景可谓满目疮痍,红巾军嗜血如命滥杀无辜,死难者陈尸街头,有人竟趁机四处劫掠,民众居住在简陋不堪的棚户中,因瘟疫死去的尸体横陈在贫民区路边的浅坑里……对于身处人间炼狱一般处境中的异国国民而言,拯救者只有以冷锋为代表的慷慨大义的中国人。有着强大祖国的华侨顺利抵达安全区,一同被拯救的还有诸多幸运的非洲面孔。影片的尾声部分,冷锋以臂膀为旗杆,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带领着满载华侨与非洲同胞的车队顺利穿越战区,仰拍镜头中的卡车仿佛变成了“诺亚方舟”,这是拯救者的神话,是大写的民族自豪感与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展现,但同时也有着浓郁的自我主体化与异己他者化的意味,显然这种立场和态度是值得反思甚至警惕的。
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相比,《战狼2》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与一定的创新性,在斩获超高票房的同时,影片口碑的不理想再一次凸显出叙事策略的重要性。主旋律电影如何“唱响主旋律”?
如果把作品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要做到骨骼肃立、血肉丰满,灵魂方可有所附丽。主旋律影片作为“主题先行”的作品,情节进展的大方向、故事的结局甚至人物的命运都具有一定的不可逆转性,如何规避观众印象中传统主旋律作品因明显说教与宏大企图而生的生硬感?首先,作品应把宏大叙事与类型叙事杂糅起来,在借鉴商业影片的创作与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完成主流价值观念的传达,《战狼2》把动作片与战争这一常见的宏大叙事议题进行了较好的结合,这是本片成功的经验之一。其次,塑造性格鲜明、形象立体丰满、具有强烈真实性的核心人物。主旋律电影在核心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诸多禁区,既要规避与集体主义背道而驰的个人英雄主义,又要避免英雄人物的“神化”。冷锋的形象还是过于高大威猛,相较之下《湄公河行动》中缉毒警察高刚、方新武的形象更具备真实感。再次,以理性的姿态传递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普适性的价值观。学者尹鸿撰文指出,“主旋律从根本上来说,就应该是能够被大众共享、代表大众利益的共同价值观,情感的忠贞、纯洁,人格的坚韧、牺牲,道德的诚信、尊重,社会的自由、平等,这些普遍性的价值从来都是人们赖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撑、相互激励的共同精神诉求。”[5]《战狼2》在传递爱国主义这一常见的主流价值理念的过程中,险些陷入民族主义的窠臼中,“爱国主义无论就军事还是就文化而言,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则与霸权的欲求分不开,具有进攻的性质”[6]。在营造困境凸显主人公的英雄特质的过程中又陷入顾此失彼的泥沼中,呈现出“新东方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战狼2》留给主旋律作品创作者的深刻教训。
总而言之,《战狼2》以高票房、高关注度被誉为2017年度的现象级影片,作为一部商业大片,作品借助于成熟的类型片叙事范式,完成了自身肩负的票房使命。另一方面,在暴力元素和血腥场面的应用、爱国主义和民族立场的廓清、丛林法则与新东方主义的规避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影片创造了票房奇迹,也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教训,供后来者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