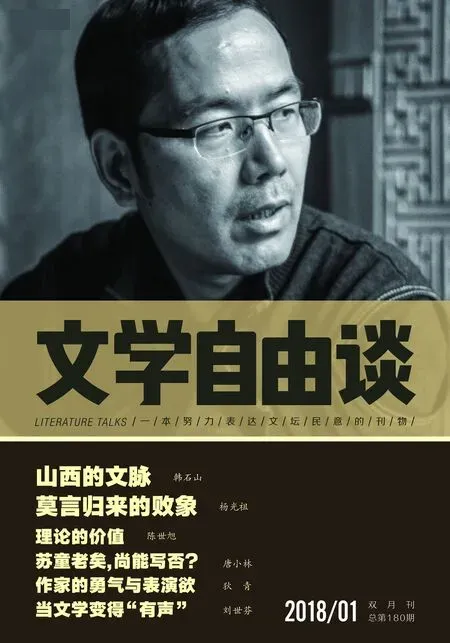贾平凹散文的真实性问题
河边草
一位年轻朋友近期含泪向我推荐了贾平凹先生的几篇散文,包括《哭婶娘》《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祭父》《写给母亲》等等。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些文章有的进了教材,有的成为高考中考阅读题,有的还出现在《朗读者》电视节目,并使朗读者和主持人感动得抱头痛哭哩。
我随即上网搜索到这几篇文章,并篇篇认真拜读,竟意外发现:这些散文作品,都或多或少有无法用常理解释的问题,或者说,有虚假、生造、移植的嫌疑!这里摘引这几篇文章的部分文句,说说我的疑惑。
《哭婶娘》是贾先生的早期作品,作于1981年5月20日,读来给人的感觉是当时婶娘刚去世不久,不过文中并没有明确其具体的日期。
——“婶娘,你死的时候,我是在西安,远隔你千里……”贾先生的老家在陕西商洛丹凤县,婶娘就住在那里。西安离丹凤不过三百多里,何来“远隔”“千里”?这三百多里路,即使是在那个交通不畅的年代,也不至于让贾先生“披星戴月”往回赶,也没赶上婶娘入土吧?
——“小的时候,过了满月,就留我在老家让你经管。夜夜我衔着你的空奶头睡觉,一把屎,一把尿,从一尺五寸拉扯我长大。”这两句话,主语游离,语病不轻。第一句,前半句主语应是“我”,后半句则不知道主语是谁了,但肯定不是“我”。第二句,“衔着你的空奶头睡觉”的自然是“我”,但“拉扯我长大”的还会是“我”吗?这几句,意在说婶娘养“我”之恩,却不免使读者以为贾先生的父母未免太不称职。
——“‘文化革命’那些年,我的父母进了牛棚,再没有钱寄回……”“文化革命”的表述不妥。贾母不是不识字的农民,按说应该不会成为“黑五类”中的一员,所以也没资格进“牛棚”吧?
——婶娘带“我”在那一年正月去探望父母这一段,说二人来回要走四百里地。这样远的路,一般大人也得走好几天,小孩子能走得下来、吃得消吗?
——“奶奶痛哭了你几日,身体越发虚弱了,我的父母决定接她老人家到他们单位去度晚年。”贾先生的母亲是当地农民,何来的单位?
对《祭父》,网络好评如潮,一位叫谢有顺的教授还称其为贾先生的散文名篇。
——“接到病危电报……一下班车,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太晚了。”戴着孝帽来班车站接人,可见家里人知道贾先生回来的准确时间,这可能是贾先生事先打电话告知的,这样一来,“接到病危电报”这话就疑似不属实。根据文中出现“1982”之类的年份,可以合理推测,贾先父去世时,应不会早于80年代中期。那时贾先生已是知名作家,即便家里尚未安电话,单位总该有电话吧?直接打电话报丧岂不是更快?
——据《哭婶娘》一文,贾先生应该没有堂兄(“咱这一家人,人口不旺……到了我们这辈,就只有我和慰儿”),但这里却突然冒出来个堂兄,这究竟是咋回事?
——“透过灯光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棵梨树,还是父亲亲手栽的,往年果实累累,今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这棵梨树如此神奇而具灵性,竟能预知人间事?
——“‘文化革命’中,家乡连遭三年大旱,生活极度拮据,父亲却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牛棚。”当时的“反革命”,主要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种,前者通常是指当事人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组织、有反革命行为,而贾父似无此“前科”;即便其真被开除公职,也不应是沾染所谓的“反革命”污迹。1972年,19岁的贾平凹以初中学历就被推荐上大学 (西北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想必其父起了积极作用,可见其父很有能力和远见,毕竟,当时受过严重处分的人士,子女几乎无上大学的机会。
——“正月十五的下午,母亲炒了家中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里,伯父买了四包香烟,让我给父亲送去。我太阳落山时赶到他任教的学校,父亲已经遭人殴打过,造反派硬不让见,我哭着求情,终于在院子里拐角处见到了父亲……”这里与《哭婶娘》中记述的那次探望是一回事吧?但细节存在差异:日子是“正月初十”还是“正月十五”?是婶娘带“我”去的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去看望父母二人,还是母亲在家,和伯父让我去给父亲送东西?
——“三个兄弟先后被绑票过三次”,“他们兄弟四人亲密无间”。对比《哭婶娘》里的“爷手里是兄弟五人,父手里是兄弟二人,到了我们这辈,就只有我和慰儿”和“伯父还是死了心,从此和家里断了关系,再不回来了”,我们真是难以判断哪篇文章说的伯父是真的。再对比《哭婶娘》中婶娘领“我”去探望父母那一段,这里的叙述更让人生疑:买香烟的是哪位伯父?他不是只有一个伯父,且无堂兄妹吗?“他把两个尚未成家的小妹留给我们”,贾的大妹当时已婚且生子,虽然夫死回娘家住,但也不能说未成家吧?
——文中有贾父为贾先生的弟弟、妹妹寻工作、谋出路的详细描述,或许其中藏有贾先生的面子,读者也不难猜出当年贾父为贾先生上大学所做的努力吧。贾父确实是精明过人,但他的一些做法,是不是俗称的“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呢?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是贾先生在父亲去世后、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主要是写母亲的。
——贾先生说他直到12岁那年,才在与别的孩子打仗时,从对方口里知道母亲的名字,这未免不大合常情。要知道,贾先生的父亲可是有文化的公办教师,他不会不让年已12的孩子知道父母的名字的。
——母亲让“我”和弟弟推磨那一段,叙述生动,让人觉得很真实,只是不知为何这时又不见了伯父们的人影,不见了贤惠能干的婶娘?
——“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她来城里住。”显然,这里已没有《哭婶娘》中慰儿的影子。
——“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公斤的柴担在山道上行走……”以前,有的成年男性农民可以达到这种水平,但少年至多能挑百十斤而已,贾先生恐非膂力过人,应不例外。姑且把这事当成真的,那么,依文中“我”的种种表现,这篇文章的标题,如果换成“我是一个好儿子”,恐怕要更贴切些。
上述几篇散文,单读尚可称赞,倘若放在一起欣赏,我们就会疑窦丛生:贾先生所写,是真的吗?这些作品不是小说吧?散文可以不讲究真实性吗?写散文,可以不诚实吗?——我是被贾先生弄糊涂了。
——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