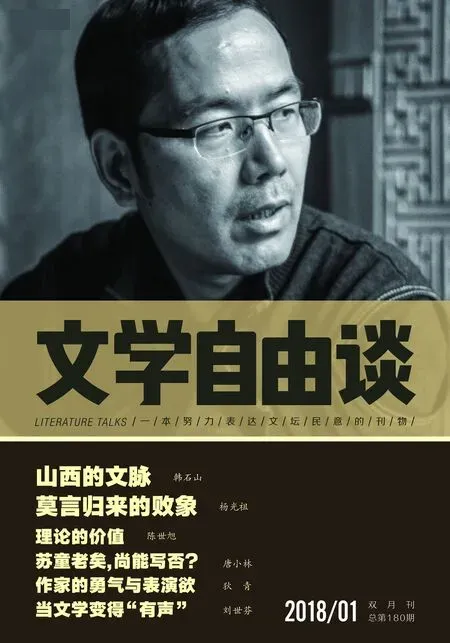魏晋风骨话伍俶
[美]陈艳群
伍俶先生的大名,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在上世纪中,他却是文人雅士中颇受尊重的诗人和学者。
伍俶生于1896或1897年,字叔傥,一比,斋号暮远楼,浙江温州瑞安人。从汪威廉教授的文章中得知,伍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刘师培、黄侃诸先生,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同学。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及“教育部”参事,另外,他也曾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等职。
1938年,伍先生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时,校园里传闻有所谓的“四凶”,指的即是伍俶、沉刚伯、方东美和王书林四位教授。据伍先生的学生,夏威夷大学罗锦堂教授的诠释,“四凶”意指四人的才气、名气和脾气。除王书林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以外,其他三位皆移帐台湾大学,皆为罗锦堂的业师。
像伍先生那样才华出众的名教授,校长都得敬他三分。每年台大师资续聘,校长总是亲自登门,呈送聘书,而不是寄去,足见那时教授的地位之高。
伍先生个头不高,但仪表堂堂。他穿长袍时,儒雅俊逸;着西装时,风度翩翩。他常常手持拐杖,或掌中摇一把折扇,其嘴唇上方一撮修剪得方方正正,比鼻子还窄的仁丹胡,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他一身西装,手持拐杖,在西湖岸边散步,被几个外国人误认作卓别林,他们径直走过来大呼“Charlie!Charlie!”令人啼笑皆非。也有人视他为日本人,但不知是否有人叫他希特勒……他似乎很中意自己的风范,这种容貌几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变。
精研六朝文学的伍先生,在台湾大学给学生讲 《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每次授课,他从不依仗讲义,而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伍先生极为欣赏刘勰的才华,对《文心雕龙》赞不绝口,认为其五十篇共数万字的篇幅,不但文字优美,而且说理透彻。有一次,他给罗锦堂班上讲授此文,正说得神采飞扬之时,忽然停住。只见他鼻子嗅嗅,眉头一皱说:“讲如此之美文,怎可在厕所旁边?厕所旁边只能讲韩愈的文章!”听到这里,众人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教室与公厕相邻,气味不时隐隐飘来。执拗的伍先生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还为此特别去与校方交涉,要求换间教室授课,学校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没过两天,教室给调换了,从此远离异味。
为讲授一篇诗文而换教室,古今恐怕只有此一人。他偏爱《文心雕龙》,认为刘勰这样的文僧仅留下传世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却没有自己的创作,甚为遗憾!而他自己也述而少作,亦令人惋惜。
伍先生虽曾于北大求学数年,但他的温州口音依然如旧,不曾改变,抑或稍有改变,常人仍旧不易听懂。这是民国时期多数教书先生的共同特征。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却没能统一语言。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虽推行标准“国语”,但当时仅仅流于形式,并未普及到地方,国人依旧南腔北调,方言各据一方,常有“十里不同音”之现象。老师浓重的乡音,对听课的学生来说,颇为吃力,惟靠勤奋和多问来弥补。时隔几十年,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由美国回台,途经夏威夷时,接受当地华侨的欢宴。罗锦堂教授也受邀出席,同时坐于严旁。他想起1966年伍先生去世时,在追悼会上看到严家淦的挽联,从而得知,严院长也是伍先生的弟子,他们二人便就此事聊了起来。严院长饶有兴趣地谈到,当年他在圣约翰大学上伍先生的课时,伍先生的话不好懂。有一次,伍先生说“秦始皇的五言诗写得很好”,台下的同学听得一头雾水,不得要领:秦始皇曾几何时会作五言诗呢?好在那时候的学生不懂即问,伍先生这才用粉笔将这句话写在黑板上。原来他讲的是 “陈思王曹植”,“陈思王”给说成了“秦始皇”。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得以释疑。
一辈子教诗和读诗的伍先生,其才华也由此体现出来。我有幸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借到了《暮远楼自选诗》一书,那是崇基学院中文系师生、校友在伍先生去世后为他编印的线装书。此书收集了伍先生的五言及七言诗一共114首,又附伍先生《谈五言诗》的长篇演讲稿。他曾说自己每日一诗。几十年下来,也应积累了数千首之多。为何《暮远楼自选诗》里只有为数极少的一部分?其他遗稿是否在他干女儿手上?抑或自己不满意而删毁?
书名中的“暮远楼”取自伍先生的斋号。博学的罗先生说,“暮远楼”自有典故,出自《史记·伍子胥传》中“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的文句。他是以漂泊在外的伍员(伍子胥)自况。
读伍先生的诗,觉得有股仙气,又像印象派的画和音乐,含而不露,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美。反复阅读,便觉句句清丽,字字珠玑。难怪胡适曾称赞说:“叔傥的诗,是用气力做成的。”胡适还向他的助手胡颂平打听“叔傥的诗印出来了没有?请他寄一本给我”。胡先生对他的诗的爱好,溢于言表。可惜胡先生没等到这本诗集的出版,便先行一步了。
罗锦堂先生非常钦佩他的老师,说他的五言诗高逸,词句优美,如阳春白雪,文风接近于《昭明文选》,颇有六朝风格。那时候,老庄的思想充满了当时文人的胸怀。可惜如今的人不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的方式了,所以,伍先生的诗,懂得的人不多。
伍先生曾养过猴子,拴在家门口。猴子见人便过来,与之亲热。后来猴子无故死了,伍先生悲伤不已,为此赋诗。如今鲐背之年的罗老清晰地记得,诗中有“清猿临死震哀音”这么一句,哀感动人。伍先生的古体诗都较长,不宜引用,这里摘一首他悼念老同学傅斯年的七言绝句。诗云:
鸣钟动角不胜哀,我为当时惜此才。
蝴蝶岂知人事改,又随吊客献花来。
伍先生心性豁达,淡泊名利,几近不食人间烟火,方东美称他为魏晋间人。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创办时,曾将合并的三所学校的教师复位级别,最高的为高级讲师(英式教育体制,相当于教授职位),此消息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执教于崇基学院的伍先生颇不以为然,他笑曰:“世无孔子,何妨低级!若世有孔子,又何必高级!”其境界之高,恐非常人所能及。
淡泊之人,却不失真性情。伍先生平日在学生面前毫无架子,总是和颜悦色。家事国事都是他的谈话资料。台大中文系的老师大多住在温州街,走出校门口不远便是伍府,那也是学生们最爱歇脚之处。有一天,罗锦堂与几位同学去暮远楼串门,见伍师愁眉苦脸,不似往日那般谈笑风生,忙问原委。他说他很难过,太太跟人跑了。众所周知,伍先生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怎料她红杏出了墙。没有经验的后生们接不上话,不知如何安慰老师,一时暮远楼里静得出奇,只有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叹息。“这事都怪蒋慰堂!”伍先生突然打破寂静,激动地说,“蒋慰堂是我的证婚人。我结婚那天,他居然忘了带名章,结果只在结婚证上签了名,没盖印,害得我太太跟人跑了,金玉良缘到不了头。”离婚之事,他不怪妻子,或自己,却怨蒋复璁先生。学生们相互交换眼神,抿嘴偷笑。老师真是个性情中人。很显然,这次打击比失去了猴子大得多。他后来竟然亲自送前妻出嫁,之后还不时关问她的生活状况,旧日的情分仍萦系于怀,且不恨不妒,可见伍先生真是个有情有意之人。
上世纪60年代,罗锦堂与伍师皆执教于香港,由此也常常聚会。伍先生身体健朗,一年四季洗冷水浴,着单衫。罗先生见老师冬天单衣裹身,佩服不已,说:“伍先生,您这么好的身体,可以活到九十多岁!”“你咒我!”伍先生并不领情,“像我这么好的身体,岂只九十岁?至少一百岁!”伍先生颇为自信。
谁知天不遂人愿。不久,即闻听伍先生因病住院了,先在九龙,后又转入港岛铜锣湾一家大医院。罗先生去医院探望,病榻前轻声唤他,没想到曾经精力充沛、有说有笑的伍先生此时已不能言语,全身软弱无力,只将手指略微抬起,表示他知道了。就在住院之前,他还曾兴奋地告诉罗先生说,儿子在新加坡开跑马场,生意兴隆,许诺要给他办个大学呢。想到这些,罗先生鼻子一酸,惟愿老师能早日康复。然而,一个多月后,伍先生竟然去世了。
和罗老聊起往事,从前暮远楼里听伍先生妙语连珠的闲聊,和伍先生一起去圆通寺郊游,伍先生赴日本东京大学执教时,罗先生为其开欢送会,以及一袭单衫的健朗身影,一一从记忆深层不断涌现出来,令罗老唏嘘不已,心中思念之情,良久不息。隔天,罗先生交给我一首《怀念伍叔傥师》的五言诗,嘱我Email给台大老同学许倬云教授,藉此与他分享对他们老师的怀念。诗云:
檀岛风吹雨,夕阳向晚晴。
楼高思暮远,难忘师生情。
忆昔垂绛帐,欨愉多欢腾。
台垣一分手,传薪向东瀛。
时时相问讯,客中苦零丁。
港九重相见,白发满头生。
长衫仍一袭,谈笑似童心。
天不随人愿,病魔忽相侵。
孑然辞世去,三地震哀音。
一别难再见,山高海又深。
罗先生以其老师最喜爱的五言诗的形式,言简意深地书写了老师的一生,以及自己对老师的敬重。这,何尝不是对恩师最好的怀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