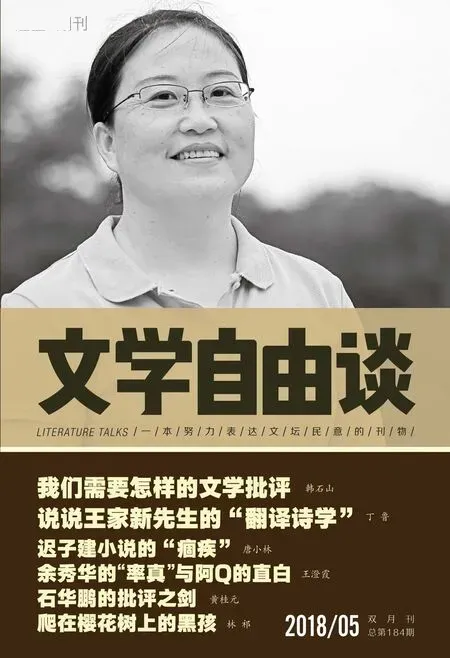给自我感觉“超好”的何英泼一点点凉水
张海成
新疆何英的风生水起仿佛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炙手可热,有点让人猝不及防。从她前几年首次成为《文学自由谈》封面人物以及鲁迅文学奖评委后所写的文字中,你可以读出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别样豪情。她大概认为,她有足够的理由“自我感觉良好”——岂止是“良好”,简直是“超好”!
首先说容貌。按理说文化人不太喜欢别人拿这个说事,现在看不对。不喜欢拿容貌说事的,只能是一些形象上不了台面对不起观众的人,而像何英这样“貌美如花,吐气如兰”(黄山《致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英》),“尤其那双眼睛,富于西域风情,顾盼生辉”(杨光祖《内藏刀锋的美女批评家》),怎么会甘心停留在“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层面?还有评论家“纳闷”地感慨:“有着如此一副漂亮脸蛋的美人胚子,为何不到影视圈去当女一号,去当‘英格丽·褒曼’或‘莎朗·斯通’,而要在一张书桌前,敲打键盘,寂寞空对窗外月?”“再看书中的文字,又让我诧异:既才情横溢,又犀利入骨。不由让我想起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那些女侠,个个天生丽质,同时又武功盖世,飞檐走壁,衣袂飘拂,让天下所有男人都爱惧交加。”(陈歆耕《美女如玉剑如虹》)
笔者孤陋寡闻,就目前所能看到的与何英相关的评论文章里,没涉及何英容貌的凤毛麟角;有些评论文章中关于文学批评的段落味同嚼蜡,但描述何英容貌的文字却活色生香妙笔生花,即使谈不上谀辞泉涌,至少也是信手拈来。当情绪取代逻辑,真相往往难以抵达。这样的评论文章,究竟会有多少理性的价值呢?
让何英自我感觉“超好”的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关于她的评论文章了。以何英目前的身分和学历,发表文章已不成问题,不要说自己早已不需要去挨门磕头烧香拜佛,就是报刊杂志的约稿也有资格时不时地“傲慢”一下。“桂元隔段时间会来约稿,侦查一下我这个不勤快的作者,使我又想起自己曾经做过杂志编辑,好像从来就没有去主动约过稿。”(何英《和〈文学自由谈〉的二三事》)。对于自己的文章,何英当然是非常满意:“看着那些折射透散着我当时的状态、见识、心情、思想的文字,还是有些小激动。”当然了,她也知道谦虚,但她的那种谦虚总让人觉得怪怪的。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个桂元,他曾经给何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何英:穿越边地抵达“中心”》。可你听何英怎么说:其实我至今也没有穿越,也还在边地混着!言下之意,我让你瞎拍,我不领这份情!文坛独行侠周涛是何等的清高自傲,最后怎么样?虽然他自称因对何英“何方人氏,什么来历,芳龄几何,性情怎样,全说不清”,而担心“恐难胜任”给她写印象记这事儿,但最终也没架得住何英那句“周老师完全可以一口回绝,那我也没什么”。
让何英自我感觉“超好”的第三个原因,自然是她的学识和著述了。在《刮一刮“生”“新”风》(《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这篇文章的后面,附有何英的一段自述。她说自己“12岁的假期看了 《红楼梦》”,“正兴冲冲的拿着两本书,一本是 《林黛玉笔记》,一本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我就想,自己12岁的时候在干什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裤在老家池塘里和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在摸鱼?在老家打谷场上玩折纸叠纸飞机?或者,跟着一辈子以种地为业的父母在水稻田里学习插秧?有一点是肯定的,我那时候绝对不会见过或者听说过《林黛玉笔记》和《上尉的女儿》。《红楼梦》或许似懂非懂地看过三五页,至于《林黛玉笔记》,不要说我,即便当时是我的老师,恐怕也闻所未闻。一个至今学术界也关注不多的清代著述,十几岁的孩子究竟有多少鉴赏与甄别能力而深陷其中?但何英就真的是关注到了,她要告诉你,《林黛玉笔记》的作者喻血轮当属曹雪芹所言“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是“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的才子,“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知道了这一点,何英的话外音你就应该清楚了吧:我为什么关注他?因为同声相求同气相应,明白不?作家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这条路也不是人人都能走的!我12岁就看《林黛玉笔记》了,你那时候在干什么?老父亲说我走不成文学这条路,我不但走了,而且自觉走得很好很顺利很踏实!我还想说,我大学学的不是文学,但这又能说明什么?我现在不但在干文学,而且还在继续深造……我想说,如果不是自我感觉超好,那段自述真的写不成这个样子!我们看过启功先生自己写的小传,也看过贾平凹先生自己写的小传,不说是谨小慎微生生把自己深深地扎进泥土,起码就是告诉你我没什么,和对门大叔隔壁老王邻家小妹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咱干的活计不一样罢了。
忽然记起,最近刚刚拿到的何英新著《批评的“纯真之眼”》里,依然有她的一篇小传,虽然没有注明是她自己撰写的,但那“每一行都像深海里随波摇曳、姿态万千的藻类,妖媚迷人且暗香浮动”(何英《〈万物花开〉后的林白》)的文字,怕是只能出自她的手笔。与这段小传同时出现在书中的,当然还有那幅“貌美如花,吐气如兰”的照片,乍一看似曾相识,翻出资料一比对,原来同样一副照片还在《文学自由谈》上出现过。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把这幅“眼神深邃犀利如鹞鹰,身姿却很女人”(韩春萍《以“纯真之眼”看何英的文学批评》)的玉照继续作为自己下一部著述的作者近照”。
关于何英的著述,我得老实坦白,仔细读过的确实不算太多,但能够看到的,绝对也和她的阅读习惯一样,“一字一句”地反复咀嚼认真学习——“一字一句”是何英在表述自己如何阅读他人作品时常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以表明她的恭敬之心;不过也不尽然,她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就是“抵制着厌恶勉强看完”的——尤其是对她自己“有些小激动”的扛鼎之作,我更是如获至宝手不释卷,比如《阁楼上的疯女人》,比如《才女何须福薄》。我想起鲁迅那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看阁楼上的疯女人》时犹如看禁书,时不时要抬头左顾右盼一下,生怕老婆孩子看到些什么;她的某些论断也让我横竖睡不着——比如:“这么大的天才只有几个女人,几个女人就成就了这么大的天才,想想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艺术家的残酷只能算是小残酷,凡事都有代价。”比如:“20世纪大师纷纭迭现是以女人的爱情和最终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为等价能量转换的,21世纪的大师仍然要凭借这种古老的能量转换法则来成就吗?或者可以找到新能源来替代,又或者21世纪根本就是一个大师阙如的世纪?”——我也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荒唐!
看《才女何须福薄》使我想起浙江大学薛龙春说过的话:“文科的研究,无非是要有图书馆,看得到资料,然后就是读书与思考。”像《才女何须福薄》这类文章,需要很大的才气吗?需要一个博士才能够完成吗?不用去太高大上的知名高校图书馆,在一般的县市区图书馆或者书店里蹲上两三天,或者去网上搜搜,然后关门加工整理,很难吗?一篇普通的读书笔记或者阅读心得而已,没有过度拔高的必要。对现成资料的归纳整理或者历史事实的借题发挥,即使再顺便抒发一下阶级感情,稍有些文字功底的文艺青年的水平已经足够。
让何英自我感觉“超好”的第四个原因,就是她的阅读了。作家也好,评论家也好,读书之于他们就像人之三餐,既是必须必要又是日常琐事。何英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当然知道这个道理,虽然她也会通过写自己看《带灯》时“一字一句看了两遍”和“一字一句”地看残雪的长篇《边疆》等等来说明自己的勤奋阅读,但她不会在那上面浪费笔墨。而对自己比较冷门的阅读,她却会时不时地专门挑明一下,以示不同凡响。她知道写自己12岁时读过《上尉的女儿》引不起人们的惊讶(谁还不知道《上尉的女儿》呀),但她说自己“一直喜欢《纽约时报》书评那样的批评文风,精准、专业、幽默、深刻,好处,不好处,糅合在一起说”时,或者说自己看库切的《耻》时,或者说自己看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时,或者说自己看菲德勒的《跨越边界》时,估计大部分读者就得自惭形秽面壁思过了。
客观地说,“自我感觉良好”是需要扎实的艺术功底、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做支撑的,在这方面,何英显然还没有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地步。她自己也曾毫不掩饰地袒露过自己的“无奈”和力不从心:“其实,我写每篇文章都很吃力,所以一直羡慕那些出手快、产量高的作者。还是积累不行,不够眼明心快,力气也小。搞评论是个力气活儿,精力不旺盛、没有说话欲的人,就不要搞了。”(何英《我与〈文学自由谈〉二三事》)女人把话说到这份上,你想不怜香惜玉都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世俗的东西也是你不能不屈服的:“人都是这么干的,你不这么干,就不让你上那些居庙堂之高的期刊,你不上这些期刊,所有的辛苦都白费。最可气的就是打着国家重点课题的旗号卡人。本来那个职称也不是你自己要评的,但你要拿工资,到社会上去混,你就得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何英《玩出自己世界的韩寒》)听明白没有?再有才华,也难以任性到无所顾忌。何英曾经是任性的,曾经因为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只有双性同体的大脑才能创造出合格的作品,这种作品由于消弭了性别偏见而对男女两性都有助益”这句话而认同别人说她的批评“超越了女性的身份”,甚至不无矫情地说“我很遗憾我的批评很多时候表现得不像一个女的”。不过,可喜的是,不愧是饱读诗书且在2岁就看过《林黛玉笔记》的人,何英还没有飘飘然到始终难以落地的地步,她终归还是认识到了自己的短板。
老百姓都知道,大汗淋漓的人是不能被兜头浇下一桶冷水的,轻则致病,重则要命。笔者深知,正在风头上的何英需要鼓励鼓励再鼓励。日子如烈火烹油的时候,你兜头泼下一瓢冷水,当然属于居心叵测用心险恶,咱不能这么干。所以才说泼一点点凉水,能让何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靠码字吃饭的普通人而已。舍此,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