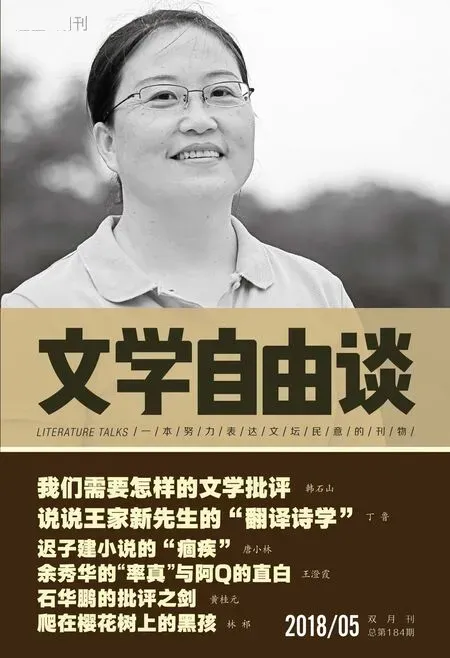在爱丁堡,司各特、彭斯还有J.K.罗琳
狄 青
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然而,至少给我的感觉是:两座城市却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实际上更像是一座英格兰城市,街道的布局走向、房屋的建筑格调,以及时尚的商业化程度,基本上与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那些英格兰城市差别不大。爱丁堡却不然,它更像是一座中世纪的古老城池被直接平移到了当下,那斑驳的古老城堡的墙面,还有那些仿佛凝滞固化了的传统文化遗存,都像是一件件历经岁月浸泡的标本。格拉斯哥这座城市能够令我想起的文学人物似乎并不多,大约只有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旗帜性人物、诗人托马斯·坎贝尔与格拉斯哥有着难解之缘。我曾经起意想寻找诗人在格拉斯哥的故居,遗憾的是,周围人似乎没有谁了解这件事。我不清楚,比起街头的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的巨幅海报,格拉斯哥的文化抑或说文学仿佛都还被局限于那些古老大学的围墙里。
但爱丁堡不是这样的,你几乎在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高达61.11米的黑色外檐、通体颇具岩石坚硬质感的司各特纪念塔,感受到这位伟大作家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你的思考、关注着你的关注。作为2004年即被联合国命名为全世界首座“文学之都”的爱丁堡,文学,无疑便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标识了;而诗人兼小说家司各特呢,无疑又属于爱丁堡这一重要标识的标识性人物,尽管这座在我看来至少算不上很大的城市,同样诞生了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柯南·道尔以及J.K.罗琳这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和诗人,但如果没有司各特,对于爱丁堡这座“文学之都”而言,也难说会是一种圆满。
在伦敦的时候,我就听说爱丁堡有一座“作家博物馆”,却不是在爱丁堡的热门旅游路线上,如果想去瞻仰的话,多半只能自己想办法前往。不过好在它就位于市中心,就隐藏在“皇家一英里”上的一个小巷子里,显得是那样的不起眼。皇家一英里是爱丁堡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同时也是爱丁堡著名的商业街。也正是因为其古老,在逛皇家一英里的时候,是要抱着一种让自己迷路的心态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哪一扇门洞的后面就隐藏着难得一见的风景。爱丁堡的作家博物馆便是如此,它就设在曾对文学极度热爱的史戴尔夫人的古老宅邸内,而这一古老宅邸与皇家一英里之间连接的小巷入口的确太普通了,稍不留神就会错过。
说是“作家博物馆”,但里面其实只有三位作家的作品展示以及相关纪念物,这三位作家便是苏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诗人和作家:罗伯特·彭斯,瓦尔特·司各特以及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博物馆内,到处都展示着他们的手稿以及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物品。我在罗伯特·彭斯曾使用过的一张书桌前停了很长时间,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彭斯坐在这张桌前奋笔创作的情景。还有斯蒂文森穿过的一双鞋子——应该算是靴子吧,我想,这双靴子是斯蒂文森在他的家乡爱丁堡穿的呢,还是在他最后的归宿地——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上穿的呢?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说的手稿,保存得十分完好,感觉离现在似乎并不久远,而笔迹则多少有一些模糊了。比起我在英格兰的霍沃思小镇看到的勃朗特三姐妹的手稿笔迹,司各特的用笔无疑更加用力且显得比较豪放。
司各特属于爱丁堡这座城市的“土著”,其小学、中学就读的都是当时全爱丁堡最好的学校,大学则上的是爱丁堡大学。考上大学时,司各特只有12岁。我所看到的资料表明,12岁的年龄也并非爱丁堡大学新生中最小的,大约只能算是最小的学生之一,至少另一位爱丁堡人,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大卫·休谟就是在他12岁那一年被爱丁堡大学录取的。
司各特降生于如今的爱丁堡大学的乔治广场一带,那曾经是司各特的父母家所在地,当年应该尚没有被划入爱丁堡大学的教学区。如今的乔治广场,分别属于爱丁堡大学的商学院、信息学院、法学院以及大卫·休谟楼所在地。早在司各特降生之前,司各特母亲所生的六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据说,司各特才一岁半时,还是得了一场大病,类似于小儿麻痹症吧,结果便是其右腿肌肉萎缩,终身都成了一个瘸子。说起来这多少像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伟大的英格兰诗人拜伦也是天生跛足,而司各特与拜伦属于同一时期的文人,他们分别被作为苏格兰与英格兰文学的代表人物。司各特往往喜欢在清晨起来创作,而拜伦则是喜欢在夜晚写诗;这一点颇具有象征性。从二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灿烂的清晨或者黑夜对他们各自作品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至今仍是英国许多大学的文学课师生所共同探讨、争论的话题。
虽然至今已无法确认哪一座房子曾经降生了瓦尔特·司各特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目前爱丁堡新老城区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曾经留下过司各特的足迹。
据说,司各特被当时的爱丁堡人认定是苏格兰唯一能够与英格兰的拜伦勋爵PK一番的文学人物,甚至在英国议会里都有这样的议论。但就司各特而言,他只是满足于自己在爱丁堡和苏格兰的文学地位,无意与英格兰的拜伦去一决伯仲。这除了性格使然,还在于司各特十分崇拜拜伦,多数时候他都是以拜伦粉丝的面目出现。没错,有关拜伦的故事与传说,在当时的英伦三岛都是上流阶层闲暇时议论的话题。拜伦的年龄、地位以及超乎常人的英俊,无疑比他的作品更加迷人。关于拜伦的魅力,司各特当年在爱丁堡对友人所讲的一段话最有分量,他说:“至于讲到诗人,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所有最优秀的诗人我都见过——可是,尽管彭斯有一双能够想象得出的最有神采的眼睛,我却认为,除去拜伦以外,他们的容貌都称不上是艺术家心目中的出色人物。神采是有的,但是够不上光彩照人,唯有拜伦的容貌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那种最美的形象。”
1802年,司各特在爱丁堡出版了《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并大获成功,同时又担任了爱丁堡高等法院的院长。虽然有钱有势,司各特却因为腿瘸,而未被自己所爱的姑娘的家庭认可,只得作罢。于是他娶了法国女郎夏洛蒂·夏潘特,二人直到终老。靠着写诗和小说,1820年,司各特被英国王室封为男爵。靠写作获得王室爵位,司各特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个。不知是因为崇拜拜伦的缘故,还是因为的确自叹弗如,司各特公开表示,他终其一生也无法在诗歌创作上超过拜伦,所以决意放弃诗歌创作,而专注于小说写作。之后,他断断续续创作了30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是迄今为止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最多的欧洲作家,其勤奋程度与巴尔扎克有一拼。当然,司各特创作小说也是为了多拿稿酬。
司各特在投资上可谓乏善可陈。仅在爱丁堡一地,他就多次投资失败,并欠了一屁股债。这些债务,司各特直到去世也没有还清。
罗伯特·彭斯的年龄比司各特大十二岁。彭斯进入爱丁堡上流社会视野的那年,司各特刚刚考上爱丁堡大学。二人仅有两次见面。我们不清楚彭斯对司各特有什么印象,但司各特无疑是兴奋的,尤其是他在爱丁堡大学哲学教授佛格森的家中见到彭斯之后,总是见人就要“吹嘘”一番。12岁嘛,怎么说都是个孩子。
司各特曾经爱过的那位姑娘的家,就在爱丁堡王子大街旁。如今,这条大街的一侧,矗立着一座非常雄伟的纪念碑,碑身就是彭斯的雕像。
爱丁堡人对彭斯极为崇拜,甚至将每年1月25日(彭斯的生日)作为民族节日来过,并命名为“彭斯之夜”。“彭斯之夜”的主角是“苏格兰国菜”哈吉斯,这道由羊肚包裹着羊内脏制成的美食几乎成了民族象征。在吃哈吉斯之前,人们通常要事先诵读一遍彭斯的诗篇《致哈吉斯》。
18世纪末的苏格兰曾是欧洲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虽然地处欧洲边缘,人口只有100多万,但苏格兰高度繁荣的教育体系却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文坛巨匠与科学巨人。这得归功于16世纪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该运动由马丁·路德以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腐败的名义发起,曾席卷全欧洲。其中,约翰·诺克斯作为苏格兰教会创始人之一,认为男女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都应该读圣经》。1583年,苏格兰便建立了四所公立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重镇。这让农民彭斯得以有机会受到比较系统的基础教育。彭斯为人津津乐道的,不仅是他的才华,还有他的英俊风流、浪漫多情。诗歌、自然、美酒、女人,就是彭斯人生的写照。除了天生的贵族身份,在其他方面,彭斯与拜伦倒是有些相像。
彭斯最优秀的诗歌作品产生于1785—1790年间。他从农民生活和民间传说中汲取素材,凭真情实感描写大自然及乡村生活。在当时苏格兰上层都崇尚英语的时代,他却始终坚持用苏格兰方言写作。这些作品多数收录在诗集《主要以苏格兰方言而写的诗》中。该书出版后,彭斯得稿费20英镑。他原打算用它买船票去牙买加,从此离开英国。恰在此时,爱丁堡传来喜讯,请彭斯到爱丁堡接洽出版诗集的事宜。彭斯喜出望外,随即于这年的11月27日找邻居借了一匹马,快马加鞭地赶往爱丁堡。翌年4月,《欢乐的卡利多尼亚诗神》在爱丁堡出版发行。彭斯名利双收,既得到多达400英镑的稿酬,还得了100枚金币的版权费。
农民彭斯在爱丁堡过得风生水起,社会名流、大家闺秀竞相与他相识,虽然他的穿戴完全就像个进城的乡巴佬。当时的爱丁堡沙龙女主人戈登公爵夫人说,彭斯在与女士们交谈时总是彬彬有礼,他的言谈既伤感又幽默,令人为之倾心。
彭斯拿着赚到的稿费开始在苏格兰漫游、吟唱,但在爱丁堡,有一个女人却在等着他,这个女人名叫艾格尼斯,其丈夫在中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服役,与艾格尼斯关系紧张。彭斯于是与她成为了情人。这段感情持续了四五年之久,这也是彭斯与爱丁堡紧密相连的四五年。在此期间,彭斯出入于爱丁堡上流阶层举办的各个沙龙,对所有文学活动都积极组织、参与,俨然成了爱丁堡的一位文学领袖。
1789年,彭斯回到他的家乡加洛韦,并谋得了一个小税务官的职位;这一点他倒是与之后的华兹华斯十分相像。彭斯每天都要骑着马去上班。就在那一段飞扬驰骋的日子里,他有了灵感。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出了《友谊天长地久》;一个半世纪后,它成为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
没有证据表明,罗伯特·彭斯与隐居在湖区的华兹华斯兄妹相识。华兹华斯兄妹到湖区隐居的那一年,彭斯已经去世了。
在离彭斯雕像不算很远的地方,有一家不大的咖啡馆,名叫大象咖啡馆,J.K.罗琳的《哈利·波特》最初就是在这间咖啡馆里写出来的。
我不是很爱凑热闹的那类人,而且对罗琳也谈不上喜欢,但既然来了爱丁堡,大象咖啡馆总还是要去瞧一瞧的。我的第一印象是,大象咖啡馆多少有一些局促,人稍微一多就感觉到拥挤。里面的桌椅则普遍有一点点新中式的味道,不清楚老板当初是怎样的设计想法。罗琳在这里写作的时候,正在爱丁堡大学进修,也经常会带着她不大的孩子一起。说实话,同样是作为写作者,我是不太好想象当年罗琳是怎么在这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只是我觉得她最大的胜利不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她由此成为了爱丁堡大学的“杰出校友”。
创立于1583年的爱丁堡大学是爱丁堡这座城市的骄傲。在爱丁堡逗留期间,我有幸赴爱丁堡大学参加了一次与学校管理层的交流活动。我记得我问到了这所大学的两位校友,一位是阿道尔夫》的作者、法国作家龚斯当,另一位就是J.K.罗琳。对于龚斯当,他们表示,一百多年前,爱丁堡大学的法国学生相当多;而对于罗琳,他们似乎不太乐意展开谈论。说实话,我不太清楚罗琳对于爱丁堡大学而言意味着什么。与该校其他著名校友——如查尔斯·达尔文、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亚历山大·贝尔、温斯顿·丘吉尔、柯南·道尔,以及被称为“怪杰”的奇才辜鸿铭等等——相比,J.K.罗琳成为“巨匠”或许还需要时间,而且这与她以她母亲的名义捐给爱丁堡大学一千万英镑无关。
身为英格兰人,爱丁堡无疑是J.K.罗琳写作生涯中最最重要的一站:1993年年底,刚刚经历了离婚打击的J.K.罗琳带着还在襁褓之中的女儿,揣着三章《哈里·波特》的手稿,走出了爱丁堡威弗利火车站的出站口。而威佛利火车站的名字就来源于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威佛利》。
说实话,我之前对于J.K.罗琳的认识基本上都来自于各种媒体。而这些媒体所共同描绘的是:一个生活拮据的单亲母亲为了节省暖气费,只能带着孩子到大象咖啡馆去“蹭”暖气,一边写作一边借此度过漫长的冬日。而事实呢?如今看来却并非如此。爱丁堡出版的一本有关罗琳的书籍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J.K.罗琳实际上并没有她自己所说的那么穷,就目前所知,罗琳曾经申请到了每周103.5美元的政府失业救济金,她还申请到了一份每周70英镑的政府低保金。她拿着政府给她的这些救济金,除了不可以出国消费之外,在英国国内还是可以自由旅行的。钱的确不多,但倘使省着花,偶尔去一趟北海边消遣也是没问题的。
1997年2月,还是因为罗琳自己的申请,苏格兰艺术协会给了她一笔13000美元的费用,以资助她未完成的写作事业。之后的事情想必大家也都清楚了。总之,女作家一夜之间红遍了全世界,她的个人财富早已经超过了英国女王。
爱丁堡显然是J.K.罗琳的福地。就像大象咖啡馆与罗琳的关系在爱丁堡不是秘密一样,如今J.K.罗琳位于爱丁堡郊区莫切斯顿的家庭地址在爱丁堡也不是什么秘密。那里属于爱丁堡的富人区,从大象咖啡馆步行半个小时便可以到达那里,有不少人专程赶过去“探秘”。听说罗琳为她的两个孩子在院子里花27万英镑盖了一座城堡,结果被邻居告到了爱丁堡市政厅,不等“城管”来,罗琳就自行拆除了。
走在爱丁堡的大街上,抬眼便是险峻高耸的城堡、古老冷硬的教堂,低头便是数百年马踏车辗的路面与草地上横卧竖躺的人们,一切关于中世纪、关于公主与王子的想象仿佛都在这里渐渐成形。和灿烂与冷冽相间的白昼相比,我还是更喜欢有荧荧灯火烘托起夜晚的爱丁堡,它总是令我想起司各特,想起彭斯,想起以写作《金银岛》而驰名的爱丁堡人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被刻在爱丁堡老城和新城交界处那块地砖上的诗句:“没有任何一颗星星,如爱丁堡的街灯般闪亮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