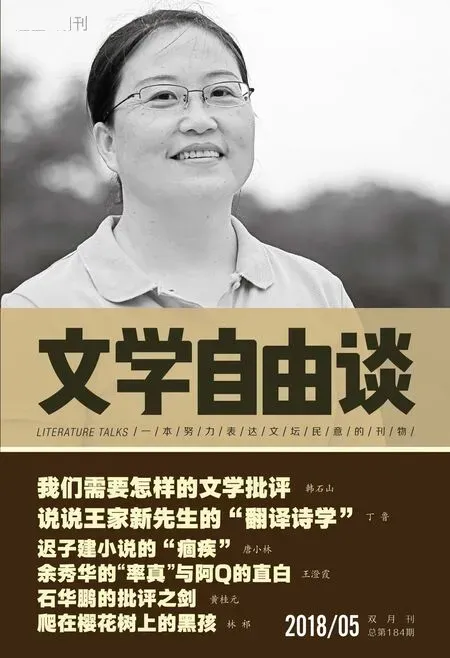迟子建小说的“痼疾”
唐小林
在当代作家中,迟子建不仅是小说生产的大户,同时也是包揽各项大奖的获奖专业户。迟子建称:“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如此骄人的成绩,当代许多作家无论怎样努力,别说一辈子,恐怕两辈子也达不到。
从事写作三十多年来,迟子建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就连她的那些写作同行,都对其非常钦佩,赞赏有加。王安忆赞美迟子建说:“她的意境特别美好,这种美好我觉得是先天生成,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走出来,好像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写进小说。”而苏童对迟子建的赞美,则更是不遗余力:“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迟子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而来,一只温度适宜的温度计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
作为一个作家,迟子建能够得到王安忆和苏童这样的写作同行的高度赞美,这肯定是值得恭喜的事,但作为读者,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样的友情评论当真。如果王安忆和苏童能够认真、理性地研读迟子建的小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或许就会完全相反。王安忆所说的“意境特别美好”,换一种说法就是“矫情的诗意描写特别多”;而苏童所说的“稳定的美学追求”,换一种说法就是“缺乏新意和变化”。
迟子建曾告诉记者说:“我出版过的小说,我会做自己的第一个批评家和读者,拿到以后再看一遍,我会反思一下这里头有些什么东西不够充分,表达不够那么准确。我老想,我下一部作品,我要把它做得好一点,可是你做完了下一部作品以后,你回过头来看,又能发现一些遗憾,文学的局限,其实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看到这样的表白,我真为迟子建着急:她难道就不明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再高明的医生,也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病根究竟在哪里,更不要说自己给自己做手术了。许多作家常常把作品称作自己的孩子,而再丑的孩子,在父母的心中都是最棒的、最可爱的宝贝。文学的魅力并不是来自那些“遗憾”和“局限”,而是来自不断的超越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读迟子建的小说,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作者对其小说创作的“痼疾”竟然浑然不知,或者说知道也久病不治。迟子建小说的“病症”之多,在当代作家中,或许可说是一位典型的“重病患者”。
一、用矫情的诗意,把小说熬成一锅“鸡汤”。
读迟子建的小说,我总是想起杨坤的那首《穷浪漫》:“记得那天/走过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得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但生活并非是靠歌曲来维持的,歌可以这样唱,日子却不能这样过。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没有钱根本就不算什么,爱情本身就可以当饭吃。为了将小说写得更加煽情和夺人眼球,迟子建添加了不少男欢女爱,甚至“大尺度”的描写。
《福翩翩》中的柴旺,年轻时在机修厂当车工,他和王莲花浪漫的爱情,就是因为一块石头。那年秋天,王莲花家里缺一块压腌酸菜缸的石头,她骑着自行车到河边去找。柴旺所在的机修厂正好就在这条河边,每到夏日正午,他和工友们喜欢到河边洗澡。就在这时,他看见王莲花抱着石头好不容易往前走了两步,又把石头掉进水里。柴旺主动帮她把石头从水中搬上自行车,从而赢得了她的爱情,二人结为夫妻。从此,这块浪漫的石头就一直放在他们家的酸菜缸上,成了他俩爱情的见证,俩人也因此幸福得就像花儿一样。“柴旺家的(即王莲花)在冬天走路的时候想柴旺,一想,身上就暖了,北风仿佛也就不是北风了,让她觉得舔着脸颊的是小猫温暖的舌头。”自从娶了王莲花,柴旺的日子过得实在是滋润得很:一进家门就会有温热的洗脸水端来,然后是可口的热饭伺候,再就是俩人相拥着,在暗夜中合唱一折“鸳鸯戏水”的戏,再然后就是柴旺发出求欢的信号。
《踏着月光的行板》中,家里穷得叮当响的农村青年王锐,爱上了同样穷得叮当响的林秀珊。当他发现林秀珊喜欢唱歌时,就认定她一定也喜欢听口琴,于是,请求家人出钱给他买口琴,但遭到父兄的反对,他为此绝食三天。最后还是母亲偷着塞给他一百元钱。他从村里跑到乡里,直到坐车去了县城,总算买到了口琴。乘车返回时,盘缠不够,只得坐到半道,剩下的路,走着回家。夜晚,他露宿野地,望着满天星斗,不由得捧着口琴,悠然地吹着。因为这把口琴,王锐赢得了林秀珊的芳心。洞房花烛之夜,林秀珊让王锐为自己吹口琴。因为怕家人笑话,二人就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关了灯,钻到被窝里去玩浪漫……小说把中国贫苦农民的生活描写得就像神仙一样浪漫和美好——当年杨朔在散文中就曾大量使用这样的手法,而在小说中这样做的,迟子建或许还是第一人。
这种一看便知虚假的“心灵鸡汤”,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数十年不变地“熬制”。它就像是杨朔散文的小说版。杨朔称自己写作散文的时候,完全是用写诗的方法来写的。所以,在他的笔下,生活总是美得一塌糊涂,即使现实有遗憾,但心灵总会把它们超额弥补。比如,在《泰山极顶》中,看不见日出也没什么遗憾的,因为作者“分明已看见了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再看迟子建的《起舞》,丢丢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被推土机挖断一条腿,但这似乎根本就不是事儿:“她在失去右腿的那个瞬间、在一生中唯一起舞的时刻,体验到了婆婆所说的离地轻飞的感觉,那真是女人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分啊,轻盈飘逸,如梦似幻!”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写出这样无视生命尊严的奇葩文字!像这种越俎代庖、充当人生导师进行空洞说教的做法,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二、故事弱智,把小说写成“天方夜谭”。
作品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这是当代作家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为了追求高产,阎连科“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莫言四十多天就“制造”出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贾平凹每隔一两年就有一部大炒冷饭的长篇小说问世……在把写作当作比速度、比长度的大竞赛中,迟子建早已把自己历练成高产能手,从字数上看,她的作品早已经超过了四大名著的总字数。但因为缺乏仔细打磨,许多小说常常呈现浮皮潦草的病象,其故事之荒唐,简直就像是发生在天上的故事。
《踏着月光的行板》中,林秀珊和王锐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在小旅馆相会,争分夺秒地寻求欢爱。日子虽然很苦,但他们却过得开心、甜蜜。王锐给林秀珊买廉价的纱巾,林秀珊不惜将好不容易享受到的福利——一床拉舍尔毛毯低价转卖,再从银行取钱,凑钱为王锐买了一把口琴。中秋节前夕,俩人因为没有电话,不方便沟通,各自都急着往对方工作的地方赶,以致一再错过,耽误了难得的欢愉时间。在去寻找王锐的火车上,林秀珊看到,一个胖男人给另一个瘦男人戴上镣铐,安安稳稳地睡起了大觉。原来,瘦男人是杀死两个人的重刑犯,押解他的胖男人是便衣警察老王。但列车上,犯人不但丝毫没有恐惧,反而一身轻松。林秀珊每次清完嗓子,犯人就会冲她眨眨眼,微微地一笑。林秀珊摆弄口琴的时候,抬头看他一眼,发现他的眼神变了,先前看上去还显得冷漠、忧郁的目光,此刻变得格外温暖、柔和:“犯人看着口琴,就像经历寒冬的人看见了一枚春天的柳叶一样,无限的神往和陶醉。”
“鸡汤”已经下锅,迟子建就越写越离谱。林秀珊天真地求警察给犯人打开手铐,让他吹一吹口琴。老王连脑子都没过一下,就欣然接受了林秀珊的建议,并对犯人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吹口琴了,就给你个机会吧!”说着,就为犯人打开了手铐。紧接着,一段充满诗意和浪漫的描写便在迟子建的笔下流淌了出来:
那小小的口琴迸发出悠扬的旋律,犹如春水奔流一般,带给林秀珊一种猝不及防的美感。她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柔和、温存、伤感、凄美的旋律,这曲子简直要催下她的泪水。王锐吹的曲子,她听了只想笑,那是一种明净的美;而犯人吹的曲子,有一种忧伤的美,让她听了想哭。林秀珊这才明白,有时想哭时,心里也是美的啊!
老王也情不自禁地陶醉起来,随着旋律晃着脑袋。乘客没听够琴声,纷纷要求老王“再让他吹一首吧”——迟子建笔下的这位便衣警察,简直就是个没脑筋,而林秀珊也好,乘客也好,也都像脑子里进了水,或者是严重智障。押送犯人通常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执行程序,尤其是在押解死刑犯时,更是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马虎,必须给犯人戴上头套,一是为方便执行以后的特殊任务,避免留下影像;二是为了防止引起死刑犯家属的仇恨,制造不应有的社会矛盾;三是为了防止黑恶势力的渗透和报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一个警察会单枪匹马地押送死刑犯,将其和普通乘客混杂在一起,还呼噜呼噜地睡大觉。迟子建有没有想过,一旦死刑犯挣脱夺枪,在乘客众多的车厢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在《百雀林》中,平素蔫头蔫脑、笨嘴笨舌的周明瓦,九岁时爷爷死了。听不到爷爷的口技,他身上的魂儿都不全了,一天到晚打呵欠,而且害渴,水瓢不离手,夜夜尿炕。甚至十一岁时,他还是连话都说不清楚。父亲周巾因为母亲和另外两个女人一起去烫了头,就认为她是“妖精”,一气之下,失手将她砸死,继而逃之夭夭。亲戚们收养了明瓦的哥哥、姐姐,明瓦则因为傻而被他们拒绝,却被家庭条件不错、结婚十年未能生养孩子的王琼阁领养。明瓦学习成绩不好,却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明瓦毕业之后,趁着当年因兵源不足,政审和体检要求宽松,到天津当兵去了。他不仅当了五年兵,养了无数头猪,并且还入了党,立过三等功。明瓦复员后,进入公路管理站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做事比正常人都正常。明瓦不仅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姐夫二歪申请营业执照,而且还给他做经济担保人,从银行贷款两万块……我真不理解,明瓦这样脑子里像有糨糊、连话都说不明白的人,是怎么在部队里经受住锻炼,被发展成党员,并且荣立三等功的?这种前后矛盾的情节,实在有辱读者的智商。
三、歪瓜裂枣的人物和夸张猎奇的性描写如洪水泛滥。
迟子建在小说中迷恋性暴力和性畸形的书写,通过这些非同寻常的经历,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性恐怖和稀奇古怪的性噱头。
《群山之巅》中,身高只有92公分的侏儒安雪儿初中毕业时,遭到村里游手好闲的暴徒辛欣来的强奸。《花牤子的春天》里的花牤子,打小就喜欢看女人的奶子和屁股,看见女人就总会动物一样发情。最后,他反而被陈六嫂“强奸”了;更为离奇的是,他因为意外事故,废掉了裤裆里的“凶器”。《第三地晚餐》中,生意人马每文的妻子因丈夫长年在外奔波,与同是教练的吕东南发生了暧昧关系,经常以训练为由,深夜在游泳馆幽会。在一次水下交欢时,她忘乎所以地欢叫,水流呛入气管,竟使她瞬间停止了呼吸,漂浮出水面——一个会游泳的人,并不会因为呛水瞬间就停止呼吸的;而溺水死亡的人,更不可能马上就漂浮出水面,而是会沉入水底。迟子建的这种描写,明显违反了简单的科学常识。
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就是一个比一个傻的“木头人”。《起舞》中的丢丢失去了一条腿,母亲刘连枝是个豁嘴;《第三地晚餐》中陈青的母亲缺胳膊;《福翩翩》中的刘家稳老师缺腿;而《百雀林》中的周明瓦、《采浆果的人》中的大鲁和二鲁、《罗索河瘟疫》中的领条、《伪满洲国》中的阿永、旧时代的磨房》中二太太的儿子、《酒鬼的鱼鹰》中的娇娥和李金富的大儿子、《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等等,更是一个比一个傻。用猎奇的心理来写小说,用夸张的性描写做“调料”,早已成为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迟子建笔下的一些女人,虽然长得丑陋怪异,却性欲亢奋;而一些男人,则是獐头鼠目、举止猥琐的酒鬼,他们到老都是把“性”当饭吃,调戏老婆,勾引邻居,对裤裆下的那些事乐此不疲。夫妻出轨,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并且描写雷同。只要写到做爱,几乎毫无例外地就要写到“叫床”,而且不分时间和场合,一律是不管不顾地嗨翻天。在《穿过云层的晴朗》中,黄主人与胖姑娘做爱,隔着门都听得见他们的大呼小叫,连狗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在《第三地晚餐》中,分别有两次“叫床”的描写:一次是陈青的哥哥和嫂子来到她家留宿,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叫了半宿,叫声把陈青的老公马每文的欲火也撩拨了起来;另一次是张灵在菊花旅馆住宿,隔壁马每文二十多岁的女儿与四十多岁的徐一加做爱时,夸张的叫床声一直持续到天亮,如此充沛旺盛的精力,让张灵觉得自己都老了。在《起舞》中,刘连枝和老公傅东山一到晚上就开始“叫床”,这样的声音让其幼小的女儿丢丢感到异常的好奇。在《百雀林》中,明瓦的姐夫二歪吃饱喝足后,一到晚上就与明瓦的姐姐又喊又叫地寻欢作乐。
纵观当代作家的写作,迟子建小说的雷同现象可说是非常惊人的,以至于让人怀疑她是在用自我抄袭的方式来复制写作、实现“高产”:
她的衣裳还被扯开了一道口子,没有穿背心的她露出一只乳房,那乳房在月光下就像开在她胸脯上的一朵白色芍药花,简直要把她的男人气疯了。他把她踢醒,骂她是孤魂野鬼托生的,干脆永远睡在山里算了。她被背回家,第二天彻底清醒后,还纳闷自己好端端的衣裳怎么被撕裂一道口子?难道风喜欢她的乳房,撕开了它?她满怀狐疑地补衣裳的时候,从那条豁口中抖搂出几根毛发,是黑色的,有些硬,她男人认出那是黑熊的毛发。看来她醉倒之后,黑熊光顾过她,但没有舍得吃她,只是轻轻给她的衣裳留下一道赤痕。
——《采浆果的人》
我突然想起了依芙琳的话,她对我说,熊是不伤害在它面前露出乳房的女人的。我赶紧甩掉上衣,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树,那两只裸露的乳房就是经过雨水滋润后生出的一对新鲜的猴头菇,如果熊真的想吃这样的蘑菇,我只能奉献给它。所以这世界上第一个看到我乳房的,并不是拉吉达,而是黑熊……
——《额尔古纳河右岸》
熊不吃有着美丽乳房的女人,这种弱智的故事,只能讲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但必须明确告诉小朋友们千万别当真,否则将会发生惨不忍睹的悲剧。再美丽的鲜花,在牛的眼睛里都只不过是一堆草;再美丽的乳房,在熊的眼睛里也只是两坨肉。过分在小说中宣扬凶猛动物的善良,怀念狼、美化熊,可说是当今小说家哗众取宠,异想天开的幼稚病。
四、移花接木,用复制+粘贴的方式来拼贴文字。
缺乏独立思考,以文字的堆积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已经成为当代文坛的普遍现象。因为缺乏想象力,创作才能枯竭,许多当红作家开始投机取巧,大量采取“新闻串烧”的方式来写作,如余华、阎连科、贾平凹、刘震云等人的某些作品即是如此。迟子建虽然不搞“新闻串烧”,却大量采用“旧闻粘贴”,把从故纸堆里翻寻出来的素材,粘贴到自己的小说中。如:
多卧两岁时,我哥哥去世了。他是为救一只蓑羽鹤死的。有年夏天,哥哥到草原来,一天傍晚,他出去散步,发现一只受伤的蓑羽鹤在河水中扑通,要沉下去的样子,他就跳到河中去救。那年雨水大,水流急,哥哥不会水,他就被激流给卷走了。草原的牧民都喜欢哥哥,我们把他葬在河边的草地上了。
——《草原》
这则故事,可说就是对东北第一位养鹤姑娘徐秀娟的故事移花接木的复制。徐秀娟勇救丹顶鹤的事迹通过媒体报道,尤其是经过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的传唱,一度广为人知。徐秀娟因为一只失踪的幼小丹顶鹤,一整天都在芦苇荡中趟水寻找,疲劳过度倒在了沼泽地里。迟子建在将这个故事写进小说时,编造得实在太离谱了:别说不会游泳的“哥哥”,就是会游泳的人,跳进湍急的河水中,照样可能是有去无回;在湍急的水流中,如果仅仅凭肉眼,通常是不可能看见一只小小的蓑羽鹤在扑腾的;这位哥哥既然不会游泳,为何要在雨水大、水流急的时候到危险的河边去散步?
迟子建小说中的许多描写,往往都缺乏原创性。如:
影片中的小姑娘救下了当年的连长,划船送连长脱离险境时,遭到日本鬼子的追击!这下好,葛一枪当真了,他扔下酒囊,抓起脚前的枪,对着银幕上的鬼子就是一枪!鬼子没影儿了,银幕被打了个窟窿,把我给心疼坏了。我责任大呀,一块银幕值多少钱呢,修复个枪眼多难呀。我停下放映机,告诉他们电影里的人都是假的,不能当真。
——《别雅山谷的父子》
这则故事明显蹈袭于电影演员陈强的那段亲身经历:他在台上把恶霸地主黄世仁演得十分真实,竟使得台下一个新战士朝他开枪;如果不是旁边的班长眼疾手快,抬高枪口,陈强就被枪杀了。
如此这般的移花接木,使迟子建的创作堕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别人作品的影子。如:
我只好对安草儿说,你不要以为优莲是死了,她其实变成了一粒花籽,如果你不把她放进土里,她就不会发芽、生长和开花。安草儿问我,优莲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呢?
我说,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我们的祖先是从那里来的,我们最终都会回到那里。
——《额尔古纳河右岸》
以上这两段描写,是不是对《圣经》的复制呢?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而后面一段则来自《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你来自尘土,终归于尘土。”文学创作追求的是原创性和艺术性,像这样用改头换面的方法来写小说,还谈得上真正的创作吗?
五、文字不通,逻辑混乱,奇葩句子屡屡出现。
汪曾祺先生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迟子建虽然获得过无数大奖,但其小说的语言却始终令人不敢恭维,存在许多常用词语搞不懂、句子写不通的情况。正因如此,我在读迟子建的小说时,总是有一种疙疙瘩瘩、莫名其妙的感觉。如(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她满面狐疑地走了……我不放心地看了马孔多一眼,他睡得的确香,那双惯于嘲弄人的眼睛偃旗息鼓了。
——《向着白夜旅行》
传说狐狸是一种多疑的动物,“满腹狐疑”是指一肚子疑问,而“满面狐疑”则根本就不能表达这样的意思。“偃旗息鼓”原是指放倒军旗,停敲战鼓,后比喻停止某种行动。睡觉闭上眼睛,怎么称得上是偃旗息鼓?
天上要出大事故了,而这事故的发生地就在我的出生地,这真让人惊喜又令人忐忑不安。
——《观彗记》
“我”对“事故”感到“惊喜”,这并非是真的幸灾乐祸,而是因为作者对“事故”一词一知半解。所谓“事故”,是指意外的损失,或生产、工作上发生的灾祸,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等等。这里的“事故”,说成“奇观”更合适。
她带给他的仇恨和屈辱也渐渐如水中的冰块一样分崩离析。
——《逆行精灵》
“分崩离析”出自《论语·季氏》:“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形容国家、集体或组织的分裂瓦解。“崩”表示倒塌,“析”表示分开。冰块在水中是渐渐融化的,那过程,哪里谈得上是倒塌?
“这人也真是个缘份,我跟了老爷这么多年,不养不生的,现在依了另外一个主,反倒是有了,我可真没想到!”
他很勤快,除了把他份内的活干好,还帮着其他佣人做些杂事……
——《旧时代的磨房》
“缘分”和“分内”都属常用词,但就是这样一些常用词,却经常将许多当红作家绊倒。他们往往分不清“分”与“份”的区别。类似的情况还有:莫言把“流火”当成是天气炎热,贾平凹称自己为寡人”,还觉得是非常谦虚。如此洋相百出,当代作家们拿什么去跟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比?
齐如云不漂亮,但她肤色白皙,身材俊美。好的肤色和身材,天生就是女人的一双“招风耳”,她也因此比面容姣好的女人要引人注目和耐人寻味。
——《起舞》
肤色和身材是一双“耳朵”(招风耳),这比喻,可是够荒唐的了。这还没完——作者明明是想夸赞齐如云。却又用了“招风”这个词。在汉语中,所谓“招风”,是指惹人注意而生出是非。如此词不达意的表达,可说是典型的自相矛盾。
等到想起它们,有一些已垂垂老矣,早已过了食用的最佳期。
——《门镜外的楼道》
“垂垂老矣”是指人的年龄渐渐老了,它与食物是否过期可说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领条再一次回头看了看死狗,现在它身上的皮毛已有被拖烂的地方了,这段俯首贴耳的路途使它面目全非。
——《索罗河瘟疫》
作者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搞懂“俯首帖耳”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然,她就不会把“帖”写成“贴”。既然这条路都“俯首帖耳”(被驯服)了,何以又会使领条的狗面目全非?
你们该去找教堂的就去,该找队伍的就去找,男孩子不能这么没出息地一辈子窝在这两亩三分地上,现在也没那么多好地可种了。
——《伪满洲国》(上)
“一亩三分地”是一句约定俗成的成语。满族原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清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及时了解农时,熟悉节令,每年惊蛰时节,皇帝会从正阳门乘龙辇到先农坛耕地,表示普天之下该种植五谷了,并以此显示皇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先农坛里这块面积为一亩三分的“皇帝亲耕地”,就被人们引申为个人的利益、势力范围,而形成了“一亩三分地”这句成语。迟子建把“一亩”扩张成“两亩”,显然是不懂它的来历,也不知道成语是不可擅改的,就像不能把“半斤八两”改成“半斤五两”一样。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囫囵吞枣地读书,匆匆忙忙地写作,确乎已经成为当代作家的一种“新常态”。迟子建小说的“痼疾”,其实也是当代许多当红作家的通病和常见病。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大都不把这些病放在眼里,以为只要批评家们不说,就可以一直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