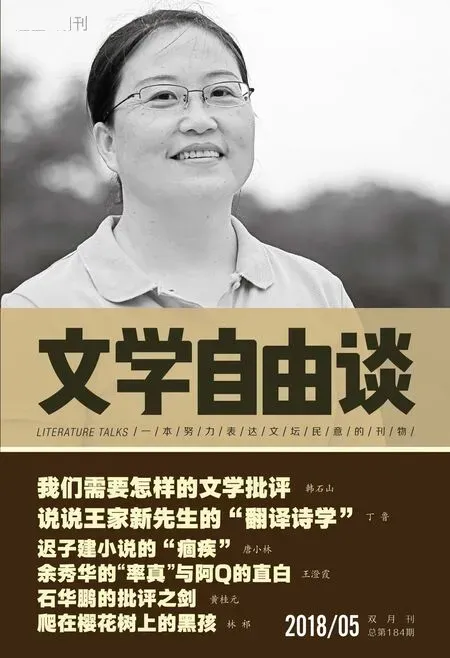说说王家新先生的“翻译诗学”
丁 鲁
诗人王家新先生近来在诗歌翻译方面相当活跃,不仅积极实践,而且做出理论总结,在《翻译的辨认》(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一书中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翻译诗学”。这就超出一般翻译观,上升到诗歌翻译指导思想的地位,和每个诗歌译者都有切身关系了。如果不愿受其指导,又不愿被斥为不符合 “翻译诗学”,就不得不起而抗争,只好请王先生见谅。
一、意外的校订
我本来是想讨论诗歌翻译的,却发现不得不先作某些校订。
《翻译的辨认》一书456-457页上,有狄金森一首无题诗,、4 行是:“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And Immortality.”72页上有王先生校订的译文,译为:“马车载着,但只有我们自己——/以及不朽。”But译作“但”,是误译。它在这里只是加强语气,held but just ourselves不过表示 “载着的只有我们”ourselves就是us的意思,这样用是节奏的需要)。
第442-443页谈雷克斯洛斯译的杜甫 《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译文3、4行是:“I atch the Spring go by and wonder/If I shall ever return home.”王先生回译成中文:“我看着这春天流逝而诧异/如果我可以回到故乡。”If译成“如果”,也是误译。这个词在这里只是表示“是不是”“能不能”之类。由wonder开始,不过是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家”。这和杜诗原意相近,王先生大概没和杜诗核对过。
这些都是较为初级的语言错误。其他地方,不再逐一校对。像大写之类的“小”毛病,就更多些。至于王先生不知道海豚是哺乳动物,并不足怪;但在218—219页肯定海豚是鱼之前不查工具书,还要告诫译者“必须时时依据词典工作”,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这是一个我不希望出现的不愉快的开头。它能引出一些什么结论,还是留给广大读者判断吧。
二、西方人怎样译诗?
讨论诗歌翻译,首先要研究评价标准。我们面对大量西洋格律诗,可是中国的白话诗至今缺乏公认的格律规范,所以最好看看西方人怎样译诗。不过,中国的文言诗太精练,翻译不能不出现改写成分;白话诗形式又比较自由,译文也不能不如此。我们还是看看西方不同语种的格律诗怎样互译吧。
他们的格律诗互译,首先重视的是格律形式,在这一框架下来考虑词句安排。王先生书上有时也提到某些西洋格律术语,但研究问题却总是脱离诗歌形式的分析。
比如书中《策兰对狄金森诗歌的翻译》一文,重点介绍狄金森那首无题诗,并附有英文原文和德文译文。二者也都有中文译文,王先生说是别人译的,经他校勘和修订。文章后面另附一个文本,看来就是经他修订的了。所以我根据第二个文本来谈。
狄金森这首诗主题是死亡。内容简单说是:人总会死,只有死亡是永恒的(不死的)。全诗共五节。第一节是: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And Immortality.
经王先生修订的译文是:
因为我不能停下等死亡——
他好心地为我停下——
马车载着,但只有我们自己——
以及不朽。
原诗是素体诗(无韵诗)。但它并非自由诗,各行都遵循“轻重”的节奏规律:单行四个“轻重”音步,双行三个“轻重”音步。mmortality的词根mort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死亡;接头部im-表示否定。至于Death,书中的完整文本用小写字母开头,后来的分析中开头却是大写字母,而大写开头有 “死神”的意思Immortality大写开头,用意相同,和Death对应)。所以我用后一种写法。这虽是技术问题,不也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吗?
此外,译文各行意思似乎连不起来,让本来清楚的句子看不太明白了。比如Death没有译作“死神”,第二行的“他”就不知何所指。莫非这就能增强诗歌“陌生化”的感觉,增加原作的神秘感和诗歌的神圣品格?如果一篇论文出现这种风格,我想会受到王先生的批评的。诗歌作为一种高级文体,文字水平难道可以比其他文体更随意?
策兰的德文译文是:
Der Tod,da konnte ich nicht anhalten,
hielt an und gern bereit.
Im Fuhrwerk saß nun er und ich
und die Unsterblichkeit.
它同原文一样,是单行四个“轻重”音步,双行三个“轻重”音步。所不同者,只是双行加上了韵脚。第三行将原文just ourselves(只有我们)译为er und ich(他和我),就是出于节奏(在这里是“重轻重”)的考虑。如果脱离格律框架,这种译法该怎么解释?可见策兰只是为了遵循原作的节奏安排。如果他地下有知,恐怕不会引王先生为知音吧?
以上这节诗,我想大体可以这么译:
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神,
他就好心地等我。
他车上载着的只有我们
和一位不死之神。
这个译文很粗糙,因为我没有通译全诗并加以润色,更没有认真研究过狄金森,故仅供讨论批评。不过读者看了大致可以弄懂原意。
三、“信”——翻译的“铁杆儿标准”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准确性是其必要条件。文学译文需要某些修饰,但必须有理由。比如翻译格律诗要符合一定的格律规范,这就是理由。否则,用个人好恶的随意性取代翻译标准,等于在翻译中以“人治”代替“法治”,实际上就取消翻译标准了。
王先生知道,不提“信”是说不过去的。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圆桌》2016年7月讨论诗歌翻译的丽水会议上,他作为主持者发言(见《扬子江诗刊》2017年第4期),一开始就提到“信”,并作了发挥。他说:
“信、达、雅”我只认一个“信”,翻译不管怎么样,要忠实可信,不仅忠实,还要可以信赖。这在今天仍是一个前提,但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忠实,是字面意义上的忠实?亦步亦趋的忠实?还是富有创造性的,更高意义上的忠实?
先说“信”和“忠实”,接着说“创造性”比前者“意义”更高,也就是比“不信”和“不忠实”更高。细心的读者会从这里闻到一种偷换概念的味道。偷换概念属于诡辩,而诡辩的起因,是理论上的胆怯。
《翻译的辨认》一书自然也提到“创造性翻译”(434页)。其实,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是被动的创造,是有所依据的创造,不同于诗歌创作的主动创造。因此,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创造,永远是一种“再创造”。
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尽量体现原作风格和原作者的特点。译者应成为无名英雄,而不应和原作者抢风头。记得俄罗斯的苏联时期也曾有“超越原作”的说法,后来无果而终,就是旁证。而王先生的“创造性”诗歌翻译理论,只会把对外国诗歌和外国诗人的研究变成对译者的研究。
诗歌翻译不需要那种独出心裁的“创造性”。它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匠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打造优秀译作的。
《翻译的辨认》一书引了中外很多人士的说法,我无法一一查证。简单说,有强调翻译可以改动的激进观点,也有另一种稳健观点,并非一边倒。王先生对西方人士只作赞扬,不加批评;对本国人士则褒贬皆有之。
这里重点说说“转译”问题。
根据“创造性翻译”理论,王先生质疑翻译是否要依据原作,进而批评那些主张通过原作来翻译的论者,扣以“直译神话论”的帽子。他在《新诗百年论坛》上说:
现在一些人对转译有一些偏见,我们姑且叫做“直译神话论”,只要直译就可靠,就好,转译就不行。一听人们这样说话,你就知道他是一窍不通,或完全在说外行话……比如说现在中国有很多俄罗斯文学的译者,但他们的翻译,包括他们的文体,总是带着“苏联文学”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助于英译的刷新。
我译过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所以,王先生提到“俄罗斯文学的译者”,这一棒已经扫到我头上,只好奉陪了。
首先,王先生似乎不懂“直译”这个术语的意思。“直译”是和“意译”相对应的,并非指根据源文本进行翻译。至于所谓“直译神话论”,不过是给批评对象贴上的杜撰的标签。
王先生常提到他译的曼德尔施塔姆。我们就从曼氏作品的译文中找两个例子吧。
王译曼德尔施塔姆诗集摘了曼氏“我的世纪,我的野兽”的话作为书名,并把这首诗的标题译为《世纪》,开始四行是: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看进你的眼瞳
并用他自己的血,黏合
两个世纪的脊骨?
汉语“世纪”,俄语有 век(另有“时代”之意)和 столетие(专指“百年”)二词,标题用的是前一个,第四行用的是后一个。为了区别,我想标题译为《时代》较好。原诗这四行是:
Век мой,зверь мой,кто сумеет
Заглянуть в тои зрачки
И своею кровью склеит
Двуx столетий позвонки?
王先生译文的“看进”显然不合汉语习惯。原文词义应该是注视”,转义则有“果敢地正视”之意。至于 позвонки,并非指整个脊柱,而是指两片脊椎骨。
这里我也译了一下:
我的时代,我的野兽,是谁能对你
勇敢地正视呀,是谁?
谁能用自己的热血黏合这两个世纪,
像黏合两片脊椎?
我想这比王先生的译文更“信”一点。至于“创造性”,那就请王先生批评了。
《辨认的诗学》一文中还有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一诗的两行译文:
我又回到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泪,
我的脉搏,我童年时肿胀的腮腺炎。
这些句子似乎彼此串不起来,很难读懂。也许王先生会说它好就好在这个“陌生化”。那么原文究竟怎样呢?我手头就有:
Я вернулся в мой город,знакомый до слез,
До прожилок,до детских припухлых желез.
其中的 знакомый до(“熟悉到[……地步]”)就没译出来,大概是英译者的失误?
我也译了一下,拿来献丑,不知有没有“苏联文学的味道”:
我回到我熟悉的城市,熟悉得热泪盈眶,
熟悉得血脉贲张,像童年的淋巴肿胀。
这个译文自然也可以商榷;但这样译,除了出于对原文词句的理解,还为了传达格律诗的诗歌形式。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转译文本,能研究曼德尔施塔姆吗?我很怀疑。通过这样的英译本来转译,就更好些?用这套“理论”就可以建立一种“翻译诗学”?如果强调译诗要根据原文,就是“一窍不通,或完全在说外行话”?
依我看,刚好相反,想翻译曼德尔施塔姆,首先就要学俄文,而且要学好。想走捷径,是行不通的。王译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首先就是迷信转译的结果。
四、关于“诗人译诗”
王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但他的评论常以个人好恶作为依据,且能明显发现双重标准。比如他对梁宗岱先生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赞赏有加,可是梁译的语言许多地方已经过时。至于王先生对“文白夹杂”的肯定(第132—134页),就把这个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说是“颠倒是非”也不为过。
他批评了卞之琳先生的译文,这无可厚非;但卞先生坚持传达原作的诗歌形式,却完全没有错,正如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可能有某些毛病,而交通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不要传达诗歌形式,评价格律诗的翻译就只能从词语译法来谈,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讨论还有什么标准?
比如王先生谈穆旦对奥登 《悼念叶芝》的翻译,说他把Earth,receive an honoured guest”译为“泥土呵,请接纳一个贵宾”译得如何好(89页)。而王先生对此句的译文是“大地,接受一个贵宾”,只是没把原文的祈使语气(“接受一个贵宾吧”)译出来,此外,与穆旦的译文并无原则区别。
又比如,卞先生一处用了“女娃”(80页),被王先生批评为以韵害意”,但另一处“毛丫头”(113页)却被评为“堪称大家手笔”,可见王先生的主观随意性:我是诗人,就能口衔天宪,想怎么评就怎么评,想怎么译就怎么译——难道这就是王先生的“诗人译诗”观?
在王先生看来,发表过诗歌创作才叫“诗人”,没发表过创作的不算。可是在格律诗不发达的新诗界,许多诗人写自由诗或半格律诗,但不惯于译西洋格律诗;又偏偏有一批诗歌译者没有发表过创作,其中许多人是为了进行诗歌形式的试验而以翻译作为实践,却入不了王先生的法眼。
最早进行以格律诗译格律诗试验的是胡适。王先生高度评价他的《关不住了》,却没有作诗歌形式的具体分析。胡适以后,闻一多也做过试验,以后就是何其芳、卞之琳。何先生和卞先生团结了一批译者,像屠岸先生、王智量先生和杨德豫先生,就是代表。(屠先生是发表过作品的,蒙王先生在书里带了一笔;可是王先生在极力推崇《诗苑译林》丛书的时候,却忘了它的编者彭燕郊和杨德豫两位先生。)这以后,还有英诗汉译界的黄杲炘先生和俄诗汉译界的顾蕴璞先生、谷羽先生、王志耕先生等人和我。这些人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做法上虽然还有不一致的地方,但都在追求诗歌形式的传达。不久前,我出版了多年来的诗歌创作的选集《风之歌》,不知是否算是跻身诗人行列了?不过恐怕还是入不了王先生法眼的。
西方就不是这样。 译 《柔巴依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又译 《鲁拜集》)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创作并不出色,因翻译在诗歌界成名,就是例证。
王先生的“诗人译诗”观不仅片面,也丢掉了主要问题,即怎样对待原作的格律形式。
建立新诗的格律理论和格律规范,是和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分不开的。新诗界许多人承认应该继承传统,却总是不能具体化,其原因就在于有意无意地避开诗歌形式问题。
王 先 生 谈 茨 维 塔 耶 娃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俄罗斯诗人、散文家、剧作家)时,说“由于俄语尤其适合于韵文写作,所以到今天格律诗仍是俄罗斯诗歌的主流”。其实我们的母语汉语,是一种元音占优势的、有声调的语言,更适合格律诗写作。其铁证,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成就。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到 “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格律诗仍是俄罗斯诗歌的主流,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界至今保持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王先生似乎并非继承传统的积极实践者。在《翻译的辨认》一书中,他就批评诗人北岛在访谈中的有关谈话。北岛说:“中国古典诗歌对于意象和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27页)王先生对这些话很敏感。他批评北岛时,举了北岛近些年的诗句“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说这乡愁奇异地和“不知从哪里来的‘玫瑰’联系在一起”,不同于茨维塔耶娃的写花楸树。其实,乡愁既可以用王先生说的“故乡的菊花或别的什么”来表现,也可以用异国的玫瑰来表现。“垂死的”玫瑰不是很形象地表现了异国的乡愁吗?不写玫瑰,难道要写蔷薇、月季或月月红?
为什么对诗人北岛如此苛求呢?王先生作为文学家,却扯上了非文学话题。他说:“问题还在于,我们今天是否依然需要不断拓展和刷新我们的语言,是否依然需要保持诗歌的异质性和陌生化力量?近十年来,伴随着国内的某种文化气氛,在诗坛上,似乎对‘翻译体’的嘲笑已成风气,‘与西方接轨’也被作为罪名扣在一些诗人的头上。在诗人们中,北岛当年是以异端的语言姿态出现的,但我发现他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所以在批评了北岛关于传统的发言之后,王先生追问道:“但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为了‘政治正确’?还是出于一种真实的乡愁和回归’之愿?”
王先生跑了题,开始扣政治帽子了。他表面上打的是受压的悲情牌,实际是不许别人说话。强调“异质性”之类,只是某一派的见解吧?别人主张一点别的就不行?就牵涉到政治了?——这个话题,我愿点到为止,不再跟着王先生跑了。
同一文中,王先生对一位诗人写的《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非常赞赏。他认为,不说从土地上而说从干酪上站起,“不仅给人以阅读的极大困惑,也有意带上了一种‘异国情调’,它以此颠覆并置换了那个时代的修辞基础”。如果这是写我国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我是可以理解的;若指汉人,能够从干酪上站起的,恐怕只能是部分人吧?写干酪就好,写玫瑰就不好?这同样体现了王先生的双重标准和评论者的个人好恶。
总之,在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下,强调诗人译诗,无助于西洋格律诗的翻译,反会导致出现不懂行者的“速成”型诗歌翻译理论。现实的做法是,承认诗歌译者也是诗人,并以诗人的高标准来要求他们,而诗歌译者也应以此严于律己。到格律体的白话新诗成熟时,诗人译诗的局面自然就会形成的。
五、几点简单的结论
第一,搞诗歌,必须先学好中文,特别是熟悉中国古典诗歌。
第二,翻译外国格律诗,必须先学好外文,而且熟悉他们的诗律。
第三,翻译某国诗歌,必须先学好该国语文。依靠转译容易出错,更不能认为转译优于根据原文翻译。
第四,翻译格律诗,必须先研究中国白话诗歌的格律问题,为此又不能不研究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
第五,评论格律诗,首先要根据格律规范,不能靠评论者的好恶而专谈文字优劣。
第六,诗歌的语言应该比一般文字要求更严格。
第七,只重意象不重意境,只重词语不重韵律,诗歌就会碎片化。创作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第八,粗枝大叶、任意挥洒的写作习惯不适于研究,更不适于诗歌。
第九,建立一门学科,须靠扎扎实实的研究。挑战中外对诗歌翻译的共识,也须靠扎扎实实的研究。
第十、诗歌翻译永远是再创造。人们希望通过译作来了解和研究的,首先是作品和作者,其次才是译者。
凡此十点看法,愿与王先生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