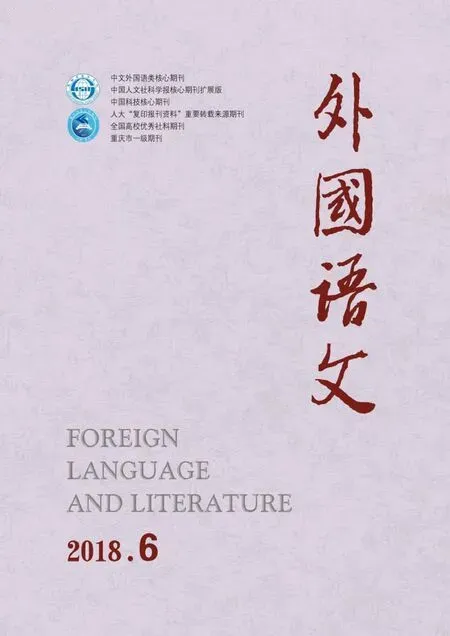论罗伯特·瓦尔泽童话剧《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的文本游戏
丰卫平
(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重庆 400031)
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在生前一直不为德语文学界认可,对他的重新发现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对瓦尔泽小说、散文、小品文等作品的研究,使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作家及其作品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选取瓦尔泽的微型剧——童话剧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探讨瓦尔泽在其中的互文游戏。瓦尔泽颠覆式的改写显然不局限于文本游戏,根据格林童话创造的虚构形象自有其艺术本质,目的在于消解固定意义的生成,尝试把握处在流变中的现实,在虚构与幻想中追求美和自由,从中亦可管窥瓦尔泽文学创作的主题。
1 文本游戏
伽达默尔在《美的现实性》中根据游戏的特征阐释了解释美学的原则,认为读者/解释者(伽达默尔称为同戏者)对文本的阅读、解释与欣赏也是一种游戏,是一种与文本的对话,并且在作品中主动灌注了自己的生活积累(伽达默尔,1991:40)。要使这种游戏似的对话得以进行,文本必须为解释者让出一个游戏的自由空间,解释者需填充这一空间。任何经典文本都为读者/阐释者留下了对话的空间(伽达默尔,1991:42-43)。因此,可将瓦尔泽对格林童话文本的改写看作是一个阅读、解释与再创作过程。下文的文本分析将呈现这一过程,尝试考察瓦尔泽对格林童话游戏般改写及与之互动的意义所在。
1.1 《灰姑娘》
瓦尔泽的童话剧开始于灰姑娘的独白。在格林童话中,灰姑娘在母亲的坟前哭泣,而在瓦尔泽的舞台剧中灰姑娘拒绝哭泣。在她的独白中,她认为:“哭泣令人讨厌,而责骂没有。”(Walser,1998:7)她容忍姐姐们的责骂,还伺候她们。灰姑娘奉承、恭维姐姐们,但她表现得不卑不亢、自信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在姐姐们的眼中,灰姑娘是一个“妄想者”,同时还是个“促狭鬼”和“伪君子”。灰姑娘看起来逆来顺受,事实上她很快乐、信心满满,她“懒散、狡猾、机灵”,甚至在暗地里嘲笑她的姐姐(9)。虽然在她两个坏姐姐面前,她扮演着给她预设的仆人角色,可她是“笑着”扮演这个角色。如此而看,与两个姐姐相比,灰姑娘已胜出一筹。灰姑娘向她的姐姐们述说她的忠心,并一再表示心甘情愿为她们效劳。对她来说,干活是“一份甜蜜快乐”和“幸福”(16)。灰姑娘特别喜欢说话,并且滔滔不绝,姐姐们因此说她“喋喋不休”。在此,说话——语言似乎对灰姑娘来说是一种救赎:“欢乐的话语”能使手里的活计倍增。
当王子与灰姑娘相遇时,灰姑娘自信又聪明地问道,王子是谁,到此的目的是什么(21)。王子直接、肯定地对灰姑娘说,她是他的新娘。灰姑娘似乎并不了解她在格林童话中的命运,于是,王子讲述了童话中之前就预设的故事,并说:“……你只需保持安静,走进那严酷的命运,一切都将做出解释。”(21)可是灰姑娘并未听从王子的安排。她仍然返回平日的生活中,继续她的仆人工作,同时也乐此不疲地继续她的语言游戏。紧接着,童话作为一个角色登场了,并给灰姑娘带来一个皇室新娘的新更衣间,说她值得拥有童话,因为灰姑娘继承了她美丽而又善良的母亲身上“最可爱”的东西(33)。童话编排了接下来的情节发展,随后消失,灰姑娘理应走进格林童话幸福的结局。可是,她一开始不愿顺从童话为她设定的命运。犹豫之后,灰姑娘穿上了新娘的服装,并认可了童话的逻辑。不过,她没有理所当然地屈从命运,而是提出怀疑并追问个中原因。
灰姑娘了解宫廷生活:“简直就是一只被捕的夜莺,颤抖着坐在陷阱中,忘记了鸣叫。”(49)宫廷里的生活就如同被困在金丝笼里的鸟的日子,这意味着身份的缺失,灰姑娘“不再是灰姑娘”了(50)。宽阔、奢华的宫殿实则狭窄、逼仄,梦想的实现限制了灰姑娘发挥想象的自由。所以她更喜欢以前的身份,因为生活更自由,还总能充满梦想。甚至在坏姐姐们面前,灰姑娘也感受到了爱:“我爱她们,她们对我冷酷无情又严厉。我爱上了不该受到的惩罚和恶言恶语,为的是愉快地微笑。这给与我无尽的满足,填满我漫长的白日,让我去跳跃,去观察,去思考,去梦想。这就是我为什么是一个梦想家的原因……”(53)
可是,王子毫不犹豫决定订婚。他不再是格林童话中的救世主,而是童话的执行者,他试图说服灰姑娘确信那不可避免的结局。灰姑娘坚持说:“一则更快乐的童话的本质就是有梦想,而在你身边我无法梦想。”(53)尽管如此,灰姑娘最后屈服了,她顺从王子并让自己的感觉与童话的必然性一致。有意思的是,灰姑娘在屈从的同时,对王子说:“为您服务,先生。”(55)显然,灰姑娘直到最后还试图保持着女佣的角色。在此,灰姑娘并没有获得拯救,而是被童话的形式俘获。
一反格林版《灰姑娘》中的人物形象,瓦尔泽笔下的灰姑娘让人耳目一新,她自信、聪明,充满求知欲,有自己的思想。她表述了做仆役、梦想和卑微是她的人生愿望,女佣的工作带来快乐,是梦想、思想和怀抱愿望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反,身为公主就没有前景(Hübner,1995:65)。显然,瓦尔泽所创造的灰姑娘形象置格林童话的意义于怀疑之中。灰姑娘、王子和两个姐姐远离了经典文本的故事情节,也远离了原有的人物设置。
1.2 《白雪公主》
一如他的灰姑娘,一开始出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的白雪公主就已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女孩了,完全不同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总是消极、被动、默默无语地听天由命。第一幕,王后、白雪公主、陌生的王子和猎人谈论过去的真相。白雪公主对继母和她之间的冲突以及格林童话中的故事一清二楚,她讽刺并直截了当地谴责继母。王后看似亲切并且想竭力忘掉过去和所有的罪孽,而白雪公主一想到过去的经历就悲伤哭泣、痛苦不安。猎人站在王后一边,他对白雪公主说,童话是谎言。王子坚定地赞同白雪公主的说法:王后一如既往地“没有母爱”(65)。如此这般,白雪公主不知真相何在。
第二幕,王子向白雪公主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同时他又朝三暮四、口是心非。王子亲眼看见王后和猎人之间的爱情场面,他心中燃起了爱的欲火,因此拒绝白雪公主的爱。显而易见,他毫无专注之心。原本应该是拯救者的王子在这里表现得如此软弱、不可靠。在此种情况下,无助的白雪公主再次尝试和母亲对话,并请求王子去寻找母亲。
第三幕与第一幕截然相反,白雪公主已经准备好忘记过去,她甚至想到童话是杜撰的、非真实的。可是此时,王后固执地坚信格林童话,还奇怪地责备白雪公主对真相的排斥。她打算将自己对女儿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白雪公主表示自己寄希望于母亲的信任,并表白自己对母亲的爱。在接下来的第四场中,王子向王后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慕之心,王后指责王子的花心,并提醒他,他对白雪公主的爱情是一种责任。她要求猎人和白雪公主表演格林童话中森林里的那场戏,在这场戏中,猎人按照王后的指令本该让白雪公主陷入困境。在此,正如格林童话一样,猎人对白雪公主没干任何坏事,王后却干预其中,命令猎人跳出格林童话中的角色,把女孩杀死。在这严峻的情况下,王子这次没有忘记他的救世主角色,他揭露了王后的阴谋,并匆忙前去帮助白雪公主。可最后,王后大笑着说这一切是一场游戏(86)。
在第五场中,白雪公主又经历了一次“无声的改变”(87)。她不能忘记童话故事,故事里母亲的仇恨让她生不如死。一想到这些,她就痛不欲生,所以她宁愿回到小矮人那里去。对白雪公主而言,小矮人所在地是一个理想国,那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那里“喜悦”和“快乐”常在,那里就像白雪一样纯静、安宁,那里爱让仇恨消失(88-89)。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梦想王国”(88),而不是像在如现在所处的世界里“鲜活的内心必定枯萎、死去”(88)。继母想方设法让女儿冷静下来,她把猎人叫过来,并要求他将一切向白雪公主说清楚。猎人一字一句地解释,童话故事就是人们编造的谎言。白雪公主内心对此充满了疑惑:“是的,而又不是。”(92)她请求猎人说点“新鲜的”,猎人回答说:“尽管开端尚未结束,但结尾以亲吻告终。”(98)很有可能,真相和谎言循环往复是一个圆圈,一如开端和结尾。剧终,白雪公主已疲于寻找真相,她无论如何都想将关于罪恶和过去的一切抛掷脑后。此时,王后重新提起罪责问题,白雪公主毫不客气打断说:“请你沉默吧,噢,闭嘴。童话仅是如此说说而已……”(103)—— 童话剧就此结束。
瓦尔泽《白雪公主》中的人物反反复复地探讨童话中真实的过去以寻找真相。真相和谎言、有罪和无罪之间的冲突推动着童话剧的情节发展。白雪公主不能摆脱格林童话中的过往,最后屈服,并以恭顺的姿态不仅尝试与继母和解,而且也接受过去及现在。当王后再次说出预示危险的话语时,白雪公主与猎人一样选择了沉默,因为似乎只能在沉默无语中稳定这表面上的和谐。白雪公主请求继母沉默,关于真相的争论也以此休止,矛盾最终似乎得以解决。在对话中经常出现的过去以及关于过去各不相同的表达方式并未从言语上有所定论,过去的一切是对是错不得而知。不同于格林童话故事的结局——王子和公主结婚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瓦尔泽的童话剧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剧终时,人物都转向沉默。如猎人所言,开端和结尾、真理和谎言沿袭循环往复的轨迹,所以关于她所处时刻的讨论也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那么就沉默吧。瑞士音乐家海因茨·霍林格(Hollinger, 2009)将瓦尔泽的童话剧《白雪公主》改写为一部歌剧。在歌剧的结尾,观众看到,舞台上幕布缓缓落下,那是一张白纸,被灯光从后面照射着,上面空空如也。如同瓦尔泽的童话剧,霍林格的歌剧也是一个开放的结局,音乐家恰如其分地阐释了瓦尔泽的童话。
瓦尔泽作品的互文性不容置疑。从形式上而言,人们可以将瓦尔泽的改写称作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解构或戏仿(Hübner ,1995:29)。瓦尔泽一直偏爱“渺小”,他喜欢在作品中塑造渺小的角色,也喜欢短小的文学形式,他一生的创作除了几部小说外,很多都是短小的散文、小品文等。“渺小”是“瓦尔泽的基本美学品格”(范捷平,2011:71)。如此而看,格林童话也契合了瓦尔泽游戏的乐趣。在文本游戏中瓦尔泽意欲解构语言和文学传统的固定模式,表述自己的怀疑。正是因为童话这种体裁的纯朴性、直线式的故事情节以及封闭性,童话才成了瓦尔泽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反思自我和现实的最佳文学形式。对童话这种短小文学体裁的改写使他获得更大的语言空间,从而满足他对世界可述性的需求。
在瓦尔泽看来,人们面对世界应该采取一个灵活的视角,才能描述世界并发现其中的秘密,因为现实是多变的,而用于描述现实的语言具有程式化的遮蔽性特征。瓦尔泽对童话的理解和改写目的在于否认不加思考的接受所有观念的有效性,并让人们意识到意义指派、产生的普遍过程。瓦尔泽通过提取著名的童话素材及童话元素,进行模仿,并且将其置入一个陌生化的关联之中。在这一模仿游戏里,瓦尔泽在想象与虚构中获取了新的象征符号,“先前文本的象征符号就能够成为后来文本的调节适应的组成部分”(伊瑟尔,2011:301),同时也揭示了普遍性的话语意义生成机制。与格林童话相比,瓦尔泽文本中白雪公主和王后之间的争执(寻找真相),灰姑娘对王子问题肯定或否定的犹豫回答,他另一部童话剧《睡美人》中睡美人被王子拯救后前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这种对立的姿态表现出人们无法对现实作出一个随时有效的、有约束力的解释(Hübner,1999:172)。在格林童话里,人物的角色是被分配的,在瓦尔泽的童话剧里,他放弃了这种被分配的角色。剧中,角色经常被调换位置,这明确地表现了现实的不稳定性。瓦尔泽笔下的人物不再是静止不变的角色,也不再是简单的童话人物,而是不断反思自我、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他们置疑被强加的、预设好的角色和故事情节,他们的身份特征是变动的,这一切都阻止一个固定的、连贯性的意义生成。
瓦尔泽颠覆式的改写是对原文本的解释并与之互动,他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对语言、对文学创作的反思融入到原文本之中,使解释变成再认识、再创造。瓦尔泽的灰姑娘虽认可童话的安排,却表示质疑,白雪公主愿意结束真理与谎言无休止的争论,但陷入沉默,睡美人最后因王子的一吻而定终身,但失去了这一形象浪漫的光环。瓦尔泽对格林童话文本的解释并未生成一个确定的意义,格林童话触发他继续提问,在游戏似的解释互动中他不断超越原文本的历史视界,而最后生成的文本又默许“无限多未言说的东西”(杜任之,1983:454)。就此而言,瓦尔泽的文本也让出一个读者/观众必须去填满的游戏空间。
2 游戏生存
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作家的幻想等同于儿童的游戏,作品就如同白日梦,是游戏的继续。作品非作家自己的创作而是对现成素材的再创造,作家的独立性则在于对素材的选取。而神话、传说和童话等民间故事隐藏着所有民族的心理结构,其中可寻找人们寄托愿望的幻想和人类祖先长期梦想的痕迹(弗洛伊德,2002:320)。这或许可以解释瓦尔泽为何选择童话作为文本游戏的对象。对于瓦尔泽而言,散步、幻想和写作是一体的,他生存于其中。在自己的想象活动中,在幻想的游戏里,他思考人生和现实,完成他对世界的认识。倘若将成人的幻想看作是儿童的游戏,那么作家凭借想象活动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用一种新的方法重新安排他那个世界的事物,来使自己得到满足。作家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弗洛伊德,2002:317)。
《灰姑娘》的主题契合瓦尔泽有关幸福的辩证法:一旦拥有,再无梦想 (Schilling,2007:18)。倘若考察瓦尔泽的生平,会发现这与他的生活有相似之处。瓦尔泽不能适应社会环境,不擅长与人相处,作为边缘小人物他为了生计也做过帮工、仆役等。他三本著名的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唐纳兄妹》《帮手》和《雅考伯·冯·贡滕》就是以主人翁与市民社会的不适应为主题,“小人物”也是他笔下常见的人物形象。在他看来,谦卑顺从和做仆役是一个特殊的立足点,它有可能开启另一番前景。为了自由地反思这个世界,他需要和社会保持距离,以此保留自己的自主性,他笔下的灰姑娘在两个姐姐面前不就是谦卑得异常固执?20世纪初,瓦尔泽生活在德国的文化、思想、政治中心柏林。在柏林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人们津津乐道尼采的权利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或者“超人”论都是中心概念。在人们夸夸其谈追求宏大、颂扬庆典式的权力和强权意志的氛围里,不融于主流的瓦尔泽萌生了卑微的想法。于是,做仆役是瓦尔泽作品中常见的惯用语,瓦尔泽提出了与尼采截然相反的“软弱意志”,在瓦尔泽看来,“做仆役实则是秘密的统领,是一种由下而上翻转的贵族统治”(Schilling,2007:46)。因此,这部舞台剧被视为解读瓦尔泽在其作品中坚定捍卫自己的理念——做仆役是幸福的——的关键性文本。
《白雪公主》以沉默告终。瓦尔泽尽管否定由语言确定的最终意义,但他终其一生都在找寻真理。在找寻真理的途中,这位漫游者一无所获。他于是远离人群、远离喧嚣的世界离群索居。由此出发,人们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瓦尔泽从1929年到1956年去世之前有23年都待在疗养院和精神病院,尽管并无他患有精神病的医学诊断。在那里,他有空间和时间思绪纷纷。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停止写作,沉默不语。可是作为漫游者,他总是在散步,在散步中幻想,直到在皑皑白雪中死去。
瓦尔泽《喜剧》的序言提到,他曾经遵从一位文学家的建议,放弃了依据森帕赫战役创作剧本的意图,而“宁愿创作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Mächler,1986:244)。灰姑娘做一个梦想家的心愿、白雪公主重回小矮人那里的渴望以及睡美人想沉睡不醒的愿望,或者瓦尔泽经常表露的对死亡的向往,这都是他退避、回归内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以便在他自己所描述的矛盾的世界里逃离一种彻底的自我异化。瓦尔泽童话剧的主题是“恐惧、生存恐惧、怀疑”(Unseld,1998:110),作品里表达的对生存的不安具有人类的普遍性,是“茫茫人流的漩涡中、大城市文明技术的、技术文明的大城市中,个体和孤独者的大主题”(Unseld,1998: 114)。瓦尔泽这个独来独往的我行我素者是如此看待自己的:“或许是不安、不确定以及对自己独特命运的预感促使我在俗务中拿起笔尝试表达我自己,不知是否成功。”(Unseld,1998:111)对于瓦尔泽而言,写作就是证明自我的方式,将自己内心的愿望付诸笔端。他将自己与荷尔德林相比,当他在精神病院生活了10年之后,关于荷尔德林,他写道:“……荷尔德林在他生命最后30年里根本没有像文学教授们描写的那么不幸。能够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自由梦想,而不必去满足没完没了的要求,这不是一种痛苦,只不过人们把它当作一种痛苦。”(Schilling,2007:144)如同荷尔德林一样,瓦尔泽远远地逃离这个世界。他需要和这个社会保持距离,然而这仅是“从这个位置上挪开”,以便他能“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谦卑——并非指手画脚——阐明人之生存那深不可测、苦难至极的裂痕”(Hollinger,2009)。针对瓦尔泽作品中那些人物形象,本雅明有如下论述:
(他们)疯了,因此而离开了一个令人分裂、如此非人性的而又不可逆转的浅薄。倘若人们想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他们身上令人喜悦而又令人不可名状的特质,那么可以这样说:他们所有人都被治愈了。可是我们从未了解这个治愈的过程,除非我们敢于尝试去解读《白雪公主》这部近代文学作品中最意味深长的作品之一,仅仅是《白雪公主》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位看似所有诗人中最贪玩的诗人是冷峻的弗兰茨·卡夫卡最喜欢的一位作家了。(Benjamin,1977)
在本雅明看来,瓦尔泽的人物疯了,不再在这个世界言说,而“治愈”在沉默中也许是可能的。在童话剧里,瓦尔泽颠覆了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念,但他并非代之以新的价值或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对瓦尔泽而言,互文的游戏既是否定原文本所要表现的意义,也是要否认固定意义的生成。20世纪初的瓦尔泽经历了自身戏剧梦的破灭、文学梦的不可实现——作品不被认可,他的文学价值在五六十年代才得到承认,为了生计他当过仆人、学徒等等。此时的欧洲也经历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和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瓦尔泽对自我、人生与世界产生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的多元化、多变性本身不能用固定的概念和体系来把握,个人由于历史和社会限制也不可能完全展现自我。因此,人没有能力把握整体的联系,人类每一次尝试认知现实的努力或许是突发奇想的游戏。由于现实的不可把握、意义的不确定性,人的认知也是瞬息的、点滴的,不可能是永恒的,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在瓦尔泽看来,人在如此困境中有了“基本的虚构需求”(Hübner,1999:184),通过虚构至少能形成表面的定位,因为虚构是“建立世界图式的创始性构想”(伊瑟尔,2011:5)。
在虚构中,瓦尔泽摆脱文化符号——童话及童话文本中的价值观念——的束缚,也表示了对世俗成功观念的质疑,所以灰姑娘对披上嫁衣成为王子新娘表示疑惑,甘愿当永远的仆人。这其实是瓦尔泽一再在作品中表述的观点:不成功具有更高的价值(Borchmeyer,1987: 131)。犹如他作品中的角色大多是失败的英雄或者是现代都市的无用人,瓦尔泽对所谓的成功持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否定主体观,即在失去所有世俗的成就感压迫之后方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范捷平,2011:193)。瓦尔泽同情失败者,反感所谓的英雄、胜利、宏大,反对主流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骄横以及高高在上的“文化”,这些主流的价值观念无视社会不适应者的思想、语言和内心世界。瓦尔泽自己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也是所有那些被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明社会所遗弃者的代言人。在他看来,主流社会的成功人士和统治者没有情感:在《睡美人》中,王子作为胜利者却是“陌生人”,神情凝固、呆板、冷漠,举止僵硬。
如此而看,瓦尔泽通过文学创作在虚构和幻想中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满足,在互文的游戏中挤压他在现实中隐匿的情感和思绪。这不仅仅是一种文本游戏,更是他生存的游戏。
3 美和自由的追求
瓦尔泽这位孤独的漫游者“总是在散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幻想、进行文学创作”(Unseld,1999:20)。散步、幻想和文学创作应当是瓦尔泽毕生存在的基本状态。
瓦尔泽对格林童话极富创造力的改编,与格林童话的互动对话是思考他自己、思考他人及世界的游戏空间。他穷其一生都在寻找真理,尽管他厌恶每一个最终的真理,厌恶语言的模式化;他寻找着安定,尽管作为一个漫游者他总是不安宁;他寻找着雪地里纯净的世界,在散步时殒命于皑皑白雪中,他终于在此找到了安定和最终的沉睡。于他——一如他在他第一部小说中描写诗人塞巴斯蒂安之死——这是 “美妙的安宁,在枞树枝下、在雪地里,如此躺着,一动不动”(Walser,1986:131)。瓦尔泽期望的是散步的时候在雪里死去,这是“幸福的死亡,倘若人能够直到最后一刻坚守住自己自身生命的结果”。这位漫游者走得离这个社会越来越远,直至和世界彻底决裂:“就这样我活着我自己的人生,在市民社会的边缘,这有什么不好吗?我的世界不也有权利存在,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更加可怜的、弱小的世界。”(Schilling,2007:144)
用世俗的观点看瓦尔泽其人,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没有令人称羡的职业和家庭,而后在精神病院终结余生,他的人生是失败的。可是,如上分析,他一再在文本中表述的观点、他所享受的心情宁静和最终获得的“美妙安宁”以及多年以后他的文学创作得到的认可,我们可以认为,他与这个世界的决裂不是一种逃避,而是“艺术家用艺术去克服困难”(席勒,2005:284-85)。如果说瓦尔泽在精神病院处于一种宁静的状态,在他乐意的散步中可以得到最后的安宁,这是一种幸福、自由的状态。而在这之前,他一直在通过文学创作从现实的藩篱中解脱、追求一种自由,现实的不完美以及他在现实中的挫败感导致他产生一种“内在驱动力”,即游戏的内在驱动力——“自由的至高无上的形式”(席勒,2005:8)。他由此构建了他的文学世界,即便是他在精神病院后来停止了文学创作,他也在钟爱的散步中展开想象的翅膀,仍然延续这种美学自由。由此,他的自我得以呈现。瓦尔泽在童话剧中表述了自己对成功、真理的质疑 ,也揭示了语言程式的遮蔽性,他在阅读格林童话文本获得的愉悦感或者审美的快感实则是自己判断力潜能的激活,因而促使他产生了文本游戏的需要(伊瑟尔,2011:323)。
瓦尔泽总是写一些“虚无、卑微、少数。但是,当他散步的时候,他先是如此的渺小,然后他敞开他的内心、越来越开怀地敞开他的内心,最后他几乎是一个宇宙”。瓦尔泽以此种方式与世界相遇、与自己相遇,追求美和自由,因为美“没有任何目的关系,没有任何预期的利益,美自身充满了一种自确定的特性而且洋溢着对自明性的喜悦与欢乐”(伽达默尔1991:21)。他呈现给读者的作品在表达他的幻想时以纯粹形式、美的享受或乐趣,使读者也感到愉悦(弗洛伊德,2002: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