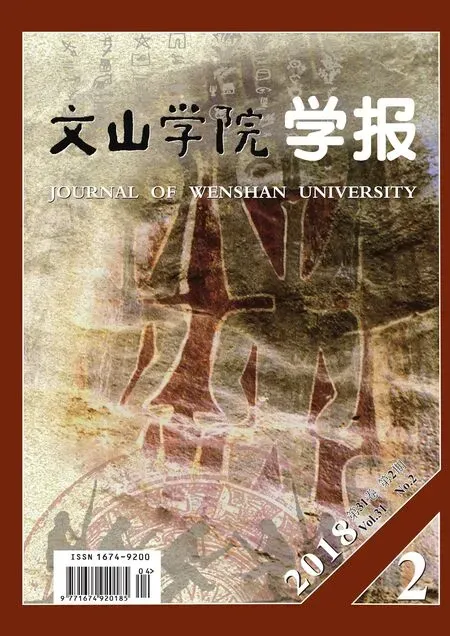刘绍棠运河文学中的政治与非政治状态下的写作
马琳娜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一、作家刘绍棠的生平
刘绍棠1936年出生在北京通州的儒林村,13岁开始发表作品,是5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神童作家”。刘绍棠是一个多产作家,在他近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27部中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其中仅有一篇是描写大学生的,其余全部是描写北方运河岸边的田园生活。在其描写田园风光和充满人物性情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运河之子”刘绍棠对故土的热爱和对家乡父老恩情的感激。刘绍棠出生的通州,就是那三千里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通州在府东45里……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
刘绍棠的成长经历跟“运河”有着深深的联系。他的父亲在北京的布店当学徒,像个文雅商人。刘绍棠是家里的长子且是个蒲柳人家的子弟。刘绍棠曾多次说过,在他有生之年曾有三十多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而且就是在他的家乡大运河两岸。他曾说:“我是一个土著作家,只能写些土气的作品。”他还说过:“我喜欢农村的大自然景色,我喜欢农村的泥土芬芳,我喜欢农村的宁静和空气清新,我更热爱对我情深义重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1]1他的作品表现了京东运河平原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向读者热情地展示了他的家乡——运河边上的乡风水色及人情百态。
二、政治背景下对传统美学的追求和政治解构
从刘绍棠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诚挚的情感,讴歌社会主义进步的人和事,虽然有些作品有概念化的弊病,在抒情写景时突然把改革政策和政治概念插入作品中,使得作品有概念化和突兀的感觉,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莲房村人》中一个外号姜够本儿的人,“自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天,他就没有守过本分。身为农家子弟却是个游手好闲的耍货”[2]。姜够本儿是倒卖西瓜的个体户,在文中确实对他的评价很低,“他是个体户”“走私贩子!”在文中利用政治意识形态来简单地评价一个人物是有偏颇的。刘绍棠的有些作品是政治运作下的产物,被很多批评家视为“某种政治表态”,因此对刘绍棠的作品分析仅仅停留在政治话语运作方式。这是一种对话语专制系统的批判和拒绝,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他不仅提供了政治立场而且提供了历史的立场”[3]。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种批评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单方面的流于贬斥,简单地对作家作品下结论,没有深入地分析文本中的意义和价值。福柯的“话语”概念就是被常常抽象化成一个功能结构或一种压迫和统治机制进行批判。福柯的权威形象成为批判者的“话语”庇护。在对刘绍棠小说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政治化的倾向中,有非政治化的运作,这就可以把他小说放在一个更复杂的视野和背景上来讨论,从另一个角度探究作家作品中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的看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刘绍棠的作品也具有时代的烙印,他的作品带有比较浓重的政治功利性,这种文化形式既区别于纯粹的传统文化,又有传统文化的影子。他的作品有别于“原生的民间文艺形式和意识形态”,但是作为文化产品又具有明显的“本土化”“大众化”的特点。这样的作品并非全部来自于农村生活,也受到国外作家如肖霍洛夫的现实主义影响。刘绍棠也认为艺术就应该来源于生活,忠实的表现生活。《虎头牌坊》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家力求还原最真实最有生命力的生活的作品。刘绍棠比较成功的作品中时代背景只是作为一个侧面,多数描绘的是在时代背景下“家乡的新人新事,家乡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写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的多情重义,写‘我的’家乡那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4]。在非政治下有政治性的运作,正因为有了非政治性的元素融入才能超越政治性的局限。但是非政治也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妥协。
(一)民间道德审美规范融入政治主题
例如在《蒲柳人家》中,作品政治化倾向只是作品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背景。文章开头描写了充满平静生活的一幕,何满子是个六岁可爱的小娃娃,因为贪玩爱撒野被爷爷用栓贼扣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何满子的奶奶一丈青大娘和她的老头子“何大学问”吵架,从大人们只言片语中何满子知道爷爷在口外有一个相好的年轻奶奶。爷爷平常不和奶奶顶嘴吵架,但是这次却理直气壮起来。何满子心里盘算着,他也想和爷爷去口外,觉得那个年轻的奶奶也一定会疼他,疼他的人越多越好。何满子被爷爷栓在葡萄立柱上觉得不自由,希望她的救星赶快到来。他的救星就是望日莲姑姑。邻居望日莲是个勤快善良的姑娘,跟何家关系密切,她是隔壁杜家的童养媳,经常带着何满子去河滩割草。她像疼爱自己的子侄一样疼爱何满子。作者把民间生活秩序的和谐理想首先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与这种和谐理想的场面相对的是杜家,杜家还没出场作者就从介绍望日莲开始着笔,从侧面描写杜家为人刻薄、心术不正。望日莲是杜家的童养媳,“可怜儿来到杜家,一年到头天蒙蒙亮就起,烧火做饭、提水、喂猪、纺纱、织布、挖野菜、打青柴”,从早忙到晚。但是“夜晚在月光下还要织席编篓子,一打盹儿就要挨她婆婆豆叶黄的笤帚疙瘩,身上常被拧的青一块紫一块”[5]。杜家还没出场,从对待望日莲就知道杜家代表民间秩序的破坏者,破坏民间的和谐秩序。杜家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平静生活的反动者,破坏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之后的出场中,杜家两口子各怀鬼胎,杜家的儿子被奉军抓伕一去不回头,何家想为望日莲出头另找婆家,但是花鞋杜四垂涎望日莲很久,一直想把儿媳妇望日莲占为己有,动起了乱伦的贼心。他老婆豆叶黄想利用望日莲当做招蜂引蝶的幌子。杜家在一开始的行为就是反民间秩序,乱伦、欺压童养媳、破坏望日莲和周檎的婚姻。杜家在成为政治敌人之前早就成为了民间伦理秩序的破坏者,是扰乱和谐的罪魁祸首。所以在下文的政治斗争中能激起对杜家人的憎恨。在刘绍棠随后的小说中出现了政治的因素也是把矛头指向杜家,民间秩序破坏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敌人。杜老四这个类型化的人物对民间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其延续机制进行破坏,是农村和谐秩序的破坏者,当成为政治的对立面时,更容易激发读者对他的憎恨。在最后的结局中杜四被制伏,因为给他撑腰的雷麻子已经溺毙身亡,这个村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周檎和望日莲结为夫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刘绍棠的作品中,政治力量不过是民间道德秩序及民间美学的外衣。在外衣的隐藏下作者发挥自己的长处描写贴近生活的人和事,才能更深地打动读者,激发读者对小说的情感共鸣。
(二)民间道德秩序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
在《蒲柳人家》中,一个以一个非政治性展开的故事在最后的结局中加上了一个政治性的结尾。杜四和雷麻子商量,自治政府警察厅下来一个十万火急的公文,悬赏缉拿京东共产党头子周文彬,赏金五百块大洋。他们为此打起了坏主意,却被墙外的何满子听到,回头告诉周檎这两个人想抓住周文彬,还要把周檎的心上人卖给董太师。周檎和村民布置好陷阱杀了雷麻子,又打消了狗头军师杜四的嚣张气焰,预示着新生力量的胜利和壮大。这样的模式代表了大众意识形态,也为新的政治力量做了宣传的作用。政治和文学两者相互渗透。类似的作品还有《瓜棚柳下》《地火》。
三、非政治化运作中的地域文学
“地域文学”,又称为“文学地域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文类。广义的地域文学即“带有异域风情的文学,这种文学往往被融进了具体地域的精神、风貌、人文气息”。狭义的“地域文学”具有多种解释。广义的“地域文学”与“地方色彩文学”容易混淆。那什么是“地域文学”与“地方色彩文学”呢?在《美国女性地域作家:1850—1910诺顿文选》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地方色彩文学的叙述者是外来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描写当地的人和事。而地域文学则是以平等的姿态从当地内部角度来描写,反映地方人文环境,目的是获得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地域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求地域文学作品的作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不可以是旅行家。对于地域文学中的本土作者和第二故乡作者而言,他们赖以寄存的是血浓于水的故乡记忆、情感记忆以及文化记忆,将这些记忆符号运用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增加地域特色。”[6]
刘绍棠正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扎根本土,人生的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后被打为“右派”时期都生活在他的家乡,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家乡的运河滩上发生的故事,用自己的创作回报故乡,把对故乡运河的爱凝聚笔端,运河犹如一个烙印深深地印在作者的心里。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二十世纪的家乡人文风俗。当然刘绍棠的创作受到了个人人生经验的影响,刚刚从农村出来到北京没多久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回到家乡。刚刚成为了一个城市文人,因为政治的原因又重回到地方,使他重新收集和创作。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紧密接触促进了地域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换和转型。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刘绍棠描绘农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地域文化是他小说的突出特点。同时,浓厚的地域范围、方言俚语、乡土气息现在读来也不失其色彩和原味。
四、刘绍棠地域文学在作品中的体现
刘绍棠的小说喜欢在政治生活外衣下描写大运河如画的风景,邻里之间和谐共处的生活,充满了童趣和理想,作品散发着清新明朗乐观的风格。刘绍棠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喜欢听书,大学期间还曾逃课去听书,对传统的艺术有很浓厚的兴趣。他曾回忆到“事过半个多世纪,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一个头上脚下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嘴里啃着黑紫色的窝头追在说书人身后,跟唱听书”[1]49。他对家乡父老一直怀揣着最真挚的热情,热情地去讴歌家乡的人和事,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刘绍棠的整个童年在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中长大,从小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受到父老乡亲的关爱。刘绍棠4岁那年,北运河闹土匪,有一回土匪三更半夜进村绑票,全家逃散,还是一名叫大脚李二的大伯爬墙上房,下到院里走进屋去,带他脱离险境。5岁那年因为他贪玩偷偷溜出门外捉鸟,一脚踏空,掉进水里,失去知觉,幸亏老叔正在放牛看到了他,才得以不死。6岁时他在田间追野兔摔倒后被茬子扎伤喉咙,是一位姓赵的老爷子给他急救。7岁那年他得了痈疽,一位姓田的老爷子找来偏方妙手回春。刘绍棠经历了1957年和十年内乱两次厄运,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作家那样把两段生活反映出来,但是他从小经历过土匪抢劫和日本侵略华北平原的动荡生活,是同共产党一起成长起来的忠诚党员,他坚信用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贴近人民最真实的生活和思想来描写亲爱的故乡大运河。他笔下的故乡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一)和谐理想的运河景致和田园风光
刘绍棠对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怀,这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在作家笔下的运河是这样的,“一出北京城圈儿,直到四十里外的北运河”“北运河一出北京的通县县境,到河北省的香河县串了个门儿,拐个弯进去天津市的武清县,却又从河北省的安次县擦身而过,一条河把三个省市的四个县栓在了一堆儿。跟北运河并肩而行的是京津公路,水旱两路像亲哥俩”“通县自古就是京东首邑,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7]。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的故乡是带着自豪和欣赏,作为“运河之子”,大部分都在写大运河,从地理环境和其历史意义来讲述这片故土。“大运河”这片土地上包含着自然地理文化和社会环境文化两种,自然地理文化是指地理位置、地形特征以及气候等因素在与人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化的自然;社会环境文化包括民族、民风、政治经济等人在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种种精神和物质的成果。“大运河”对作者的影响是多方位的,而且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环境,也是逐渐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所以刘绍棠小说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生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渗透着作者的热爱之情,这样的运河养育了一群民风淳朴的人。“十八里运河滩,像一张碧水荷叶;荷叶上闪烁一颗晶莹的露珠,那边是名叫柳巷的小小村落……村外河边一片瓜园……瓜园里,坐北朝南,柳梢青和女儿柳叶眉埋下八根柳桩立柱离地三尺支起两件瓜棚,也叫瓜楼。”在这样充满乡村田园的景致中有一个瓜农柳梢青,“早已人过四十天过午,年交五十知天命了。瘦骨嶙峋的大高个儿,大步流星的两条鹭鸶长腿,刻满深深皱纹的瓦刀脸……”他会种瓜还会武艺,“十岁那年也是在巴掌大的瓜园里,他爬上一棵老龙腰河柳。运河上,客运和货运大船,高高的桅杆扯满了白帆,好似行云流水”[8]。这里把大运河的景色和柳梢青这个人物融入其中,把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相结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和谐温馨的田园景色。
(二)农耕文明和牧歌生活的抒写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据了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曾长期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这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有所变化,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并没有大的改变,加之现代意义的城市在二十世纪初才刚刚诞生,因此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乡土文化之上的,具有较强的乡土性。乡土性的社会结构和乡土性的文化心理,造就了许多人尤其是远离故园乡土的人们的特有的乡土情结,作家也概不例外。”[9]刘绍棠在病重之时还想回到家乡的土地上进入小说里描写的许多情景中。他在病重时更加怀念故乡,他是故乡的崇拜者,想念自己的父老乡亲。二十年来在运河滩上,跟父老乡亲一起土里刨食,后来少年得意一帆风顺的到北京读了大学成为城里人,虽然也会下乡体验生活,但是就像作者说的“不过是水上的浮萍菜汤里的油”。刘绍棠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Antaeus)只有贴近大地才能获取源源不断的力量。对作家而言,运河滩就是创作的源泉。在作家看来,体验生活和真正的融入生活两者的感受有很大不同。只有真正的融入才能描写出更感人的作品。所以在五七年又重新回到运河,家乡父老对他的爱护,成年后更能深刻体会周围的生活。对刘绍棠而言,那段时期的岁月坎坷与他个人的得失相比,是得大于失的。他认为“在农民身上,尽管存在着小生产者的种种缺点,但是更具有劳动人民的纯朴美德,保持着我们伟大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又因为“在我遭遇坎坷的漫长岁月中,家乡的农民不但对我不加白眼,而且尽心尽力地给以爱护和救助;人人在劫难逃的十年,我独逍遥网外,并且写出了作品”。在《瓜棚柳巷》中柳梢青和女儿柳叶眉在十八里运河滩的柳巷村外的河边有自己的一片瓜园,父女俩相依为命住在瓜棚里,别看是个小瓜棚,后窗外垂柳依依,挂起一幅飘动的柳帘。瓜棚下有青柴,灶台轻烟渺渺,锅台上摆放着红土瓦盆、猫耳绿罐、青葫芦瓜瓢、蓝花饭碗、大肚儿盐缸……这样宁静的田园生活虽然清苦却充满了温馨的氛围,一片片的绿色映入读者的眼里和心里,清新明朗的空气在蔓延,是牧歌似的生活和理想。柳梢青是个种瓜的好手,每到栽瓜点豆时节他的瓜园充满了扑鼻的香气。刘绍棠善于写传奇故事,也带有牧歌色彩,结局都是充满着理想和希望。
(三)熟练优美的乡间俚语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刘绍棠在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乡间景物的同时,更注重家乡俚语的运用。他不但在人物对话上使用农民口语,而且在叙事上也尽量使用地方口语,使作品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的语言、生动活泼的人物性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克服了同类小说常见的语言分裂。在刘绍棠的作品中运用地域性的乡间俚语并不是像《暴风骤雨》那样仅仅是描写农民时才用,这样只是在形式上的模仿,其他的叙述仍然是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而刘绍棠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描写的是最熟悉的家乡,所以对方言俚语比较熟悉,在其他叙述时也尽量用地方的语言去描绘,不会让作品整体有割裂的感觉。这点对于刘绍棠也并非难事,他前后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年,自幼习惯讲方言土语,有深深的恋乡情结。民族和地域的因素对于作家的写作自然紧密相联。作家在创作时,依然与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保持着近距离的关系。这正是作家刘绍棠具有的地域优势,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位置形成了与周围事物的反差,在反差中得到新的认同和接纳就需要寻求一个共同的环境,那就是刘绍棠笔下的政治环境引入小说创作。这样就具备了广泛的传播与推广。他对家乡的土语和乡间俚语具有高度的认同和接纳,认为是“最生动活泼,富有诗情画意。农民口语的最大特点一个是具体,一个是形象。使人看得见摸得着”[10]。在《荇水荷风》中,形容爷爷耳聋严重,“炒豆子似的连天响也不眨一眨眼”。形容刚正不阿的人是“桑木扁担宁折不弯”。在《瓜棚柳巷》中形容花三春尖叫是“猫爪了似的尖叫,凤凰落地不如鸡”,语言形象生动活泼,可以想到花三春是个烈火心性,刁蛮不吃亏的泼辣女人。这样的语言在刘绍棠小说中举不胜数。这些口语具有突出的地方色彩,具体生动活泼,运用自如,不露痕迹。在对具有地域特点的乡间俚语的吸收过程中,刘绍棠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民间乡间土语有着藏污纳垢的特点,但是作家摒除糟粕对其进行古典的改造,才使得作品具备更多的美学特征。
刘绍棠在文学创作中的政治与非政治状态中,并没有因为政治性掩盖了他的作品,相反在非政治中加入了地域性的因素,使得作品具有超越性、大众性、民间审美性。
[1] 刘绍棠.我是刘绍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 刘绍棠.莲房村人[A]//刘绍棠中篇小说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267.
[3]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M]//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1.
[4] 刘绍棠.蒲柳人家二三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98.
[5] 刘绍棠.蒲柳人家[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
[6] 姚斌洁.地域文学的审美审视与反思[J].沈阳: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6(1):80-84.
[7] 刘绍棠.京门脸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39.
[8] 刘绍棠.瓜棚柳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3.
[9]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29.
[10]刘绍棠.乡土文学四十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