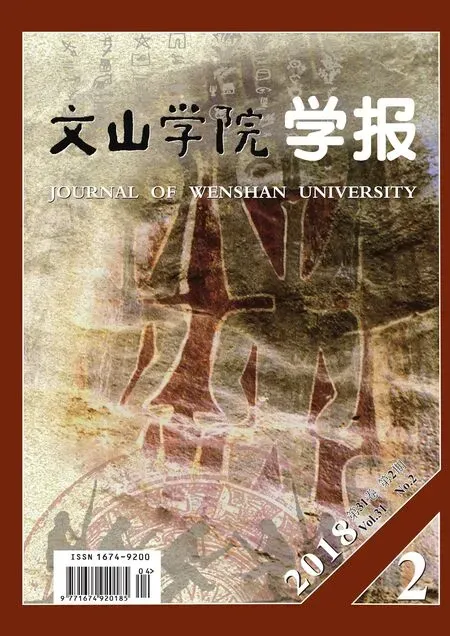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对云南乡村社会信仰影响探析
何廷明 ,崔广义
(1.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663099;2.文山学院 滇东南区域经济社会研究所,云南 文山663099;3.衡水第二中学,河北 衡水053000)
民国时期,云南自然灾害频发。据统计,1912-1949年间,云南共发生旱、涝、雹、疫、霜、雪、冷、虫、震及其他灾害共计2740县次;发生死亡人数在一万人以上的特大灾害6次,平均6年一次,其中1923-1925年滇东的冻灾导致死亡人数达30余万人[1]。如此频繁且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云南农村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打击是巨大的,以致遭灾期间迷信盛行,灾民信仰发生偏移。
一、民国时期,云南乡村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
民国时期,云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加上国家赋税繁重,农民整日辛勤劳作,所剩无几,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便衣食无着,陷于饥馑,生产停滞,回天乏力,灾民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乡村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李文海先生指出:“愈是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方,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愈弱,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支配力愈强。”“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有有效的防灾抗灾能力,一遇水旱或其它自然灾害,只好听天由命,束手待毙。”[2]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导致农村耕地大面积荒废,粮价飞涨,民力丧尽,农村经济恢复困难,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自然灾害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于人类来说却是无情的灾难。灾害造成民众对自然的极度恐惧心理,在人们心中留下阴影。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长期恐惧心理,使灾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减弱。灾荒越是频繁严重,人们求生存的心情就越急切。遭灾的乡村,灾民生存无望,人心惶惶,饥饿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而此时,迷信则可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于是,灾害频发,迷信活动盛行。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农业就是农民生存的命根,而灾害却是农业的威胁。民国时期,云南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侵害着乡村民众的心灵,他们抗灾、救灾无望,自然转向求助神灵,企图借助信仰禳灾祈福,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迷信因此盛行。因灾而起的迷信活动对民众带有极强的心理麻醉作用,因为“灾是农业的威胁,对此除了祈祷烧香,立庙供奉之外,农民们并没有积极控制的方法”[3]。灾害往往被看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就只好求助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天神”了。
二、民国时期,云南乡村民众为多神信仰
民国时期多发的自然灾害进一步巩固了云南乡村中由来已久的“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在远古时期,人们刚从蒙昧中进化出来,就开始了对自己处境的思考。由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低,因此根本无法抵御大自然的侵袭,一次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恐惧。列宁指出“恐惧创造神”,可谓一针见血。当人们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无可奈何的时候,大自然便成为人类最原始的崇拜对象。但是另一个独特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由自发性的宗教过渡到人为宗教并最终进化至一神宗教时,中国的宗教却固滞在以自然崇拜为主题的多神体系之中。”[4]133一直到民国时期,云南乡村中的自然崇拜仍然没有消亡的迹象。这里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探讨,但是既然是自然崇拜,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求。也就是说,严酷多灾的自然环境为自然崇拜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其实这也说明了民国时期云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小,无法在心理上给自己一个利用自然的信心。
民国时期,在云南农村,家家供奉各种天神,每于年节朔望之日,大批量购置香烛纸箔,以祭祀焚烧的形式,咒告天神,请求降福消灾,因之农家祀神祭祖的消费占农家支出的相当一部分[5]。各家供奉的神灵不尽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家庭都在自己家的堂屋内供奉一块“天地祖宗”或者“天地君亲师”[6]的牌位。到了民国时期,“君”已经不存在了,有的百姓将其改为“天地国亲师”,但无论如何变换,各家各户供奉的“天”的概念是不会变的。“天”在这里被赋予了上帝的意味,具有无穷的神力,掌管着世间的一切,但是又不等同于一神宗教中的神,因为人们对“天”的供奉仅仅来源于欲借“天”的神力消灾解难,祈求平安。“天”在农业社会与人的关系最为直接,风、雨、雷、电、日、月、星、辰,一切可以带给人类灾难的天气灾害都与天有关系,一切可以保证农业收入的因素也基本来自于天。“天”成为被自然灾害阴影笼罩下的云南乡村供奉的第一神灵。
民国时期,民间信仰仍然是多神体系,人们在对“天”顶礼膜拜的时候,又不忘记将其他神灵纳入自己的礼拜范畴。因为农耕民族从种到收,无时无刻不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于是人们又想象出各种各样掌管各种自然灾害的神灵。凭着千百年来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经验积累、应用,人们在某种灾害盛行的时令,就会自觉地对掌管这种灾害的神灵进行祭祀。昆明官渡的彝族同胞,一年内祭祀的对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主要神灵有:“大帝天尊万方主师”,该神是人修行而成能止淫雨,使普天下阳光和照;“元始天尊”,撒梅人每次祭祀都要请该神光临;“土主”,能在辖区内呼风唤雨;“地母”,决定土地的肥瘠,管理平坝区的土地,也保护妇女;“五谷神”,专管五谷的生长。[7]38-39文山地区的壮族信仰有土地、山神、龙王、牛王、灶君、太阳、虫灵、鸭神等等;彝族祭祀,正月祭山神,二月祭龙王,三月祭苍天,四月祭猪王,五月祭田公地母,六月祭太阳,七月祭祖先,八月祭庄稼,九月祭小米,十月祭牛王,冬月祭土地[8]。
三、自然灾害与云南乡村民众信仰的特点
祈福禳灾的迷信活动往往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通常,水灾祭拜龙王,旱灾跪求雨神,这反映了遭灾乡村民众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寻求精神慰藉,而迷信正好给了他们一剂良药。民国时期,云南最为频繁、对农民收入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当属水涝、旱灾,因此,祭祀掌管水旱的龙王在民间的宗教祭祀中十分盛行。在查阅云南方志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滇东所有的地区都把二月二祭祀白龙神看做宗教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人们普遍认为,龙王主雨,雨神就是龙王。龙王是行云布雨的雨神,人们通过祭祀龙王来求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昆明西山,立夏之时,龙潭乡大河和小村的白族要在龙王庙和水塘处祭龙,祭完龙王才能开塘水灌田[9]124。文山的马关县,“三月辰日,官绅士民共往大龙潭祭龙,为祷雨祈年也,亦甚灵异。是日,虽不大雨,亦必稍见飞洒,以显感应。”[10]祭龙成为该地区长期以来的习俗。每年的祭龙日,各地村民都要停止田间劳作,举行各种祭拜龙王的祈雨活动,以求一年风调雨顺。发生水灾时,村民则会去河边烧香、烧纸,献饭、献刀头、献鸡,祈求河神消除水灾。楚雄的大姚县群祀祠中有观井龙祠、旧井龙祠、乔井龙祠、黑井龙祠、尾井龙祠。各井龙祠边有对应的井神台[11]。谢彬在云南游记中记载:“夷人最信仰者为龙树。龙树云者,树下需有泉水,足供全村居民之饮料,干需古大,枝叶需繁茂,由全村公认之所,群至树前烧香求福”[12]。红河的绿春县哈尼族的祭龙祭词更是直接告诉我们祭祀龙神的目的:“今日我们这样虔诚地来祭你,来日你一定得给我们灭掉灾虫兽害,得给我们消灾解难,永保平安。”[13]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祷告通达神灵,以借助神灵的力量,达到消灾降福的目的。
民国时期,民众对自然灾害无法抵御,又缺乏科学的认识能力,总认为是自然界的神灵鬼怪在危害人间。云南乡村盛行的“巫术”在灾害发生后迎合民众解救灾难的心理需求,对民众的信仰产生着极大的导引作用。当自然灾害发生之时,人们总是祈盼有超自然的人或神为人类消灾弥祸,希望借助巫术祈求神灵消灾除害。“巫术是企图借助于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是人类试图控制自然力并拔除不祥的一种手段。”[14]长期以来,巫术在民间尤其是在乡村对人们的生活有较深远的影响。巫术虽然是鬼神崇拜、祈神许愿的迷信活动,尤其是巫师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口中念念有词,对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但巫术“对于稳定灾区民众的情绪,从精神上寻求支持战胜灾害的力量,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至少在心理上会使灾民们得到某些安慰与希望”[15]。人们对巫师有敬畏之情,以致即使被骗也心怀虔诚。
四、自然灾害对云南乡村民众信仰的影响
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民间信仰的影响较为显著。民国时期,由于防灾抗灾手段十分落后,民众只能将求生的希望寄托于民间塑造的诸神,修庙建宇,塑立了许多神像,以适应人们祈求消灾的种种需要。于是,民间建庙现象十分普遍,村村寨寨皆有供奉各种神像的庙宇,如土地庙、山神庙、王母娘娘庙等等,每逢年节,善男信女前往庙宇跪拜烧香祈求者络绎不绝。因为自然灾害的打击面比较广泛,它不单独对一家一户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这种神灵的祭祀并不是一家一户的个体行为,而是整个村寨或几个村寨一起进行,俗称“做会”。玉溪的江川县民间有做青苗会的习俗,“农历六月间,挂功德,选一个属‘龙’日,做青苗会1-2天,念经祈祷,这时正值田中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时期”[16]。官渡的农业祭祀,撒梅人称之为过会。“天光会祭天光谷神,土主会旨在求土主保佑今后风调雨顺,庄稼长好,牛马健壮。主师会求主师保佑当地风调雨顺,牛马不遭疫。五谷会也兼祭主师、地母、土主,以求明年五谷丰登。‘牛马猪王会’保护牲畜。三皇会保佑万物生长丰茂,来年丰收。重阳会再祭五谷神及主师、地母。十月十八日‘地母会’,求其保佑土地肥沃,避免地震、水灾。”[7]45-47在昆明西山阴历六月初六,白族以村为单位集体在五谷祠祭祀“青苗太子”,“该地白族皆建有五谷庙,有者一村一庙,有者数村一庙。”[9]124这种集体行为是在恐惧灾荒的心理作用下形成的,同时它又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心理。仔细分析,这些祭祀基本上都是和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从事某种农业生产之前开始进行祭祀,以求平安。如撒梅人正月十五“天光会”后紧接着惊蛰,便开始一年的耕种工作。二月十九“土主会”后正当清明前后,昆明附近农村正开始准备种红薯、玉米。三月三的“三皇会”后紧接着谷雨,开始育秧。三月十五“五谷会”后几天就是立夏,开始了紧张的插秧、抢收夏粮的农忙工作。六月以后农忙告一段落,人们开始修理工具,以备秋收秋种,于是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举行“牛马猪王会”,待九月“重阳会”后,又开始了紧张的秋收[7]44。而在宜良地区“关岭西行途中见到稻田里插有许多小白纸的旗,后来向人询问,方知这是秧苗神旗,用以保护秧苗,使秧苗不受灾、不生虫,可获丰收。凡稻田里插旗的人,都是在秧苗会”[17]。这不是一种灾荒到来之时的自发行为,而是在心理上的自觉行为。不管耕作之后是否会发生自然灾害,为求风调雨顺,希冀粮食丰收,民间对掌管灾害的神灵的祭祀却是永不间断的。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僻远的乡村,沿袭祭龙祈雨的习俗,遇天旱之年,祈雨活动更甚。届时,人们暂停一切农活,以村寨为单位,由村寨内德高望重之人召集,杀猪宰羊,请巫师念经做法,举行祭拜仪式,祭龙、祭龙树、祭龙潭等,焚香烧纸,虔诚祷告,祈雨祈丰年,延时2~3天,仍未能完全摆脱迷信禳灾的旧习。以减轻灾害为目的的鬼神崇拜、巫术等各种迷信活动渗入到一般民众的生活中,影响到部分民俗、节日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民国建立之后,现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取代专制王朝的中华民国也开始破除迷信的努力,下令废除了大量的庙宇和祭礼。但是对这种努力的认同只存在于知识分子和高层中间,神怪塑像的消失并不能驱走乡村农民头脑中掌握自然灾害的神灵。相反,几乎每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会激起一波或大或小的拜神求巫的迷信潮。首先,民间平常的宗教祭祀会在灾荒到来的时候举行临时的祭祀。官渡洞经会例会,在各神诞辰日举办,有祈禳消灾会,于地震、雷雨、瘟疫流行成灾时举办[18]。而更大的问题是,每当灾难来临,就会出现一些巫婆神汉,打着“与民消灾”的旗号,散布谣言,骗取钱财。受灾民众因为恐惧的心理作怪,也容易接受这样的宣传。盐丰县三台区连年天旱,瘟疫流行,当时就流传着加入白莲教可以消灾解难的传言[19]。而大关县“河东乡天星场民妇,乘地震之余,自称地母娘娘。化水持咒,诈取民财”[20]。
本来人们信仰神灵、定期祭祀,其最终目的不外乎希望五谷丰登、百畜兴旺,“结果当他们把移山镇海、呼风唤雨、救劫免灾等种种自然社会功能赋予了各自心目中的鬼神之时,又被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窒息了其自身开拓进取的精神和与自然抗争的信心,人类在现实和虚幻的双重枷锁的挤压下萎缩了。”[4]135
在灾害的打击下,灾民情绪低落甚至丧失继续生存的信心和勇气的消极社会心理及他们那种“听天由命”的迷信心理占据主导。而且灾害越重,对乡村民众的打击越烈,而祈神的方式也愈加多样繁琐,表达了人们想摆脱灾害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说明了灾民祈神禳灾的心态也愈加根深蒂固。灾害的确给灾民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当时社会的衰败,无助的灾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这种消极的御灾方式。
民国时期,由于云南乡村民众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他们把自然灾害看作是各路神仙对人类不规范行为的惩罚,因此在生活中产生了很多约束人们行为的禁忌,使人们敬畏于神的惩罚。这些禁忌的传承,又规范了人们保护自然的行为。
[1] 何廷明,崔广义.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云南乡村社会冲突[J].文山学院学报,2017(4):34-37,80.
[2] 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J].近代史研究,1990(5):4-25.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1.
[4]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王心波.云南五省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2辑)[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中文资料中心,1977:26596.
[6] 林泉.重返老昆明(上册)[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268.
[7] 邓立木,赵永勤.官渡区阿拉乡彝族宗教调查.云南省编辑组编.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六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88.
[9] 宋恩常.昆明市西山区龙潭和沙朗白族农业节庆和宗教信仰资料.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何廷明,娄自昌.民国《马关县志》校注[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55.
[11]郭燮熙.民国盐丰县志.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170.
[12]谢彬.云南游记.沈云龙.近代史料丛刊初编(册九十)[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272.
[13]罗书文,罗理诚.哈尼族祭龙的祭祠.政协绿春县委员会编.绿春县文史资料选辑(一)[Z].内部发行,1997:69.
[14]王芙蓉.论两晋自然灾害与信仰意识[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6(4):83-86.
[15]孙湘云.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与中国古代救灾措施[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38-43.
[16]云南省江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川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660.
[17]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55.
[18]周亮,周开德.官渡古镇的洞经会.政协官渡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昆明市官渡区文史资料选辑(二)[Z].内部印行,1989:155.
[19]李兴口述,杨恩美整理.普光彩降生闹事.李道生.云南社会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42.
[20]张铭琛.大关县志.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昭通旧志汇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