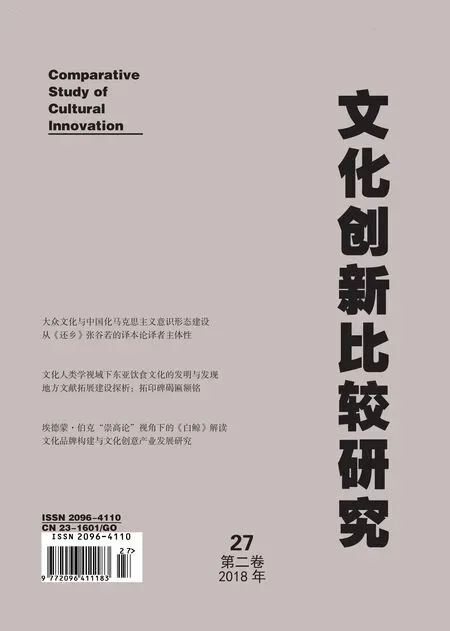埃德蒙·伯克“崇高论”视角下的《白鲸》解读
吴越萌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埃德蒙·伯克认为,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情感,也即痛苦与恐惧。“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这是从整体层面上来看崇高的来源,引发崇高感的直接原因则具有恐怖、模糊、力量、巨大、困难等特质,甚至包括特定的色彩、声音和节奏。在埃德蒙·伯克“崇高论”的视角下,《白鲸》中的崇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不可战胜的自然伟力、挑战认知的非理性内容、主人公偏执而顽强的抗争。
1 不可战胜的自然伟力
在故事正文开始前,梅尔维尔摘录了书中从古至今有关鲸鱼的记录。在这些资料中,鲸鱼似乎与三个关键词紧密相连:巨大,力量,未知。它的嘴里是一片混沌,肚子是个无底洞,体型之巨大超出凡人的臆测,而其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伴随着“鲸鱼”一词而来的是死亡,它无与伦比的伟力击碎了无数梦想发财的捕鲸船,“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无论是鲸鱼巨大的体型,还是它惊天的力量,都足以唤起人们心中恐怖的情感,更何况鲸鱼这一神秘存在介于传说与现实之间,人们对它所知甚微,只能凭想象和猜测来勾画它的魅影。而莫比·迪克是鲸鱼这一族类中异乎寻常的存在,它是一头及其狡猾凶狠的抹香鲸,有关它的传言在广阔的水域上传播,并最终赋予了莫比·迪克“与人们所目击的任何事物毫无关涉的新的恐怖因素”。伯克认为,如果引起痛苦和危险的原因直接作用在我们身上,就会引发实际的痛苦,如果我们只是受到痛苦和危险的观念的影响而非身处其中,就会产生所谓的“崇高感”。鲸鱼的巨大、力量与未知,正好构成了引发读者崇高感受的要素。
如果对鲸鱼做进一步的延伸,其巨大、力量与未知恰恰象征了不可战胜的自然伟力。《白鲸》所讲述的故事不逊于一场战争,战争双方和战场的选择体现了赫尔曼·梅尔维尔心中的宏愿:“必须挑选一个巨大的主题。”战争双方是人类和鲸鱼,前者是万物灵长、理性的象征,后者是造物奇迹、力量的化身,而他们之间的战争,就在天地间最为宽广的海洋上拉开了序幕。埃德蒙·伯克说,“海洋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物”,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对于鲸鱼而言,海洋是它们熟悉的领地,对于生长于陆地的人类来说,那风急浪高的海洋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一个浪头、一阵疾风就会威胁他们脆弱的生命。与其说《白鲸》讲述的是人类轰轰烈烈的捕鲸行动,不如说它象征着渺小的人类如何在汪洋大海上挣扎求生,如何带着莫名的愤怒向压迫着他们的自然发起了总攻。根据伯克的崇高论,“对力量的胆怯是如此自然,而它又是如此强烈地存在于我们心中,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克服这种恐惧感,而只能通过转移注意力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中,或者以最大的暴力行为来反抗这种自然安排”。“披谷德号”上的捕鲸人选择了后者作为对力量和恐惧的回答。这种暴力的倾向似乎与理性相悖离,并且具有传染性,当埃哈伯鼓动全体船员追猎莫比·迪克,水手们都被仇恨的情绪所感染,以实玛利的内心描写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我跟着他们一块叫喊,我的誓言已经同他们的融合在一起;因为我内心的恐惧,我叫喊得越响,我的誓言越是板上钉钉,定而不移。我心里有一种野性的神秘的同情的感觉,埃哈伯的那种万难抑制的仇恨似乎就是我的仇恨。”
《白鲸》中的自然景物描写和埃哈伯的内心活动反映了人与自然从和谐走向对立的过程。小说的前半部分多次出现精彩的环境描写,其基调是明朗、轻快、充斥着喜悦与赞美的。明媚的春光、晴朗的天气明显地作用于水手的情绪:“那些凉爽中有暖意,晴朗,空气中响着银铃飘着香味,丰满殷足的日子就如一只只盛着波斯美酒的水晶杯,堆积起香水凝成的雪——又将雪碎成片片。”伯克认为,面对一种极大的力量,我们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征服,而是惟恐它被用来掠夺和破坏。但当人身处一种极大的力量的包围中而不自知时,也即“披谷德号”船员面对自然的伟力而不自知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船长埃哈伯率先打破了这种和谐。他坦白说:“以往,日出东方会激励我上进,夕阳西下则令我感到镇静。如今再也不是这样。”白鲸、海洋和自然似乎成为了某种“全身力大无穷,还有不可思议的歹毒心肠支撑着”的东西——一种不知来源的恶意的象征,于是他把矛头指向了自然。“披谷德号”的船员们则屈从于埃哈伯的威压与煽动,稀里糊涂、不明所以地与自然决裂了。从这时起,成为“敌人”的自然逐渐展现出骇人的面目,它所带来的威胁不仅不可战胜,并且常常是致命的。
赫尔曼·梅尔维尔以其超凡的笔力描绘了多处雄浑壮观的捕鲸场面,其中最为震撼的就是“披谷德号”与白鲸莫比·迪克的决战。气得发狂的埃哈伯赤手空拳地抓住了莫比·迪克的颚骨,想把它拧下来,而莫比·迪克“恶毒地尽情戏弄着这艘大限将到的艇子”,把船长乘坐的小艇咬成了两截。在这海洋领主的面前,在大自然不可抵挡的威力面前,人的脆弱表露无遗,侥幸逃生的埃哈伯“两眼充血,失去了视觉,脸上的皱纹里结着雪白的盐花……”,“有一段时间,他躺在斯德布的艇子底板上动弹不得,像一个遭了象群践踏过的人。他发出一种莫名其妙地仿佛来自远方的哀哭声,一种像是从谷地里传出来的凄惨的声音。”这场斗争中悬殊的力量对比令人不寒而栗,人终于为其敢于挑战自然的狂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海洋如同尸布一样收殓了他们卑微的肉体,他们如同“一个忿忿不平的白浪一头撞在它的峭壁上,终于大败而归”。
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的第一部分中说:“痛苦、疾病和死亡让人们心怀恐怖感,生命和健康虽然也能使我们获得愉悦感受,却无法给我们如此强烈的印象。”《白鲸》中灼烧的痛苦、惨淡的失败和壮烈的死亡带给读者恐怖的阅读体验,并从这种带有距离的恐怖中产生了崇高感。
2 《白鲸》中的非理性内容
梅尔维尔的《白鲸》与霍桑的《红字》几乎同时出现在美国文坛上,二者都带有那个时代的超验主义色彩。劳伦斯在评论《白鲸》时说,正是这种超验的深奥使整本书美不胜收。《白鲸》中的一些内容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不仅是超自然现象,还包括一系列的预言、暗示和直觉。伯克说:“崇高不是通过理性分析产生的,它通过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们席卷而去,使我们根本来不及进行理性分析。”崇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背离理性的,它本身就是阅读接受过程中激情的产物。《白鲸》中的非理性内容也是引发崇高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说开篇就将鲸鱼置于神秘主义的范围内,其后对莫比·迪克的描写更是如此。“莫比·迪克”这一章收录了各种闪烁其词又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有人认为莫比·迪克无所不在,它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在相反的两个纬度为不同的人遭遇;有人说莫比·迪克长生不死,它受伤后喷出的血液仅是苦肉计和障眼法。同时,小说中的莫比·迪克又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圣经》的记载中,鲸鱼是上帝命令吞下约拿的使徒,因而莫比·迪克也就不再作为单纯的鲸鱼而存在,它成为了上帝惩罚的象征,背负了独特的宗教意义,它带给人们的恐怖也就不止于鲸鱼本身带来的恐怖。伯克认为,自然界中恐怖的事物会因神的显现而让人感觉更加敬畏和庄重。因此“披谷德号”船员在捕杀鲸鱼的过程中受到罪孽感的压迫,这种罪孽感是潜藏的,只通过以实玛利的内心活动流露稍许,但读者已经能感受到神秘和宗教的双重威压。
书中的直觉和暗示的成分无处不在。最明显的暗示就是姓名的暗示:以实玛利,埃哈伯,以利亚。他们是《圣经》中的人物,不仅性格和身份与《圣经》的人物设定相似,其命运和结局也与《圣经》相契合。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庶子,被父亲和上帝放逐的人。以实玛利的存在暗示着两次放逐,第一次是他将自己从熙来攘往、奔走忙碌的尘世放逐,奔向海洋,追寻“生命捉摸不住的魅影”,第二次则是逃脱了死亡的命运,从葬身大海的“披谷德号”上幸存。“以实玛利”这个名字还暗示了他是作为边缘人物而存在的,在披谷德号航向死亡的过程中,以实玛利始终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在感情上与船员们处于一条战线,在理智上又与他们相偏离,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埃哈伯的原型则是个心狠手辣、十恶不赦的暴君,遭到上帝惩罚的人。他的结局与《圣经》中如出一辙,违背“上帝的旨意”,不仅自己惨死,还带累了“披谷德号”的船员。以利亚也如《圣经》中那位先知,准确地预言了埃哈伯的结局。暗示的意义在于,它们最后无一例外地全部应验了,这种类似命运或符谶的情节极易唤起读者的恐惧感,使人们认识到这世界上存在许多无法解释、不能改变的事情,从而引发崇高的感受。
另一条主线是死亡的征兆以及以实玛利的种种直觉。以实玛利上船前先是住进了考芬(意为棺材)旅店,后来在教堂看见捕鲸人的大理石墓碑,之后在油锅客栈又看见了绞架和一对大得出奇的黑锅。种种迹象都表明这艘船从一开始就在驶向死亡。书中以实玛利直觉的描写是对读者无声的暗示,登上“披谷德号”之前,以实玛利就感到这次捕鲸之旅是“老天爷许久以前就已一手策划好的宏图的一部分”;初见“披谷德号”,以实玛利觉得这艘老捕鲸船“高贵而忧郁”;听闻了独腿船长的事迹,他对埃哈伯既同情又恐惧,不祥的预感始终如阴云笼罩。越是接近死亡的结局,以实玛利的预感就越发强烈,他手握着舵、身背着罗盘打盹,醒来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身上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僵硬的感觉,与死亡的感觉一样。”这一段的描写令人联想起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奇异、诡谲却又充满宿命感。
《白鲸》还涉及色彩引发的崇高感。“白鲸之白”这一章具体论述了白色的恐怖。作者写道,白色蕴含的内在的意念中潜藏着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一旦它脱离那些比较善良的联想而和任何本身就是可怕的东西相结合时,便会将恐怖感提高到极限”,比如那令人闻风丧胆的白熊和鲨鱼,比如柯勒律治笔下白色幽灵般的信天翁,无不引起“惊叹的心情和灰色恐惧的云彩”。而有些白色则是精神层面上的,它赋予承载物类似“神性”的特质,“这种神性中又隐含着既令人崇拜,又唤起某种无名的恐惧的东西”,它不需要通过恐惧就能直接引发崇高的感受。这就跳出了文本的范围,甚至在理论上与埃德蒙·伯克的崇高论相契合了。
神秘、暗示、直觉这些非理性的内容从本质上点破了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而人所面对的世界、所无法掌握的知识是无限的。伯克在解释模糊对引发崇高的作用时说:“在所有观念中最能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莫过于永恒和无限,但我们了解最少的也就是永恒和无限了。”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感到恐惧,所以产生敬畏。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一艘驶向宿命的死亡之船,载着一位魔鬼般的暴君和一群支持他复仇的船员,他们行走在最黑暗、最恐怖的神秘莫测的海洋上,迎向白色抹香鲸冰山般的身躯,承受上帝最残酷的刑罚。这些意象的组合暧昧不明、混杂难辨,隐藏在各种象征和隐喻背后,但正因如此,文本的模糊和客观对象的模糊才能引起敬畏,构成崇高。
3 偏执而顽强的抗争
伯克的《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书还提到了“困难”引发崇高感的作用机制:“当任何工作需要非常大的力量和努力去完成时,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宏大。”但伯克在阐释这一点时仅一笔带过,并未深究。我个人认为,以极大的顽强和毅力去完成不可能的工作,去挑战不可企及的对手,最后的结局无论胜败,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偏执和疯狂恰恰是引发崇高感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梅尔维尔的《白鲸》塑造了古希腊英雄式的悲剧人物——埃哈伯,他有着“不受拘束、勇猛剽悍的性格,出众的自然伟力,囊括全球的头脑,负载万物的心”,“在寂静和孤独中漂泊历险,背离传统。尽管有病态性格却无损于为人,因病态而更显得伟大”。他拖曳着肉体凡胎、扑向比他强大千百倍的白鲸的身影,一如背负命运的诅咒却执意完成复仇的阿喀琉斯。尽管抗争的结局是失败,但抗争的过程才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部分。
崇高感通过文本的冲突得到了强化。首先是埃哈伯的心理冲突,他觉得白鲸就像一堵墙壁,遮蔽了某种未知但仍可理喻的事物,但有时他也想,或许墙外什么也没有,这一切不过是他的臆想,他还是决心“把憎恨发泄在它身上”。斯塔勃克以为他疯了,但他自己说:“其实我已经成了恶魔,我是疯上加疯!”埃哈伯试图理解命运的真相,试图找到使他伤残的“主使”,他陷身于一种丧失理性的病态心理中,但通过阅读他的内心冲突不难发现,他对自己的非理性状态有着清醒的理性的认识。当斯塔勃克百般劝说他放弃复仇、回家与亲人团聚时,埃哈伯似乎短暂地摆脱了疯狂的状态,找回了一丝半缕的理智和柔情,他痛苦地呼喊:“青翠的故乡啊!快乐的家庭生活啊!”心肠软下来的埃哈伯甚至反过来劝说斯塔勃克不要跟随他冒这一次风险。英雄的踌躇总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但埃哈伯至此并没有放弃他的疯狂,而是把故事情节引向了更为崇高的走向:“可是埃哈伯的眼珠一转,他像一棵遭了病虫害的苹果树一般地把最后一个蛀空了的苹果抖落在地上。”
其次是行为的表象和实质的冲突。埃哈伯的复仇从实质上来说是无意义的。白鲸虽然使他失去了一条腿,但所有事件的缘起是他对莫比·迪克的伤害,他却精神错乱地把莫比·迪克视作世间恶意的总和、上帝有意安排的惩罚,“披谷德号”的沉没实际上源于船长埃哈伯固执的偏见。但读者从表象中看见人以一己之渺小与造物的伟力相抗衡,看见人如何反抗命运的安排,使身为人的尊严得以永存,因而产生崇高感。反过来看,或许埃哈伯的复仇从表面上看来是无意义的,但其实质却是人类值得悲悯、值得赞颂的不朽的抗争?尽管我们难以判断孰是孰非,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诠释,这部作品带来的崇高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再次是有关自由意志的讨论。埃哈伯在自己的心中清楚地看到:“所有我的手段都是神志清醒的产物,所有我的动机和目的都是神经错乱的产物。”埃哈伯的疯狂变成不易辨认的形态,敛藏在他坚毅沉着的外表和镇静自若的号令之下,他的智谋与勇气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内心的胡言乱语还在继续。从表象中看,《白鲸》呈现了人在与鲸的搏斗中体现出的勇敢、智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但从实质上看,人已经成为了被欲望驱使的工具,并且“没有能力来取消、或改变、或规避这一事实”。那么把复仇的矛头指向莫比·迪克,究竟是人出于尊严的自由选择,还是欲望支使下身不由己的被动选择,抑或是之前所说的命运的安排?这三种念头在《白鲸》一书中反复出现,相互驳斥,不仅体现了人的复杂性,也叠加出了更为崇高的效果。
作为小说剧情中的主要人物,以实玛利与《白鲸》整体的崇高感是格格不入的。在小说的开头,以实玛利就说:“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作为舞台监督的命运诸神要我充当出海捕鲸这寒酸角色,而派别人在堂堂正正的悲剧中演可歌可泣的角色,在高雅喜剧中演简短轻松的角色,在闹剧中演叫人笑破肚皮的角色。”这就昭示了就故事情节而言,以实玛利是一个边缘人。在海上捕鲸的历险中,作者也没有花费笔墨讲述以实玛利如何在捕鲸船上发挥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以实玛利对于整部小说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他是旁观者和记录者,以相对中立的观点看待发生在船上的一系列事件,时而受感情左右,时而摒弃成见,他所呈现的是一个具有辩证思想的人对于“披谷德号”、捕鲸业、自然、社会和人类的观点,并且包括对以实玛利自身的看法。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以实玛利的背后存在一个隐藏作者,就像看见海洋的底部潜伏着“披谷德号”的既定命运,这种模糊感和距离感非但没有弱化崇高感,反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