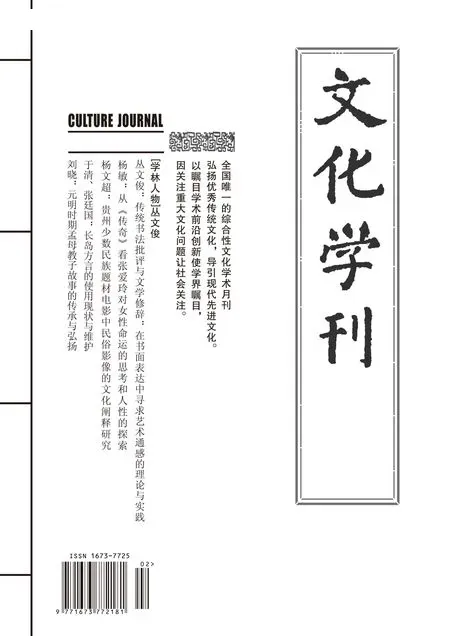论王华小说的动物叙事特色
杨一男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贵州仡佬族新锐作家王华自2001年步入文坛以来,至今共发表、出版包括长篇小说《雪豆》《傩赐》《家园》等在内的三十余部作品。这些作品情节精彩、思想深刻,深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喜爱。王华女士的写作主要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写作立场,以敏锐的女性视角揭露和反思社会黑暗面,擅长用精炼、机巧且唯美的文字书写城市与乡镇两大类文学题材。但如果深入探究王华小说的叙事特色会发现,作家通常会集中笔力描写动物的形象及情状,并将其作为故事角色之一,构建一种动物叙事的文学效果。这里的“动物叙事”直观上自然指同动物存在密切关联的叙事方式,它饱含着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思想诉求,以及价值观念等深刻意义。
一、表层结构:角色设置
作为研究事件叙述过程中凸显出的方式、方法、技艺、类型之学科,叙事学相当重视对文本结构的探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人物(character)属于叙事学“故事”层面,但在叙事“话语”层面中也存在着人物概念,其中普罗普(Vladimir Propp)形态学范畴里的“人物”观较具代表性:焦点集中在人物(角色)行动上并重视行动对故事结构的意义,“以动词作为中心,提倡构建一种普遍适用的‘叙事语法’”。因此,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称其为:“不是心理学而是语法范畴的人”[1]。这一界定对认清叙事作品的结构特征起着重要作用。“人物在篇章中的每一个句法结构里要充当主语与宾语的作用,特别是作为叙事主语(即施动者)的人物直接指向与导引其具体的行动及一系列行为方式的发出”[2],叙事主语的“行为发出”会被叙事宾语(即受动者)接受,形成“施动者+动作+受动者”的原理性行为模式。
纵观王华小说作品的动物叙事部分,可以提炼出两类角色关系模式:“主人+动物”与“动物+陌生人”。前者将“主人”作为叙事主语,“动物”为叙事宾语,其主要依据“家养”这一语义概念,至少在形式上彼此含有家庭成员式的“亲近”;后者将“动物”作为叙事主语,“陌生人”作为叙事宾语,单纯强调二者相遇前毫无感性基础,体现彼此疏远之关系。“主人+动物”关系时常会表现出主人对动物“加害”“利用”“爱护”的叙事谓语(行为)范畴;“动物+陌生人”关系模式,则侧重于“加害”“阻挠”“保护”“依恋”的叙事谓语(行为)范畴。
王华动物角色的设置首先是以猫和狗为主体,突出家庭宠物的表征内涵,在两种动物中,狗的出现最频繁,足见作者对于狗形象入文的重视程度之高;其次,动物角色总同人物角色(自然人)建立密切关联,然而也只有立足于关联之中,才会在“故事”层与“话语”层双结构下产生丰富的内在属性。譬如,作品里的动物角色时常在不同的情节中既以施动者姿态主导文本的话语空间,又以受动者形态显现,这样的建构形式引导读者不但关注“故事层面”中动物形象的具体出现情形,而且进一步比照每次出现时的细节差异;又如,加害、利用、爱护、阻挠、依恋、保护六种叙事谓语隶属于“话语”层,但它们也概括了“故事”层里动物与人所生发的主要线索。
二、叙事主题:现实主义批判态度
小说作者在动物形象上总会寄托一些特定却又相通的意义,而当具体展开叙述时,往往会艺术化地表现出特定的主题观念或思想诉求。动物的存在,不仅反映出王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体会与思考,其背后还隐含着作者现实主义批判性态度。这些无疑增强了叙事主题的哲理化意味——表面上叙写动物,实则借此重视人的境遇,关注人性的善恶,并给予人们告诫与警示。总体上,作者动物叙事主题可分为三大类:生态主题、爱心主题和苦难主题。
(一)生态主题
生态主题是王华动物叙事的一大亮点,意在揭示自然环境恶化的现实危机,代表作者对保护生态的急切呼吁。突出生态问题,既是一种文学功能的具体效用,又无疑彰显了作者关怀人类命运的意识。
小说《福子》表现的记忆中故土的空间环境,并非单纯停留在对风光的牵挂或依恋上,而是融合了对亲情的追念,形成萦绕在人物心头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美与情的况味。更重要的,人们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享有的事物越可能成为毕生珍视的东西,甚至会生成指导人们某种思维观念形成的重要元素。作为沙漠中罕有的生机符号,胡杨林、骆驼的核心意义正在于召唤出“母亲”对生命的热情与尊重,从未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胡杨林、骆驼群等形象一直都与“母亲”相伴相随,不但构成了其灵魂深处的安乐“家园”,更是“母亲”思想空间里那从未远去的“至亲”,它们始终都以生的力量感动、影响着“母亲”。这样,假若高龄的“母亲”能再次见到记忆中的景致,除了了却牵挂、激发起对乡土爱恋最由衷的幸福感外,也一定具有对乡土物事的感激之情。但遗憾的是,那片胡杨林只剩下几颗枯死的树桩,面对此情此境,作者这样写道:“母亲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她的目光跟着夜幕的降临而渐渐变得黯淡”[3]。在母亲的记忆中,人本同动物建立了非常和谐的关系,无论是儿时的她还是父亲,均将憨厚的骆驼视为生活中最忠实的好伙伴,但如今骆驼却成为商人们的牟利工具。譬如,福娃的骆驼驮一位游客观光就挣五十块钱,而将老骆驼借给福子骑,竟诈骗了对方两万块钱,以致作者讽刺道:“因为是跟福子做生意,老骆驼就变成金骆驼了”[4]。足见人与动物先时相互依存、相对平等且饱含情谊的关系俨然已被一种功利性意图破坏,虽然在表面上主人也养育动物,但其行为的实质却是“为己”的。因此,驼娃与骆驼之关系基于利用与被利用,重利的情结无疑在其内心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致故事结尾处,当驼娃朦胧感觉到福子可能遭困于大风沙时,并非在第一时间前去救助对方,而是“回他的驼队那边去”,继续招揽游客。
(二)爱心主题
爱心主题是王华动物叙事另一亮点。这里的“爱心”重点指动物对人流露出的关爱情谊,含有该情感的动作,可能只是依偎、凝视或轻微地触碰等几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行为;亦有可能是保护人类权力,帮助人类(尤其是主人)劳动等成功解决疑难的实际行动。但不论是哪种动作,其所表现出的保护、忠诚、乖巧、温存、憨实、英勇等均为爱心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奸猾算计、没有尔虞我诈,动物们单纯朴实、可爱可敬,无疑是作者由衷赞赏的高尚品德。涉及该主题的作品,包括《在春风里洗头》《一只叫耷耳的狗》等。
王华塑造的很多动物形象不能帮助人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它强调的只是一种感恩的纯情,或对恩人(主人)的依恋状态。例如《一只叫耷耳的狗》中,当大雨天人们把郑二媳妇的尸体抬出来放在医院外的街道上时,只有江湖郎中郎医生的爱犬耷耳守护在担架旁,却没有任何人认真关心或看守死者,甚至连医院里的大夫都说:“死人又没人偷,守它干什么”。即使面对人群的两次驱赶,小狗耷耳依旧看守尸体,毫无去意。“烛光把它的影子退得好远,比它的身体大了十几倍。”这里,烛光下的影子隐喻耷耳爱心的崇高,在烛光的照耀下甚至凸显出了这只满含爱心之犬的神圣形象。当郎医生说自己的狗是在守灵时,“(周围的人们)觉得烛光里的狗神秘而高大起来。它在他们的眼里不再是一只白狗,而是一团能点亮黑夜的圣光,有人便良心发现一般,在尸体旁边烧了些纸钱,还点了三柱香”[5]。在人与人关系冷漠的黑暗世界里,一只狗的仁爱之心体现着传统、美好的人情,如曙光一样启迪、引导人们回归到淳朴、真善的人伦关系中。
又如《在春风里洗头》里,一批批学生、士兵来孤寡老人牧奶奶的家里“学雷锋”,并在未经老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给她洗头,导致最后老人得伤寒而死。人们“学雷锋”似乎“有模有样”,但在牧奶奶得重病最需要“活雷锋们”救助时,却无一人挺身而出。不过,老人饲养的白猫在其病榻前的行为却非常感人:白猫跳到牧奶奶床上亲切地与主人“打招呼”,并用自己的体温为病入膏肓的主人取暖。猫与主人间的深情厚意,以动物自身的生命关怀意识体现出来,虽然不能以语言交流,但它那种急切的关切和充满爱意的依偎却是许多为儿为女的人类难以做到的。
两部作品里,王华思索了最理想化的人与动物关系,即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平等往来、视如至亲。当然,为营造和谐的关系,需要人最先做出善举,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小动物们才会流露出感恩的情谊。同时,动物们的爱心又同医生、看客、“学雷锋者”们那种冷酷、虚假的人性产生鲜明对比,在褒贬中,亦足见作者的价值趋向。
(三)苦难主题
动物叙事中的苦难主题基于“压迫性”情节设立,其意在表现“撕破生活‘美好’的神话”,以造成对角色正常状态的颠覆。当然,比起前两类主题,该主题往往进一步突出对人性、物性的深层思考。而从美学体验看,由于作品具有因“生活对自身‘美好’的坚持”而“将苦难归于一种阶段性现象”[6]的写作意识,其情节时常呈现一波三折的效果,也就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老北京布鞋》《曹赛是条狗》等小说均为该主题触及的作品。
动物叙事过程中,造成苦难的施祸者形象可以是动物本身。《老北京布鞋》里匪老板儿子饲养的狗,便是阻扰英梅寻夫行动的施祸者之一,其恐怖的吼叫搅扰着女主人公的神智,亦渲染了黑心煤窑险恶、阴森的气氛。狗的吼叫隐喻着黑心煤窑老板——匪老板一家人疯犬式的险恶性格,以及毫无人性的行为:英梅的丈夫在窑洞突遇事故而死,匪老板一家将尸体扔到荒堆上填满,并隐瞒此事。而狗越是叫得凶,反倒令读者感觉其内心的虚妄,正如匪老板全家对英梅表面谩骂,实则心虚一样。
《老北京布鞋》揭示人们过分关注金钱利益所得到的消极后果。“人们用‘风险’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比以前更生活在一个奉献社会里。”[7]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造福人民的同时,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和一系列生产安全问题在内的风险事件,无疑也令其步入了高风险社会行列。究其原因,正是对“重利轻义”资本关系的过多依赖打破了社会实践里招致与反制风险的相对平衡性。而人们在牟取利益的过程里,不但促成物质生产领域扩张,亦将非物质领域纳入产业化范畴。这样,“当情感、道德、精神、价值观等被作为一种要素纳入到资本生产逻辑的时候,人们在资本面前就失去了反思和批判能力”[8],其极端化的表现就是金钱被扭曲成衡量个人成就与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而其可怕之处在于最终形成“个人独立于社会整体和他人之外的倾向与感觉”,致使人们认为凭借金钱的作用可“轻松地突破语言、文化、信仰、地域等阻隔,实践着自我的各种各样的兴趣”[9]。
动物叙事中的施祸者也可以是动物与人相复合。譬如寓言性短篇小说《曹赛是条狗》里,一方面,宠物狗曹赛被送到“我”家后,打破了家中的安宁状态:全家人竞相悉心照顾着一条狗,只因它是“我”官太太奶奶的爱犬。这点在母亲对“我”的一番训导中显露无余:“儿子,听着,你照顾好了曹赛,你奶奶就高兴,你奶奶高兴,你爷爷也就高兴,你爷爷高兴了,对你爸就有好,以后对你也有好。”[10]而曹赛则仰仗着奶奶的高地位,总摆出十足的派头,俨然一副“狗仗人势”的丑态。另一方面,地位崇高的奶奶作为隐线不但掌控着“我”家的全局,也玩捏着宠物狗的命运:小说前半部分,奶奶经常给家里打来电话,询问曹赛的情况,似乎令人感觉她与宠物间情谊深厚,但发展到最后,她又在电话里突然对“我”说:“曹赛我送给你了,你就逗着玩儿吧”,又补充道:“奶奶不想它,奶奶要养条狗还不容易呀”[11]。自然,奶奶根本没有考虑到曹赛日后的现实窘境,当失去强大的“保护伞”后,曹赛昔日所有的幸福也便消失了。
《曹赛是条狗》精心构造的权力隐线使得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向一只狗卑躬屈膝,体现出人们对“官本位”价值观的认同。“所谓官本位,顾名思义就是以官为中心、为至上、为主宰”[12],许多做官的人狂傲十足,霸道武断,将官职作为显示地位的标志;无权的人则“把是否为官、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身份、地位”[13],拼命巴结、讨好官员,以盼望从对方身上获得嗟来之食。而在“官本位”不良观念的诱导下,一些长辈不但为孩子们做出极坏的示范,而且干扰着他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其次,奶奶对曹赛的利用是真,但在饲养过程中也充斥着对它的溺爱,这从曹赛来“我”家时飞扬跋扈的态度中便能看出。然而,人们很难想象一只仅依赖主人而毫无生存能力的狗在失去主人眷顾后将会怎样过活,从天堂坠入地狱,等待曹赛的极可能是一条身、心彻底沉沦之路。实际上,曹赛来“我”家之前被溺爱的情形,正象征着父母对“我”的娇养。“我读完初中,没能考上高中,爸出高费让我念了三年高中,高中读完后我又没考上大学,爸又让我去读了三年自费大学,回来以后,爸把我安排到他的下一级政府,也就是他原来掌管的那级政府里干事。”这样,“和曹赛呆的时间太多,我已经变成一条狗了。”[14]“对孩子的溺爱和对宠物的爱有一致性,可以说是一种父性或母性的本能。它不需要努力,不需要经过意志抉择,并且对心灵的成长毫无帮助,所以不能算是真爱。”[15]这种爱既磨灭了动物(指宠物)顽强生存的自然天性,也使得孩童随成长蜕变为依赖性十足的无用之人。作者无疑抓住了宠物爱与孩童溺爱的相似之处,在文本内部巧妙缔造了“狗故事和人故事”的二元结构,令两者相互映衬,而在思想含义方面又视溺爱为危险的软暴力——即使目前未给人以苦难,却种下令人日后蒙难的祸根。
三、伦理范畴:生命意识
由前文可知,王华绝大部分作品中大的动物书写均被意识形态化的动物叙事逻辑所支配。在这种叙事逻辑中,“动物作为象征符号出现,其功用是为了或伦理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某种‘普遍性的意义’之呈现”[16]。其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具体显现,即以人之眼光审视动物、描绘动物、书写动物与人的关系,最后影射或警示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伦本身的严肃问题。但以人类为“中心”,又绝非磨灭动物角色的个体自足,相反,小说里主人公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显露着作者的伦理价值取向,该取向致使那种“普遍性的意义”别具内涵与深度。
如聂珍钊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17]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伦理取向必然是具有“利人”规范性的。尊重生命无疑是生命意识的形成根本。试想,如果一个人连生命都不知道尊重,又谈何而来自爱与爱他(它)呢?笔者在前文中已提到,作者提倡一种人与动物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平等往来、视如至亲的关系。显然,“尊重”在构建理想关系中享有首要而关键的地位。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讲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应当受到尊重,甚至大自然中的一切,包括山脉、河流、天空、大地在内都体现了一种神圣的和谐。”无疑,尊重生命最简单的举动就是不杀戮,或者“即使人类迫不得已尽可能损伤到它们时,也应当怀着敬畏之心,谨慎为之”。这自然也是一种保护行为,它应是“无条件的、超功利的,并且已经接近了信仰与审美的境界”[18]。王华热爱小动物,这点从《一只叫耷耳的狗》《在春风里洗头》等作品中便可明显感知。在其笔下,凡是残害动物的人物都是她着力讥刺的对象,这些人物绝大部分也没有好报。
另一方面,净化心灵又是生命意识的价值所在。同尊重生命侧重于对外在肉体的关怀有所不同,净化心灵突出人类本体的德行修为,属于精神范畴。美是道德的象征,只有内心纯净的人,才能在面对世界、自然与社会时,不虚妄、不盲目,编织出和睦而完美的伦理维度。但如今真正心灵纯净的人又有多少呢?王华在作品中亦深刻地反思了这一问题:驼娃、匪老板、曹赛的奶奶等,这些人象征着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心灵受金钱、物质、权利腐蚀的人。在这些人的意识中,不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利益链条侵蚀,不再具有真挚、朴素的情分,就连人与动物(主人与宠物)间也被强烈的功利性阴霾所污染。正如前文所说,动物已变成人类谋福利的工具了。而一旦处处用利益的眼光评判一切,人类本应珍重的富足精神家园也会被无情践踏。人们需要从小动物们身上收获一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譬如真诚、忠贞、温情、关爱,诚如前文所说,很多时候,猫、狗就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它们简单而不减“真”,可爱而又尚义,与它们平等相处,善于向它们学习,自然是弥补人性缺失的良方。人们亦只有净化心灵,将智、情的份量提升到同等重要的高度,生命的内涵才会完满而富足,生命意识也将显露出它自爱、爱他(它)的最大价值。
[1]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M].李幼燕,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0.
[2]陈佳冀.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任务角色类型研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22-30.
[3][4]王华.福子[J].山花,2009,(18):29-35.
[5]王华.一只叫耷耳的狗[J].民族文学,2002,(12):42-47.
[6]刘川鄂,王贵平.苦难的叙述和文学的关切——评王华的中篇小说《傩赐》[J].理论与当代,2006,(7):51-52.
[7]斯万·欧维·汉森.知识社会中的不确定性[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3,(1):37-45.
[8]庄友刚.资本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从当代风险社会谈起[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191-193.
[9]陈水勇.从货币哲学视角看金钱与人的异化[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6-19.
[10][11][14]王华.天上没有云朵[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238.238.249.
[12]袁蕊.官本位一种[J].文学理论与批评,1993,(4):68-69.
[13]郑焱明.论“官本位”意识的根源、危害及治理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03,(5):240-243.
[15]李颖.溺爱孩子是一种软暴力[N].科技日报,2013-02-27(4).
[16]唐克龙.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92.
[17]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8-11.
[18]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