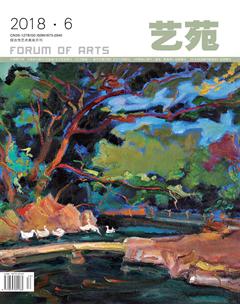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爱与死”的双重主题
黄琼瑶
【摘要】 《明室》是罗兰·巴特的摄影研究札记,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在他的作品星系里显得尤为独特。《明室》中罗兰·巴特从主观私我出发,迎向摄影的现象学世界。本文首先论述了《明室》中所呈现的现象学视角下的摄影研究,再分析了摄影的本质与“爱与死”的双重主题之间的关系,最后回到罗兰·巴特在言语之间所针砭的现代社会的病症,这些病症至今仍拷问着我们所生存的数码摄影时代。
【关键词】 罗兰·巴特;摄影;现象学;情感;时间
[中图分类号]J40 [文献标识码]A
一、现象学视角下的摄影
谈论摄影是困难的,因为当我们在谈论摄影时,总是滑向谈论摄影对象、摄影技术,抑或摄影的历史性或社会性意涵,以致我们似乎谈论了一切,却都无关“摄影”。我们也许可以对一张照片说出很多,却很难抽象地讨论摄影的一般概念。摄影是否有自己的“语法”?摄影的本质是什么?摄影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可以谈论的?巴特始终关注着摄影的这些问题,在巴特的文艺批评文集之三《显義与晦义》中专门有“照片”一章,收录了《摄影讯息》《图像修辞学》《第三层意义》三篇巴特此前专门谈论摄影的论文,但是其采取的是符号学的方法,将照片拆解为符号,以分析其结构化的内涵。而《明室》中巴特选择重谈摄影,却选择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道路。
《明室》是巴特作品星系里特异的一部作品,文体上难以归类,氛围上哀婉动人,理论方法上无拘无束。此时的巴特刚刚经历丧母之痛,尽管此前已经写作了《哀悼日记》但仍旧不能宣泄和化解失去唯一挚爱的悲恸。所以,与其说《明室》是一部关于摄影研究的札记,不如说是巴特在寻找母亲在这世界的影像留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趟知性的追寻之旅”[1]79,在这过程中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彻底地敞开。这样的《明室》散发着一种与罗兰·巴特的其他著作相比非同一般的气质:其一,巴特忧郁的笔调使得文字和影像间毫无距离,因为他之前的作品“从没有任何一个言论论述试着将机械影像看为一对等的异质物”[2]62,因此几乎让人忘记这是一本有关摄影的理论著作,更像是一本普鲁斯特式的回忆录;其二,巴特完全放弃了此前的摄影的研究方法,另辟蹊径,从主观性出发描述有关摄影的体验,运用经过他修改的现象学原则,以求呈现出摄影的本质。巴特说:“我愿意把自己当成整个摄影的中介,试图以个人的某些感情为出发点,列出摄影的根本特点即一般概念。”[3]11是不是因为这样《明室》所谈论的摄影具有过强的主观性就不具有普遍性了呢?恰好相反,摄影是一门极度现象学的艺术,是一套极度浓缩的语言,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一张薄薄的相纸上,清楚明了,简单直接,没有其他任何一门艺术能达到这样的复制和模拟的效果。也正因如此,谈论摄影的时候总是在外围打转,环绕着摄影对象和技艺喋喋不休,却无法进入摄影的本质。巴特使自己成为摄影知识的衡量标准,以自己的情感为中介,用经过他修改的现象学的方法,进入照片,直达本质,真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切身可感的阅读照片的方式。
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摄影,首先要问的是摄影和意识有何相似之处呢?照片最明显的特征是指涉性,没有成像的照片并不能称之为照片,一张照片总是关于被拍摄物的照片,两者因为偶然相遇而陷入了永恒的固定之中,这是否可以假设照片有一种“意向性”的可能性呢?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有意识对象时,意识才出现;同理,拍摄对象总是附着在照片上,由此我们才能看到“摄影”。假若将摄影和意识放在同等的地位讨论,那么摄影就和意识一样,我们不能看到摄影本身,只能看到被摄物所在的照片,若没有照片的这种呈现作用,要谈论摄影更是不可能的。照片是“偶然性的轻盈透明的外壳”[3]5,这句话翻译有一些拗口,实际上罗兰·巴特的意思是说他所要研究的摄影正是那个偶然抓取了拍摄物的那个东西(意识),不是指底片。巴特特意用了“轻盈透明”去形容摄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消除其物质性和空间性,它使照片被看见,它自身却不可见。摄影因为具备透明性的特质所以才能够完完全全地模拟和复制拍摄对象,使得照片和被摄物之间的“不相似性”减至最小,但并非因为摄影的透明性就否认了摄影的存在。但这种透明性又不是绝对的,因为拍照成像首先是建立在相机本身的物质性身上,一张照片再还原再写实也无法突破相机和成像过程中其物理和化学上的客观局限。摄影的这种“不绝对的透明性”正和意识的意向性一样,因此摄影才被认为是极度现象学的,才有了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谈论的前提。摄影活动中不是只有从摄影本质的层面来谈意向性,“摄影是三种活动(或三种感情,或三种意图)的对象:操作、忍受、观看”[3]12,这里的意图即intention。操作者(摄影者)的意向不是巴特想讨论的,因为他没有太多拍摄者的经验,他只能从自己有所体验的忍受者(被拍摄者)和观看(观看者)角度出发。巴特想要谈的摄影意识并非摄影师的意识,而是已经成为照片的抽象意义上的摄影的意识,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角度,将摄影者放入括弧,把摄影技巧和内容意涵悬置,从观看者自身出发,看照片是如何引起观者的情绪反应。由此,巴特的摄影研究凸显了其最重要的两个主题:爱与死。巴特采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摄影是他自然又必然的选择,但是他却并非是完全按照现象学的理路步步推进,其中既有此前符号学研究的影响,也有对现象学本身的修改和反思,由此形成了一套属于他的摄影现象学。
二、痛的刺点和爱的救赎
情感,是现象学没有过多触及的部分,巴特说:“我不记得古典现象学、我年轻时就熟悉的那种现象学(那以后也不曾有过别的现象学)谈论过欲望或哀伤。”[3]28的确如此,古典现象学谈论的是从主体自身出发对意识对象进行描述,最终获得对意识对象的认识,情感往往是被装入括弧的对象之一,可是谈论照片能够仅仅止于对照片的描述而不掺杂观者的情感吗?说到底,照片对于每个观者有不同的吸引力、不同的回忆、不同的“刺点”(巴特提出的重要概念,下文将进行解释),这种不同其实都是基于情感的。要是一张照片不能够“哀婉动人”,不能够引起观者情感的反应,那么也就没有了去观察和思考的必要。
对于当时的巴特,要进入摄影照片,情感几乎成为他自然而然的路径。因为巴特写作本书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母亲的去世,在不能释怀的悲戚之中他不由自主地寻找母亲过去的照片,想借此与去世的母亲再次面对面,此时他才发觉过去所谈论的摄影是多么无关痛痒,他要回到真正的、令人动容的摄影上去。在《明室》中,巴特创造性地运用“情感的意向性”这样一个概念,照片的观看者在看到照片时会产生相应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可以化约,也不能推及他人,是专属于在看照片的“我”对这张照片特有的情感,不同的照片引起不同的情感,也就是说照片是以情感的形式呈现在观者面前的。观者看到的不是照片,而是各种各样的情感,在巴特这里,更多的是悲怆、伤感、怜悯等刺痛观者的情感。
一个人被某张照片吸引,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被拍摄对象的新奇、拍摄角度的独特、被拍摄者勾起“我”的回忆或经验,最根本的是照片唤起了观者的情感共鸣。巴特认为能引起人感情的照片有两个要素(不必同时存在):意趣(studium)和刺点(punctum)。意趣来自拉丁文“studium”,指的是“某种一般性的精神投入”[3]34,是一种相对容易获得的、宽泛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要经过道德或政治的修养作为中介才能获得。也就是说,意趣是看一张照片时,经由观者的文化修养或道德观念而产生的兴趣,这是一种“一般的兴趣”。意趣的意义通常可以被破解、被研究,世界上许多广泛传播的照片通常都是有意趣的,巴特将这样的照片当作历史档案来欣赏。欣赏照片中的意趣的同时也是在体会摄影师的意图,履行观众与摄影者之间签订的“文化契约”,将照片的意义稳固在不会对社会造成威胁的主题之中。巴特把这类照片称作“一元的照片”,没有任何间接,没有任何意外,只有单一的主题,新闻照片多属此类。
“刺点”是巴特的摄影现象学里最重要的词汇之一,这个词是他以主观情感看待摄影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核心。“刺点”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unctum”,有针眼、小斑点、小伤口、甚至还有碰运气的意思。巴特选用这个词汇太贴切不过,刺点常常是照片中的一个或一些细节,它不用经由道德或优雅的情趣就能直接地体会到“痛楚”,它突如其来甚至要靠运气获得。刺点最惊人的力量在于它可以使摄影超越其在呈现事物时的中介作用,而直接成为事物本身。比如对巴特来说,在凯尔泰什(André Kertesz 1894-1985)摄于1921年的一张由一位小男孩牵引着盲人拉小提琴行走的照片之中,他们脚下的土路便是刺点,它就是巴特曾走过的中欧小镇的土路,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中介,它直接对应到巴特曾体验过的那条土路。刺点有时甚至可以扩展到占满照片整体,改变整个照片的意义。刺点会使一张照片变成二元的照片,拥有超出平庸的意趣之外的意义,但刺点的意义又是不能破解的,它是非符码化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相较意趣,刺点通常是一个更难获得的要素,因为它不能刻意制造,摄影师对于它的产生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只是他正好在现场拍下了照片。意趣和刺点之间不可能确立一种联系规则,两者更像一种偶然性的共存。意趣在大多数优秀的照片中都存在,但刺点可遇不可求。巴特有一个很精辟的说法:“一个摄影师在拍摄对象整体的同时,不可能不拍摄对象的局部,攝影师的超人之处不在于能见人所未见,而是他正好身临其境。”[3]65因为正好有刺点的存在,我们才可能觉得想到的照片比看到的照片还清楚,刺点可以带来“盲画面”,一种超出照片之外的活的想象。
刺点之“刺”,在身体层面上是指锐物扎进肉身的瞬间引起的疼痛神经的反应,照片中的刺点能带来痛感,却穿透身体到达了情感层面。巴特在《明室》中使用了很多与情感有关的词汇:悲伤、温情、哀婉动人,忧愁伤感……看完《明室》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感情最终都汇集到“爱”,母亲与他自己的“爱”。巴特一开始翻遍了所有母亲的照片都无法找到真正的母亲,直到《温室庭院里的照片》的出现,他才宣布自己找到了自己所认识和爱戴的母亲。摄影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它以一种非现实的方式达到了对一个独特之人的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认识和理解”[3]92。巴特并未在书中展示这张照片,实际上展示了也徒劳无功,因为对好奇的读者来说,那不过是一张平淡无奇的照片,对巴特来说却布满刺点,它就是他的母亲。从这张照片里,巴特说他发现了摄影的实质:“我已经明白,从今以后,探寻摄影的实质,不能从爱好的观点出发,而应从摄影与我们罗曼蒂克地称之为爱与死的关系上着眼。”[3]98巴特接下来就顺着这条“阿莉阿德尼线”,找到了摄影的本质。
三、封闭的时间见证与开放的情感空间
巴特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肯定地表明摄影的显而易见的本质:“这个存在过”[3]103,这里笔者更倾向于使用《明室》的台版译者许绮玲教授的翻译——“此曾在”。摄影的本质是“此曾在”,也就是说,对于照片我们能确认的就是彼时彼刻彼物是在相机镜头面前真实存在过的,所有的照片都是一纸证明。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摄影的证明力大于其表现力,巴特认为摄影的革命性就在于摄影使人类开始相信过去、相信历史。摄影的“此曾在”是对过去的无法否认的见证,这是其他任何图画艺术品不通过其他媒介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摄影时,一定有真实的某种事物那一刻在镜头面前出现过,这跟其他模拟现实的艺术不一样。绘画可以描画不在眼前的事物;文字可以记录想象中的东西;而电影把演员和角色的“此曾在”混为一谈;只有照片,必得有所指涉,并且不能通融,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真实,一个是过去。光是真实与过去的证明,无论是传统摄影还是数码摄影,呈像原理仍然是利用光的显像,所以拍摄对象在被拍摄时实际上就是抓住了其身上反射的光。那个光在彼时彼刻切实地照在这个真实存在的拍摄对象身上成为照片,如今看到照片的“我”再次看到了那时的光线,并且触及到“我”的感情。
巴特更近一步思考了摄影时间的矛盾性,他在书中列举了一张由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1821-1882)拍摄的将要执行死刑的青年的照片,它同时呈现的是:他将要死了,以及他已经死了。在这样一张照片里,将要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并存,如此直接,没有丝毫回转的余地,照片的观看者对这个事实毫无作为。照片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照片仅仅是其所是,所以当照片表现出这种令人悲伤的时间的矛盾性时,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可以去化解其悲伤。在这个意义上,摄影是残酷的,照片拍出来以后就静止不动了,照片自身永远无法化解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无论喜乐悲伤。照片上,什么都不能省略,什么都不能改变,照片甚至不能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哪怕把底片放大无数倍,本来以为可以看到更多,实际上除了放大的颗粒感什么也没有多出来,又或者将一张照片反复观察摩挲,翻来覆去,所看到的也不会比第一眼看到的更多。正是因为照片的见证性的残酷内涵牵引着观者的情感,对于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发生的事在照片上的共现,尤其是与死亡有关的想象,令观者刺痛,故巴特将时间定义为“刺点”的第二种内涵。
时间能够哀婉动人,是因为时间与死亡密切相关,摄影的广泛运用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想要保存“生”的渴望,或者说图像的起源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和抵抗。德布雷在《图像的生与死》里对图像追本溯源,认为艺术诞生于墓葬之中,图像走进墓葬,布置出生的喜悦。德布雷把图像的诞生理解为一种对生的留恋,“上帝是光,而只有人是摄影师。因为只有过客,而且自知是过客,才会有留下的欲望”[4]10,越是担心宽限期即将结束,越是疯狂地进行记录,所以图像与死亡的关系是本源性的。摄影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成为保存生命的最佳载体。桑塔格在《论摄影》中也说,摄影是一门挽歌艺术、一门黄昏艺术。美丽的东西被拍摄下来就是为了规避其会衰朽的恐慌,所有照片都会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拍照就是参与另一个人(或物)的必死性、脆弱性、可变性。所有的照片恰恰都是通过切下这一刻并把它冻结,来见证时间的流逝。[5]15巴特认为摄影与戏剧密切相关,用他的话说,摄影与戏剧之间有一个中介:死亡,戏剧的起源与亡灵祭祀仪式有关,戏剧中的涂脂抹粉的扮相是为了更加生动,就好像照片也力求栩栩如生,但越是追求生动,越是恐惧死亡。
巴特敏感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承受死亡的方式是:以生的狂热作为否定性托词来承受死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摄影和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死亡危机有某种关系。”[3]123但是,巴特认为与其从社会和经济背景里去寻找摄影出现的原因,不如从死亡和图像的人类学联系上去进行思考。他解释到:“有一点必须说明,作为和礼仪衰退出现在同一时代的摄影,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回应可能就是这种死亡对社会的侵入,这种死亡是非象征性的、宗教之外的、礼仪之外的,是一种突然陷入字面意义上的死亡。生/死:这个聚合体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金属声,即那个把最初的曝光和最终的相纸分开的声音。”[3]124这个不可见的声音正是“摄影”,被拍摄的对象被固定在照片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台湾学者陈传兴用“失落”形容拍摄成像的过程:“当你拍一个东西时,你已经把他从‘现在时推向‘过去时,而透明性就是想要把失去的时间再现,这就会让人失落了。”[6]36-37把一个东西从现在推向过去,就是把它从生的状态转变为照片上的静止的死的状态,所以巴特才会说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个声音其实就转化了生死。
现在再回过去思考摄影为什么一定要在“爱与死”的双重主题下进行,便有了答案。摄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两个根本特质是:摄影与摄影对象之间不可分离的指涉性和摄影“此曾在”的见证性,这两个特质只有在与“爱与死”的关系中才能更深刻地显现。因为被拍摄物在相机镜头面前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它被拍成照片保存下来,可以说照片是为了保存“生”却制造了死亡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封闭的见证档案。死亡无论在摄影的历史起源之处还是在摄影行为的发生之处都如影随形,将时间和死亡封闭于其中却又无法自我消解的照片,却因为观者的情感投入打开了想象的空间,“此曾在”与“此已不在”引发的情感只能被爱救赎,也因此,摄影的本质更加凸显。
四、结语:数码摄影时代重读《明室》
巴特运用经他修改的现象学的策略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将摄影置放到“爱与死”的主题之下,一步一步接近摄影的本质。巴特虽然看似是以“我”为中心,从主观性出发思考摄影对于个人情感的触及,由此推导出摄影的本质,实质上通过这样的推导,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摄影所面对的危机,“(巴特)从私我出发,最终巴特仍延续着随笔散文的传统,将个人感想逐渐引向了普遍化的思考,从摄影洞见的,最终是要针砭整体当代文化中的病症”[1]79,而且这样的病症在如今的数码摄影时代也依然存在。
从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来说,在《明室》“出其不意”一章中巴特指出了摄影师为了拍出“有意思”(的极致)的照片,通常会有以下五种情况:稀有(不断收集稀有的拍摄对象)、抓拍肉眼无法固定时刻(突破视觉范围的极限)、成绩(挖掘摄影设备潜能的行为,比如坚持不懈拍摄一滴正在落下的奶)、技术加工(叠印、变形等突破摄影条件限制的行为)、新颖(通过道具进行视觉修辞)。总而言之,摄影师变成了“杂技演员”,不断挑战极限,以博得观众喝彩,但谁能说出拍这样的照片到底有什么意义?而如今大量充斥着我们的视觉的正是这样无意义的照片,观众除了附和地表示惊奇和意外,并不会感到其“哀婉动人”。再加上如今相机设备有足够的技术不必全盘接收拍摄时的瑕疵,再加上影像后期处理技术的变革让照片偏离真实,“此曾在”也许具有欺骗性。
从摄影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因为摄影的“此曾在”,所以摄影的真实性是绝对本源的,现实与真实合二为一,完全模拟,无法删减,但照片自身又无法化解,那摄影对观者所引起的冲击将是巨大的,这样的照片既是“指证式”的也是“感叹式”的:“它把形象提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是情感(爱、激情、哀伤、冲动、欲望)成了存在的保证。”[3]158这正是摄影的疯狂之处,让观者与“爱与死”直接照面。在全书的最后一篇“被驯化的摄影”中,巴特指出了为了规范和稳固摄影的意义,抑制其疯狂的特性,现代社会所运用的策略有:一、将摄影收编为艺术;二、将摄影普遍化。第一种策略使摄影屈从于油画美学,屈从于理想化展示手法,将疯狂转变为幻觉的修辞,这样的摄影将不会再对巴特、对观者起作用。第二种是使摄影变规矩的手段,是使它泛滥成灾,使照片蛮横地压倒其他图像,使社会处于幻象中,在“景观社会”之中照片比真人更真实更具活力:“我们按照一种普遍流行的想象出来的事物生活着,在美国,一切都变成了照片,只有照片,只生产和消费照片。摄影被普及之后,它就打着彰显人类社会的幌子,把充满矛盾和欲望的世界彻底虚化了,所谓的先进社会,其特点就是完善影像,而不再像以前的社会那样完善信仰;因此,今天的社会多了些宽容,少了些狂热,但也更‘虚假。”[3]158所以,巴特呼吁要拯救无中介的欲望,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想要将摄影规范为艺术、稳固摄影的意义的行为,让摄影保留其“疯狂”的特质,让观者可以全情投入摄影,感受摄影中“爱与死”的冲击。
台湾学者詹伟雄说:“继《明室》之后,巴特可能会创造出第三种作品星系——也许是他挑战普鲁斯特叙事里程碑的小说,或者是他基于丧母情怀所写的新散文——《明室》即属此类,由最深的知性与无从救赎的伤痛所造就。”[7]2《明室》在巴特的作品谱系里显得太过独特,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巴特没有意外去世是否还会有《明室》般的作品,值得庆幸的是,他至少留下了《明室》。如今,摄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为摄影研究和摄影批评提出难题,巴特从摄影观看者主体的收受经验出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在“爱与死”的双重主题下阅读照片的方式,他所思考的问题至今仍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摄影美学课题。
参考文献:
[1]许绮玲.寻找明室中的“未来的文盲”[J].艺术学研究,2009(4).
[2]陳传兴.银盐热[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法)罗兰·巴尔特.明室[M].赵克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法)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M].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阮义忠.摄影美学七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7]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江灏,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