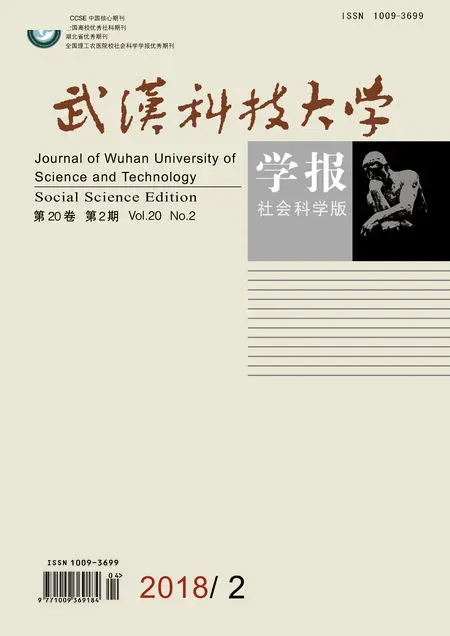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
——《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王钧林
(1.孔子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00;2.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近年来,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书》学研究日益兴盛,《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其中,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考据详实,论述精到,是近年不可多得的《尚书》学研究力作。其中,该著关于“孔氏家学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相比之前的《尚书》学研究论著,《两汉〈尚书〉学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尚书》学中孔氏家学的正本清源
《尚书》学中的孔氏家学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在厘清学术渊源的基础上,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力求做到正本清源。由于孔子及其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孔氏家学成为包括《尚书》学在内的诸多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两汉时期,《尚书》学与孔氏家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能弄清两者的关系,很多疑难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例如,孔安国问题是两汉《古文尚书》学研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1]208。关于孔子与《尚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难题。马士远采取了看似笨拙却非常可靠的办法来梳理文献,将相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等汇总整理,可谓“一网打尽”“涸泽而渔”,发现了新的线索和思路。马士远经过缜密考察后发现,虽然孔子撰写《尚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但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孔子确实曾对《尚书》进行过整理,而且将其用于教授弟子和子孙,是真正以《书》为学的第一人。马士远论著的依据是出土文献中的《孔子诗论》《易传》等,以及传世文献中《易》的《系辞》、传述《春秋》的《左传》、传述《礼》的《礼记》等,而这些都属于“述”,因此,孔子对于《尚书》的诠释,完全可以称之为“传”。
《史记》关于《尚书》时间断限问题,即“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说,马士远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取舍,孔子“删”《尚书》的说法是成立的。马士远认为,由“文”到“字”再到“书”,特别是用于政教、记言的、较长的《尚书》必定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即使已经产生《尚书》,也是非常少的。另外,《左传》《国语》所引《尚书》一类资料又有唐尧虞舜之前的资料,孔子在编撰《尚书》时自然会剔除荒诞不经、不雅的资料。因此,《史记·五帝本纪》言皇帝之文“不雅训”,孔子皆“雅言”,可以作为孔子编《尚书》断于唐虞之际的证据之一。而“下至秦缪”的文献是受秦汉时期“秦继周朝正统”影响的产物,并不符合史实,但不等于说孔子未编过《尚书》,《孔传》所言“迄于周”更有可能是孔子编次《尚书》的时间下限。更为重要的是,孔子在诸侯争霸、《诗》《书》等文化消亡的危急时刻,积极倡导周代礼乐文化,对早期《尚书》进行整理、传播和诠释,将官方顺《尚书》以教的传统下移至民间。
孔子《尚书》学观经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孔子之于《尚书》可以分为几个时间段。马士远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记载,认为孔子在四十二岁之前、四十二岁至五十岁之间、五十岁之后至六十七岁返鲁之间三个时间段以不同的态度和观点诠释和传播《尚书》。其中,孔子两次对《尚书》进行了系统研究,孔子以《尚书》为学,其《尚书》学观主要体现在其“《书》教”思想中[1]213,而《书》教是与《诗》教、《礼》教、《乐》教等同时由孔子提出的。孔子把《尚书》的教化作用概括为“疏通知远而不诬”(《孔子家语·问玉》),把《尚书》当作历史来看待,通过《尚书》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汲取上古诸侯能臣在复杂的斗争实践中总结的先民智慧,从中可以探寻王朝更替、历史变迁的原因,从而促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这基本可以概括孔子早期的《尚书》学观。马士远根据《艺文类聚》《孔丛子》等文献的解读,认为晚年孔子《尚书》学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孔子在以《书》为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书》为训”的“《书》教”思想,《书》对于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孔子《书》学思想对于后世儒家思想影响甚大。
正是因为《尚书》对于孔子思想的重要影响,孔氏《尚书》家学的创立过程,也是孔子教授弟子门人的过程,马士远认为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孔门儒学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在孔子死后受到严峻挑战,依靠弟子门人的努力才加以传播,到战国时期成为两大显学之一,其中就得益于《尚书》的传播。孔子“《书》教”传统被漆雕开、子张、子夏、子思等孔子弟子传承,对儒学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马士远专门考察了孔子后裔学习《尚书》的情况,认为孔子后裔多精熟于《尚书》学,包括孔伋、孔白、孔穿、子顺、孔鲋等一代代的孔氏后人逐渐形成了周秦孔氏《尚书》家学传统,为后世《古文尚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为了厘清西汉《尚书》孔氏家学传承,马士远考证了孔鲋、孔腾之后还有一个弟弟孔袝,并对三者世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尤其再三考证了孔安国一支,确定孔安国为孔氏第十二代孙、孔襄之后,孔延年、孔霸、孔光等祖孙三代皆治《尚书》今文学[1]229-230。
孔氏家学的传承是孔子后裔的责任和使命,孔子后裔也因为孔氏家学而得到很高的地位,以孔安国为代表的孔氏后裔为了治学、功名等目的大都致力于研习儒家经书,尤其是在《尚书》学领域世代相传,分支较多,也存在很多争议。例如,马士远重点考证了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问题,认为孔安国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而且在孔氏子孙和弟子中形成了两支传授系统和谱系,这些考证基于《汉书》《后汉书》《孔子世家谱》《阙里文献考》等文献的相互印证,思路清晰,论证缜密。
二、《尚书》学研究史中的孔氏家学
只有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更为开放的视野里审视,才能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马士远认为,两汉《尚书》孔氏家学研究之所以不够深入,就是因为受到所谓“伪书”公案、疑古思想的影响和制约,李学勤[2]、黄怀信[3]、李存山[4]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推进了东汉《尚书》孔氏家学研究,应该大胆借鉴。马士远据以考证的资料,除了《孔丛子》等书籍文献之外,还有洪适《隶释》《隶续》所录存的汉碑,以及曲阜现存的部分汉碑。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西汉今文经学是鼎盛时期,儒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设立了五经博士——所传经典皆为今文。到了汉宣帝,博士经学从一家分化为一经数家,仅《尚书》经学就从武帝时欧阳一家发展为欧阳、大夏侯、小夏侯等三家博士。在经学分化发展过程中,孔氏家族学者中就有孔安国、孔延年、孔驩、孔子立等顺应学术潮流研习今文经学,被立为《尚书》今文学博士。其中,孔安国与孔延年为叔侄关系,由于汉武帝在位时间较长,孔延年出于长房,叔侄两人年龄差别很可能不大,这样叔侄同为博士的可能性非常大。承续前面所定西汉孔子后裔世系脉络,马士远仍以孔鲋之后、孔腾之后、孔袝之后为脉络考辩东汉孔子后裔世系,兼有《尚书》今文学、古文学之分。马士远对照了《汉书·孔光传》《汉书·夏侯胜传》等文献,可知孔延年之子孔霸为孔子第十四代孙,曾治《尚书》今文学,师从夏侯胜,汉昭帝时期为大夏侯学博士,汉宣帝时期为皇太子即汉元帝师。孔霸又继承家学传统,传《尚书》今文学于第四子孔光,开大夏侯学派中的“孔氏之学”。孔光为孔子第十五代孙,学识渊博,三世官居高位,在西汉时期孔氏家族中官职最高,《汉书》有《孔光传》,记载孔光曾以《尚书》授徒讲学,其弟子很多成为博士、大夫。因此,孔霸、孔光皆为经学大家,而且都因明经高行成为帝师。无论是叔侄同列博士,还是父子皆为帝师,都说明两汉时期孔氏《尚书》家学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另外,孔霸长子孔福之后的《尚书》孔氏家学以今文《尚书》大夏侯学为主,孔安国一系在东汉传有《古文尚书》家学无疑。
对于汉代《尚书》孔氏家学的贡献,马士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孔氏一族保存并整理了《古文尚书》,传承周秦“《书》教”传统、创发完善了《古文尚书》经学,丰富了汉代《尚书》学诠释体系,对《尚书》今、古文学融通等多有贡献。汉代《古文尚书》学的发展建立在孔氏家族保持和整理的《古文尚书》之上,孔壁出书是中国经学史上无法回避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周秦时期孔氏家族藏书就显得至关重要。孔壁所出的《古文尚书》资料可靠,对当时流行的伏氏今文《尚书》有着重要的匡谬补缺的版本勘校价值。孔氏家族不仅及时保护了出世的珍贵文献,而且能够根据自身具有的今文《尚书》功底和古文献基础进行整理、释读,适时上献朝廷、下传民众,推动了整个文化学术的发展。
从学术史发展来看,马士远认为,有经未必有学,而孔氏家族学者承继“《书》教”传统,对《古文尚书》的诠释直接造就了《古文尚书》经学,孔安国为《古文尚书》经学的开创者,其嫡系后裔传承其学,到西汉后期逐渐兴起《古文尚书》经学。孔氏家族学者在传承《尚书》学过程中,坚持学术理念,不因权贵世故丧失立场,对于当时的学术风气和文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马士远认为应该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经学史等角度去认识《尚书》孔氏家学的地位和作用。
从学术融通的角度来说,《尚书》孔氏家学大师辈出,能够融会贯通、古今兼治,为后世学术融通树立了典范。孔氏家族学者在汉代学术史上地位显赫,汉惠帝时期的博士有孔腾,汉文帝时期的博士有孔忠,汉武帝时期的博士有孔武、孔延年、孔安国,等等。可以说,孔氏家族学者大都在《尚书》学上有所成就,无论是专治古文,还是专治今文,还是古今兼治,很多是当时学界翘楚。我们知道,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古文经学有学风严谨的优点,也有食古不化的弊端;今文经学有经世致用的优点,但是也有繁琐化、谶纬化的弊端。如果能将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优点加以发挥,同时克服两者的弊端,就会大大促进经学的发展。孔氏家族学者能够做到古今兼治、取其优点,抛弃古今缺点、缺陷,马士远指出,孔氏家族学者不是仅仅为了功名利禄而治学,而是能够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相互纠偏,为后世《尚书》古今文学合璧创造了条件。
三、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
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尚书》孔氏家学的内涵和意义。马士远将《书》教“七观”说视为两汉孔氏家学的核心理念,并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有“《书》标七观”的说法,指出《孔丛子·论书》篇中也有《尚书》“七观”说的相关内容,这与孔子论《诗》提出“兴、观、群、怨”说同出一辙。《书》教“七观”说并不是汉晋时期的产物,而是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孔子作为《尚书》的整理者和传播者,并且用于教授弟子门人、后世子孙,完全有可能创立或发展了《书》教“七观”说。根据《尚书大传·略说》《孔丛子·论书》等文献记载,“七观”说确由孔子提出,虽然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但是恰恰说明孔子诠释《尚书》的言论以不同的学派流传下来,更为可信。
关于《尚书大传》,有的认为是汉代《尚书》今文学派的开山始祖伏生所编,有的认为是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等根据记录伏生教授《尚书》之大义所成[5]。马士远从文献记载考论《尚书大传》成书后在汉代流传很广,夏侯胜曾进行过阐释,郑玄的《尚书大传注》曾转引过夏侯胜的阐释,刘向的《洪范论》是其“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的结果,《白虎通义》更是多见其内容,等等。学界多认为《汉书·艺文志》的“《传》四十一篇”为《尚书大传》,大概是受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等体例影响。马士远认为,刘勰所见《尚书大传》应该是汉代郑玄所注的八十三篇本向隋唐时期的三卷本转变时期的版本,至宋《尚书大传》的流传本还出现过四卷本,而且已经出现前后不伦、版面残缺的现象[1]370。到元明两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著录《尚书大传》,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多为清人辑本。马士远认为,《尚书大传》作为沟通周秦《尚书》学与汉代《尚书》学的桥梁,内容广博,可以据此推断先秦《尚书》学说的具体模式,很有史料价值。“七观”说见于《尚书大传》七卷之一的《略说》卷,虽然《尚书大传》已经失传,但是“七观”说的内容得以保存在一些相关传世文献之中,包括《路史·外纪》《太平御览》《困学纪闻》等都明确引用了《尚书大传》,可以视为《尚书大传》文本。
关于《孔丛子》及其“七观”说问题,马士远首先考辩了《孔丛子》真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阐发。《孔丛子》在宋、明多视为伪书,当代学者李学勤、黄怀信等认为此书不是王肃等伪造,而是孔子家学,可能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孔季彦或其后的孔氏后裔搜集先人言行所编。王钧林则认为《孔丛子》没有作者,只有编者,编者可能是孔鲋,孔鲋没有完成,由其后人继承未竟的事业,连带将孔鲋的言行一并编入书中[6]。根据马士远的统计,“七观”说在《尚书大传》中包括“六誓”六篇、“五诰”五篇以及《甫刑》《洪范》《禹贡》《皐陶谟》《尧典》等,共计十六篇;而《孔丛子》中包括了《帝典》《大禹谟》《禹贡》《皐陶谟》《益稷》《洪范》《秦誓》《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甫刑》等,其中《帝典》无法确定是《尧典》还是《尧典》《舜典》的合称,因此共计十三篇或十四篇。根据其他传世文献考证,《益稷》应该统一于《皐陶谟》,《舜典》可以统一于《尧典》。可以说,《尚书大传》与《孔丛子》有差异篇名只剩下了《禹贡》与《大禹谟》《禹贡》以及“六誓”与《秦誓》的差异。这种差异不能说明《尚书大传》和《孔丛子》就是伪作,反而说明《尚书》学传播的年代久远及学派差异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士远在考辩了《尚书大传》和《孔丛子》中所记《书》教“七观”之后认为,《尚书大传》所记“七观”为观义、观仁、观诫、观度、观事、观治、观美,《孔丛子·论书》所记“七观”为观美、观事、观政、观度、观议、观仁、观诫,两种“七观”虽存在“义”与“议”、“治”与“政”的字面差异,且次序不一,但涵义相同,都体现了孔子《尚书》学的基本主张。
马士远认为,孔子“《书》教”思想是孔子教化思想与《尚书》所蕴含的政治思想的有机结合,义、仁、诫、度、事、治、美等七者是孔子实施王道政治的基本主张,“七观”中的仁、义、美是孔子对《尚书》中所倡导的“德”“治”“事”“政”等命题的扩展与深化,儒家早期的中庸思想也是孔子对《洪范》之“度”命题的把握、提升的结果。马士远用提问的方式,论述了孔子如何可以从“六誓”中观“义”、从“五诰”中观仁、从《甫刑》中观诫、从《洪范》中观度、从《大禹谟》《禹贡》中观事、从《皐陶谟》中观治和政以及从《尧典》或《帝典》中观美,这“七观”集中体现了孔子对《尚书》大义的诠释,这是对孔子《尚书》思想最为核心和本质的认识。
此外,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全书体现出学术史的宏观大气,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尤其是在文献考证方面,体现了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下大功夫梳理《古文尚书》等经典文献,以史料甄别真伪、以理性辨别是非,尽量还原历史原貌,避免了盲信或盲疑两种极端和偏激。对于证据不确凿或孤证的材料,或大胆猜测,或指明存疑,都力求客观全面。在资料使用上,除了书籍文献资料之外,还充分运用新出土的简牍资料、汉碑文献等,将多种文献交互印证,再用多种学术观点推演、判断,补正或修正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不确和谬误,澄清了困扰学术界的很多盲点,具有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还附录了汉代《尚书》传本及其篇名目次总表、汉代《尚书》今文学派传承表、汉代《古文尚书》学派传承表、汉代《尚书》孔氏学世系传承表、汉代学者《尚书》著述总表等,对于继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马士远.两汉《尚书》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2):60-64.
[3]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31-37.
[4]李存山.《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J].孔子研究,2003(3):8-15.
[5]郑裕基.谈谈《尚书大传》和它对语文教学的助益[J].国文天地,2006,22(5):17-29.
[6]王钧林.论《孔丛子》的真伪与价值[J].齐鲁文化研究,2009:19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