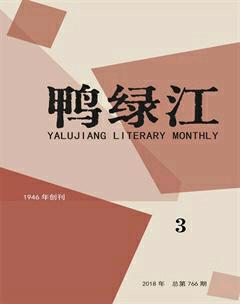悬念在故事中的可能
陈崇正
悬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会因为内聚焦和外聚集的不同而产生效果上的差异。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我更愿意将悬念分为大悬念和小悬念。大悬念直接参与了整个故事的核心建设,能够决定故事是否成立;小悬念则成为故事的调节,能调节故事的速度,影响叙述的效果,制造局部的紧张感。
提到大悬念,我们一般会想起侦探推理、悬疑破案一类的小说,比如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等小说,他用一个大悬念结构了故事,并围绕这个大悬念又设置了诸多小悬念,将主线变成暗线,将小说变成智力游戏。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他善于将悬念与人物的情感形成交织,人物情感的千回百转,也为大悬念的设立提供了合理性。在传统的悬疑小说里,悬疑关乎人物的生死,同时,更重要的是关乎钱财,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一个白富美被一对苦鸳鸯坑杀的故事,背后的杀人动机更多是因财起意。豪华游轮成了屠宰场,为掩盖真相而连环杀人让这艘船成为恐怖游轮。如果我们诟病这个故事设置过于巧合:为什么这么多仇家都聚集在同一条游轮上?故事中给出了解释,但这个解释还是过于巧合。那么,在她的另一部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阿加莎·克里斯蒂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她将所有嫌疑人聚集在一列火车里,但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预谋。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悬念直接与多年之前的一桩绑架杀害儿童的案件相关,而火车中的受害人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这就将悬念与社会正义纠缠在一起了。十二个人对于一个恶人的私下审判,显然是另一种犯罪,而谜底揭开之后我们又觉得更应站在道德层面去看待这个替天行道的举动。悬念解开的过程,也是每个人内心中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这两架天秤之间的纠结和较量。
悬念与情感、钱财、社会正义的交织,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和深度。主人公能否逃过本来属于他的劫难,或者主人公因何而死,这自然成为故事的悬念。而简单地设定了这样一个悬念然后破解它,就显得很没意思。“如果突然一个炸弹爆炸,引起的只是恐慌,并不会有什么悬念;但是如果事先让读者知道桌子底下有个炸弹,而主角却不知道,这样就会自然引起悬念了。”(希区柯克语)所以,设置悬念最怕简单粗暴,将炸弹引爆完事。也就是说,炸弹最终是否爆炸反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炸弹藏在桌子底下为故事赢得了另一种叙事的时间。再换一种说法:炸弹的存在,让故事存在两种不同能量的时间,一种时间属于故事中人,他们的时间十分松弛,没有炸弹;而另一种时间属于读者,他们都知道炸弹就在那里。直到故事中的人物知道了炸弹的存在,或者炸弹爆炸了,两种不同的能量就得到了转化合并,故事中的能量线又重新统一。这是从閱读和写作的角度来审视故事中的悬念,会获得不同的观感。
在具体的故事中,能量的互相转化往往是制造悬念最常用的手段。比如名篇《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于勒叔叔从能量很小到能量大增,及至成为全家的希望,最后发现他穷得要死,一直在船上卖牡蛎,能量瞬间降为负数,而前面所有的铺垫都为了这个能量骤变而存在了很久。《项链》中,一路上能量递增,艰难攀升,结果到最后才发现能量骤变,打开真相原来项链是假的,这就出现翻转,也就是民间说书的“抖包袱”。
在故事中操纵悬念,需要作家有严密的思维逻辑。也就是说,你不能自己写着写着都露馅了,而应该层层包裹,不露痕迹。我们看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如果其中埋藏的结局一早就被拆穿,那就索然寡味了。当然,设置悬念不能变成玩弄悬念,与悬念住在一起的应该还有人性和人心。比如我们阅读《解忧杂货店》,这部在东野圭吾作品中最不像悬疑小说的小说,我们能读到勇往直前的善念,以及对这种善念毫不掩饰的表彰;其中的时空跨度为三十三年,涉及杂货店和孤儿院中众多人物的生死别离,前后时空穿越错综复杂,如果有一个细节对不上,那么整部小说就垮掉了。
当然,大悬念的设置其实是需要承担风险的。金庸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跌宕起伏,悬念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比如在《天龙八部》里头,丐帮帮主乔峰的身世之谜,成为一个巨大的能量旋涡,牵引着我们的好奇心:为什么一个响当当的汉子,偏偏要蒙受如此不明不白的冤屈?冤案、受委屈往往能储备大量的负面能量,在读者心中形成补偿的巨大欲望。沉冤得雪,水落石出的瞬间,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将达到最大的共鸣,在同一个频道之中释放储备已久的能量。当乔峰的父亲现身,与慕容复的父亲双双出现在少林寺中,读者的所有疑问也就得到合理的解答,在少林寺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点,慈悲的佛法最终化解了这段陈年血案孽缘,所有诡异的故事也有了合情合理的回响。也就是说,你的悬念设得越大,悬念在整个故事脉络中越重要,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赌注越大,你必须很好地给出答案,不能草草收场。所以,失败的悬念对于故事的建立有毁灭性的影响,代价沉重。如果你给出的答案早就被读者猜透,或者你给出的答案无法说服读者,你设下的埋伏轻易就被读者识破,那么整个故事也就变得毫无意思。在作者与读者的博弈之中,悬念的棋盘倾向读者,作者也就将一无所有。所有能量的转换最终必须在读者的心中唤醒求解的欲望,而对于人物越关切,这种求解的欲望就会越强烈。
至于悬念在故事中的存在形态,其实取决于写作者与谁同谋:如果写作者与读者同谋,只有作品中的人物不知道炸弹什么时候爆炸,则难免让人牵肠挂肚,总怕主人公踩了地雷;如果写作者与人物同谋,则读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必须看到最后读者才恍然大悟,明白主人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时给出的答案必须有说服力,不然读者就不买账;最难的是写作者设置了悬念,主人公也不知道,读者也不知道,这样就进入了探险揭秘模式,它不单单是牵动一种情绪,更多是在不断挑战作者布局的智商;最牛的还是金庸,有人问小说《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究竟砍下去没有,金庸笑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和类型小说中,悬念的运用比比皆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故事本身的需要,也是说书人的立身之本。在先锋小说兴起以后,小说的各种形式实验被玩坏了,天马行空,飞沙走石,差不多要将故事灭之而后快。沉静下来以后,先锋作家又开始重新思考回归故事。据说马原有一回到格非家里去,对格非说,时代变了,我们可不能再装神弄鬼。格非听了反驳说,你装神弄鬼,我可没有装神弄鬼。先不说两人究竟谁装神弄鬼,也不说先锋小说有没有装神弄鬼,但后来先锋派小说家的集体反思和回归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即便如此,经过一番先锋的洗礼以后,小说在80年代以后已经不尽然是以前的故事,可以说整整一代作家的小说观念由此得到了升级。我们再重新审视余华、苏童、莫言、格非等人的后续创作,就会发现这些作家讲故事不再像“林冲风雪山神庙”那样依靠跌宕起伏的转折,也很少依赖一个大悬念支撑整个故事。更多时候,悬念变成小悬念,穿插在故事的缝隙里,带来了逆转和惊喜。比如格非《人面桃花》开篇父亲出走的悬念,苏童《黄雀记》中“仙女”被强奸的悬念,都属于小悬念。在严肃文学的体系里很难再让作家冒险投资一个大悬念,因为大家的叙事焦点不在故事,而在故事之外。当下在场的作家中,最喜欢使用悬念建构故事的作家,还是迟子建。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彻骨之寒的小说,故事里的蒋百嫂每到停电的晚上就歇斯底里大喊大叫,非常不正常,只因她丈夫的尸体就被冻在家里的冰箱里。这个巨大的悬念中有这巨大的悲哀,让我们看到社会的畸形对于灵魂的扭曲。两个遭逢丧父之痛的人在小镇相逢,各自悲哀,是不同的凄楚。迟子建的另外一个小说,我也非常喜欢,叫《一坛猪油》,这也是一个用悬念手法刻画人物的小说。一坛猪油中埋藏着一个不幸福的男人霍大眼对主人公“我”的深深情意,只有在谜底揭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猪油中藏了一枚祖传的宝石戒指,无比珍贵,再反观屠夫霍大眼来送猪油的情景,才会感受到其中强烈的辜负和无限的唏嘘。最致命的细节是“我”还弄了一根高粱秆来探猪油的虚实,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个人如此真诚地对另一个人,但另一个人浑然不觉,丝毫不懂这个丑男人不求回报的深情,而人世沧桑,转眼烟云散尽,一坛猪油最终成为永恒记忆。
善于利用悬念无疑能增加故事的张力和美感,悬念中包含着讲故事这门古老手艺中灼灼生辉的精髓。无论文学未来走向如何,应该都离不开故事的支撑;只要存在故事,悬念就大有用武之地。就我目前有限的阅读视野来看,悬念正是沟通融合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最具有普适性的技术工具。
人世太闷,如果没有悬念解乏,没有大吃一惊和虚惊一场,那也太无趣了。
【责任编辑】 邹 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