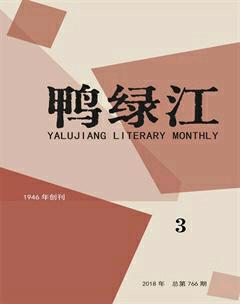瞬间的思想
王威廉
上帝给我们的装备
这是随便的、普通的一天。因为种种原因,我滞留在一家麦当劳中。不知为何在麦当劳无法上网,用自带的网络也不行,出去蹭商店的WiFi也不行,可能是手机的问题吧。但断开了网络连接,导致我无法预约滴滴打车。这里离地铁和公交车站都挺远,我只好站在路边打车。差不多是下午四点钟的光景,打车是最难的,因为恰好是出租车白班和夜班的交接时间。
过了半个小时,我才打到车,然后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刻,酝酿已久的倾盆大雨落下,从下车到屋檐下十几米距离,我如老鼠样狂窜,虽仅仅三秒钟,亦成了落汤鸡。
我是悲伤的。一种莫名的悲伤,一种生活在巨型城市中说不清的烦躁不安。仅仅是连接不到网络造成的不便吗?我站在屋檐下避雨,掏出手机,发现网络又能连上了,刚才也许是环境的什么问题。我用手机看看新闻,却发现诗人沃尔科特去世了。我的心这下真正感到了沉重,这是一名我喜爱的诗人,他在语言中洋溢着的热情与生命力让我念念不忘。
新闻中沃尔科特的照片,看着有点像马尔克斯。一个生于圣卢西亚,一个生于哥伦比亚,也许是加勒比海的阳光过于强烈,他们的脸庞都是深棕色,呈现出一种黑白照片样的效果。所謂加勒比海,因为电影《加勒比海盗》而闻名,但对我来说,那里也是文学圣殿,除了上述两位,还有一位文学大家,那就是奈保尔,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国家译名中的“和”是音译还是汉语的连词。
我想找一张沃尔科特清晰的大照片,但网上出现的全是球星沃尔科特,这个诗人的身影被覆盖了,哪怕这个诗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这个时代,彻底的众声喧哗。这一定会像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好在,沃尔科特的诗还是能找到的。他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只是一个热爱海洋的红种黑人,
我受过良好的殖民地教育,
我体内拥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统,
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
一个人就是一个民族,这是多么强大的自信。也许是离北美也不远的原因,他的诗歌充满了惠特曼的雄浑。“我谁也不是”这句话也很重要,这句话不单单是为了引出后面那句金刚般的话语,它自身也包含奥妙。这里的“我”已经不再是第一句中的那个“我”。第一句中的“我”,可以看成是沃尔科特本人,但是第四句中的“我”,已经不再局限于作者本人,这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的主体,是诗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是一个民族的自信,不是沃尔科特的盲目自信,这种自信,恰恰来自于诗歌本身,伟大的艺术内部。
“我最初的朋友是海。如今是我最终的。”这种对海的深情,也让我动容。我也是有大海情结的人,浩瀚的大海每每让我激动。但大海,是沃尔科特的朋友,朋友之间是平等和相称的,那么,沃尔科特拥有怎样的一个灵魂才能去平衡大海?
这句诗出自他的长诗《“飞翔号”帆船》,这里面流露出了罕见的温柔。
有时我独自一人,伴随温柔剪碎的泡沫。
当甲板变白,月亮开启云门,
我头上的光
是一条路,在白茫茫月色中带我回家。
这样的句子,让我有一种眼睛酸涩的沉郁情感。尤其是想到诗人就在几个小时前,已于八十七岁高龄无疾回家,那种感慨更是深刻。我感到了生命本质的痛苦,犹如一眼泉水,从地底深处不断地冒出痛苦的汁液,这是无法解脱的困境。
这种痛苦,无法与人沟通,再亲密的人,都不行。这是形而上的痛苦,如同黄昏时分在海边的沙滩上迷失了返回的道路。
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说:“你遭受了痛苦,你也不要向人诉说,以求同情,因为一个有独特性的人,连他的痛苦都是独特的,深刻的,不易被人了解,别人的同情只会解除你的痛苦的个人性,使之降低为平庸的烦恼,同时也就使你的人格遭到贬值。”
因此,我也不能对他人言说,我只能写下来。写下之际,那个痛苦的我已经成为过去,即便是我自己,也许都会成为过去那个自己的陌生者。但是,无法忘记的是:那种让心灵鸡汤没法救治的痛苦,那种意识本身的必然痛苦,一种不是痛苦的痛苦,我们必须去接纳它,迎接它的滋养。
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要伴随人一生。诗人米沃什在诗歌《晚熟》中说: “要迟到接近九十岁后,我才逐渐地感到/有一扇门在我里面打开,我走进了清晨的澄澈之中。”这首诗显然是写实,因为米沃什活到了九十三岁。那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居然到了九十岁,才迎接到自己的“成熟”,也实在是够“晚熟”的了。可是,在这样的智者面前,又有谁能够说自己是成熟的呢?
还是这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我可以背诵的:“我们多么可怜,上帝为我们漫长的旅程所准备的装备/我们用了不到百分之一。”人的卑微与无奈,人的未来与潜能,都在这句诗里边。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这篇文章里提到的这些诗人和作家,曾经和我同时生存于这个世界当中。我在读大学时——一个人一生中知识结构形成的创始期,读他们的作品,知道这些人还活着,虽然远隔天涯,无法相见,但是他们活着这个事实本身,给我带来巨大的安慰。他们的巨大存在,通过语言来抚慰我,来庇护我,来拯救我,让我坚信语言与艺术的力量。就像米沃什,他说艺术和语言是人的“第二空间”,我从不质疑“第二空间”的合法性,我还想象那里面有精神的火种可以照亮人间。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对于历史而言,这只是一瞬间,但是这个“一瞬间”发生了太多太大的改变。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大师们,基本已经作古。每一位大师的离去,都会让我感到“第二空间”的版图在缩小。这让我惊慌。我想,上帝给我们的装备究竟还有哪些呢?我没有太大的奢求,我只求我们能用到装备的百分之三就好。也许,“第二空间”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项重要装备吧?我要带好这项装备。至少我深知,这项装备能与那些大师们目前所处的“第三空间——永恒空间”,保持住最后的连接。
关于《加缪手记》
2016年,我购买了太多的书,坦率地说,很多书还没有拆封,但是,有一套书,对我个人而言,有着里程碑样的意义。endprint
那就是三卷本的《加缪手记》。
这是一部由随感、笔记、灵感、独白构成的碎片之书。不过,仔细想来,称其为书都不知道是否成立,因为它完全不具备一本书所具备的条理性。那只是一行行的句子,零零散散,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完全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也不像诗集,在捕捉着精致的意象与语言。这些手记,只是一个作家躲在幕后的喃喃自语。
可我盼这套手记在中国出版,已经很久了。很多年前,读加缪的传记,便知道他有随手写笔记的习惯,这个习惯陪伴着他,直到车祸发生的最后一刻……因此,它的珍贵来自于一个伟大的灵魂:作家在源源不断地把生命的样态注入到这些手记中。即时的、流动的、不可复制的当下,被出自生命深处的语言俘获,时间变慢了,世界敞开了。
不妨把这套书视为一个精神性的空间,一座捕获了时间的语言建筑。我们的阅读,是对作家生命的一次次复活。文学作品的完成,意味着切断了与作者的联系,那些文字终于获得了独立性;而这些未完成的,或者说,把完成置放在未完成之中的,像是依然完好的血脉与神经,连接着另外一端那看不见的生命。
因此,这些手记绝对不是草稿,它是一个作家最隐秘的生命瞬间,它揭示了写作的来路与去处。甚至,能看到究竟是什么在激发着写作的生成。那是瞬间的思想,如事物彼此撞击时强烈而炫目的火花。智慧借助语言,在这样的瞬间中完成了自身,万分迷人,叹为观止。加缪自己也被这样的景象迷惑了,他写道:“我是个写作者。但不是我而是笔在思考、回忆或发现。”这不是什么谦逊的托词,而是一种直觉的感受。
寥寥数语便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他写道:“人们习惯用影像去思考,如果你想成为哲学家就去写小说。”他还写道:“心理学是一种行动——而非对自我的反省。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界定自我。完全了解自己,就是死。”这样的话对我如大音入耳,是难以承受的战栗。
也有小說的构思与片段。有些构思成为名篇,有些构思永远也没能写出。但是,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已经闪现在加缪的脑海里,那些人物和生活从他的世界中得到了滋养,却随着他的艺术想象力跳跃到了别处生长,成为新的世界。作家是一种虚构历史的制造者,那些并不存在的人,那些无名的、可笑的、卑琐的人,突然在语言的光芒中闪现,抵达存在的理解。从而,那些荒诞不经的卷帙,胜过正襟危坐的卷帙。
这是顿悟的智慧,也是加缪在不同生命状态和生活境遇下的真实体验,不可能借由长篇大论,条分缕析,去弄成一个四平八稳笼子样的体系。这些出自生命根基的思想,有着激光一般的精确,它不懂迂回,它只听信自身,它所击中的,往往是沉疴陋习、陈词滥调、蒙蔽教化,不乏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口号。加缪的思想比萨特的哲学更有对历史与未来的洞见,无非因为如此。
类似这种笔记式的哲学表达,自然不只有加缪,还让我们想起维特根斯坦和尼采等巨擘。那两位的絮语也是极为迷人的,但相比较而言,加缪的絮语所构造出的,还是一个作家的世界,也就是说,它永远牢牢立足于生命和语言的本身,不希图僭越,也不试图转移困境,而是真诚与直面。这样的世界,是普通人能够进入,也深得滋养的世界。这与维特根斯坦的缠绕以及尼采的冷漠完全不同。那些天才影响巨大,但是时过境迁,终归不及生命的涓涓细流。是的,加缪不是天才,他只是用尽心力去深情活着的一个普通人,一个男人,一个写作的人。
【责任编辑】 邹 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