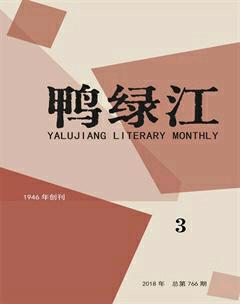《头发的故事》:鲁迅晚清一张奇特的写照
[美]+周杉++译者+史国强
20世纪之初,一批颇有创造力的作家宣告现代中国文学从此开始,在这批作家中鲁迅的成就最大,其地位也最为显著。之后鲁迅早年的小说和杂文所引领的类型与题材成为新文学的一大特点和新文学最初的楷模。鲁迅以自己的写作,以新文学这一形式探讨与民族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同时,个性鲜明的人物和无法模仿的句式,也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家。此外,他驾驭语言的能力还证明,白话文作为一种严肃的写作方式是行之有效的。鲁迅从一开始就在风格上把新文学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其中有鲁迅个人魅力的因素,但又与他笔下人物的魅力互为依存。总之,在大变革的时代塑造个性化的现代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几乎在中国新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他的印记,后来新文化的特点又在五四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彰显。
如何评价鲁迅,这一问题几乎从他逝世之后就已经开始,而且从未消退。在鲁迅研究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个分水岭。在此前的半个世纪里,大陆的鲁迅研究被“左”倾人士所左右。在漫长的五十年里,因为鲁迅是毛泽东推崇的作家,所以要对他不停地大唱颂歌。80年代中期之后,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研究成为可能,鲁迅的遗产再次引发极大的关注。此时,人们开始重估鲁迅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五四文化。政治环境宽松之后,文学几十年来第一次再也不必被迫歌颂社会现实,因此,研究有意义的、连续不辍的现代文学传统才有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这一系列逐渐形成的变化,连同西方和日本鲁迅研究取得的众多成果,共同达成了一个结论:要定义鲁迅的遗产,更为困难。如今,中外学者从新的角度研究鲁迅,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真实的鲁迅将与那位生前被人崇拜的作家有所不同,也比政治宣传的那位楷模更为有趣。
研究范式正在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拙文才试图刻画出更为丰满的鲁迅。为此,拙文从鲁迅生活中选取了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著名的时期和一篇令人费解的小说,最终要说明这个时期和这个故事能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鲁迅的写作和人生。下文讨论的小说就是那个奇怪的、很少被人提及的《头发的故事》,时间从鲁迅1909年自日本回国至1911年共和肇始的两年,这两年也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故事的题材和自传性的关联正好用来分析与作者相关的那些问题。《头发的故事》写的是辫子,鲁迅写辫子,写到旁人,妙笔生花,写到自己,又语焉不详,这一点我们将在小说里见到。在辫子的问题上鲁迅没有一视同仁,拙文正是从这耐人寻味的地方开始的。提到别人的辫子,鲁迅能以通俗的文字和独特的技巧将实实在在的现实与文化象征提炼出来。七斤和阿Q尤其令人无法忘怀。比如《风波》里的七斤,共和革命那年他进城后被人剪去了辫子。小说一开始,传言说皇帝要回来,又要辫子了,七斤听后惴惴不安。在《阿Q正传》里,现代中国大名鼎鼎的阿Q,头上也有一根辫子,这辫子虽然是点缀,但意义还是有的。阿Q的辫子在故事里多次出现,一次阿Q与他的对手小D相遇,二人扭打成一团,互相抓住对方的辫子,同时用空出的手护着自己的辫子,最后双方力竭,不分胜负,其打斗的姿态无不与辫子有关。这些寓意深刻的故事出现在现代文学发生之初那几年,读者将其视为他们自卫性的自我和他们所在民族的写照。这些故事,连同那些犀利的文章,很快就把鲁迅推到现代文学最高的位置上。
上述故事是对国民性的鲜明写照,但几乎没人注意,在这些故事里,这位著名作家还有一幅自画像,提到了他的辫子——或没有辫子。从细节上说,鲁迅的经历与其创作的人物不相上下。他1902年抵达日本,不到半年就剪掉了辫子。如他在1936年的文章里所述,1909年回国后,他身上还有一根从上海买来的假辫子。在故乡绍兴,他发现家人和乡亲对这件东西格外好奇,在“装了一个月”后,就扔到了一边,再次穿上西装。他的短发和其他装束已是一目了然,在街上引来一次次的嘲讽。鲁迅先在杭州教书,之后又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教务长,此时旧传统依然存在。在那两所学校里,他先是被上级怀疑,继而又因为拒绝建议学生剪掉辫子被他们所轻视。1911年革命之后,鲁迅北上京城,结束了生活中的这一阶段(《病后杂谈之余》)。
上文提到的几件小事,为鲁迅写传的作家很少提及。那些固定的话题才是他们总要提到的:鲁迅的教职、教授的课目与方法、他在学校的进步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这些事实有时能得到合理的分析,①但更多的时候成了研究者寻找鲁迅后来与政治关联的素材。②与此形成对照,假辫子、谩骂、学生就剪辫子提出的问题等就少有提及,读者只有在鲁迅的大传里才能找到,③如卜立德(Pollard)所指出的,这些传记把现有的材料一股脑地寫入不分彼此的一大卷。然而,事实上鲁迅不止一次提到了自己的那些经历,如1920年在《头发的故事》里,此外在1926、1935、1936年的文章或其他小说中也提到过。
那些诱人的信息没有流传开来,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原因之一与鲁迅的写作手法有关。当辫子与鲁迅的个人经历稍一接触,这位文笔犀利的作家就不再使用他用在阿Q或七斤身上的那些闪光的画面或鞭辟入里的比喻。一碰到鲁迅的个人遭遇,读者就读不到那些因困顿生发出的不安和教益。为了理解这些与鲁迅生活相关的因素,拙文将一一指出并探究那些削弱作者写作效果的文学特点和作者的情感,同时剖析那些令批评家和传记作家颇感迷惑的地方,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鲁迅,因为他个人的心理总是个有趣的话题,同时更好地理解他的写作手法,尤其是一些文章和《头发的故事》等不被重视的小作品是如何写成的,最终理解这些作品与写作手法之间的关系。
虽然鲁迅的态度和表达方式使我们无法对其亲身经历一目了然,但好在这里还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小说叙述的话题:辫子(或没辫子)。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希望纠缠他民国之前的经历。在描写鲁迅的文字里,也很难找到与辫子相关的事件。问题不是不知道辫子的存在。相反,辫子是人人皆知的。辫子是满人1644年入关后强迫推行的发式。民元之前十五年改革者就提出要剪掉辫子,后来剪辫子被视为反抗满清的标志,不久又成为拥护革命的行为,所以等到1911年革命成功后,剪辫子已是明日黄花。问题是,这些为人所知的事实皆为政治史的素材。与之相对,鲁迅所写的故事不在人们熟知的民族斗争的范围之内,更确切地说,是辫子演变史的一部分。《阿Q正传》和《头发的故事》里的讽刺,其感染力并非来自排满情感,而是来自身陷新旧国度之内个人的一片茫然。以结构上更为简洁的《风波》为例:其中的人物——不仅是七斤,还有七斤嫂、众乡亲、高人一等的店主——就个人经验来说,辫子的意义在他们那里已经打了折扣,是政治象征所不能涵盖的。因为鲁迅在《风波》和《阿Q正传》里牢牢地把握了语调,所以读者轻易就能从人物身在其中的尴尬里品到乐趣,虽然他们稍感苦涩。不过,一旦作者自己成为话题之后,主人公如何应对周围的变化,要从中发现合理的解释就大为不易,原因是作者的引领少之又少。endprint
与鲁迅的辫子相关的话题,从下文引用的小说、回忆文章到鲁迅早年的方方面面,因为读者态度谨慎,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无从说起。首先,在读者的心目中,即使当初人人有辫子,拖着辫子的鲁迅也是不可想象的。(至今还未见到鲁迅留辫子的清晰照片,这也加固了他在后人脑海里的形象。)如此一来,说到他的辫子大家是三缄其口,下文提到的画面就是两个例子。画面上的是鲁迅一生中为后人熟知的时刻。一幅是木刻,画的是1898年少年鲁迅离家赴南京接受现代教育,为赵延年(1924年生)所作,他选择的角度和明暗对比法似乎有意遮掩画中少年的辫子。张祖英(1940年生)的油画也是如此,画上是1902年将赴日本留学的鲁迅,一名学生站立船舷,凭栏凝望,目光中充满活力与使命感。鲁迅身后乌云排空,烘托出作品的感染力。我们知道此时的鲁迅身上还有辫子,但画家选取人物正面,把辫子挡在视线之外,而且额头上方画上了头发。①以上作品表明一种不安,这不安与鲁迅作品中自己的头发是分不开的,又使这些作品在研究中遇到的批评减少到最低程度。上述态度对鲁迅作品和辫子话题的接受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从这些作品设定的限度来说,这也应成为作品分析的一部分。
必要性就成了问题。就鲁迅的生活而言,读者更熟悉他公开的那些信息,这是必然的,如他在《呐喊·自序》里说自己的身世。材料少还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鲁迅的心理。这里我们能看出鲁迅的另一面:沉默。对一位著述等身的作家来说,不说话也能表达意义。1906年鲁迅与朱安成婚,1923年后与弟弟周作人失和,但鲁迅对此绝口不提,这两件事对鲁迅来说显然不是小事。鲁迅在这两件事上的沉默是众人皆知的,没人无视鲁迅的沉默,对此进行的研究也有不少(如孔慧怡、McDougall、俞芳等)。①此外,鲁迅的沉默还有一例:此时经过八年的短发生活和新式知识分子洗礼的鲁迅已经从日本回国,其重要性也将在下文一并讨论。
作为钥匙的《头发的故事》
研究民国之前的鲁迅,他当初的经历在《头发的故事》里的表述方式就成了一把钥匙。②按照小说的内容,不定冠词a要比定冠词the更合适。请比较“A Story of Cats”与“The Story of Cats”。不同的名字说明内容有所不同。为使二者有所区别,我使用了介词about(如“A Story about Cats”)。故事写得很奇特,连批评家也不知其中的所以然。因为《头发的故事》被划入小作品之列,所以研究的人不多(其他小作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或是为鲁迅说句公道话,或是充实故事的内容。下文的分析不是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而是为了提高我们对小说的理解,使其成为鲁迅作品研究的一部分。
故事梗概是必要的。虽然标题已经指出小说的大概,但其中的不少话题不过是松散地相互关联,作品总的目的还不清楚。此外,从梗概里我们也能看出,小说里的信息毫无遮掩,但情感取向又令人不好把握,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头发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开始,叙述人揭开一张日历,发现已是十月十日,之后自言自语说,双十节在日历上也沒记载,前辈同事N听见后不满地回了一句:“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N插话进来后开始兀自说了下去,到小说结尾才停下。叙述人不过是插了几句话。起初,N抱怨人们没有铭记双十节,批评他们在警察吩咐后才挂出旗来,到了晚上又忘了收旗关门。他说自己也是个忘却纪念的人,之后话锋一转,从揶揄转为严肃,因为双十节总让他回想起痛苦的往事,革命时的众多少年被囚禁,遭酷刑,或是被暗地里杀害,他们先是被人恶骂,如今连坟墓也被人忘却。
这时叙述人建议N换个高兴点的话题,N听后开始讲述,从头发的故事开始,旁及其他话题,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鲁迅的亲身经历或他的兴趣所在。N现出笑容,说革命之后他在路上不被别人笑骂了,之后提到辫子的来历,清人入关后如何强迫留辫子,太平天国时祖母那辈人如何左右不是,官兵要辫子,长毛不要辫子,N又说他在日本读书时剪掉了辫子,后来他们的监督也被人剪掉了辫子,N回国后买了一根假辫子,在路上被人笑骂,他拼命用手杖打了几回。他还说,一个日本游客不懂中国话和马来话,就拿上手杖,说他们都懂。N说自己在中学做监学,因为头上没有辫子,同事都躲着他,但学生又请他支持他们剪辫子。第一个双十节后,N来到北京,数月之后辫子风波才消退。N不再讲述自己的头发,此时小说也接近尾声。最后他提到当时的女子因剪了短发考不进学校。
接下来是三句神秘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反思:一句引自阿尔志跋绥夫,说革命承诺一个黄金的未来,但对今天却毫无用处;一句说中国不大可能发生变化;第三句以尼采式的比喻提到毒蛇。最后N发现对方无意听下去,于是收住话题,起身取帽道别。小说到此为止。
即使从这个梗概里也能发现几个问题。对读者来说,小说写了一系列的感慨与奇闻,但结构松散。就连那些视鲁迅为完人的批评家也承认“风格跳跃”(卢今)。①还有,虽然小说陈述了不少信息,从史上的轶闻到新近的时事再到N过去的经历,但各个部分既无法独立存在又不能相互贯通。即使把N独立出来,读者也不能下结论:这个故事就是披着外衣的自传。确实如此,鲁迅研究者们为寻找传记材料,哪能放掉任何线索。要是有人偶尔把小说当成素材,划入传记之列,也非易事。
这个故事不好破解,其中还有另一原因。1935年鲁迅在文章中说,他个人的经历与N相同。虽然与N的巧合很可能从来也不是秘密,但外人是在1935年之后才知道的,所以,此时读者才把鲁迅与N联系起来。因为真相要等到鲁迅生命最后一年才为外人所知,所以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头发的故事》写的就是鲁迅的故事。即使在鲁迅的话公开之后,也没人从新的角度研究《头发的故事》。此外,鲁迅提到自己与N的关系,语言依然晦涩,这也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鲁迅的文章分为五个部分,与《头发的故事》相关的话出现在第三部分里,文章表面上以历史为题,写他逐渐发现明清王朝的凶狠及最终的覆灭。①最后还有一点,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并未提及《头发的故事》是如何写成的,所以,虽然鲁迅在文章里提到他与N的关系,但并没有引起大家对小说的注意。endprint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使剖析《头发的故事》越发诱人。鲁迅晚年三言五语提到他与N的关系,这说明要剖析的并不仅是一篇被忽视的小说,也不仅是比较信息相近的两个作品。小说1920年发表,1935年的文章又道出了小说原型,所以小说与文章之间的关系才是研究的目的所在。我们从这一关系中发现的东西,并不仅仅是鲁迅在民国之前的经历。我们将发现更大的问题,鲁迅就自己说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说出来。
借文学来推迟和遮掩要说的话,这是鲁迅明显的倾向。推迟的目的是遮掩或欲说还遮,因为他要说的话是一时的自我感悟,未必能引起外人的关注。对鲁迅来说,以这种方式道出真相,既是写作特点又是个人倾向。推迟与遮掩大概是鲁迅辛辣文风的相互对照,凸显出他毫不退缩的率真。不过,鲁迅不希望公开隐私,这是众人皆知的,拙文提出的仅仅是又一例证,一个比普通现象更为有力的证据。在鲁迅那里,事物演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行——过去的时光在他的心灵中不停地徘徊。如他在著名的《呐喊·自序》中所说:“而我偏苦于不能完全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由来。”上面的话对《头发的故事》里的记忆来说,是格外真实的。韩南(Patrick Hanan)的评语也道出了一个有趣的特点:“鲁迅个人经验中的成分写入他的小说,一般是与其个人的良知和愧疚相关的”。①
分析之前我要强调:《头发的故事》与鲁迅此前的所有小说都不一样。虽然也有相同的地方,主要是两点——一是缺少情节,二是小说与他生活中的事实相关——但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实为例外。一如《头发的故事》,鲁迅的一些早期小说,素材来自他的生活,但另外一些小说都是虚构的,杜撰的情节,杜撰的人物。但在这其中的两篇小说里,他并未刻意遮掩个人的经历,所以《一件小事》《故乡》又有所不同,写的就是当时的事,不是过去。总之,《故乡》有完整的情节。虽然《一件小事》速写的成分要大一些,但速写也是19世纪欧洲短篇小说确立的一个亚型(subtype),鲁迅对此是有研究的。②后来鲁迅在1933年又详细描述了他的写作手法:“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③
鲁迅的小说强调故事的连贯性和文字的表现力,他也将此视为自己的写作手法,但在《头发的故事》里确实看不出他有此用意和目的。读者还以为这是鲁迅的早期小说,是现代文学发轫之初的作品,其实不然,那些新作家还要探索写作技巧,但鲁迅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从一开始他的所有小说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他此前创作的六篇及此后不久的两篇,虽然各自大不相同,但就技巧和目的而论,堪称短篇小说的楷模,无一例外。④他的写作技巧也不是才练就的。他的功夫早在1909年就练成了,当时他与弟弟翻译了欧洲短篇小说大家的作品,取名《域外小说集》。其时短篇流行,鲁迅从中选译故事,足以悟出其中的技巧,小说集的出版也证明兄弟二人成熟的目的(Semanov)。⑤此外,1920年3月,《头发的故事》发表的同年,鲁迅又回到《域外小说集》上,希望再版这部译著,撰写新序。①在短篇小说上鲁迅一贯严谨,所以《头发的故事》没有連贯性,问题不在技巧或能力上。原因究竟如何,拙文将一一探讨。我的意见是,这表明鲁迅在头发话题上的情感从文学的角度很难定性,所以小说资源提供的艺术拆分在这个问题上是行不通的。
小说的创作
线索之一,小说应上海《学灯》之请,为10月10日特刊而写,《学灯》乃《时事新报》颇有影响的文学副刊。这一信息很快被读者遗忘,因为,虽然最初的读者还能见到发表日期等相关信息,或许也能猜出是应约之作,但后来的读者是在小说集《呐喊》里读到的小说,所以无从知道。②如此说来,选集里的解释并不全面,因为就算约稿一事能解释鲁迅动笔的原因,也无法解释他为何写了这个故事。如上文梗概所示,小说一开始那几句挖苦忘却双十节的话还与纪念相关,其他都是自由联想。
线索之二是1935年的文章《病后杂谈之余》,文中鲁迅谈到回国之后的亲身经历,不少复述的细节并未发生变化,如辫子的来历、剪掉辫子惩罚奸夫的习俗以及他的个人经历。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自由联想的材料来自何处,但没有说明在小说里使用这些材料的原因。
结合以上线索,据我推测,《头发的故事》是专为杂志之请才写的,因个人的回忆写走了,到了结尾才回到正题。作为专稿,一开始还有个固定的题目,虽然中心还不存在。等到叙述人建议“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吧”,小说转入1911年之前作者与辫子的经历。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和信息取自作者的个人生活,分毫不差,所以必是作者有意为之,但又不像他的事先安排,而且始终没有中心。记忆没有按照顺序出现,也没有推进。N的古怪和脾气被作者信手拈来:N的自言自语如意识流,没完没了,叙述人并没鼓励N,但他还是兀自说个不停。说到最后,N提到少女剪发一事,此时作者试图把小说从个人回忆里收回来,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少女剪发后不许上学,这在当时是一大新闻。那年一个来自绍兴的少女就因为头发的问题投宿在周氏兄弟的宅子里,所以这事与鲁迅个人也有联系。①为把答应的稿子写完,才有了N的最后那句,好在那一天就要过去,明天不再是十号。如我所说,《头发的故事》结构之所以别扭,与杂志约稿有关,这也能解释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写的都是现时,但其他地方小说写的都是过去,而且并不连贯。
关于写作过程中故事走向发生变化,上文就此提出的分析还能从小说的外部找到一些证据。从周作人那里我们才知道,被叙述人称为“前辈”的N与夏穗卿相仿,此人在教育部确是鲁迅的前辈,说话口无遮拦,与小说里的N不相上下。②这能说明鲁迅开始不是想写他自己。这无意中的转向还发生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为了找回原题就与N谈起了剪掉头发的女学生。等N以几句晦涩的评语结束其独白时,他已经回到作者关注的话题上。N引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那个月鲁迅正在翻译他;③N用了一个尼采式的句子,鲁迅1920年也用过;④N说只有造物的皮鞭才能造成中国的变化,连同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鲁迅三年后在其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里也使用了这一生动的比喻。有趣的是,《呐喊》出版后,茅盾发表评论,N最后这三句感慨是茅盾从小说里挑出来的,茅盾认为,这些话自然能说明作者的心境。⑤endprint
《头发的故事》是按题作文,这也是小说结构形成的原因。在《头发的故事》之前,鲁迅那些严谨的小说,无一不是自发的结果,进度因作者而定(速度慢)。⑥鲁迅写完第一批小说之后,编辑们就继续约稿。他写道,他很幸运,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所以从不强迫自己写小说。⑦因此,这次答应写小说——至少他要写小说的话——未必就能信手拈来。我们要问,鲁迅真要写小说吗?他以第一人称开始,叙述人就日历上的日子发了一句感慨。之后N进来聊天,因为第二个虚构人物的出现,故事开始朝着小说转变。这一特点还出现在《阿Q正传》上,徘徊不定的第一人称开讲之后,才慢慢转向小说,叙述人的学究式的“考据”占据了第一章,等到第二章人物和行动才出现,这部小说也是应约之作。最后《阿Q正传》写成了小说,但《头发的故事》没有,原因上文已经提到。
还未消化的记忆、还未改变的情感、还未统一的动机——这个小说他为什么不再写一次?从理论上说,这个不连贯的故事可能是一次沟通小说与散文的试验,但事实上又找不到这种企图的证据。答案可能来自两方面,为杂志赶稿造成的压力——他十天后将小说送出;①再写一次也未必能改过来。如果把小说改成文章,不连贯的材料就不是大问题了——鲁迅的文风是打了就走,不是逻辑推演——但如此一来就要挪走N,作者自己就要站出来。结果鲁迅写出了小说式的杂文,如李欧梵所指出的。②在后来的杂文里鲁迅再次提到那些事件,这说明杂文这一形式更适合不连贯的记忆。比如1936年因鲁迅逝世没有写完的一篇杂文就适合众多话题,他在清末不拖辫子也是话题之一。
其实鲁迅没兴趣解释,虽然他说过他选择写作是为了唤醒中国人。两年前他出版《狂人日记》,当时的文化环境根本不适合阅读这种寓言式的作品,但鲁迅一句解释也没有,也没写序文。后来读者在印数有限的杂志和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他们的读后感。③《头发的故事》发表一年之后,《阿Q正传》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读者的惊呼和误解,原因之一是他用了新的笔名,结果读者无从寻找笔名鲁迅为人所知的语境。在这个小说里,似乎没理由指望作者写出另一个故事来。
《头发的故事》只有对读者来说才是小说。N的话就是鲁迅要说的话,因为以小说的形式出现,所以作者才能退到后面。故事的自传性质,十年之前只有他的熟人才能知道。还有,小说发表十五年之后,小说里的事件发生二十五年之后,一般读者才能知道故事的真相。这能说明,对作者来说,推迟和伪装是自发的行为。或许我们要把1929至1920这十年视为不同的推迟:因为鲁迅1918年才开始写小说,所以他把自己的过去写进小说,更适合我们发现他不为外人所知的心理根源。这里讨论的推迟,发生在故事里的感情发泄与1934年之间。鲁迅进入晚年之后才在文章中表明,故事里N的经历就是他的经历。一些传记作者以有限的方式注意到鲁迅的话,但他的话并未引起他们对小说的关注。就连那些可能关注小说的学者,也没有再次研究,原因大概是小说里自传性的材料有限,从文学的角度写不明白。拙文接下来将要寻找小说与自传之间那些复杂的关系。
小说的分析
回答有关鲁迅的问题,先要厘清N的角色。N为什么大发感慨,过去的经历为什么仍然令人无法忘怀,N如何看待生活中那些令他不满的人,要理解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这些问题又是理解一部文学作品所不能回避的,当作品的弦外之音不好把握时,对上述问题就更要关注。总之,我们遇到的不是一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必然指向鲁迅:我们知道,N就是鲁迅,但N的感慨是不是鲁迅的呢?不折不扣都是鲁迅的吗?这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所以才有必要剖析《头发的故事》。
同一件事几次描述又不相同,或是不太为外人所知,或是令人感到意外,这是少见的现象,我的分析就从这里入手。先要分析两组段落,第一组里有五个要点,第二组里有三个(见下文)。各组第一段选自《头发的故事》。每段文字都讲述了N的进退维谷:第一段,国内显然是反对短发的,他回国后如何是好;第二段,学生要剪辫子,问他的意见,他如何回答。显然,N是左右为难的。鲁迅在其小说里化解这种矛盾总能驾轻就熟。但在N的问题上,鲁迅没有,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他的作品。通过分析鲁迅对N的态度,之后要找出理解N的难点所在,最后能发现这些风格特点在其他段落里的再度出现。如此分析是为了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加深我们对《头发的故事》的理解,拓宽我们对作者的认识,而不是为了一般的文本比较。
我们将探讨几个提到短发的段落。第一段选自《头发的故事》,其中说话的人是N,他脾气有点乖张,是叙述人的“前辈”,是个不必与他较真的怪人,因此才任他自言自语。在这个段落之前,N说到历史上因发式引发的矛盾,之后话锋一转,说到他自己: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等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①
N的话里充满晦涩,以上引文便是明顯的一例,所以读者才不知所云。这些文字的特点下文将逐一讨论,以便分析其他例子时,再不必如此繁复。
引文里N的行为和感情,如鲁迅所描写的,始终不好把握。先说第一点,作者对如何回应N剪掉辫子一事,并未提供明确的指向。但当时的读者一定知道,剪辫子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摆脱满清统治,恢复汉族身份。从众心理是额外的原因,可能不那么崇高,但对个人来说必然重要。但N对自己剪掉辫子不作任何解释,不过是说:“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鲁迅在其他小说里使用过众多技巧,如对话、人物、描写、语境等,借此表达对人物行为的态度,但在上述引文里,鲁迅没有表态。对N后来的行为,鲁迅也没表态。N才从国外回来,对他来说,掩盖短发这一决定,必然涉及复杂的情感,但鲁迅仅仅让N说:“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endprint
之后N决定脱掉假辫子,穿上西装,朝骂他的人打手杖,至于如何理解这些行为,从上下文的语境里还是找不到线索。N的行为和想法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有据可依,比如,可能不光彩,可能无法避免,或二者兼而有之,但读者不知其中的究竟。在读者那里,N似乎还能博取有限的同情,这是往好处说,要是往坏处说的话,他就是个懦夫,是个恶棍。也许读者的资格仅仅是观察,不是判断——或二者兼而有之。反话和讽刺频频出现,这是必然的,但这些技法不好把握,要用一件件伪装,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才行,或许鲁迅的这个故事披上了太多的伪装。不过,在N的叙述里要写入多少自我意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鲁迅好像也不知如何是好。说话含糊其词的不是别人,是那位在第一部作品里就以熟练的技巧把握疯人语调与视角的作家。这说明,即使在十年之后,有关头发的经历,其性质还是不好把握,其述说还是令人局促。
接下来我们在一个小段子里才发现,N的处境是以读者能理解的、不必诉诸道德的方式描述的。这段文字出现在N说他在道上用手杖打人之后。读者正要分辨孰是孰非,但鲁迅话锋一转,其文字更加晦涩。N说:“这件事很使我悲哀。”他说在日本读到报上对一位日本旅行者的采访,这日本人吹嘘说,他不懂中国话和马来话,但他发现人人都懂他的手杖。N为此气愤了好几天,但他接着说道:“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鲁迅的几句话就化解了一个困境:N早就在報上知道手杖的事,但还是“不知不觉的”扮演了他憎恶的角色,使他的中国同胞扮演了被强加的角色。以三言五语概括复杂的处境,并不说明孰是孰非,鲁迅贯以这种巧妙的手法化解矛盾,但在《头发的故事》里,这还是少有的例子。
读鲁迅的小说,要从字里行间寻找线索才行,因为鲁迅的观点很少浮在表面上。即使表面上一清二楚——比如,N那些好事的亲戚端详他的辫子——读者也不能据此推测,鲁迅要谴责这些亲戚,因为鲁迅的反应总是复杂的,就算这不是N的反应。要是没有线索的话,很多情节就能引发出不同的道德判断。这一现象从鲁迅画传的两幅插图也能看得出来,画传是1953年两位画家和两位作家共同创作的(正慧、青山编辑,文西、一蒙)插图。插图从上段文字中选出两个场景,道德高地都在鲁迅一边(但并不是N,虽然《头发的故事》是插图的唯一来源)。第一幅插图里的鲁迅锁眉攥拳,显然是强压怒火。他面前一个老者正责备他,他身后两个留着辫子的亲戚正乐滋滋地端详他的假辫子。插图上的鲁迅一脸怒容,当然读者也可以说,此时的他感到痛苦或羞辱,但后两种情感与道德环境不符。第二幅插图里的鲁迅身着西装走在街上,面无表情,一个路人正把鲁迅指给同伴。据图上的文字,这说明鲁迅“不怕社会的压力”,虽然小说没这么写。为了避免道德上的纠缠,插图并未描写鲁迅用手杖打人。事实上,手杖没在画中出现,后面我们还将发现其他变化。
道德判断还能推演出其他结论。比如,许钦文指出那些骂人者冥顽不化的原因,希望以此来为所有的人开脱。大概他发现,让普通的中国人强烈拥护辫子,反对短发,怕是不好自圆其说。或许出于同一原因,插图把笑骂弱化成指指点点。总之,许钦文是鲁迅的信徒,与周家又有关系(他的妹妹就是在周氏兄弟家里借宿的短发学生),他以这个身份说话,将故事的矛头指向那些谩骂N的旁观者。在许钦文那里,这些旁观者代表“盲目的保守主义”,但他不想深责他们,他还说这些人“被统治阶级操纵,被封建观念毒害”,所以才“麻木不仁”。①他对中心人物、鲁迅的替身要承担责任这一敏感问题却只字未提。其实,那些骂人的人很可能来自社会底层(虽然画面上他们身着长衫),因为N能用手杖打他们。这就与道德发生了关联,但鲁迅的地位不同一般,许钦文是写不出来的。《鲁迅画传》1956年出版,作者(此时)已没有其他选择,但他的特殊身份为后来的批评家们定下了调子。
再说鲁迅,我们可能要问,他打过骂他的人吗,如小说里的N?这一问题又能推演出与文学和传记相关的问题。鲁迅没说他打过人,从一般印象里也推演不出他动粗的结论,不过,在分析这一小说证据之前,还不能轻易将其排除。如果在这件事上N的行为不是鲁迅的行为,那么打人一说就是作者虚构的,而且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小说里的其他事件都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如果我们相信鲁迅没有打人的话,我们就得同意故事里仅有一处是虚构的,这也是文学原理。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了相反的解释。他一定发现了这唯一的例外在文学上是成问题的,因为他含糊地指出,还有其他的例外,小说写的是真事,但有“一两个地方”是“小说化的”。换言之,据他的意见,《头发的故事》在事实与虚构之间。他据此断言,打人“并不是事实”,虽然他并未指出另一个虚构的地方在哪里。不过,他承认,另一件事与手杖打人关系最近,报上有关日本旅行者的采访,鲁迅确实读过,而且读后一连数周深感不安。周作人试图证明鲁迅不仅没打人,而且绝无可能。他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鲁迅1903年的一次省亲上,写道:“那年,住在国内,他外出时才戴假辫子,所以戴得次数不多。”又写道:“此时鲁迅大概戴假辫子才有几次,所以骂他的人不太多。当时我也在国内,所以我知道。”①接下来周作人写到乡下人为何讨厌假辫子,表面上是要讨论鲁迅提到的嘲笑,虽然周作人并不承认嘲笑的意义。与此不同,《头发的故事》讲的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我们可以说,小说是虚构的,其中不足为信的证据是容易打折扣的。鲁迅的完人形象有着坚实的历史和众多拥护者,对这一形象进行一次次复杂的分析,能在文学上更好地把握《头发的故事》。不过我们可能发现,作者之所以提到打人,目的是向读者传递更复杂的想法,而非简单的责怪。
将读者的注意力指向1903年,或至少离开1909年,这等于为批评家和传记作家避开了令人尴尬的问题。鲁迅在小说和文章中说他的经历是最终回国之后发生的,他明确指出,他的假发戴了“一个多月”就扔了。但周作人又为1903年的省亲提出了不少确凿的证据,黄乔生也在传记里暗示,辫子是上次回国(时间不明)时买下的,没提1909年买辫子的事。②那么,鲁迅是不是每次都买了假辫子,他上几次回来没有领教过吗,要是上次已有所知的话,为什么后来还感到痛心?以上可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鲁迅自己提出的问题有关。如拙文的一位读者所说的,虽然日期是1909年,但鲁迅在1935年的文章中,将过去写入了一个记忆,《头发的故事》的写作也在其中,比如,假辫子的价钱也不相同(小说里是两元,文章里是四元)。endprint
就鲁迅提出与虚构的N相同的问题,这是顺理成章的,但因为话题敏感,提出的问题不免让人尴尬。所以屈正平才分析手杖,引用N就日本游客所发的感慨,说N“气愤了好几天”,但他就是不提N用手杖拼命地打了几回。③他的写法与插图的画法不相上下:省掉手杖。不牵扯N,就是不牵扯鲁迅,免得说不清。卢今的办法与屈正平有所不同,盧今反复用“前辈”指代N,以此强调N与作者的距离,指出他们在年龄上相差很大(据夏慧清,不过是十六岁),因此他们的经历大不相同。④
一般来说,人物与人物的作者不能等同,虽然他们经历相同,所以将人物与作者混为一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面对的问题与此相反。鲁迅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说明他要保留一定程度的隐私,不希望牵扯进自传性质的写作之中。鲁迅把N写在小说里,也许是让读者评断,当然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无法把握,这时作者却站在外面。为了与N保持更大的距离,作者还在故事里写了两个叙述人。如果读者要对号入座的话,那也要选择那个听N絮叨的叙述人。所以,无论是从传记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如此安排叙述结构,鲁迅都不必为N的行为负责。
我们要比较的第一个段落与上面的引文竟如出一辙。《头发的故事》才发表一年,我们就在《阿Q正传》的第三章里发现了相同的经历,其中一个人物头戴假辫子,一根棍子不离左右,他就是鲁迅笔下著名的假洋鬼子。他是钱家的人,钱家与赵家是庄上的大户,一贯媚上压下。文字如下:
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 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
对方还拿着手杖,因为阿Q刚说出“秃儿”,就发现,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①
这场面是读者熟悉的,与《头发的故事》形成平行结构。钱家少爷的特点与N的特点如出一辙,大概也如N的特点,取自鲁迅及其同代人的经历。不过,读过这个段子的人有谁不知道应该对假洋鬼子采取怎样的态度?八十几年来没有读者不知道。他在钱家的身份,仅此一点就能判定他在读者那里的印象。阿Q那些在当时很是流行的修饰语——秃儿、假洋鬼子——不过是公开地表达了大家的评断。
几乎《头发的故事》里的每一个成分在《阿Q正传》里都颠倒了。那里没有的价值判断和叙述倾向在这里跃然纸上。令N感到极为痛苦的“假洋鬼子”这一称谓,用在钱家少爷身上才名副其实。N在讲述中对路人的嘲讽深恶痛绝,现在这态度成了主人公阿Q的态度,因此,其有效性得以确立,虽然方式有些扭曲。读《头发的故事》,无法对戴假辫子进行评断,但在这里却是泾渭分明的,而且评断是透过阿Q那刁钻的视角投放出来的:“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他对此还嫌不够:“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N那些让读者不知所以然的行为在这里也变得清晰了:假洋鬼子买假辫子,结果只能成为笑料;他打阿Q,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他生气了;他是上等人,阿Q不是。《阿Q正传》里的颠倒也凸显出我们作为读者和批评家矛盾的地方:没人重视N,但也很少有人批评他;因为作者对语气和态度的巧妙把握,我们张嘴就能谴责假洋鬼子;我们对鲁迅自然要持宽容的态度。鲁迅希望我们采取怎样的立场?他似乎希望读者读出阿Q的滋味,理解阿Q对假辫子的轻蔑,至于假辫子与自己那缥缈关系,却一字不提。诚如胡尹强所说:“读完《头发的故事》才知道鲁迅对假洋鬼子的态度何其复杂。”①
才一年之后,鲁迅就在《头发的故事》的改写版里,再度分派了其中的角色,原来的人物改动之大,读者已无法将他们分出彼此,这些新角色演技一流,读者的视线被吸引在故事里,没必要在故事之外寻找人物的来源,尽管故事里的素材可能成为寻找的诱因。人物来源在个人经历上留下的印痕被彻底抹掉。鲁迅通过与假洋鬼子对换位置,表明在写完《头发的故事》之后不久,他就知道自己及同志在嘲笑者眼中的印象。如果他也动手打人的话,场面将更有趣,因为那将有个阿Q“耸了肩膀等候着”,知道自己要挨打。相同的材料,使用上又大相径庭,如此高明的作家在创作N的独白时就一定知道,他还能刻画出另一个人物。
下面的引文选自鲁迅1935年的文章,对此上文已有提及,写的是他自己的辫子,如同在小说里,毫无掩饰地写到了同一个经历。如上文所述,作者并未提及那些与《头发的故事》平行的地方。
我……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①
虽然《阿Q正传》里的故事与《头发的故事》互相颠倒,但上述引文所写的却与《头发的故事》格外相似。经历还是那些经历(手杖除外),写法也相似,尤其是刻意省掉了动机和情感的写法。endprint
读者能在引文中发现鲁迅写文章惯用的技巧之一:不写情感,将笔锋指向琐碎的事件,其中引人入胜的素材和辛辣的语气,必然是他有意为之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安排诱人的细节,显然是为了掩饰强烈的情感。引文里的四个例子从上到下,几乎占了整个段落。在每个例子里,作者写入细节之后,并不提及发生的行为和事件,也省掉了与之相关的所有情感。第一个例子是购买假辫子。这当然是复杂的时刻,但他只是说“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没说买),之后就写装假辫子的人,写价钱(“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写货色。至于当时的感觉或为何要买,作者并未提及。紧接下来作者写到在一些情况下假辫子能被人发现,但他并没说自己也被周围人“研究”。之后作者借用贤人的话“解释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写道:“装了一个多月,我想,……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这些文字也出现在《头发的故事》里。还是这个决定,N说道:“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接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了。”贤人以现成的话取代了N个人解释。最后,在下一段里,作者借讨论“待遇”二字的语义,回避了在大街上如何被人奚落。以上每个例子出现时,正是N的动机和语气令人难以捉摸的时候。
我们比较两段文字后发现,在鲁迅的小说里,仅有《头发的故事》在修辞层面及其繁杂的内容和松散的结构上更像散文。N像鲁迅,不仅仅因为在个人经历上难分彼此,还因为那种充满回避与掩饰的行文(也许是个人的)风格是相同的。这种相同性表明,作者的真情实感并未改变。1935年,鲁迅回望清末,其时《头发的故事》已发表十五年,与辫子相关的经历已有二十五年,但他并没有选择《阿Q正传》那么超然的态度。时光流逝,不仅没有改变他的情感,连他的表达方式也没有改变,这足以说明,虽然他刻画出假洋鬼子,但非小说仍然是表达那些经历的必要形式。
孙伏园(1894-1966)在鲁迅逝世后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相同的情形。孙伏园1911年在绍兴是鲁迅的学生,他们终生为友,他还编发过鲁迅的作品。下文选自孙伏园的回忆文章:
许多留日回国的学生,为适应国内的环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辫子,那些没出息的,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隔两三天到理发馆为假辫子理头发,擦油,使人骤然看不出辫子的真假。鲁迅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决不肯套假辫子,头发也不常理,平时总是比现在一般所谓平头的更长约五分的乱簇簇的一团。……身上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此外,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①
文章不是鲁迅写的,但印象是他留下的,提及的信息是平行的,其中几个地方写得也有趣。首先,孙伏园断定,鲁迅哪怕是片刻也不接受社会的压迫,他怎能戴假辮子。读者不明白孙伏园为何如此自信。这里要指出一点,孙伏园是在鲁迅扔掉假辫子之后才与他的老师相识的,所以他的说法不可能来自亲身经历。孙伏园在北大读书及后来编辑杂志时才与鲁迅相识(他是《阿Q正传》的编辑)。不过,虽然二人接触频繁,但当孙伏园1920年读到《头发的故事》后,他好像也不知道N的素材取自作者。后来鲁迅在1930年代发表的文章似乎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最后,孙伏园在去世后被发表的文章中为N和叙述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关系,在道德上将二者区分开来。②总之,孙伏园的说法(或他选择的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至少是在事实之后评判“革命者”的尺子。他提供了在鲁迅所描述的个人经历和N的经历中并不存在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他同意阿Q的态度:戴假辫子是可耻的。当年茅盾也是中学生,忆及浙江另一镇上的学校也有同感。他说到一位英文教员,因为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自然没有辫子”。但茅盾也更开放:他写道,校长要与教员见面,于是“他就‘戴上假辫子,但在操场上他一般不戴假辫子”。①
文中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孙伏园说鲁迅有一根手杖,还强调手杖像《阿Q正传》里假洋鬼子的。这一说法令人感到尴尬,因为N和假洋鬼子都用手杖打过人。但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没说有手杖,虽然手杖是一战之前欧洲绅士的标准饰物,一如他们服装上的其他物件。
按说鲁迅的同代人写鲁迅和他的假辫子,信息应该是客观的,但从上文来看,无论是孙伏园还是其他人,未必如此。一些人提到清末鲁迅不留辫子,在这些人里,周作人似乎要为鲁迅辩护,大概是怕有人也攻击鲁迅不革命,戴假辫子。他说鲁迅1903年秋回国后才戴了假辫子,而且次数不多,“才几次”“不过几次”。他并未提及鲁迅1906年回国省亲(虽然这一次鲁迅被迫成亲后携周作人再度赴日),他对鲁迅1909年最后一次回国更是三缄其口。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写了不少鲁迅的文章,但是与鲁迅头发相关的文字颇多修改,不足为凭。②
最后几个平行的例子不是文字的,是鲁迅1909-1911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留着短发,都是为正式场合拍的照,所以他一定经过了精心打扮。其中一张摄于1909年,鲁迅身着西装,这张东京照相馆拍的照片构图讲究,轮廓清晰,令人印象深刻,读者很少见到(现存上海鲁迅博物馆),也是鲁迅回国后赠送亲友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物与那个在大街上被人笑骂的归国知识分子判若两人。此外还有一张照片,知道的人更多,据陈漱渝,上面的鲁迅穿着同一款西装,说明这一时期鲁迅以同一姿态拍下的照片不止一张。两张照片烘托出清末鲁迅复杂的写照。
鲁迅的第二张照片是1910年的众人合影,这张照片知道的人不少,鲁迅也是身着西装,也许是同一款(陈漱渝)。前排右三为鲁迅。其时鲁迅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这是他的第一个教职,众人合影纪念他们反对孔学再次入校取得的胜利。虽然鲁迅和三位西装短发的教师与其他二十一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但照片上的人在思想上都是盟友,因为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回来的,教授现代课目,在这次教学风波上同属一派。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这张合影视为视觉对比上的存念,我们就可以从外部的或旁观者的角度发现鲁迅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不必等阿Q的笑骂或孙伏园的辩护。照片上身着西装的四位教师,不论他们对自己的形象有何感想,总之是格外显眼。西装革履,短发分头,还留着八字胡,他们显然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事,不过,他们的同事也大多身着传统服装。这一对比也能说明在N的中学里为什么“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与此相同,身在绍兴的鲁迅无论怎么做也摆脱不了“里通外国”的标签。鲁迅写道:“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①上述照片里的鲁迅,无论发式、八字胡还是装束,每个细节都走在了社会的前面。endprint
总之,上述引文所表现的鲁迅形象,都是他自己在不同的时间上直接或间接地刻画出来的。就其中的一个时段来说,读者并不感到陌生,但要是作为回忆文字,将其并列起来的话,各自的关联却有所抵牾。各段的异质性凸显出真实生活与传记文字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矛盾,即使或尤其是有些证据出自鲁迅之手。这里要强调,写到N与鲁迅的关系,我并不认为N就是百分之百的鲁迅;我要说的是,真实的信息来自作者的生活,对此不能等闲视之,不然我们就可能损伤与文学和传记相关的信息。
与传记相结合
下文以第二组平行段落为例,将其中的材料与鲁迅的传记合并研究,同时坚持以连贯的态度解读《头发的故事》。在这组文字里,我们将发现已不再陌生的诱惑:从我们或孙伏园的角度解读,以为鲁迅“自然”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下文选自《头发的故事》,学生为剪辫子征求老师的意见。这些学生要以N为楷模,但他的回答却模棱两可: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从表面上看,N好像对过去的他并无溢美之词。那些年轻浪漫的学生请教他们崇拜的人,但他却用令他们不满的、显然是胆怯的回答把他们打发走了。鲁迅脾气不好,为人严苛,传统上这些特点是与刚正不阿相关联的,鲁迅又被人顶礼膜拜,以此为出发点的解读,与胆怯的回答怎能合拍?
克服偏颇并不容易,因为片面地或不连贯地解读鲁迅已经成为倾向。如传记作家遇到麻烦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所以,讲到鲁迅做教员的时代,典型的描述是:“学生们不仅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很快开阔了视野,他们以鲁迅为榜样,决心投身到推翻满清的民主斗争中去。”①再就是把主人公划入“前辈”,如范增画的插图。②插图上的教师表情严肃,坐在那里转身面对学生,伸出一只手表示拒绝或阻拦。五个学生中的代表,一手抬起辫子,另一只手做出剪子的手势。他身后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拽另一个学生的辫子,画面告诉我们他们多么可爱。N已经拔顶,头发蓬松,戴着眼镜。N长着长眉毛,尖下巴,相貌平平。他显然是“前辈的”N,不是鲁迅化身的N。
N不让学生剪辫子,但不能就此说他在逻辑上与鲁迅没有关联。我要请读者注意,在这里评判N未必容易。鲁迅不喜欢表态。我们确实应该问一问,小说的作者有没有明确的态度。小说里找不到证据。他在关键时刻并不告诉读者朝哪个方向走。学生知道自己怎么想。他们是充满理想的青年,要是有人令他们失望,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表达不满。但读者不是学生,读者要问,在学生对N的评判——“虚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评判?一方面,N告诉学生“没有辫子好”“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显然学生对他的回答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几句普普通通的话,经过作者的点化,也可以说得有滋有味。说到底,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透过暗示来传递掩盖在普通言语中那些无边的复杂性,将平凡的短语变化成充满意义的短语。事实上,这是鲁迅的特长,如《端午节》里反复使用的普通短语“差不多”或《祝福》里叙述人回话时用的“说不清”。这些都是普通的短语,但作者巧妙地重复使用,才使它们不断生成出意义来。不过鲁迅在这里并没有重复他的短语,虽然这是他在《头发的故事》里唯一使用对话的地方。鲁迅以其惯用的感知力告诉读者,要使浪漫的青年学生明白那些只有生活才能教给他们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但读者并不能断定,N知道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
后来鲁迅又有(或找)机会就作为政治原则的发式提出相同的建议。这一次他的建议没有引发评论,也许因为很少有人评论他的文章,但更可能是因为鲁迅列出的原因更符合我们对其性格的理解。他的建议发表在1927年的文章上。鲁迅在报上读到女生因短发不能入读高中,一如1920年,这次鲁迅有感而发,与报刊约稿无关:
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女子剪发也一样,总得有一个皇帝(或者别的名称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虽然如此,有许多还是不高兴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载,也就忘其所以了;两年以后,便可以到大家以为女人不该有长头发的世界。这时长发女生,即有“望洋兴叹”之忧。倘只一部分人说些理由,想改变一点,那是历来没有成功过。①
“我不赞成女子剪發”“等一等罢”,这两个建议正是七年之前鲁迅借N的嘴说出来的。但这一次鲁迅写出了原因:政治权力和变化着的社会规范很快就能实现个人行为无法实现的目的。鲁迅对权力的评判不仅准确而且辛辣。他将发式视为象征,建议大家等待发式失去其象征作用之后再说。他显然——有意地——没有顾及女生的要求。他是在挖苦当权者,但女生也被裹挟在里边。鲁迅提出的原因使其“建议”和性格能为读者接受,但N却被视为胆怯的或虚伪的,原因何在?他在文中讲出了原因,而且是以其惯用的辛辣和对现实的绝望讲出来的。
下面的引文选自鲁迅1935年的文章,鲁迅提到他在绍兴因头发与学生的遭遇。如同上文,鲁迅也提出了(不剪辫子的)原因,虽然原因有所不同。开头与N的经历相似。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如同在小说里,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然而老师的回答却是令他们不满的“好,但是”。上文的对话不是通过直接引语完成的,其中的文字也没有弦外之音。学生悻悻地离开,对老师颇不以为然。endprint
此时的鲁迅与N不同,等学生走后,他开始思考,结果还是不得要领——政治行动的真正的风险: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①
鲁迅陈述原因,其结果与N的相同,虽然他对现实一以贯之的批评精神和对学生的关怀更引人注意,这才使令人泄气的回答为读者所接受。N也可能持这种态度,但读者不知道,也无从猜测。
再次分析这几句话,我们能发现其中的重要原则,鲁迅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暴力事件,他对这些事件的很多回应,始终以这些原则为出发点。对他来说,那些学生不仅轻视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且还没有牢记秋瑾等先行者为他们付出的牺牲。生命的价值——学生的生命和秋瑾的生命——是根本的原则,这一原则看似简单,但颠覆了众多概念,如王得后所指出的,也是对革命行为的颠覆。②与此相关的是鲁迅对忘却的关注,忘却二字反复出现在鲁迅的作品里,强调稍纵即逝的记忆对个人行为的反驳,无论是学生的行为还是秋瑾的行为。这两项原则确实对学生建议的行为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这些原则在鲁迅作品里一次次出现,其与政治活动的关联在这里实现了最初的表述。然而他没有告诉学生,N也没有告诉学生。即使他说了,学生也未必能接受。因为他和N都没表明态度,所以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失去威信,也在意料之中。在后来的选择中,鲁迅也没通过解释来维护他的威信。
这一次鲁迅的预感没有被验证。这与时代潮流是分不开的。1911年年初,不少中国学生就剪掉了辫子,因为他们预感到大清的法律将发生变化。①在N的故事里,六名学生因剪掉辫子被开除,他们留在校内不行,回家不行,等到民国成立才摆脱困境。后来鲁迅做监学,他在第一次讲话中就同意学生剪掉辫子。②对于剪辫子,其他作家的回忆显得更轻松,比如茅盾。茅盾的同学剪掉辫子后成了“校长的同志”(他们也戴上了假辫子),有人因为家里不同意,其他人觉得离开校园太显眼。他的一个同学因病“牺牲”了头发,医院特意给他开了一个说明(茅盾)。③这没人相信的借口让人联想到假洋鬼子,他母亲就说他喝醉了酒被无赖剪掉了辫子。鲁迅担心发生悲剧,这不无道理,但真正上演的是一场场闹剧。
总之,在互相对照上述引文里的例子之后,能推演出更多的信息,这是孤立的段落办不到的。比如同一个建议,在《头发的故事》里似乎仅有一个对N不利的解释,但在第二次第三次出现时,建议后面列出了原因,读者对此接受下来,因为后两次是以鲁迅的口吻和态度表述的,表达了鲁迅一生的关怀。这不是说同一个道理在N那里也一定适用,但足以提示我们,对待鲁迅的作品,明显的结论总是流于片面。
结 论
买假辫子,被人评头品足,扔掉假辫子,在道上被人嘲笑,可能用手杖打人,与亲戚、同事和学生的关系紧张:鲁迅生活中的这些素材对批评家和传记作家是有用的。我希望拙文为这些素材提出了足够的证据和分析,从而走出“问者坏,鲁迅好”的道德模式。我将在结论部分提出几个分析这些插曲的语境。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将这些插曲视为鲁迅才从国外回来那几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这语境是由那些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如此构成的语境可能为事件提供最适度的角度。他们经年旅居国外,不少人有了自己的习惯、世界观、追求——外表——这些东西在1911年的革命将其合法化之前一般不大为世风所接受。迁入大城市的人大概要好一些,比如,1910年年末,上海的《东方时报》就“惊叹大批短发男士出现在公开场合”。①绍兴必定要慢一些,但民国成立之后不久,据鲁迅1935年回忆,“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②这是一幅令人高兴的画面,我们在鲁迅自己的文字里发现,外表上要与众不同,这是他们那代人的共同理性,不过此时他们遇到的敌意已经有所减弱。将个人经历合理地安排在他们的传记里,我们等待一部社会史来鉴别、描述、分析这一过渡时期的辫子和短发。
另一个方式是,将这些经历视为回忆文字,也就是对其作者來说历历在目的事件。这一方式能把我们引入鲁迅秉性构成的语境——尤其是他顽强的记忆和与之相伴的强烈情感。我们可能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情感强烈,文章辛辣,能不能因此与他的同代人有所区别?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也不存在确定的答案,但比较之后就能发现鲁迅的文字情感更强烈。许寿裳也在文章中写到鲁迅剪辫子,他自己到东京次日就剪掉了辫子,后来在鲁迅之前一头短发返回浙江,但他写的是周围的朋友,不写他自己的经历。在那张杭州师范学堂教员合影上,前排居中者就是许寿裳(据倪墨炎、陈九英),也是身着西装,但他就学生和辫子没有复杂的故事要讲。茅盾的回忆也不相同,他写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文笔风趣,但写自己的地方很少,革命之后他也是短发回校的。鲁迅在《头发的故事》和《阿Q正传》里显然是把自己伪装起来了,虽然他在文章里没有。其他人空白或风趣的地方,他又故弄玄虚。毫无疑问,更多的信息才能改变这一现象,但鲁迅可能还将是极端的一例。
鲁迅就短发陈述的意见使我们联想到他与政治原则相关的秉性,尤其是他再三再四,将短发视为历史事件的尺度。他让N说经验告诉他革命的真实原因:“那是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他在1935年的文章中又亲自解释了这一观点:“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在文章将近结尾时他再次写道:“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次年,鲁迅在其生前最后没写完的文章里又提了一次:“我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①鲁迅的讽刺为什么如此辛辣?发式与革命相提并论,意义同等重要。不论是个人承担的后果,还是国家经历的动乱,结果都不大好(在文章发表时“舒愤懑”及其他一些句子被新闻官删掉了)。显然,鲁迅及其他知识分子不久就对共和革命不再抱有幻想,但他为什么还要借辫子发议论?这里我们发现秉性与有限的评判结合起来了。在这个结合点上的是辫子的政治化,剪辫子这一行为需要英雄主义才行。与此相反,其他原因,如社会的同一性,是没有政治基础的。唯一的评判标准是以政治的和个人的英雄主义为指向的。在这个语境里,鲁迅既没有公开他自己或N选择发式的政治原因,也始终没有在政治上表现反叛的态度,所以说他拒绝把自己或N划入英雄之列。如同N,他剪辫子就是为了方便。鲁迅拒绝在政治上站队,一生如此。因此,要把鲁迅打扮成英雄,不仅在证据上有难度,在他的文风上也不好把握。鲁迅并非不关心政治,不然他就不会拒绝所有指向英雄主义的政治。endprint
接下来我们要走入与经历相关的最后一站:作为文学素材的经历。在毫无英雄色彩但又模棱两可的状态下,按说,虚构的小说要有形式和意义才对。如同社会史,小说并不要求英雄主义,因为一般来说小说不必专写崇高或英雄。此外,小说技巧经过提炼之后,用来剖析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性的本质,刻画人生百态及其后果。这些都是《外国小说选集》传达的经验,也是鲁迅在其众多小说中所实践的。他剃发之后的种种遭遇构成了复杂的反讽,这些无一不是小说的素材,但他仅仅在《阿Q正传》的讽刺里才用了一些,在《风波》里用得更少。鲁迅以其娴熟的写作技巧将读者的视线从朴素的评断转向所谓复杂的迟钝。然而,在N那里,因为没有鲁迅的引领,读者开始转向片面的、道学的结论。若是有他的引领,我们一定能读出更多的信息。但在N身上鲁迅并没用文学语言改变他的经历,对此我们要感到满足。
鲁迅撰写《头发的故事》遇到麻烦,所以有必要再次分析他在其他小说里使用了多少自传性的材料。显著成功的小说《故乡》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故乡》表面上写的不过是作者1920年回绍兴省亲,但其中处处可见作者以娴熟的技巧借用小说资源,如选材、描写、对话和场景等。那么,写法大不相同的《弟兄》或充满矛盾的《在酒楼上》又有多少是作者的经历呢?在小说里寻找自传可能变成按图索骥,但在发现了问题的小说里,作者与个人经历的角力,可以把我们引向新的问题或问题的新方面。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头发的故事》告诉我们,评价鲁迅,先要更好地理解他的所有小说。到目前为止,鲁迅的二十几个短篇小说仅有八九篇被人深入研究,虽然研究得很透。大概因为这些小说写得好,所以才吸引了批评家的注意,不过,这仅仅是一般的推断,因为还没人明确指出鲁迅小说的高低之分,也没人提出另一个模式来。结果其他十几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也在其中,不过是在研究鲁迅的小说时,偶尔才提一提,以为次要的证据。就《头发的故事》来说,仅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必定是不够的,好在其存在就能证明价值所在。同理,鲁迅作为有力的复杂的个人和作家,他那些不被重视的小说可能还有着未被发现的关联。
从秉性上说,鲁迅在其经历中投入的严肃性是他所无法摆脱的,到他的晚年依然如此。如他对自己的描述,“我偏苦于不能完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他不能完全忘却的记忆,一般来说是从他的少年开始的,包括他部分的旅日岁月。现在看来,他很少提及的那些回国之后的日子,也是他不能完全忘却的过去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周杉(Eva Shan Chou),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文学教授(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aruch College)。
译者简介:
史国强,山东莱州人,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翻译与文化传播中心教授,出版《喜福会》《赛珍珠》《格利弗游记》《上帝知道》《布什自传》《普京自述》《简·方达回忆录》《灼痕》《暮光地带》《时光倒流》《塞林格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 》和《对话潘基文》等多部译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