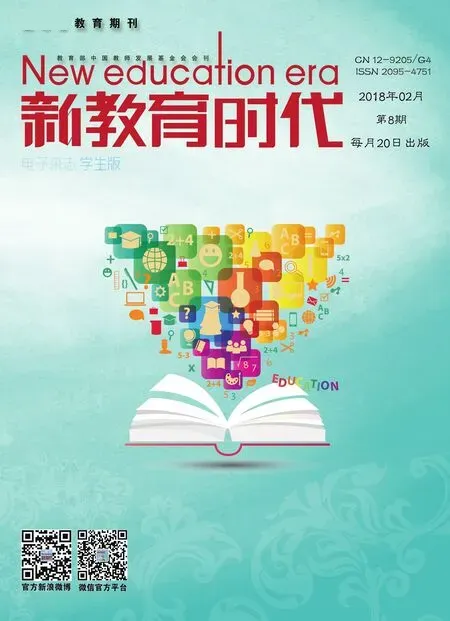汉语外来词同义译名规范化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454000)
语言的发展不可能是故步自封的,随着国际间交流日益密切,语言也逐渐走出各自的国界,各国语言携手并进,来到国际舞台。语言的跨文化交际依然成为热点。在跨文化背景下,语言的翻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严复有云:“一名之立,数月踟蹰。”一语道出了翻译过程的艰辛。在当今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外来词汇涌入其中,一时间造成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情况,同义译名词就是其中的一项,所以,对同义译名规范化研究迫在眉睫。
一、同义译名产生过程及原因
1.历时层面
类似于汉语词汇中的古语词[1],一些同义译名词在当下极少出现,但是由于特殊需要(如字典、历史书籍等),一些词也会进入公众视野。现对其分类如下:
(1)先音译后意译或音译兼译
一种语言流传到另一种语言中,人们接触到的最初形式就是语音,所以人们往往倾向于根据己方言的语音对外来词进行翻译。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利用己方言的语义进行翻译。如严复在《天演论》中将“ultimatum”译为“哀的美敦”[2],这就是单纯的音译。而现在人们往往将其译做“最后的通牒”,“哀的美敦”使用频率越来越低,这就由音译发展到了意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作家亦舒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这个词,但大多数都带有修辞等手法。2000年后,这个词就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2)先音意兼译后借形或意译
曹炜先生将音意兼译词称作“外来词的理想形式”[3],认为音意兼译是外来词翻译层次最高的,是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最佳形式。但是由于语言的不断发展,一些词的翻译方式发生变化。“index”一词,最初在汉语中译为“引得”,既表音又表意;但自从日本将之译为“索引”,我国也纷纷将之译为“索引”,这显然仅仅表意,是一个借形词。“引得”这个形式逐渐消失,恢复成为最初的语法功能:动词“引”+“得”的短语形式,如“引得我直流口水”。再如“president”一词,我国最初将其译做“伯理玺天德”[4],意思是掌理玉玺,享有天德的人,这就是音意兼译的形式。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就有“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现在人们将其译为“总统”,意思是民主国家最高行政首长,变为完全意译。这是由于语言自身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原则。
2.共时层面
共时层面的同义译名现象是造成混乱的重要原因。在同一阶段层面下,一个概念对应了多种形式,具体分类如下:
(1)音译和意译或音意兼译同时存在。例如“摩登—时髦”、“马达—发动机”、“迷—粉丝”等;还有一部分在方言中为音译,方言进而影响到普通话,例如“秀—表演”等。
(2)字母词和意译词并行。例如“GDP—国民生产总值”、“CEO—首席执行官”等。
(3)意译和音意兼译并行。这种情况很少,如“微型—迷你”。
二、同义译名词的影响
同义译名现象体现了汉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为灿烂的中华文化锦上添花。但同时它所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现象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由于同一个概念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导致了文化交流上会出现一些混乱的现象,进而也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而随着外来词汇日益成为汉语词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义译名对国内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诸多不便。
为了克服这种现象的消极影响,同义译名规范化工作已迫在眉睫。
三、同义译名现象的规范
1.音译词的规范
音译是翻译汉语词汇方法中最直接的一种,但由历时的同义译名可知,这并不是词汇的最终形式,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状态存在。所以汉语中如果有合适的意译词时应尽量选择意译,例如我们现在一般不说“镭射”而称“激光”等。但如果有些汉语词在大众中普遍以音译的形式存在,那就说明这个词还未发展成意译的形式,那我们通常选择其音译的形式。
2.字母词的规范
在当今英语全球化的趋势下,字母词常常伴随着日常交际的出现。对于字母词,很大一部分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对于一些行业词,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非专业人士尚且还能一知半解,但对于“CAD”、“CMOS”这样的纯字母词只能是一头雾水。因此,尽管字母词在书写形式等方面都比意译词或者音意兼译词较方便,人们还是倾向于后者。但是一些字母词在使用上几乎达到了全民性的程度,例如“GDP”、“CEO”等,这些通用的字母词就可以在一般交际中使用。但是在一些较为正式的文件中,还应注明其意译形式。另外,字母词中有存在一些半字母半意译词,例如“O抗体”、“Y染色体”等,这也是基于书写的简便性。
结语
大量的同义译名词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对汉语中存在的一些传统文化因素构成挑战,所以同义译名的规范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孔秀祥教授认为语言具有“自我净化能力”,即语言的规范化“靠立法、倡导都是无济于事的。”词汇往往形成于交际之间,因此我们使用这些外来词汇时应自觉地承担起责任,保护汉语的纯洁性,传承词语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