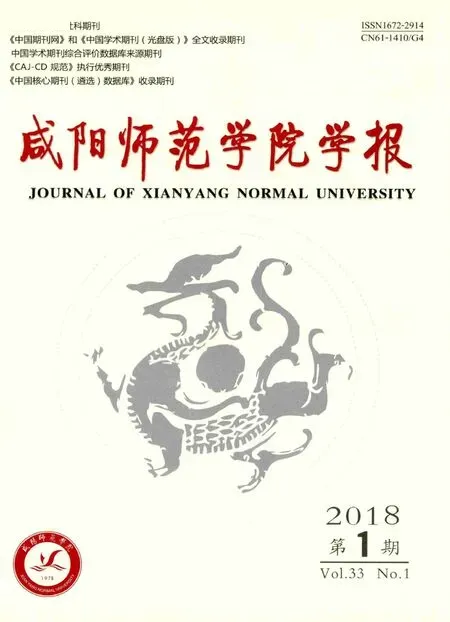实用、实学、实业:刘古愚格致救国思想的精髓
姚 远
(西北大学 a.西北联大研究所,b.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刘古愚(1843—1903),名光蕡,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曾任味经书院、崇实书院院长,甘肃大学堂总教习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卒于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任上。他“身服儒冠,却不事科举;手无寸柄,却矢志富国强兵;长居江湖,却为国事忧伤涕零,忧忿之切,以至目盲”。[1]2他主张维新,推进科学教育,出版《天演论》《梅氏筹算》《豳风广义》等科技图书,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筹办实业。他不仅通晓经史,亦通音韵,知天文,懂数理,有着丰富的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
然而,目前学界对刘古愚科学思想与科技活动的研究虽有少量涉及,[2-5]但总体上还很薄弱,尚待深入探讨。
1 “专求旧学,不足以维护中国之局”,“欲救今日时弊,非洞悉西方政治、工艺不可”
刘古愚自青年时代起就关注张载、冯从吾、吕泾野、李二曲等关学先辈。会试进士不第,便绝意仕途。他通过弟子陈涛、李岳瑞等的介绍,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联络,从而立志废八股,习算术,立新学,举实业,培养新型人才,与康梁变法运动相呼应。
刘古愚在应考期间,从省城到京城,痛感西方列强入侵和丧权辱国条约之耻,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国以后将时时与英德等国相周旋,专求旧学,不足以维护中国之局”,“中国唯变法不能图存”。在《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中,亦指出“欲救今日时弊,非洞悉西方政治、工艺不可”。[6]34
刘古愚在《学记臆解》序言中对中国封建教育提出强烈批评:
呜呼!今日中国贫弱之祸谁为之?画兵、吏、农、工、商于学外者为之也。以学为士子专业,讲诵考论以鹜于利禄之途而非修齐治平之事,日用作习之为。故兵不学而骄,吏不学而贪,农不学而惰,工不学而拙,商不学而愚,而奸欺。举一国为富强之实者而悉锢其心思,蔽其耳目,系其手足,伥伥惘惘,泯泯棼棼,以自支持于列强环伺之世。而惟余一士焉,将使考古证今,为数百兆愚盲疲苶之人指示倡导,求立于今世以自全其生,无论士驰于利禄,溺于词章,其愚盲疲苶与彼兵、吏、农、工、商五民者无异也。即异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势矣。[7]16-17
刘古愚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是将有用的实学排除在学问之外,是将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排除在教育大门之外,必须提高从业者的素养,才能言中国之富强。因此,他进一步提出“化民成俗”说:
救国之贫弱孰有捷且大于兴学者?特兴学以化民成俗为主,而非仅造士成材也。风俗于人材犹江河之蛟龙也,江河水积而蛟龙生,风俗醇美而人材出焉。无江河之水即有蛟龙亦与鱼鳖同枯于肆,而安能显兴云致雨以润大千之灵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学其水也。化民成俗则须纳士、吏、兵、农、工、商于学,厚积其水以待蛟龙之生也。兵练于伍,吏谨于衙,农勤于野,工巧于肆,商智于市,各精其业,即各为富强之事。而又有殊异之材挺然而出于群练、群谨、群勤、群巧、群智之中,以率此练、谨、勤、巧、智之群,自立于今日之世界,不惟不患贫弱,而富强且莫中国若者矣![7]17
这里,刘古愚强调“救国之贫弱”的主要途径就是“兴学”,而兴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化民成俗”。
2 求“实用”,“当事事责实”,勿“空谈而不适于用”
刘古愚认为“西人之学,皆归实用,虚不如实,故中国见困于外人也”,“西人之艺则极神奇,此殆天为之开”。他所谓的“西人之学”,就是“西艺”,即工艺科技,是西方之所以富强的源泉。他在《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中说:
味经之设,原期士皆穷经致用,法非不善也。而词章之习锢蔽已深,专攻制艺者无论矣。即有研求经史、励志学修者,第知考古而不能通今,明体而不能达用,则亦无异词章之习。已今时变岌岌,中国文献之邦,周孔之教,其造就人才竟逊于外域,岂吾道非乎?盖外人之学在事,中国之学在文;文遁于虚,事征于实,课虚不如求实,故造就逊于人也。[8]1
这是说,同治十二年(1873)创设陕甘味经书院的初衷,就是要学生学习“致用”之学。但为何我们造就之才逊于外国呢?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文遁于虚”,“课虚不如求实”,只有求实,才是正确、良善的育人途径。
刘古愚进一步指出:
古固无不切世用之学也。中国人士日读周公、孔子之书,舍实事而尚虚文,甘让外人以独步,事不如人而遂受其制,反若圣道亦逊于彼教者,岂不大可痛恨哉?今既知其弊之所由,始力为矫之,爰立时务斋于味经书院,俾人人心目有当时之务,而以求其补救之术于经史。人人出而有用,中国之势,孔孟之教,未必不可雄驾诸洲也。[8]2
他认为国人“舍实事而尚虚文”,是“不切世用之学”,是受制于外人的关键,矫正之策就是“人人心目有当时之务”,如此则可“雄驾诸洲”。
为了验证是否实用和有效,刘古愚还提出要对西方科技、工艺学“施之试验”,一观其效:
至于艺学,非一一施之试验,空谈何补于事?故格物、考工两门,非备购其器,无从讲求,强为讲求,徒拾西人牙慧,空谈而不适于用,其弊当甚于八股。八股虽空谈,尚有一、二道义语可以维持人心,若以依稀惝恍之词谈光、化、电、热之事,其流弊更何所纪极哉?故今日崇实书院当事事责实,以祛中国之弊,然后能用西国之法。至于艺学,西人已格之物,已成之器,我皆能亲试而知其用,方为可贵,而不必以能读其书,谈之可听为贵也。[9]120
这是说,如果“依稀”、仿佛、迷迷糊糊地谈论西方科学,必使流弊更甚,故必须对待每件事情都要“责实”“亲试”“知其用”,这才是最宝贵的,才能祛除流弊,使西国之法发挥真正的效能。
3 “崇实学”,“融中西”,“精心以究其所以然”
刘古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向陕西学政赵惟熙提出“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12字革新教育的建议,并倡议创建实学书院。赵惟熙遂与陕西巡抚张汝梅联名上奏:“迩来时局多艰,需材尤急,自非储其用于平日,万难收其效于临时。兹据书院肄业举人邢廷荚、成安,生员孙澄海、张象咏等联名呈恳自筹款项,创建格致实学书院,延聘名师,广购古今致用诸书,分门研习,按日程功,不必限定中学西学,但期有裨实用,如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类,互相讲求,久之自能洞彻源流,以上备国家之采择……近来讲求实学,风气一变,然自京师同文馆外,如天津等处之武备各学堂,类皆选取幼童俾习西学……今该举人等请设书院,由学政调取年少聪颖之生员而肄习之……久之授受渐广,风气渐开,未必无杰出之才奋发而起,似于培植人才之方不无裨益。”[10]68-69由此可见刘古愚对于“实学”的崇尚。
刘古愚为味经书院时务斋所设的实学课程,具体包括:
道学类,须兼涉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史学类,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经济类,须兼涉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训诂类,须兼涉外洋语言文字之学。以及历算须融中西;地舆必遍五洲;制造以火轮舟车为最要;兵事以各种枪炮为极烈;电气不惟传信,且以作灯;光镜不惟测天,且以焚敌;化学之验物质,医学之辨人体,矿学之察地脉,气球以行空,气钟以入水,算学为各学之门径,重学为制造之权舆。诸艺皆天地自泄之奇,西人得之以贶我中国,我中国不受其利,将受其害,可不精心以究其所以然乎?凡此诸技,均须自占一门,积渐学去(各学均有专用之器,均积渐购置,见其器则各学均易学矣)。[8]3-4
刘古愚将诸科学之母“算学”作为精研西方格致的锁钥,认为算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时务斋学生无论专精何业,都必须习算。其学生张鹏一在《刘古愚年谱》中说:“陕人多精几何,明测算,师所启迪也。”[11]24除算学之外,还开设了西方各国史地、政治、语言,兼学电、化、医、矿诸学。同时,将崇实书院初设的“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并为“政事”“工艺”二斋,将格致、算学、制造、英文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学要求实,就必须“观时”,洞察当时的社会,了解时事,故味经书院订购了许多报刊,如《京报》《申报》《万国公报》等,将阅读报纸作为时务斋学生的必修课,并定期讨论、宣讲所读之文,交流认识和体会。
除此之外,刘古愚还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味经书院创办了陕西最早的期刊——《味经书院时务斋随录》,及时报道时事和新的格致消息。他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唯俊杰者乃识时务也”,作为对时务斋的解释,并认为“报章为救国之奇”。[12]146-147该刊现存两本实物,为小16开,线装书册型期刊本。第一本刊有曾国藩的《拟选子弟出洋学艺奏折》,左宗棠的《船政奏折》《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折》《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江岸坍筹堵情形折》等。第二本载有丁日昌的《海防条议》《商务务陈》《推广学校疏》,沈葆桢的《机器到工已齐并船厂现在情形折》等。
4 “急刻造器各书,造器之原均由格致,故宜急刻格致诸书”
与“实学”课程相联系,刘古愚认为急宜循序刻印教材,用于实学教学:
中国之患西祸为急,则时务莫大于洋务。西国之谋人国也,以商贾笼其财,然后以兵戈取其地,故今日中国以整顿商务为先,宜急刻商务及通商条约、各国交涉等书。西商所以获利者,制造精也,故宜急刻造器各书。造器之原均由格致,故宜急刻格致诸书。商贾之中即伏兵戎,故宜急刻战阵军械等书。西学之精非算术不能窥其奥,故宜急刻算术各书。然吾中人则虚骄自大,谓读洋书者即为变于夷,则请以中兴诸贤文集事涉洋务者先焉,其他则从算学始。[8]5-6
光绪十一年(1885),刘古愚在味经书院设“求友斋”,“而苦无书,则集资以刻之”。光绪十七年(1891),复经陕西督学使柯逢时奏设味经刊书处,“陕西藏书既少,板本无多,自南中返运来者多由陆路,其价甚昂,寒士每苦难得,往往购买俗恶坊本,经文则删节不全,字句则讹谬不堪,积久相沿,遂成风气。南北路距省更远,并坊本亦复难寻。臣上年咨商抚臣筹捐银两于书院刊刻书籍,捐廉俸千两,以之为倡。……已于本年在味经书院开办,先刊正经、正史。即以院长刘光蕡总理其事,委监院周斯亿监管杂务。调肄业诸生通晓六书、留心古籍者加给膏火分司校勘,不更另筹薪水,以期费不虚糜,可成善本。俟书本刻成,听各属书院尽数刷印,藉资流布”。[13]11刊书处建于味经书院大门外,有西向房三架二楹,东向房三架二楹。又于东构房三架二楹,北厦五间,院门东西刊工房各七间,陆续增置书院。改修南房五间,东西厦各三间,北厦三间以为存版印刷之所。第二年又修建了售书处。[14]
刊书处专门制定有《校勘章程》:“绅为经理,官为督察,费不得虚糜,庶可持久。已敦请味经院长刘古愚总理,一切凡董事、帐房、视勘诸生及经费出入皆归院长主持。”复规定:“严校勘书,板本美恶全视”,“文试帖及俚但淫邪犯禁之书永不准刻”,“每刻一书,董事即送初校,次送复校,再呈院长鉴核,不得臆改,字画如差谬过多即行更换,刻出样本仍交原校勘定卷”。要“宁详勿略,宁严勿宽,宁泛博勿固陋。校书之体宜然,即看书之法亦是如此。不但经书本文须详加考核,即注疏所引各书亦须详晰对勘,一字一画必求其的确,始则本书自相考证又与他书对勘,必使一毫无憾,则刊出必为善本,其人亦即为善读书也”。[15]12又要求“凡校书须逐字逐句校过,然理义、训诂、考据、词章以及天文、舆地、兵刑、礼乐、农田、水利之类,心有专好必学有独得。况每校书其可为图表者,必先为图表,已开专精一门之端。故此次校书于照常校勘外必须自择性之所近,专精一门。凡校一书随手自录一册,则一书校毕即自成一业,岂非快事?若漫不抄录,随得随失,是入宝山空手回也,岂不可惜”。另外,还要“重道义,不言利”,随时“编印书目,悬牌院门,不准加价”,“陕西、甘肃官府并各书院备文印刷,不取板资”。刊书处有刻工40人,“刻案缮几,数十累百,充满隙地”。每人日刻200字,则40人日刻8 000字,月刻24万字。另有校勘人员20余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原宏道书院改为宏道大学堂(复改为宏道高等学堂),将味经、崇实两书院并入,味经刊书处改为味经官书局,改用聚珍铅字,在上海购买铅版活字大小数号及铜模机器等件,仍由官书局绅董刘古愚经理。书局后迁至西安南院门,并逐渐演变为刊印新办学堂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同时生产粉锭、钢笔头、石笔、图书簿、借书表等文化用品。宣统三年(1911)改归陕西省图书馆。
从味经刊书处到味经官书局,20余年间共刻书300余种。其中西学和科技书籍主要有:《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豳风广义》《天演论》《原富》《强学会序》《天文地学歌略》《地球各国考略》《五大洲国名歌》《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西洋史要》《支那通史》《中国现势论》《舆学入门》《重学须知》《化学歌括》《伦理学》《英文文法》《东语初阶》《法国格物课程》《简明物理教科书》《富国学问答》《理财学课本》《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等。
刘古愚尤重数学教育,亲自校勘了不少算书并为之作序,如《九数通考》《白芙堂算书》《笔算数学》《代数术》《微积溯源》《几何原本节本》《代数备旨》《开方别术》《算式集要》《八线备旨》《平三角举要》《测地肤言》《代微级拾级补草》《勾股细草》《借根演元》《泛信数衍》《学计髓言》《径求和较术》《盈勾股互求公式》《火炮量算通法》《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演草》等等,从而为实学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材料,并涌现出了张秉枢、邢廷荚、张元勋、王章等一批数学人才。[16-17]
5 “西商所以获利者,制造精也”,“故欲效法西洋之制造军器,必先法西洋制造日用之器”
刘古愚认为:“中国之患西祸为急,则时务莫大于洋务。西国之谋人国也,以商贾笼其财,然后以兵戈取其地,故今日中国以整顿商务为先……西商所以获利者,制造精也,故宜急刻造器各书。”[8]5另外,发展本国实业也极为重要,“欲效法西洋之制造军器,必先法西洋制造日用之器。近日金生粟死,中国之农势已不敌,工商安能敌外洋?则工商困农益困。困即易之,所谓穷通变”。[6]35
他的这些思想体现在“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的实践中。他提出“机局为书院之根本,书院为机局之羽翼”,并制定了章程。其机器织布局厂址设在泾阳县城内,仿湖北办厂先例,采用股份制,拟由股东推举正副总管,一年一换,另设委员2人;拟筹集白银30万两作为启动资本,1 000两为一大股,100两为一小股,公开向各界筹资,股东的最初股息为一分二厘,随发展酌情增加。最后特拟一条,织布局办成后,由官府奏明朝廷20年内不准在陕西开设织布工厂,而本厂股东则可以另办“织造羽呢各货机厂及一切汽机者”。这些构想大致符合近代股份公司的运作规则,管理上也体现了民主、监察机制。
刘古愚还准备在织布局初获成功后,“染法、印花亦宜渐次讲求,以及洋紬洋绉,羽毛、洋绒、哔咭、羽绫呢等类均宜推广”。他在《南行诫约》中指出:“我辈名办织布,其心不止织布也,将以讲求时务、练习人才,为陕士开风气,以为后日自强之本。今日上道之始,不啻入学之始。”他要求南行考察织布机器的学生对于沿途关山要塞、道路广狭、河流流速、风土人情、所读之书都要记录,为将来运购机器、开展商务做准备。他安排学生拜见当地的陕籍官吏,求得办事方便;告诫学生尤须注意向商人学习,遇到陕商尽量拜会,听其识见,以积累经验,汲取教训;考察机器时,要拜会各种委员、局中办事之人,及主管机器的工程技术人员,关键的工匠也要拜会。1897年4月,被刘古愚派赴南方考察的学生杨凤轩回到了陕西,买回一架日制人力轧棉籽机器,经在味经书院试用,效率相当于陕西当时通用机器的10倍。于是,官方准备在泾阳设立纺织局,并派人到英国购买人工纺纱机。同时,刘古愚也聘请技术人员仿造轧花机器,开设了轧花厂,迈出了陕西民用工业采用近代机器的第一步。
刘古愚在《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一文中明确指出,机器将在中国盛行,“机器入中国,天欲合五大洲为一,气运之所趋,不惟中国不能阻,即西人亦不能秘其术不令入中国也”。“呜呼!嗜欲将至,有开必先。舟车、弧矢、书契之作,天欲合中国之九州为一也。火车、电线、机器之作,天欲合地球之万国为一也。天欲开之,谁能违之?西洋人固感于气运之先而惟恐或后,中国人乃欲怠于气运之后而不思争先,其能焉?否耶!”最后,他呼吁重振黄帝、尧、舜之功,“萃万国之玉帛于涂山,诛后至之防风氏,为两间重新气象”。像禹一样把各种力量、人心收拢起来,诛灭像防风氏部落那种消极怠惰的势力,重振华夏雄风!但是,终因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响应入股者太少,资金不足而未能办成。
6 结语
在刘古愚创办时务斋和提倡实学时,遭受到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在味经书院就有讥讽西学教师的打油诗:“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张密臣(算学教师),何足算也;南腔北调,北调南腔景济光(外语教师),是何言哉!”[18]49刘古愚筹办陕西保富机器局时,也遭到陕籍江苏巡抚赵舒翘的极力反对,指责“我陕本无异类,今为此举,又要报效洋人,是开门揖盗,教猱升木也”。[19]说明在那个时代,崇尚实学、兴办实业要遭遇巨大的艰难险阻。在此意义上看待刘古愚的贡献,就更为钦佩其拓荒之功!
刘古愚克服重重困难,强化了自张载以来关学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关注实际的作风。他重续秦地筹算绝学,开创了以算学为核心的西北科学教育新纪元;他以味经、崇实书院为试验场所,脱离以科举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系,拉开了近代西北新式教育的帷幕;他于1895—1898年创刊了西北地区最早的期刊《味经书院时务斋随录》,其女婿胡均与宏道学监于1906年创刊西北最早的学堂学术期刊《关中学报》;他造就了李仪祉、李异才、毛昌杰、郭希仁、吴宓、于右任、张季鸾等一批西北乡贤,为新生时代的到来积聚了有生力量。
明清实学,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而提出的,至明代后期形成一种实学思潮,将中国儒学由宋明理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学术思潮以“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为主要特征,以乾嘉时期的实证学风和道咸时期的实学思潮为代表,演至近代又形成“新学”思潮,成为一种以救亡图存、务实革新为特征的新思潮,冲击着传统思想和礼教,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光彩。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新浪潮,在陕西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古老文化区激起了层层波澜,特别是到了晚清,以泾阳、三原、西安为代表的整个陕西的社会面貌产生了显著的变化,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刘古愚作为引领这一时代转变的关键性人物,在其继承关学、发展关学的心路历程中,以其实用、实学、实业为核心的格致救国思想影响着西北士子和普通大众,从而将大西北带出了漫漫长夜。
参考文献:
[1]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2]姚远.陕西科技史人物传略[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3]姚远.西安科技文明[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
[4]姚远.西安近代科技源流以及西方科学的传播——西安清代科技文化发展史[M]//姚远,杨海成.新世纪科学论坛.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12-124.
[5]王天根.《天演论》版本时间考析两题[J].安徽史学,2005(3):24-29.
[6]刘古愚.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M]//烟霞草堂文集:卷一.苏州:思过斋,1918.
[7]刘古愚.《学记臆解》序[M]//烟霞草堂文集:卷二.苏州:思过斋,1918.
[8]刘古愚.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M]//《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编委会.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9]刘古愚.与叶伯皋学政书[M]//《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编委会.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1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1]张鹏一.刘古愚年谱[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
[12]张光.陕西省志·报刊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13]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吴廷锡,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M].西安:陕西通志馆,1934.
[14]刘光蕡.味经书院志[M].泾阳:陕西味经刊书处,1894(光绪二十年).
[15]刘古愚.味经刊书处校勘章程[M]//烟霞草堂文集:卷八.苏州:思过斋,1918.
[16]张惠民.清末陕西著名的出版机构——味经官书局[J].编辑学刊,1995(4):82-83.
[17]张惠民.味经、崇实书院及其在传播西方科技中的历史作用[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9(1):88-92.
[18]吴永涛.渭北学界泰斗刘光蕡[M]//韩学儒,吴永涛.三秦近代名人评传.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
[19]陈焘.与苏抚赵展如中丞问答记[M]//审安斋遗稿.民国刻本.
——喜迎十九大 追赶超越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