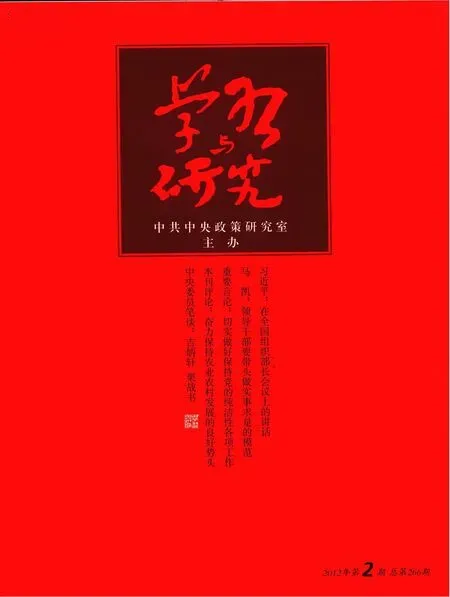“新实学”刍议
苗润田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近年来,随着实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建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新实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在“新实学”理论的建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也还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许多问题还有待进行深入细致地梳理、研究。这里拟就“新实学”的意涵做些初步探讨,以求深化对新实学理论问题的认识。
在实学研究领域,“新实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从已有的资料看,“新实学”概念最早是由韩国学者尹丝淳、姜春华提出的。他们认为,伴随着迟到的近代化,现代化也急速地向我们走来,我们不知不觉地处于和其它民族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同分担现代化所带来的优虑的境地。核战的威胁、环境破坏、日益荒废的伦理道德秩序等问题,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课题。这样的现实问题,过去的性理学不可能解决,朝鲜朝后期的实学也不可能解决。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可以扔掉儒学的传统,即扔掉实际性追求的理论—“实学”精神。如果今天也要自负“儒学是实学”,那么今天的儒学者们必须把这些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探索解决的端倪。今天的儒学者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在试图解决今天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儒学就可能重新复兴为今天的“新儒学”或“新实学”。与此同时,能否成为新实学的儒学的新的起点,在于我们如何解决现实所面临的问题(《新实学的展望》(《孔子研究》1993.4)。这里,作者站在儒学研究者的立场上使用了“新实学”一词,提出面对新的、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建构新的实学,但对于何谓“新实学”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据作者说他早在《新实学的地平线》(在1989年莫斯科第十二次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中就谈到了“新实学”的问题(见尹丝淳《新实学与新理念的探索—以韩国为中心》,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秋之卷),但同样没有对“新实学”概念的意涵给出必要的规定。
葛荣晋在中国传统实学研究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学术背景下,为促进、推动中国实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提出在当下只有建构一个富有时代精神的现代“新实学论”,才能赋于中国实学以新的社会生命力,实学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在他看来,“研究中国古代实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把中国实学的优秀传统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建构一个富有时代精神的现代‘新实学论’呢?如何对中国实学进行现代转换呢?中国实学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哪些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呢?中国实学的现代社会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只有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才能赋于中国实学以新的社会生命力,实学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中国实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开封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这是中国学者最早提出并使用“新实学”一词。虽然葛先生也没有对“新实学”概念的意涵给予必要的规定,但他提出了“新实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新实学”需要解决和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周树智、孔亚菲在《新实学论纲》(《江海学刊》1998.4)一文中,开始就什么是“新实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所谓新实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南的,立足个人现实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务实为本的新科学。”这是一个颇具时代色彩的“新实学”定义,也是关于何谓“新实学”的初步规定。在说明什么是“新实学”的基础上,作者对新实学与旧实学的关系、新实学的理论源泉、新实学与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梳理。强调新实学是一种科学实证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是一种能动的实践认识论,是一种实学实用、注重实效、务实为本的价值论,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方法论;其最大特性就是实践性,它把实践原则贯彻于自己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新实学产于中国,中国需要新实学。应当说,《新实学论纲》对什么是“新实学”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之后,大家也偶尔使用“新实学”一词,但对何谓“新实学”并没有展开讨论。
虽然“新实学”的概念晚出,但是对“新实学”的思考,建构“新实学”的理论努力,这之前就已经为研究者所关注。葛荣晋于九十年代前期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时代呼唤实学”,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代呼唤实学,时代急切地需要实学,实学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并在《中国实学思想史》的“导言”中专就中国实学的现代转换问题作了系统论述,强调“中国实学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并没有死亡,在中国思想史上它是属于最接近于现代的文化,它的原典精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所以,现代人可以通过古代实学原典去领悟它的精神实质,并以现代人的心态和需要去转换中国古典实学,将中国实学与现代沟通起来,努力寻找二者的衔接点,由传统走向现代化之路。”(《哲学动态》记者:《实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访葛荣晋教授》,《哲学动态》1994年第10期)这里所说时代呼唤的“实学”当然是指“新实学”;这里所倡导的以现代人的心态和需要去转换中国古典实学,将中国实学与现代化沟通起来,也就是指要在继承传统实学精神的基础上建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实学”理论体系,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葛荣晋认为,在“新实学”的理论建构方面,“构建‘新实学’,不同于创建‘新理学’和‘新心学’,应突出实学中的‘外王之学’,将其经世致用传统和实践品格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化。要完成这一转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走出困扰中国学者百余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以‘文化自觉’精神,融会‘中西古今’之学,走‘综合创新’之路。必须从哲学高度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衍生出的主要社会问题,诸如将王夫之等实学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转换为超越西方‘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建构起现代生态哲学,以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针对现代人的‘心理文明病’,从中国实学中吸取其‘心灵哲学’的合理思想,为现代人构建真善美和知情意统一的理想人格、寻回人类失落了的‘自我’;面对‘文明冲突’和‘单极世界’的霸权意识,我们应从传统实学中吸取‘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文化资源,以整合、协调正处于分裂对抗的人类社会,为人类创造一个‘多元和谐’的现代社会提供理论根据等,做出理论说明。”(《“实学”之三国“演义”》,《光明日》2007.4.19)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葛荣晋对“新实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又有新的思考,在《时代呼唤东亚“新实学”》一文中,强调为应对道德滑坡、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全人类课题,在东亚构建符合21世纪发展要求的新实学具有重要意义。在方法上,应准确地解读与把握时代精神、走哲学“综合创新”之路、坚持多元诠释学方法;“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是构建东亚“新实学”的根本途径。“文本解读”是指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东亚各国实学文本。只有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历史实际和历史文化资源,全面深刻地解读实学文本,还东亚实学真实面貌,并且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之长,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才能谈及构建东亚新实学。“时代解读”是指对东亚实学作出合乎时代精神的新诠释,并在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时作出新的理论说明。(参见姜璋玮:《实体、实心、实学、实用——第十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孔子研究》2010.4)这都是着眼于“新实学”理论建构而提出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思想认识。从实学研究的状况看,经过实学研究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在“文本解读”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绩,在“时代解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显然还是不够的。“新实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既是“文本解读”的接续,又是“时代解读”的思想结晶;没有“文本解读”的接续不能称之为“实学”,没有“时代解读”不能称之为“新实学”。
基于“新实学”研究的理论需要,对“新实学”的意涵做出明确的规定是非常必要的,这应当是开展“新实学”研究、建构“新实学”理论体系的前提。那么怎样界定“新实学”呢?我想,对“新实学”概念的界定至少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新实学之“新”,也就是充分体现“新实学”与“旧实学”的本质区别;二是新实学之“实”,也就是充分体现“新实学”的实学本质亦即它与“旧实学”的内在联系。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拟应把“新实学”界定为:秉持传统实学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和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以科学方法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对问题的理论体系为宜。前者突出强调了“新实学”与“旧实学”的内在联系,后者突出强调了“新实学”与“旧实学”的区别,亦即它是以科学方法、为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对问题而形成的一种实学理论。